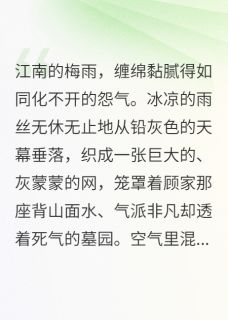江南的梅雨,缠绵黏腻得如同化不开的怨气。冰凉的雨丝无休无止地从铅灰色的天幕垂落,
织成一张巨大的、灰蒙蒙的网,笼罩着顾家那座背山面水、气派非凡却透着死气的墓园。
空气里混杂着浓郁的土腥气、被雨水打得七零八落却依旧固执散发着甜腻香气的百合花圈,
还有一种更深的、属于新翻泥土和昂贵金丝楠木棺椁的、令人心头发沉发冷的腐朽气息。
我站在送葬队伍的最前列,一身肃穆的黑色羊绒长裙,
裙摆早已被泥泞的草汁和冰冷的雨水浸透,沉甸甸地贴在同样冰冷的小腿上。小腹的位置,
一种熟悉的、带着翻江倒海意味的酸胀感,正不受控制地、一阵紧似一阵地翻涌上来。
我死死咬住下唇内侧的软肉,用疼痛和意志力拼命压制着那股恶心。不能吐。
绝不能在这里吐。怀里空空如也。顾廷烨的骨灰盒,
正由他那位面容悲戚、眼神却锐利如鹰隼的母亲——顾家主母秦佩兰,亲自捧在胸前。
她一身昂贵的黑色香云纱旗袍,外罩同色羊绒披肩,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插着一支素雅的珍珠发簪。她微微垂着头,保养得宜的脸上布满哀伤,眼角的泪痕清晰可见,
每一步都走得沉重而缓慢,仿佛捧着的是她自己的心肝。而我,苏念,
顾廷烨新婚不过半年的妻子,更像是这场盛大葬礼里一个突兀的、不合时宜的背景板。
一个不被期待的存在。一个…克死了顾家麒麟儿的“扫把星”。哀乐呜咽着,压抑而悲凉。
沉重的金丝楠木棺椁被十六个壮汉抬着,缓缓移向那个早已挖好、如同巨兽张口的墓穴。
每一步都像踩在所有人的心尖上。我亦步亦趋地跟在秦佩兰身后半步的位置,低垂着眼睑,
努力忽视四面八方投射过来的、或同情、或探究、或毫不掩饰鄙夷的目光。
那些目光像无数根细密的针,扎在我**的脖颈和手臂上。
小腹的坠胀感和那股熟悉的恶心感越来越强烈,胃里如同有只手在狠狠搅动。终于,
棺椁被小心翼翼地放置在墓穴旁特制的支架上。牧师开始念诵冗长的悼词,
声音在淅沥的雨声中显得模糊而遥远。“……尘归尘,土归土,
穆、人人屏息凝神的时刻——“呃…呕…”一股无法再压制的、带着强烈酸腐气味的呕吐物,
猛地从我紧捂的指缝间喷涌而出!溅落在脚下湿漉漉的青石板路上,
在黑色的裙摆边缘染上刺目的污渍!死寂!绝对的死寂瞬间笼罩了整个墓园!所有的目光,
如同被无形的磁石吸引,齐刷刷地、带着惊愕和嫌恶,死死钉在了我的身上!下一秒!
“啪——!!!”一声极其清脆响亮、带着雷霆之怒的耳光,狠狠掴在了我的左脸上!
力道之大,打得我整个人猛地一个趔趄,眼前金星乱冒,耳朵嗡嗡作响!
脸颊瞬间**辣地肿起,嘴里泛起浓重的血腥味。“**!
”秦佩兰尖利刻薄、充满了怨毒的声音,如同淬了毒的冰锥,狠狠刺穿死寂的雨幕,
清晰地砸进每个人的耳朵里!“克死我的烨儿还不够?!连他的葬礼你都要搅得天翻地覆?!
还有脸在这里装模作样地孕吐?!你这个丧门星!扫把星!你怎么不去死?!
你怎么不跟着我的烨儿一起去死?!”她涂着鲜红蔻丹的手指,
因为极致的愤怒而剧烈颤抖着,直直地戳着我的鼻尖,精心维持的优雅贵妇形象荡然无存,
只剩下一个被丧子之痛彻底逼疯的、歇斯底里的母亲。屈辱!巨大的屈辱如同滚烫的岩浆,
瞬间烧遍全身!脸颊的刺痛,嘴里的血腥味,胃里翻江倒海的恶心,
还有那四面八方如同实质般的鄙夷目光,几乎要将我彻底淹没、撕碎!我死死咬着下唇,
尝到了更浓的铁锈味,指甲深深掐进掌心,用疼痛强迫自己站直。眼泪在眼眶里疯狂打转,
却倔强地不肯落下。不能哭。苏念,你不能在这里哭。
就在这片令人窒息的死寂和秦佩兰怨毒的咒骂声中,一个身影分开人群,缓缓走到了我面前。
是我的小叔子,顾廷轩。他穿着一身剪裁完美的黑色西装,身姿挺拔,面容英俊,
只是那双和顾廷烨有几分相似的桃花眼里,
此刻却盛满了毫不掩饰的冰冷和…一丝不易察觉的嘲讽。
他手里拿着一个小小的、透明的、没有任何标签的玻璃药瓶,里面装着淡粉色的液体。
“大嫂,”顾廷轩的声音清朗,带着一种刻意的温和,却比秦佩兰的尖叫更让人心头发寒。
他将那个小药瓶递到我面前,唇角勾起一抹看似关切、实则冰冷刺骨的弧度,“节哀顺变。
您还怀着身子,情绪不宜太过激动。这是专门给您配的安胎药,舒缓神经,平复孕吐的。
大哥在天有灵,想必也不愿看到您和肚子里的孩子出事。”安胎药?
我看着那瓶在阴雨天光下泛着诡异粉色的液体,
又抬眼看向顾廷轩那双深不见底、带着冰冷审视的眼睛。一股寒意,比这梅雨更刺骨,
瞬间从脚底板窜上天灵盖。秦佩兰的咒骂声戛然而止,
她狐疑地、带着怨毒地看了一眼那药瓶,又狠狠剜了我一眼,冷哼一声,不再说话,
只是抱着骨灰盒的手收得更紧。周围的宾客窃窃私语,目光在我和那瓶药之间逡巡。
我没有接。顾廷轩脸上的温和笑意淡了些许,眼神里的冷意更甚。他不由分说,
将药瓶塞进了我冰凉僵硬的手中。玻璃瓶壁冰冷的触感,激得我指尖一颤。“喝了吧,大嫂。
”他的声音压低,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命令,“为了孩子。也为了…顾家的体面。
”那“体面”二字,像两把淬毒的匕首,狠狠扎在我的心上。在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
在秦佩兰怨毒的逼视下,在顾廷轩冰冷的命令下,我颤抖着拧开了瓶盖。
一股极其淡的、难以形容的甜腻气味飘散出来。仰头。冰冷的、带着诡异甜味的粉色液体,
顺着喉咙滑下,像一条冰冷的毒蛇,蜿蜒着钻进我的胃里。时间在顾家大宅压抑的死寂中,
流淌得格外粘稠缓慢。像一潭散发着腐朽气息的死水。葬礼的喧嚣早已散去,
留下的是更深的、令人窒息的冰冷和无处不在的监视。我住在主宅最偏僻角落的客房,
曾经的新房早已被锁死,里面属于顾廷烨的气息,连同他这个人,一起被抹去。
佣人们对我保持着表面的恭敬,眼神里却充满了鄙夷和疏离,
送饭、打扫都像完成一件不得不做的、令人厌恶的任务。秦佩兰将我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在她眼里,是我这个“丧门星”带来了厄运,克死了她引以为傲的儿子。她看我的眼神,
永远淬着冰冷的恨意和毫不掩饰的厌恶。她不允许我踏足主厅,
不允许我出现在任何可能有宾客来访的场合,仿佛我的存在本身就是对顾家的玷污。
她甚至几次三番在佣人面前,用最恶毒的语言诅咒我腹中的“孽种”早点流掉。
“顾家的门楣,不能毁在一个扫把星和一个来历不明的野种手里!”她的话如同淬毒的针,
隔着门板都能清晰地扎进来。唯一会“关心”我的,只有顾廷轩。他每隔几天,
都会在固定的时间,带着那种看似温和、实则冰冷的笑容,出现在我的房门口。
手里永远拿着那个小小的、透明的玻璃药瓶,里面装着淡粉色的液体。“大嫂,该喝药了。
”他的声音总是那么平静,却带着不容拒绝的强势。“安胎要紧。
这可是大哥唯一的骨血了。”他刻意加重“唯一”二字,眼神里的幽深让人不寒而栗。
每一次,我都如同木偶般接过药瓶。指尖触碰到那冰冷的玻璃,
胃里都会条件反射般地一阵翻搅。那股诡异的甜腻气味,仿佛已经渗透进我的骨髓。仰头,
灌下。冰冷的液体滑过喉咙,带来一种短暂的、虚假的平静。
那股翻江倒海的孕吐感似乎真的被压制下去了。但随之而来的,
是一种更深的、无法言说的疲惫和一种莫名的、如同跗骨之蛆般的虚弱感。四肢总是乏力,
精神也时常恍惚,仿佛生命力正随着每一次服药,被悄无声息地抽走。
我曾小心翼翼地藏起过小半瓶药液,想找机会送去检验。但第二天,顾廷轩送药来时,
那双锐利的眼睛仿佛能穿透一切,他状似无意地扫过房间的角落,淡淡地说:“大嫂,
药要按时按量喝才有效。别辜负了…大哥的心意。”那“心意”二字,带着冰冷的警告。
从那以后,我再不敢轻举妄动。肚子一天天显怀。薄薄的衣衫下,
那个小小的生命在顽强地生长、律动。每一次胎动,都像黑暗中微弱的火苗,
支撑着我在这冰冷的牢笼里活下去。这是我的孩子。廷烨的孩子。
也是我唯一的希望和…筹码。三个月,像三个世纪般漫长。终于到了例行产检的日子。
在顾家保镖寸步不离的“护送”下,
我被带到了顾氏集团控股的、本市最顶级的私立妇产医院。环境奢华得像五星级酒店,
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和昂贵香氛混合的味道。接待我的是医院最权威的产科主任,
一位姓吴的中年女医生。她笑容可掬,态度恭敬,
但眼神深处却带着一种职业化的疏离和一丝不易察觉的…谨慎?显然,顾家早已打点好一切。
检查过程繁琐而冰冷。冰冷的仪器探头在小腹上滑动,屏幕上模糊的影像里,
一个小小的生命在羊水中舒展。听着那强健有力的胎心音,我冰冷的心才稍稍有了一丝暖意。
“胎儿发育指标基本正常,胎心有力。”吴主任看着仪器屏幕,公式化地报着数据。
她拿起一叠厚厚的化验单,翻看着。突然,她的目光在其中一张单子上停住了。
眉头几不可察地蹙紧,眼神瞬间变得凝重。她抬起头,目光锐利地看向我,
之前那职业化的笑容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严肃的探究。“顾太太,
”她的声音压低了,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惊疑,“你最近…有没有接触过什么特殊的东西?
或者…长期服用什么药物?”我的心猛地一沉,瞬间提到了嗓子眼!“什…什么意思?
吴主任?”吴主任将那张化验单推到我面前,指着上面几项标红的数值:“你看这里,
血清胆碱酯酶活性异常降低,
尿液中检出微量有机磷类代谢物…还有这几项神经传导相关的指标…都显示异常。
”她顿了顿,目光紧紧锁住我瞬间煞白的脸,一字一句,
清晰而沉重地说道:“这些指标综合显示…你的体内,有慢性神经毒素沉积的迹象。
而且…时间不短了。”轰——!仿佛一道惊雷在脑中炸开!炸得我魂飞魄散!
慢性…神经毒素?!吴主任后面的话变得模糊不清,像隔着一层厚重的玻璃。
我只看到她嘴唇翕动,眼神充满了忧虑和警惕。“……对胎儿的影响目前还无法完全评估,
肯定存在风险……必须立刻停止接触毒源……需要进一步排查……”毒源……那瓶粉色的药!
顾廷轩那张看似温和、实则冰冷如毒蛇的脸,瞬间清晰地浮现在眼前!还有他每次递药时,
那不容置疑的“安胎要紧”!巨大的恐惧和一种被彻底愚弄、濒临死亡的冰冷感,
瞬间攫住了我的心脏!四肢百骸都冻僵了!安胎药?!那分明是…要我命的穿肠毒药!
“顾太太?顾太太你听清楚了吗?”吴主任的声音带着一丝焦急。我猛地回过神!
巨大的愤怒和求生的本能如同火山般喷发!烧尽了所有的恐惧和犹豫!“药!是那瓶药!
”我失声尖叫起来,声音因激动和恐惧而嘶哑变调!顾不上仪态,我猛地从随身的手包里,
颤抖着掏出那个早已被我藏起来的、空了的透明小药瓶!瓶壁上还残留着一点淡粉色的痕迹!
“是他!是顾廷轩!他给我喝的!他说是安胎药!”我将药瓶死死攥在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