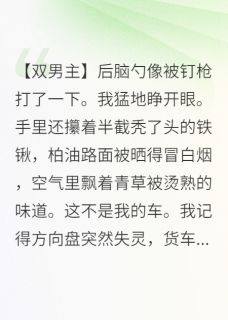【双男主】后脑勺像被钉枪打了一下。我猛地睁开眼。手里还攥着半截秃了头的铁锹,
柏油路面被晒得冒白烟,空气里飘着青草被烫熟的味道。这不是我的车。
我记得方向盘突然失灵,货车大灯像两团火球砸过来,然后——“林默!发什么愣?
”有人踹了我一脚,工装裤口袋里的硬币硌得胯骨生疼。我转头看见个穿保安服的老头,
他手里的保温杯磕在我工具箱上,“王虎他们刚过去,你还在这儿磨蹭?”王虎?
这个名字像根针,猛地扎进脑子里。无数碎片涌进来:公园绿化队的临时工林默,父母早亡,
跟着远房叔叔过活,三年前被叔叔以“找个正经活”为由塞进公园,
其实是来给王虎这群地痞当提款机的。昨天就是因为没交上“保护费”,
被他们推搡着撞在篮球架上,后脑勺开了瓢。而我,
一个刚在家庭法庭上被父母逼着签下“自愿放弃遗产”协议的倒霉蛋,
就这么穿到了这个同样窝囊的家伙身上。喉咙干得发疼,我直起身想找水喝,
眼角余光突然瞥见篮球场。阳光把铁丝网晒得发烫,一个男人正站在三分线外投篮。
黑色背心被汗水浸成深灰,贴在背上勾勒出菱形的肌理,每一次抬手,
手臂上的肌肉都像活过来似的,随着投篮动作绷紧、滑动。他跳起来的时候,
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声。不是因为动作好看,是他落地时,
运动裤顺着紧实的大腿往下褪了半寸,露出一小截**边缘,
被阳光晒成蜜色的皮肤晃得人眼晕。男人似乎察觉到我的目光,突然转身。
视线撞在一起的瞬间,我像被烫到似的低下头。他在笑。不是那种客套的笑,是嘴角勾着,
眼神带着点玩味,像在看什么有趣的东西。我能感觉到他的目光落在我发颤的手背上,
落在我被汗水浸湿的工装领口。“喂。”他开口了,声音比柏油路还烫,“借个火。
”我这才发现他手里夹着根烟,没点燃。手忙脚乱地摸口袋,原身不抽烟,我也不抽。
指尖碰到裤缝里磨出的破洞,才想起这工装裤早就该扔了。“没、没有。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抖。他挑了挑眉,没再说话,转身继续投篮。篮球砸在篮板上的声音,
一下下敲在我太阳穴上。就在这时,三个影子罩了过来。王虎叼着烟站在最前面,
T恤领口敞着,露出胸口的龙形纹身,旁边的李三和瘦猴一左一右,
手里还把玩着昨天抢来的折叠刀。“哟,林大傻子,看什么呢?”王虎用烟卷戳我的脸,
“眼珠子都快粘人身上了,怎么着?想男人了?”李三在旁边怪笑:“虎哥,你不知道,
这小子前阵子还被人撞见偷看男厕所呢。”“真的假的?”王虎眼睛一亮,
伸手就要抓我的衣领,“那可得好好查查,咱们公园可不能留这种变态。”我往后躲了一步,
后腰撞在工具箱上,扳手掉出来砸在脚背上。疼。但更疼的是那几句骂人的话,
像针一样扎进耳朵里。无论是原来的我,还是现在的林默,好像都逃不开被人踩在泥里的命。
“滚开。”一个声音突然**来。王虎的手僵在半空。
那个打篮球的男人不知什么时候走了过来,手里还转着篮球,背心下摆沾着草屑,
汗珠顺着下颌线往下掉,滴在凸起的喉结上。“**说谁滚开?”王虎梗着脖子站起来,
他比男人矮了半个头,得仰着下巴说话。男人没理他,眼睛盯着我脚边的扳手,
突然把篮球往地上一砸。“砰”的一声,篮球弹起来,正好撞在王虎膝盖上。
王虎疼得嗷嗷叫,李三和瘦猴刚要上前,就被男人看过来的眼神钉在原地。
那眼神里没什么火气,就是冷,像冬天结了冰的河面,看得人心里发毛。“他是公园的人。
”男人说话时没看他们,目光落在我被草叶划破的手背上,“你们在这儿闹事,
我可以叫保安。”王虎显然认识他,或者说,是怕他。捏着拳头骂了句脏话,
突然踹了我的工具箱一脚:“算你小子运气好!明天要是再不把钱凑齐,看我不扒了你的皮!
”三人骂骂咧咧地走了,瘦猴经过男人身边时,还啐了一口。男人没动,
直到他们的影子消失在公园拐角,才弯腰捡起地上的篮球。“谢、谢谢。”我捡起扳手,
指尖还在抖。他把烟塞回烟盒,没说话,转身要走。“等等!”我突然喊住他。他停下脚步,
回头看我。阳光从他背后照过来,给他周身镀了层金边,我能看见他睫毛上沾的汗珠,
像碎玻璃似的闪。“你……”我想问他叫什么,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问了又能怎么样呢?
我们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他好像看穿了我的心思,突然笑了,
这次的笑里带了点温度:“陈野。”说完,他转身走向篮球场,黑色背心在阳光下晃来晃去,
像团烧得正旺的火。我站在原地,摸了摸后脑勺的伤口,那里已经不疼了。
口袋里的手机震动起来,是原身的叔叔发来的短信:“王虎刚才打电话了,说你又没交钱,
是不是想让我亲自去公园‘教育’你?”手指攥着手机,指节发白。原来的我,
在父母面前忍了二十八年,最后落得个净身出户的下场。难道穿过来,
还要继续当别人的提款机,被人指着鼻子骂变态?陈野投篮的声音又传了过来,一下,
又一下。我看着自己磨出厚茧的手掌,突然把手机塞回口袋,抓起铁锹。
王虎不是要扒我的皮吗?那就看看,到底谁扒谁的皮。今天下午的灌木还没修剪,
明天的“保护费”也还没着落,但我知道,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就像陈野刚才那个投篮,
弧度很漂亮,带着股不管不顾的劲儿,砸进篮筐时,震得整个世界都在响。
第二天我揣着攒了半个月的零钱去上班,刚进公园就看见王虎他们蹲在长椅上。
李三吹了声口哨,瘦猴直接把脚翘到我工具箱上:“林傻子,今天够自觉啊。
”我把钱掏出来要递过去,王虎突然一巴掌拍在我手背上。硬币撒了一地,滚得叮当作响。
“这点钱够塞牙缝吗?”他揪着我的工装领往篮球架那边拖,
“昨天帮你的那小子叫陈野是吧?听说在健身房当教练,很能打啊?
”后背撞在生锈的篮球架上,疼得我龇牙咧嘴。“虎哥问你话呢!”李三踹我的膝盖,
“那小子是不是跟你有一腿?不然凭什么帮你?”周围开始有晨练的人围观,
指指点点的声音像针一样扎耳朵。我死死咬着牙不说话,原身的记忆里,越是辩解,
他们闹得越凶。突然有人喊了声“陈教练来了”。王虎的手松了松。我抬头看见陈野走过来,
今天穿了件灰色连帽衫,拉链没拉到底,露出半截锁骨。他手里拿着个保温杯,
看都没看王虎,径直走到我面前。“昨天的伤没事吧?”他的目光扫过我发红的手腕。
王虎突然笑了:“陈教练这么关心他?难道传闻是真的?”陈野终于转头看他,
眼神冷得像冰:“再不让开,我不保证你的手还能握拳头。”王虎的脸瞬间涨成猪肝色,
撂下句“走着瞧”,带着人骂骂咧咧地走了。陈野把保温杯递给我:“蜂蜜水,消肿的。
”杯壁的温度烫得我指尖发麻,抬头时正好看见他喉结动了动,连帽衫的帽子滑下来,
露出额角的疤,听说练拳的人都有这样的疤。“谢……谢谢。
”我捧着杯子往绿化队办公室走,后背像是长了眼睛,能感觉到他的目光一直跟着。
那天下午我蹲在花坛里种月季,王虎他们又回来了。这次没找我麻烦,
直接踩着刚铺好的草皮往篮球场走,故意把我刚栽的花苗踢得东倒西歪。“有种别躲啊!
”李三冲着正在擦器械的陈野喊,“刚才不是挺横吗?”陈野擦器械的动作没停,
金属摩擦的声音在安静的午后格外刺耳。我急得想站起来,后腰突然被什么东西砸中。
低头一看是块石头,瘦猴正举着第二块朝我这边比划。“住手!”陈野的声音炸响时,
他已经站在我面前。石头砸在他后背上,发出沉闷的响声。他没回头,
只是盯着瘦猴:“再动一下试试。”王虎突然掏出手机对着我们拍:“拍下来发网上去,
就说健身房教练光天化日欺负老百姓。”陈野突然笑了,一步步朝他们走过去。
王虎几人下意识地往后退,直到退到公园门口,才敢指着我们骂:“你们给我等着!
”等人走远了,我才发现自己的手抖得握不住铁锹。陈野蹲下来帮我扶花苗,
手指碰到泥土时,我看见他手背上有道新的划痕,像是被什么尖锐的东西划的。
“你的手……”“没事。”他把最后一棵月季扶好,“他们经常这样?”我点点头,
又摇摇头。原身以前都是忍着,从没想过反抗。“明天起,我晚点走。”他突然说,
起身时连帽衫的下摆扫过我的手背,“正好加练。”接下来的日子变得很奇怪。
王虎他们还是天天来,但总在陈野“加练”的时候。陈野练拳时,他们就蹲在远处抽烟,
眼神像狼一样盯着我。陈野会在休息时买两罐冰可乐,把拉环拉开再递给我。
指尖碰到的瞬间,两人都会像触电似的缩回手。有天我正在修剪冬青,陈野突然站到我身后。
“小心。”他的呼吸扫过我的耳廓,“那根枝桠有刺。”我猛地转身,鼻尖差点撞到他下巴。
他的连帽衫拉链没拉,能看见里面黑色T恤上印的健身房logo,
还有随着呼吸起伏的胸肌。距离近得能闻到他身上的味道,像是薄荷混着阳光,清清爽爽的,
一点都不腻。“谢……谢谢。”我往后退了半步,后腰撞在冬青丛上,疼得龇牙咧嘴。
他伸手想扶,手在半空停了停,最后递给我一张创可贴:“刚才看见你手指流血了。
”创可贴的包装被他捏得有点皱,我接过来时,指尖不小心碰到他的指甲,修剪得很干净,
边缘带着点粉色。那天晚上王虎给我发了条彩信。是张照片,
陈野穿着病号服的弟弟躺在病床上,鼻子里插着氧气管。
下面还有行字:这小子在中心医院住院,听说要换肾呢。我的心沉了下去。
第二天陈野来的时候,我发现他眼底有红血丝,连帽衫的帽子一直没摘,像是没睡好。
他递给我可乐时,我没接,直接问:“你弟弟是不是住院了?”他的动作僵住了,
过了好一会儿才点头:“嗯,肾病综合征。”“需要很多钱?”他没说话,
只是把可乐塞进我手里,转身去投篮。篮球砸在篮板上的声音,比平时重了很多。
中午吃饭时,李三突然坐到我对面,把一碗麻辣烫往我面前推:“虎哥说了,
只要你帮我们个忙,以后再也不找你麻烦。”我没动筷子。“很简单。”李三压低声音,
“陈野不是天天帮你吗?你找机会把他锁在器材室,我们就去他健身房‘借’点钱,
保证不动他弟弟。”我猛地站起来,饭盒差点被带翻:“你们做梦!”“别给脸不要脸!
”李三抓住我的手腕,“你以为陈野是真心帮你?他不过是看你可怜,玩腻了就把你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