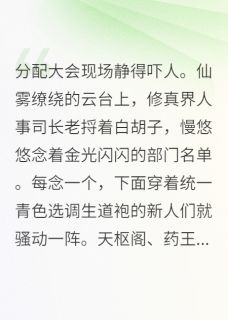丙字区的铜铃,响得毫无规律。有时一天响几次,有时几天都不响一次。**也嘶哑难听,像是快断气了。
来报到的魂,形形**。有哭哭啼啼的妇人,有骂骂咧咧的壮汉,有懵懂无知的孩子,也有沉默寡言的老者。无一例外,都带着浓重的迷茫和对未知的恐惧。
我的工作流程固定且低效。
铃响。
走到门口,对着空气(或一团模糊的影子)问:“姓名?籍贯?死因?”
对方回答。
我回到案几,在“丙字区接引录”上歪歪扭扭地记下。
然后拿出一个刻着“验”字的木章,蘸点劣质红印泥,盖在册子上。
再拿出一张薄薄的黄色符纸,让魂在上面按个手印(魂的手印按上去,符纸会显出一道淡淡的黑痕)。
最后,指指墙角:“去那边等着,会有人带你去该去的地方。”
新魂茫然地飘到墙角,融入那片昏暗。然后,就是漫长的等待。引路司的鬼差,确实像老赵说的,神龙见首不见尾。运气好,当天能来;运气不好,等上几天。那些新魂就缩在墙角,无声无息,像一堆被遗忘的破布。
殿里其他鬼差,依旧维持着他们的状态。赌钱的,睡觉的,发呆的。只有角落里那个小鬼差,叫阿吉的,偶尔会偷偷帮我扶一下快倒的卷宗,或者在我被某个特别难缠的魂(比如一个坚持说自己是被毒死的员外,嚷着要见阎王)纠缠时,递过来一个同情的眼神。
崔判官大部分时间都在嘬他的小茶壶。偶尔殿里闹得实在不像话(比如赌钱吵起来了),他会敲敲桌子,哑着嗓子吼一句:“都消停点!”然后一切照旧。
我带来的那点微薄灵力,在这阴气沉沉的环境里,增长缓慢得几乎感觉不到。身体倒是越来越容易感到那种阴冷的疲惫。
但我没闲着。除了应付那点可怜的“工作”,我大部分时间都在观察,用那本破破烂烂的《幽冥基本工作条例》做掩护,在底下偷偷记录。
记录引路司鬼差出现的频率和时间段(毫无规律)。
记录不同鬼差处理魂的速度(极慢,且态度恶劣)。
记录那些堆积如山、明显被遗忘了的卷宗上的标签(很多写着“甲字急”、“乙字重”,却落满灰尘)。
记录大殿各个区域的功能划分(混乱不堪,文书流转毫无章法)。
我还利用去交还“已处理”名册的机会(虽然大部分根本没处理),偷偷靠近过那个叫“幽冥阁”的小门。门紧闭着,挂着巨大的铜锁。门口没有守卫,但门缝里透出一点点微弱却精纯的灵力波动,还有……一股若有若无的霉味。
这就是生死簿存放的地方?为什么锁着?崔判官自己也很少进去的样子。
时间在阴间流逝得仿佛格外粘稠。不知道过了多久,也许一个月,也许更久。殿里的鬼差们大概觉得我这个新来的“傻子”也没什么特别的举动,除了干活死板点,渐渐也懒得再关注我。
这天下午,殿里一如既往地死气沉沉。赌钱的吆喝声都透着股懒洋洋的劲。阿吉在角落里吃力地搬动一大箱卷宗,累得直喘。
丙字区的铜铃突然尖锐地响了起来,比平时急促刺耳得多。
我习惯性地起身走到门口。
外面站着的魂,有点不一样。是个穿着锦缎长衫的老者,须发皆白,但精神矍铄,眼神锐利,完全没有新魂常见的迷茫恐惧。他身上甚至带着一丝极淡的、尚未散尽的护体灵光。这绝不是普通横死的凡人!
“姓名?籍贯?死因?”我按流程问,心里提高了警惕。
老者捋了捋胡须,神情倨傲:“老夫张百川,云州清河府人士。寿终正寝。”他顿了一下,补充道,“老夫乃清河府首富,张家家主张百川。”
张百川?我脑子里嗡了一下。这个名字我听过!就在前几天,我“无意”中翻到一本被垫在崔判官茶壶底下、边角烧焦了的《阳间名流功德簿(残卷)》,上面赫然记载着:张百川,云州清河府巨贾,乐善好施,修桥铺路,活人无数,身具功德金光,当享百二十载阳寿,福荫子孙。
按照那残卷记载,他至少还有二十年好活!怎么会“寿终正寝”?
我立刻看向案几上的“丙字区接引录”。这册子只记新魂自述,根本不会核对生死簿!如果按流程登记成“寿终正寝”,分去审判殿走个过场,估计就直接安排投胎了!
这绝对有问题!
“老人家,您确定是寿终正寝?”我盯着他,放缓了语速。
张百川眉头一皱,有些不悦:“老夫自己的事,还能有假?你这小吏,问这么多作甚?速速登记,老夫还要去面见阎君,禀明功德,为子孙求个福报!”
他的神态语气,不像说谎。那就是……生死簿出错了?或者有人篡改?
我的心跳有点快。这可不是小事!一个身具大功德、阳寿未尽的人被错拘,一旦投胎,后果难料,牵扯的因果大了去了!地府绝对要吃挂落!
我转身走回案几,没有立刻登记。拿起毛笔,蘸墨,故意磨蹭。眼角余光瞥向崔判官。他还在嘬茶壶,眼皮都没抬一下。殿里的鬼差们更是各忙各的。
“程大人,快点登记啊,后面还等着呢!”负责隔壁乙字区登记的一个胖鬼差,正和对面赌骰子,头也不回地喊了一嗓子。
我深吸一口气。阴冷的空气刺得肺疼。不能按流程走!流程本身就是错的!但直接质疑?我一个刚来的选调生,人微言轻,没有证据,谁会信我?崔判官会信?他可能巴不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张百川在门口不耐烦地踱步,身上的灵光微弱地闪烁。
墙角,阿吉搬着箱子,偷偷看着我这边,眼神里有点担忧。
赌钱的喧闹声,睡觉的呼噜声,交织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