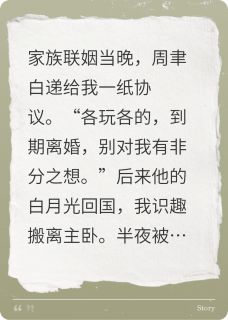家族联姻当晚,周聿白递给我一纸协议。“各玩各的,到期离婚,别对我有非分之想。
”后来他的白月光回国,我识趣搬离主卧。半夜被抵在客房墙上,
他气息灼热:“周太太想去哪儿?”撕碎协议那晚,家族巨变,
我冷眼看他护着白月光:“原来我是替身?”他红着眼跪在碎纸堆里:“你偷换我药时,
就没想过那是我母亲的遗物?”浴火重生的庆功宴,我挽着新贵笑容璀璨。
周聿白当众扯开衬衫,露出我咬的牙印:“夫人气消了么?不消的话…再咬一口?
”【第一章始于虚假】水晶吊灯的光砸下来,白得晃眼。
空气里浮动着昂贵香水、酒气和鲜切花过度浓郁的甜腻。耳朵里嗡嗡作响,
全是司仪那句慷慨激昂的“周聿白先生,你是否愿意娶林晚女士为妻,无论疾病还是健康,
贫穷还是富有……”红毯尽头西装笔挺的男人侧影挺拔得像把淬了寒光的刀,
那是我这场盛大表演的唯一共犯。他开口,声音隔着嘈杂传过来,平直得像机器合成的,
连一丝婚礼该有的起伏都吝啬:“我愿意。”司仪转脸朝向我,脸上铺着夸张的笑意。
聚光灯热烘烘地烤着我的脸,裙摆里的双腿有点僵。全场安静下来,
只有老式留声机放着慢板的小提琴曲,拖沓得让人心烦。我张了张嘴,喉咙发干。
那三个字像卡在喉咙里的鱼刺。“我…愿意。”声音不大,勉强够前排听见。
旁边观礼的姑妈翻了个白眼,嘀咕声穿透背景音乐:“没吃饭啊?
”终于捱完了所有繁文缛节。关上新房厚重的实木门,
外面人声鼎沸的喧嚣被瞬间压制成模糊的背景音。周聿白扯下勒得死紧的领结,
随手扔在铺着大红喜被的床上。他没看我,径直走向靠窗的沙发,拉开公文包,
抽出那份A4纸打印的文件。纸张边缘锋利,在灯光下泛着冷硬的微光。他走过来,
距离不远不近,恰好是个商业谈判的尺度。他把文件递过来,姿态和眼神一样,
是纯粹的、不掺杂任何温度的例行公事。“林晚,”他念我的名字,口吻公式化,
“看看这个。”我接过来,目光落在标题几个加粗的黑体字上:《婚前补充协议》。
下面一行行罗列清晰,是比陌生人住一起更冰冷的规则:*婚姻存续期:协议有效期三年。
*居住安排:各自独立卧室(主卧归男方)。*社交规则:互不干涉彼此私人交往,
双方均拥有完全独立自主空间。*财务分割:婚前婚后财产独立,
生活开支每月由男方固定转账(数额待商定)。*保密条款:对外维持恩爱夫妻人设,
不得泄露协议内容。*到期处理:三年期满,自动解除婚姻关系。
最后那项“期满即散”像根冰冷的针,瞬间刺透那点强装出来的镇定。纸边硌着指尖。
指尖用力到泛白,我甚至听见纸页在细微地发抖。我深吸一口气,
想把那份维持了大半天的、名为新嫁娘的温顺壳子再披上一点。唇角扯开一个弧线,
却像冰面上砸开的裂痕,又冷又硬。“演了一天恩爱,周总迫不及待就卸磨杀驴?
”我盯着他镜片后那双深不见底的眼睛,语气里的刺没压住,“这么怕我会缠着你?
”周聿白似乎没料到这突如其来的尖锐。他眉峰几不可查地蹙了一下,
像被这直白的、难听的话轻微地触怒了。随即,那点不悦又被他极快地摁下去,
脸上覆了一层更厚的霜。“林**多虑了。”他声音沉下来,每个字都像冰豆子砸在地板上,
“我们结合的原因彼此心知肚明。林家需要周家那块港口的地翻盘,
而周家需要林氏在医药渠道上的遮掩……”他停顿半秒,眼神在我脸上逡巡一周,
带着毫不掩饰的、居高临下的审视与警告。“所以,保持距离,守好本分。
”他轻轻点了点那份协议,“各取所需,互不相欠。别有任何不合时宜的想法。对你我都好。
”“不合时宜的想法?”我重复了一遍,舌尖舔过有点发干的嘴唇,
尝到一丝腥甜的铁锈味——大概是刚才用力咬破了哪儿。积攒了一天的火气,
被这针锋相对、尤其是他那种看我如同看一件待价而沽货物的眼神,“轰”地一下烧了起来。
我捏着那几页纸,手臂猛地一扬。撕拉——!清脆得刺耳。纸张从中裂开,
破口像丑陋的伤疤。再撕,几下粗暴的拉扯,昂贵的厚实A4纸被揉成乱七八糟的团。
我狠狠地将这团废纸砸向他胸口!动作快得像闪电。纸团撞上他剪裁合体的昂贵西装前襟,
发出沉闷的一声轻响,随即掉落在他锃亮的皮鞋前。周聿白似乎完全僵住了。
大概从没人敢这么对他。他镜片后的瞳孔骤然收缩,难以置信地盯着我,
那片深邃的寒意几乎要凝成实体扑出来。他下颚线绷得死紧,喉结重重地滑动了一下。
空气凝固得如同坚冰。我直视着他瞬间变得异常危险的眼神,胸口剧烈起伏。
那点强撑的气焰在死寂里一点点冷却、塌陷,手指有点发凉。……冲动了。
新婚当晚彻底撕破脸,对林家没半点好处。心,沉下去。我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
脚跟撞到床边立柱,发出一声闷响。这细小的动静仿佛撕开了冰封。
“呵……”周聿白忽然从喉底滚出一声意味不明的低笑,极冷。他慢慢弯腰,
捡起那个皱巴巴的纸团,动作带着一种刻意的、沉甸甸的优雅。他一点点,慢条斯理地,
将揉皱的纸团展平。碎裂的文字在灯光下扭曲。“撕得挺利落。”他低头看着残破的协议,
指尖在上面轻轻一弹,灰尘在光束里浮动,“那就按我的规矩来。”他抬眼,目光锁死我。
“门外的宾客,今晚住下的周家人,”他嘴角扯开一个毫无温度的弧度,“明天午饭前,
给我安分地扮演好你的‘周太太’。别把林家的脸,在这第一天就丢光了。”说完,
他再不看一眼床上刺目的红,拿着那份揉烂又展平的协议,转身就走。皮鞋踩在厚地毯上,
只发出沉闷的、碾压般的闷响。主卧的门开了。门外走廊的灯光和隐约的谈笑声涌进来一点,
随即又被彻底隔绝。厚重的实木门在我面前,稳稳地关上。隔绝了他,
也隔绝了我身后这片华丽而孤寂的婚房。只剩下冷气口嘶嘶的送风声,还有我擂鼓般的心跳。
咚、咚、咚。林家需要的港口合同在周家老头子周崇山手里攥着,像勒住命脉的绳索。
我咽下那翻腾的酸涩和愤怒,告诉自己,装,也得装下去。第二天中午的家族聚餐,
鸿门宴都不足以形容。周家主宅的餐厅大得能跑马,红木长桌长得像望不到头。
周崇山坐在主位,花白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眼神鹰隼似的扫过我,
锐利得像手术刀片割过皮肤,带着精准评估货物价值的冰冷。“小晚啊,
”他放下青花瓷的汤匙,声音不大,却压住了整桌低语的嗡嗡声,“以后就是周家的媳妇了。
聿白性子独,当他的贤内助不容易。不过……周家的规矩,最重要是‘安分’二字。
”最后两个字,咬得格外清晰。我的筷子顿在精致的蟹黄豆腐上,指关节用力到发白,
脸上还维持着温婉得体的浅笑。周聿白坐在长桌另一端,隔着他几个装腔作势的叔伯兄弟,
像是隔了一道冰冷的光年。他慢条斯理地切着盘子里的牛排,眼皮都没抬一下,
仿佛我只是个无关紧要的背景板。“崇山说的对,”旁边的二叔周文达接口,笑得一脸伪善,
“聿白以前那场轰轰烈烈的恋爱,闹得满城风雨,差点把老头子气背过去……啧,
现在总算收了心。”他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淬了毒的针,细细密密地扎过来。
“林晚贤惠识大体,这才是正经过日子的人嘛!那种太有‘主见’的,心太大,终究要惹祸。
”整桌人的目光,或明或暗,又都胶在我身上,
等着看我这个刚进门就顶着“上一位”阴影的新妇,是如何失态。手心里沁出细密的汗。
指尖死死掐进掌心,痛感让我保持着最后一丝清明。我缓缓掀起眼皮,
脸上漾开一个过分纯净无害的笑容,特意带了点刚过门新妇该有的羞涩和懵懂。“二叔,
”我放下筷子,声音放得又轻又软,带着恰到好处的困惑,
“您说的‘那种’……是什么样啊?我没经历过什么场面,不太懂呢。”我歪了歪头,
眼神干净得像玻璃珠子,纯粹地看向二叔周文达:“我就知道嫁给了聿白,就要本本分分的,
让他在外面安心。其他的,不敢想太多。”茶里茶气的味道熏满了整个餐厅。
长桌另一头的周聿白,一直沉默进食、对周遭毫不关心的周聿白,握刀的修长手指,
几不可查地停顿了零点一秒。他极慢地抬起眼,视线隔着满桌佳肴和人影,
第一次落在了我脸上。那眼神很沉,很深,像潭底打捞起的古井寒水,
带着无声的审视和探究。仿佛第一次真正“看见”我。晚餐如同裹了一层蜜糖的酷刑,
终于结束。踏出周家老宅那座沉重压抑的大门,外面已经飘起了细密的雨丝。
丝绒般粘腻潮湿的空气涌入口鼻,却比宅子里更舒服几分。坐进回程的库里南后座,
车厢里只有冷气单调的嘶嘶声。皮质座椅散发出新簇簇的味道。周聿白上车后就闭目养神,
仿佛身边坐的只是团空气。**着冰冷的车窗,雨水在玻璃上蜿蜒扭曲地爬行,
映着窗外飞驰而过的模糊霓虹。身体里的那股劲一松,宴会厅里强装的羞怯顺从瞬间剥落。
疲惫感像铅块一样从骨头缝里渗出来。车子驶入车库幽暗的光线里。无声的电梯一路攀升。
“滴”的一声轻响,冰冷的电子锁解开。玄关处的感应灯应声而亮,
在空旷的大理石地面上投下一小片惨白的光圈,瞬间又熄灭了,只留下朦胧的轮廓。
这栋顶复公寓大得离谱,也空旷得吓人。顶级的装修,昂贵的物件,处处透着疏离的完美感,
像一个精心打造却毫无人气的豪华样板间。我和他,是误闯进来的两颗孤单螺丝钉。
他径直走向主卧,门锁开合的轻微“咔哒”声在寂静中格外刺耳,像隔绝了两个世界。
我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向另一头的次卧,那是我暂时的栖身地。高跟鞋敲在大理石地上,
回声在空旷的客厅里撞来荡去,更显得死寂。次卧很大,衣帽间空着一大半,
浴室光洁得没有一丝水痕。躺进那张过分宽大、垫着昂贵羽绒垫的床铺,身体陷进去,
却觉得四肢百骸都悬着,无处着力。黑暗中,
天花板上隐约的几何浮雕纹路模糊成一片深海似的暗影,沉沉压下来。
、周聿白那张戴着完美面具却冰冷入骨的脸……一种巨大的、深入骨髓的孤独感猛地涌上来,
像是突然被扔进了真空,连呼吸都变得困难。胃部一阵阵地抽搐痉挛,闷闷地疼。
喉咙干得像砂纸打磨。鬼使神差地,我爬下床,赤脚踩在冰凉的微水泥地面上,
悄悄摸了出去。客厅没开灯。窗外的城市灯火透过巨大的落地窗漫进来,
给整个空间铺上一层沉浮不定、光怪陆离的幽蓝色调。酒柜是半开放式的,嵌在客厅侧墙,
透明的玻璃门后是琳琅满目的各色酒瓶,在微弱的光线下幽幽反射着诱惑的光泽。手有点抖。
我踮着脚,拉开玻璃门,没发出一点声音。冰凉的瓶身,
威士忌特有的烟熏泥煤味道冲入鼻腔。……能麻醉一会儿就好。找开瓶器。
这地方设计得极简,抽屉都隐藏得巧妙。凭着印象拉开一个嵌在墙面的窄抽屉,
手伸进去摸索——指尖碰到一个冰冰凉凉、方方正正的金属盒,表面印着褪色的烫金字母,
是种我不认识的洋文。不像开瓶器。有点沉。疑惑地掏出来,借着窗外微弱的光看,
像是个老式的雪茄盒。周聿白的东西?管他呢。随手丢在一边。再摸。
指尖终于触到开瓶器熟悉的金属轮廓。成功!瓶口被撬开发出“啵”一声轻响。
甚至来不及倒进杯子,直接对着瓶口灌下去。辛辣**的液体粗暴地冲刷过喉咙,
灼烧感一路向下,在胃里轰然炸开!“咳……!”猝不及防被呛到,火烧火燎地咳了起来。
辛辣的灼痛感从嗓子眼一直蔓延到肺里,生理性的泪水瞬间就涌了出来,狼狈不堪。
咳声在死寂空旷的客厅里被无限放大,撞在冰冷的墙壁上又弹回来,显得格外突兀和难堪。
我捂住嘴,咳得弯下腰,感觉整个五脏六腑都在痛苦地挤压。身后,通往主卧的走廊方向,
一束冷白的光毫无预兆地泼了过来,利落地切开客厅里的幽暗。光线的尽头,
是被拉长的、一个高大的阴影。脚步声,沉稳,清晰,带着被扰眠的寒意,
不疾不徐地踏过来。每一步,都踩在我绷紧的神经上。我僵住,后背瞬间一层冷汗。
擦泪的手顿在半空,另一只手还死死抓着那个惹祸的酒瓶。不敢回头。
那令人窒息的脚步停在身后几步远的地方。我能感觉到他审视的目光,
像冰冷的刀锋刮过我的后颈。黑暗中只听到自己粗重的、压抑着喘息的声音,
还有那沉缓逼近的脚步。每一步都碾在我绷紧的神经末梢上,寒意顺着脊柱往上爬。
“酒不错。”低沉的嗓音在身后响起,带着刚睡醒的微哑,
还有一丝压抑的、不易察觉的恼火。“选它自残,品味差了点。
”我死死攥着酒瓶粗糙的玻璃,指甲刮在上面发出轻微的吱嘎声。喉咙里**辣地疼,
想反驳,却咳得发不出声音。就在这窒息般的僵持里,
一股极其特别、难以形容的香气忽然钻进鼻腔。冷冽。微苦。像深秋雨后被冻住的松林。
不是香水,更清新也更霸道,带着一种久远的、被时光浸透的沉重记忆感。
这缕冷香混合着周聿白身上原本那种昂贵的、疏离的木质调气息,
莫名地形成一种奇异的、不容忽视的存在感,霸道地弥漫在狭小空间里。
我脊背的肌肉下意识地绷紧了些,呼吸凝滞。
就在这诡异的、混杂着酒气、呛咳和他那神秘冷香的沉默里,周聿白又向前踏了一步。
阴影彻底笼罩下来。一只温热宽大的手,突然覆上了我攥着酒瓶的那只手背!
皮肤接触的瞬间,像被一小簇静电猛地蜇了一下,我全身的寒毛都竖了起来。他掌心很热,
带着男性特有的干燥和力量感,完全覆盖住我的手背。滚烫的温度通过皮肤接触传导过来,
与威士忌灼烧胃部的痛苦内外夹击,几乎将我点燃。他的手没有多余动作,
只是稳稳地按住我的手背,和下面紧握的瓶颈。“放手。”命令式的低语,
气息擦过我颈侧脆弱的皮肤,引发一阵细微的颤栗。他掌心的温度太具侵略性,
混合着那丝若有若无的冷苦松香,像一张无形的网,困得我动弹不得。
原本就被烈酒呛得难受,此刻更是连喘气都艰难。指尖动了动,想挣扎,
却发现自己那点力气在他面前如同蚍蜉撼树。徒劳的僵持只持续了一两秒,
全身的力道仿佛被那只滚烫的手瞬间抽空,颓然一松。沉重的酒瓶从失去力气的手中滑落,
被他稳稳接了过去。瓶身相撞的闷响在空旷的客厅里惊心动魄地回荡。
手背上的压迫感和灼热终于撤开。但那股奇异馥郁、掺杂着冷苦松香的气息却像有生命般,
反而更紧密地缠绕上来。它混合着空气里残余的浓烈酒气,
形成一种微醺又清醒、眩晕又清晰的复杂感官漩涡。大脑一片空白。胃里翻江倒海。
身体失去支撑,晃了一下,软软地朝旁边的大理石吧台栽下去。没有预想中冰凉的撞击。
一条结实的手臂迅捷地揽住了我的腰侧。隔着轻薄的丝质睡裙,
他臂膀的力道和灼热如同烙铁,带着不容抗拒的强悍。我被这股力量猛地带向他身侧,
身体失衡地撞进一片坚实温热的胸膛里!
浓烈的、独属于他的男性气息混合着那霸道的冷苦松香,瞬间裹挟住所有感官,铺天盖地,
密不透风!鼻腔被彻底侵占。
脸颊撞在熨帖平整、甚至带着一丝昂贵浆洗味道的深色真丝睡衣面料上,质地微凉丝滑,
但底下包裹的胸膛却有着灼人的热度,强健的肌肉线条透过轻薄衣料清晰可辨。心跳。
不知是谁的,擂鼓般急促地震动,隔着胸腔传来混乱沉闷的回响,分不清源头。
血液“轰”地一下全涌上头脸,像被无形的火焰点燃,
灼烫感从被触碰的腰侧、撞进他怀里的脸颊,迅猛燎原般烧遍全身。
这个认知带来的惊悸甚至压倒了醉酒的不适。指尖僵硬得如同冰雕。
他扶在我腰间的那只手臂,热度惊人,带着掌控性的力道,烫得我不由自主地微微发颤。
我们身体贴合得严丝合缝,我能清晰地感觉到他胸腔的每一次起伏、他肌肉的紧绷轮廓。
他比我高太多,我的额头抵在他胸口偏下的位置,
鼻尖甚至能嗅到他衣领间更清晰的、掺杂着冷杉木与烟熏皮革的气息。死寂。
空气里的尘埃仿佛都凝滞不动。时间被无限拉长,
每一秒都在放大身体的接触和感官的触觉——腰侧臂弯的钳制感,
脸颊下隔着布料传来的强健心跳,
鼻尖霸道缠绕的、混合了汗意与那冷苦木质调的浓烈男性气息……我像被点了穴。
周聿白似乎也僵住了。他的呼吸有半秒短暂的凝滞,温热的鼻息拂过我头顶的发丝。
整个胸膛的肌理绷得像块硬邦邦的石头,抵着我的脸。不知过了多久,可能几秒,
也可能更长,久到我快溺死在这片令人窒息的紧密拥抱里——他的手臂终于微微动了动,
似乎是要松开的动作。喉咙里火烧火燎,胃里翻搅的酸楚感被这强烈的冲击猛地压下,
又被猛地勾起来。“呕——!”喉咙深处无法控制地涌上一股强烈的酸腐气,胃袋抽搐着,
有什么东西不受控制地顶到了嗓子眼!我下意识地、死死地捂住了嘴!
这个粗暴的动作打断了即将抽离的怀抱。紧贴的身体猛地一僵!
周聿白几乎在瞬间绷紧了全身肌肉,搂在我腰后的手臂骤然收紧,像铁箍般勒紧,
阻止了我不受控制要前倾的动作。“你敢!”压抑着的低喝从头顶传来,
带着一丝狼狈的切齿声,是惊怒,甚至有点难以置信!他那张永远波澜不惊的冷脸上,
此刻写满了被冒犯的震惊。下一秒,
我被他几乎是半提半抱着冲进最近的、开着门的小盥洗室!
冰凉的洗手台边缘猛地撞上我的小腹,钝痛袭来。我眼前发黑,
胃里翻江倒海最后一点理智崩断。顾不上任何形象,也顾不上旁边那尊煞神黑如锅底的脸色,
猛地对着光洁如镜的白色台盆弯下腰。
“呕…呕咳——”生理性的剧烈呕吐声伴随着酸腐的气味,在狭小封闭的空间里回荡,
格外难堪。耳边仿佛还残留着他那句惊怒的“你敢”在嗡嗡作响。脸颊滚烫得像着了火。
胃袋空了,只剩一阵阵难受的痉挛。力气被抽干,我软软地趴在冰冷的大理石台面上,
连抬头的力气都没有。冷水龙头开着,哗哗的水声掩盖不住狼狈的喘息。
盥洗室明亮的顶灯泼洒下来,有些刺眼。眼角余光能扫到一抹深灰色身影靠在门框上。
那人影动了一下,似乎是伸手要扯纸巾的动作停顿在空中,
然后极其烦躁地将一盒纸巾精准地丢在洗手台离我手边最近的位置,动作带着明显的嫌弃。
接着,是沉重的脚步声,快速离开了这片狼藉区域。很快,外面客厅的方向,
传来一声明显不悦的、带着命令式冰冷语调的通话声,
穿透了哗哗的水声:“……送醒酒汤上来。现在。”那声音里仿佛还裹着冰碴子。
水哗哗地流。我撑在冰凉的台面上,手指紧紧抠着边缘,骨节泛白。
胃里的恶心在冷水**下稍微平复了些许,但另一种更陌生、更滚烫的余悸,
却在那冰冷的木质与微辛的松香混合的气息无声蔓延中,
顺着被勒紧过的腰、脸颊残存的温度,丝丝缕缕渗透进四肢百骸,无声地灼烧。
【第二章裂隙渐生】醒来时头疼得像要裂开。
眼前是陌生的、挑高的、素雅得没有一丝多余颜色的天花板。
晨光透过厚重的遮光帘缝隙挤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一条刺眼的白光。
宅那些人刻薄的打量、呛辣的威士忌、失控的呕吐……最后定格在混乱盥洗室明亮的灯光下,
那个靠在门框上的深灰色身影,眼神里的冰冷和无声的嫌恶清晰如昨。
脸颊不受控地烧了起来。翻身下床,双腿还有点虚软。走出冰冷空旷的次卧,
偌大的客厅里空无一人,空气里只有中央空调低沉的送风声。
昨晚的一片狼迹已经被清理干净,光洁如新的大理石地面能倒映出人影,
空气里只有一丝微不可查的消毒水气味。餐桌上倒是放着一个保温壶。揭开盖子,
是温热的醒酒汤,里面沉着几颗饱满的红枣。没留任何纸条。显然,
是来自周聿白的授意——一种极致的疏离与程式化的“照料”。
他甚至不愿亲自看见我此刻的狼狈。自嘲地扯了扯嘴角,灌下半壶温度正好的汤,
胃里总算熨帖了些。手机震动打破了死寂。屏幕上是父亲略显颓唐的照片。点开,
他的声音透着深重的疲惫和小心翼翼:“小晚…醒了?昨天……还好吧?”“嗯。爸,
怎么了?”声音有点哑。那头沉默了几秒,像是积蓄力量,或者说,难以启齿。再开口时,
那份疲惫里掺了更多焦灼。“港口那块地……周老那边,
还是没有最终签字的动静……风声……最近不太好……”他话语支吾,刻意压低了音量,
背景有些嘈杂,“有些…资质的问题,被…翻了出来?
卡在很关键的审批环节…你能不能……问问聿白?”心猛地往下一沉,像坠进了冰窟窿里。
我甚至能想象周崇山那张冰冷精于算计的脸。
协议婚约的本质被**裸地揭露——林家求来的救命稻草,终究系在别人的喜怒之上。
而周聿白?他和他那个爷爷,更像是一路货色。“我知道了。”喉咙发紧,简短应了三个字,
仿佛再多说一个字,那股屈辱的浊气就要喷涌而出。挂了电话,指尖冰凉。看向走廊尽头,
那扇紧闭的主卧门,像隔着一座冰山。踌躇再踌躇。时间一分一秒,都像是压在心头的巨石。
下午五点整。书房门口。深吸一口气,抬手敲门。门很快开了。周聿白站在门内。
他应该是开了一天的会,西装外套搭在椅背上,只穿着剪裁精良的白色衬衫,袖子挽到手肘,
露出手腕上那只价值不菲的宝玑表。灯光在他深邃的眉眼上投下淡淡的阴影,
神情依旧是那种公私分明的疏离和冷静。“有事?”他垂眸看着我,语气平淡,
没有任何波澜起伏,像是在问一份无关紧要的文件。
“港口那块地……”我尽量让声音听起来平静,不去想父亲电话里那点卑微的哀求,
“……爷爷那边,是不是还有些考量?”他没立刻回答。视线越过我,
落在客厅茶几上一个摊开的皮质文件盒上。那盒子做工极为考究,低调的深褐色,
金属搭扣泛着温润的光泽。“爷爷的考量,向来以周家利益为先。”他收回目光,
重新落在我脸上。那双眼睛里没什么温度,只有一种洞悉了交易本质的冷然。“你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