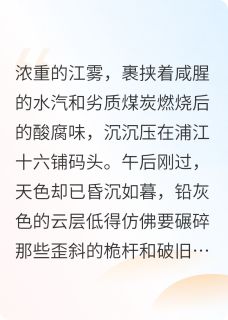“还有,”柳佘的声音再次响起,如同冰水浇头,“那个盒子。”
杜仲的脚步猛地停住,霍然转头看向柳佘。
柳佘的目光投向巡捕房走廊的尽头,那里是证物室的方向。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凝重:“二楼书房书柜顶层的檀木盒子。赵彪的供词里,完全没有提及它。但直觉告诉我,那东西……比吴铁山的死,更危险。”
杜仲的心猛地一沉。他想起了柳佘在书房门口那瞬间的异样和极度警惕的眼神。那个不起眼的旧盒子……里面到底藏着什么?
“走!”杜仲当机立断,抓起桌上的警帽,“去证物室!”
两人快步穿过巡捕房嘈杂的走廊。推开证物室的门,里面光线昏暗,充斥着灰尘和旧纸张的气味。负责管理的老李头正在打盹,被杜仲的脚步声惊醒。
“吴铁山书房搜出来的那个檀木盒子呢?”杜仲沉声问。
老李头揉着眼睛,指了指靠墙的一个铁架子:“喏,最上面那层,编号物证A-07。”
杜仲和柳佘立刻走过去。那个古朴的檀木盒子就放在架子最上层,蒙着一层薄灰。杜仲戴上手套,小心翼翼地把它取了下来,放在中间的长条桌上。
盒子没有上锁,只是用一根褪色的红绳松松地系着。杜仲解开红绳,屏住呼吸,缓缓掀开了盒盖。
一股陈旧纸张和淡淡霉味扑面而来。
盒子里面,没有金银珠宝,只有厚厚一沓泛黄发脆的旧文件、几张模糊不清的老照片,以及……一本薄薄的、深蓝色硬皮封面的小册子。
杜仲拿起最上面一张照片。照片背景像是一个破旧的院落,一群穿着灰扑扑、不合身衣服的孩子排着队,神情麻木呆滞。照片一角,一个穿着修女服饰、面容模糊的外国女人正低头看着什么。照片背面,用潦草的钢笔字写着:“仁爱育婴堂,民国五年夏”。
仁爱育婴堂?杜仲皱紧眉头,这个名字有点耳熟,似乎是法租界二十多年前一家由外国教会开办的孤儿院,后来好像因为一场大火关闭了?
他又拿起一张文件,是一份泛黄的、字迹娟秀的名单登记册。上面罗列着一些孩子的名字、编号、年龄和极其简短的备注。杜仲的目光扫过那些备注:“左臂胎记”、“右耳缺失”、“足内翻”、“疑似痴愚”……冰冷得如同在记录牲口。
当他翻到一本深蓝色硬皮小册子时,里面的内容让他的血液瞬间冲上头顶!册子内页是打印的英文表格,记录着一些他完全看不懂的、冗长复杂的化学分子式、剂量、注射时间、观察记录。表格抬头印着一行英文小字:ProjectChimera(PhaseIII)–NeurologicalResponseObservationLog。
“ProjectChimera……喀迈拉计划?”杜仲艰难地念出那个单词,心头涌起强烈的不安。喀迈拉,希腊神话里狮头羊身蛇尾的怪物!他用询问的目光看向柳佘。
柳佘一直沉默地站在桌边,目光落在那些文件和照片上。当杜仲拿起那本深蓝色记录册时,柳佘的身体几不可察地绷紧了一瞬。他伸出手,动作异常小心地接过那本册子,指尖微微有些发凉。他快速地翻看着那些英文记录和分子式,苍白的脸色在昏暗的光线下显得更加透明。那双深潭般的黑眸里,翻涌着杜仲从未见过的、极其复杂的情绪——震惊、冰冷,以及一丝……难以言喻的、源自灵魂深处的剧痛和厌恶。
“神经反应观察日志……”柳佘的声音低得如同耳语,却带着一种金属摩擦般的冰冷质感,“这是……人体实验记录。他们用孤儿……测试某种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的药物。”他指着其中一页表格下的几行潦草英文批注,“记录显示……药物引发剧烈痉挛、定向力障碍、不可逆脑损伤……死亡率……极高。”
“什么?!”杜仲如遭雷击,猛地攥紧了拳头,指关节捏得咯咯作响,一股狂暴的怒火瞬间吞噬了他!人体实验?用孤儿?!这他妈还是人干的事吗?!
就在这时,柳佘的目光定格在册子最后一页夹着的一张小小的、裁剪下来的旧报纸上。报纸日期是民国九年。一则豆腐块大小的社会新闻标题赫然在目:“仁爱育婴堂昨夜突发大火数十名孤儿不幸罹难疑为炉灶管理不善所致”。
报道旁边,还附着一张极其模糊的火灾现场照片,只能看到一片焦黑的断壁残垣。
柳佘的手指,轻轻抚过那则报道的标题。他的指尖冰凉,没有一丝温度。他的目光抬起,越过证物室污浊的空气,投向虚空,深不见底的黑眸深处,仿佛有来自地狱的火焰在无声地燃烧。那火焰冰冷刺骨,焚尽一切。
“那场大火……”柳佘的声音轻得像叹息,却带着千钧的重量,“不是意外。”
杜仲只觉得一股寒意瞬间冻结了他的四肢百骸。他顺着柳佘的目光,也死死盯住了那则火灾报道。一个恐怖的猜想,如同毒蛇般缠绕上他的心脏:吴铁山的死、仁爱育婴堂、人体实验、神秘大火、贺天彪的嫁祸……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庞大到令人窒息的黑暗漩涡!这个漩涡的中心,恐怕远不止一个贺天彪!那个檀木盒子,果然是一个散发着血腥诅咒的潘多拉魔盒!
证物室里死一般的寂静。灰尘在昏黄的光柱里缓缓飘浮。盒子里的文件、照片、记录册,无声地躺在桌上,散发着陈腐的死亡气息,却比任何刀枪都更锋利地刺穿着两个男人的神经。
柳佘缓缓合上那本深蓝色的记录册,动作轻柔得像是在合上一具棺椁。他抬起头,看向杜仲。那眼神里,所有的沉静都被一种冰冷的、燃烧的决绝所取代。
“名单,”柳佘的声音斩钉截铁,打破了死寂,“这份名单上记录的孤儿,编号,去向……必须查清楚。”他指向盒子里的那份名单登记册,“还有当年育婴堂的负责人、医生、资助者……所有关联者。”
杜仲用力抹了一把脸,粗糙的掌心擦过下巴的胡茬,带来一丝刺痛,让他从滔天的愤怒和寒意中强行挣脱出来。他重重地点头,眼神重新凝聚起属于老探长的狠厉与决心:“查!从根儿上查!老子倒要看看,这潭黑水底下,到底藏着多少吃人的王八!”他抓起桌上的名单登记册,像握着一把烧红的烙铁,“就从这上面的人开始!活要见人,死……也要见尸!”
法租界边缘,一条被遗忘的陋巷深处,“慈心孤儿院”的破旧招牌在连绵的阴雨中显得更加黯淡无光。几棵歪脖子老槐树在风雨中摇曳着枯枝,如同鬼影。空气里弥漫着潮湿的霉味、劣质煤球燃烧的硫磺味,还有一股若有若无的、令人不安的消毒水气味。
杜仲和柳佘站在孤儿院锈迹斑斑的铁门外。雨水顺着杜仲深灰色旧雨衣的帽檐不断滴落,他脸色阴沉得如同此刻的天空。柳佘站在他身侧半步之后,依旧是一身刺眼的白大褂,外面罩着透明的雨披,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那双深潭般的黑眸,比平时更加幽暗,警惕地扫视着孤儿院斑驳的围墙和黑洞洞的窗户。
他们按照名单登记册上的线索追查至此。名单上标注为“疑似痴愚”的一个编号为“丙柒”的孩子,最后模糊的“安置”记录指向了这家“慈心孤儿院”。而更令人心悸的是,根据警局尘封的旧档案,这家孤儿院的第一任院长,赫然就是当年仁爱育婴堂火灾后仅存的几个核心管理人员之一——周文彬!一个披着慈善外衣的恶魔!
“开门!巡捕房查案!”杜仲用力拍打着湿滑的铁门,沉闷的声响在寂静的巷子里回荡。
许久,一阵迟缓的脚步声从里面传来。铁门上的小窗被拉开一条缝,露出一张布满皱纹、眼神浑浊的老妇人的脸。她是看门的哑婆,只能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比划着询问。
杜仲亮出警徽,哑婆看清后,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但还是慢吞吞地打开了沉重的铁门。
门轴发出刺耳的**。一股更加浓重的、混合着劣质消毒水和潮湿霉烂的气息扑面而来。院子不大,坑洼的水泥地上积着浑浊的水洼,几件破旧的童装湿漉漉地挂在歪斜的晾衣绳上。几个面黄肌瘦的孩子缩在屋檐下,睁着空洞的大眼睛,麻木地看着闯入的不速之客,脸上没有任何属于孩童的好奇或恐惧。
一个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阴丹士林布旗袍、围着素色围裙的中年女人匆匆从主楼里迎了出来。她约莫四十岁上下,面容清秀却带着挥之不去的疲惫,头发一丝不苟地在脑后挽成一个髻。看到杜仲的警服,她脸上掠过一丝紧张,但很快被一种职业性的温和笑容掩盖。
“警官先生?我是这里的老师,陈静。请问有什么事吗?”她的声音很轻柔,带着点江南口音。
杜仲锐利的目光迅速扫过陈静全身,最后落在她那双骨节分明、指甲修剪得很干净的手上。这双手,正下意识地绞着围裙的边缘。
“周文彬,认识吗?”杜仲开门见山,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压迫感。
陈静的身体几不可察地僵硬了一下,眼神有一瞬间的闪烁,随即垂下眼帘:“周……周院长?他……他是我丈夫的远房表叔,也是这家孤儿院以前的院长。不过,他……他身体不好,很多年前就回乡下老家养病了。后来这里就由我和我丈夫打理……”她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是吗?”杜仲逼近一步,高大的身影带来无形的压力,“我们查到他和你丈夫,当年都在仁爱育婴堂做过事!”
陈静的脸色瞬间褪尽血色,变得惨白如纸。她猛地抬起头,嘴唇哆嗦着:“那……那都是过去的事了……我……我和我丈夫只是……只是帮着照看孩子……其他的……我们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她的声音里充满了恐惧,身体微微发抖。
柳佘站在杜仲侧后方,一直沉默地观察着陈静的反应,以及周围的环境。他的目光掠过屋檐下那些神情呆滞的孩子,扫过主楼窗户上积满灰尘的玻璃,最后停留在院子角落一个半掩着的、低矮的工具房门上。那扇门里,透出比外面更浓重的消毒水气味。他的眉头几不可察地蹙了一下,一种极其微弱的、混杂着血腥和消毒水的怪异气息,被他的嗅觉敏锐地捕捉到,正从那工具房的方向隐隐飘来。
“陈老师,”杜仲的声音放缓了一些,但眼神依旧锐利,“我们不是来找你麻烦的。只想了解一些过去的情况。能让我们进去看看吗?特别是……周文彬以前住的地方,或者他留下的东西?”
“这……”陈静显得更加慌乱,眼神下意识地瞟向主楼二楼一个紧闭的窗户,又飞快地收回来,“没什么好看的……都……都堆着杂物……很乱……”
就在这时,一阵压抑的、断断续续的哭泣声从主楼后面传来。那哭声很稚嫩,却充满了恐惧和绝望。
陈静脸色一变,连忙说:“是……是小宝!那孩子又犯病了!我得去看看!”她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转身就要往后院跑。
“等等!”杜仲一把拦住她,眼神如电,“我们一起去看看。正好,这位柳大夫是医生。”他指了指柳佘。
陈静的身体彻底僵住,眼神里的恐惧几乎要溢出来。
柳佘的目光则越过陈静的肩膀,死死盯住了主楼侧后方,那扇半掩的工具房门。那股混合着血腥和消毒水的诡异气味,陡然变得清晰起来!像一只冰冷的手,扼住了他的咽喉!
“工具房。”柳佘的声音突兀地响起,清冽如冰,穿透了压抑的雨声和陈静压抑的抽气声。
杜仲瞬间明白了柳佘的暗示。他不再理会陈静,猛地转身,大步流星地冲向那个角落的工具房!陈静发出一声短促的惊叫,想要阻拦,却被柳佘无声地挡在了身前。少年法医的眼神冰冷而锐利,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警告。
工具房的门被杜仲一把推开!
浓烈到令人作呕的血腥味和消毒水味如同实质般扑面而来!昏暗的光线下,只见一个穿着和陈静同款蓝色阴丹士林布旗袍的身影,面朝下倒在一堆散乱的麻袋和破旧工具中间。暗红色的血液,正从她身下汩汩地蔓延开来,在地面肮脏的水泥上晕开一大片粘稠的、刺目的猩红!
杜仲瞳孔骤缩!是陈静?不对!那身形……比陈静更年轻些!
他一个箭步冲进去,蹲下身,小心地将尸体翻转过来。
一张年轻、清秀却因痛苦和恐惧而扭曲的脸映入眼帘!正是昨天下午还去巡捕房报过案、声称自己掌握了仁爱育婴堂一些秘密的实习老师——林晚晴!她的喉咙被粗暴地割开,伤口深可见骨,染红了半边衣襟。但更让杜仲瞬间血液逆流、浑身冰冷的是——一把沾满鲜血和碎肉的铁钩,正深深地嵌在她微微张开的嘴里!
那铁钩!那扭曲的形状!那熟悉的、带着倒刺的冰冷弧度!
轰——!
杜仲只觉得眼前猛地一黑,仿佛被一柄无形的重锤狠狠砸中了后脑!二十多年前那个潮湿、阴暗、散发着同样浓烈消毒水气味的禁闭室,那个穿着白大褂、笑容狰狞的男人,手里晃荡着的、闪着寒光的铁钩……所有被刻意封存的、地狱般的记忆碎片,如同决堤的洪水,带着撕裂灵魂的剧痛,瞬间将他吞噬!
“啊——!”
一声压抑到极致、仿佛从灵魂深处撕裂出来的野兽般的低吼,不受控制地从杜仲喉咙里迸出!他高大的身体剧烈地摇晃了一下,脸色惨白如金纸,额头上瞬间布满了豆大的冷汗,那双总是锐利如鹰的眼睛,此刻充满了血丝和一种近乎崩溃的惊骇!他死死盯着那把铁钩,像是看到了从地狱最深处爬出来的恶鬼!
柳佘紧跟着冲进工具房。刺鼻的血腥味和杜仲那声痛苦的低吼让他心头一凛。他的目光第一时间落在尸体喉咙的致命伤上,快速评估着创口形态和出血量。随即,他也看到了那把深深嵌在死者口中的铁钩。那东西的形态极其凶残,带着一种刻意施加的侮辱和折磨意味。
柳佘的视线立刻转向杜仲。探长此刻的状态极其糟糕,高大的身躯佝偻着,靠着门框才勉强站立,一只手死死捂着头,指关节捏得发白,身体无法控制地颤抖,眼神涣散而痛苦,仿佛正经历着非人的折磨。
柳佘的心猛地一沉。杜仲的反应绝非仅仅是面对凶案现场的震惊,那把铁钩……触发了某种深埋的、极其恐怖的创伤记忆!
就在这时,柳佘眼角的余光瞥见尸体那只垂落在血泊中的右手。手指微微蜷曲,食指的指尖似乎沾着一点深褐色的、尚未干透的泥土。而那泥土的颜色和质地……柳佘的目光闪电般扫过工具房泥泞的地面——这里的泥土是黑色的!而尸体指尖的泥土,是黄褐色的!
他立刻蹲下身,不顾血腥,靠近那只手。果然,在食指指甲缝里,除了血迹,还嵌着几丝极其细微的、新鲜的黄褐色草屑!
林晚晴临死前,接触过外面的、有黄草的地方!她不是在这里遇害的!这里只是抛尸现场!
这个发现如同闪电劈开迷雾!柳佘猛地抬头,目光锐利如刀,穿透工具房昏暗的光线,投向门外——刚才那阵压抑的哭声传来的方向,是后院!
“后院!第一现场!”柳佘的声音斩钉截铁,带着不容置疑的穿透力,试图将几乎被痛苦淹没的杜仲拉回现实。
杜仲的身体剧烈地一震!柳佘的声音像一道冰冷的电流,瞬间刺穿了他意识中翻腾的血色地狱!后院……哭声……林晚晴指甲缝里的草屑……
他猛地抬起头,布满血丝的眼睛里爆发出骇人的凶光!那不再是崩溃,而是被最深沉痛苦点燃的、不顾一切的狂暴!他像一头受伤后暴怒的雄狮,喉咙里发出一声低沉的咆哮,甚至顾不上工具房里的尸体和柳佘,猛地转身,如同一道灰色的闪电,撞开呆若木鸡、瘫软在门口瑟瑟发抖的陈静,疯狂地朝着后院方向冲去!
柳佘没有丝毫犹豫,立刻起身跟上。他的动作迅捷而无声,白大褂的下摆在浓重的血腥味中掠过一道冰冷的轨迹。他一边疾奔,一边从随身携带的勘察包里快速取出橡胶手套戴上。杜仲的状态极度危险,他必须跟上!
后院比前院更加荒凉破败。几畦蔫头耷脑的蔬菜,几棵半死不活的果树,角落里堆着高高的、潮湿发黑的柴垛。雨水冲刷着泥泞的地面。杜仲像无头苍蝇一样,赤红着双眼,在泥地里疯狂地搜寻着,用脚踢开散乱的杂物,目光扫过每一个可能藏匿罪恶的角落。
柳佘则截然不同。他停在院门口,目光如同最精密的扫描仪,快速而冷静地扫过整个后院。泥泞的地面布满杂乱的脚印,大部分是孩子的,也有大人的。他的视线掠过那些脚印,最终定格在柴垛附近一小片被踩踏得异常凌乱的泥地上。那里的黄褐色泥土被翻起,几株稀疏的野草被踩倒,倒伏的方向凌乱,显示出剧烈的挣扎痕迹!痕迹的边缘,散落着几点极其微小的、颜色略深的喷溅状血点,几乎被雨水冲刷干净,但在柳佘眼中却如同黑夜里的萤火!
“这里!”柳佘指向柴垛边缘。
杜仲闻声猛地冲过去,目光死死盯住那片凌乱的泥地。当他看到那几点几乎消失的血迹时,暴怒的情绪如同被冰水浇头,瞬间被一种更加深沉的、带着血腥味的冰冷取代。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蹲下身,像个真正的猎手,仔细观察着泥地上留下的痕迹。
成年男性的脚印!尺码很大,鞋底纹路很清晰,是那种廉价胶鞋的粗齿印!脚印在挣扎区域非常密集,拖拽的痕迹指向柴垛后面那条通往孤儿院后墙小门的、更加狭窄肮脏的死胡同!
杜仲的眼神瞬间凝聚如刀锋!他站起身,没有丝毫犹豫,拔腿就朝着那条死胡同追去!柳佘紧随其后。
死胡同又窄又深,两侧是斑驳的高墙,堆满了各种废弃的垃圾和杂物,散发着浓烈的腐臭。雨水顺着墙缝流淌下来。杜仲像一头追踪血腥的猎犬,目光在泥泞的地面和两侧的杂物堆上飞速扫视。突然,他的脚步猛地钉在原地!
在胡同尽头,靠近后墙一个废弃狗窝的旁边,泥泞的地面上,清晰地印着半个带血的脚印!那血脚印的旁边,散落着几枚沾着新鲜泥污的烟蒂——飞马牌的,很常见的廉价烟。
杜仲蹲下身,用戴着手套的手指,小心翼翼地捡起一枚烟蒂。烟蒂的过滤嘴部分,被雨水打湿,上面似乎沾着一点极其微小的、深褐色的污渍,像是……凝固的油漆?或者……某种深色的油彩?
他抬起头,目光锐利地扫视着周围。墙根下,散落着几块破碎的、褪色的木头招牌残骸。其中一块稍大的碎片上,隐约还能辨认出一个模糊的字迹——“……漆坊”?
“油漆工?”杜仲的声音低沉沙哑,带着一种捕猎前的兴奋。他立刻拿出随身的小本子和铅笔,飞快地勾勒下那个血脚印的形状、尺寸,并小心地将那枚沾有可疑污渍的烟蒂装入证物袋。
柳佘站在杜仲身后几步远的地方。他的目光并未停留在烟蒂和脚印上,而是越过杜仲的肩膀,投向胡同尽头那堵高高的、爬满苔藓的后墙。墙头上,几块碎瓦片被蹭掉了新鲜的苔藓,留下几道明显的攀爬痕迹。痕迹很新,雨水都还没完全冲刷掉上面的泥印。
凶手翻墙跑了。外面……就是迷宫般错综复杂的棚户区和更深的黑暗。
柳佘收回目光,看向蹲在地上、浑身散发着狂暴气息却又强迫自己专注于线索的杜仲。探长沾满泥污的雨衣后背微微起伏着,像一头压抑着随时会爆发的猛兽。那把染血的铁钩,显然勾起了他最深沉的噩梦。柳佘的嘴唇无声地抿紧,深潭般的眼底掠过一丝极淡的、难以解读的波动。他沉默地退开一步,目光再次投向孤儿院主楼的方向,那里,还有一群被恐惧笼罩的孤儿,和一个浑身颤抖、明显知道些什么的女教师陈静。
后院的风雨似乎更急了,呜咽着卷过破败的院落,将血腥味和消毒水味搅得更浓。慈心孤儿院的破旧招牌在风雨中发出不堪重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