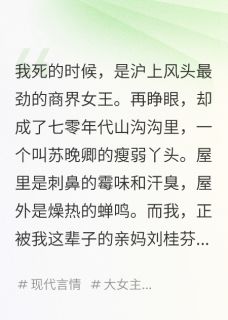我死的时候,是沪上风头最劲的商界女王。再睁眼,却成了七零年代山沟沟里,
一个叫苏晚卿的瘦弱丫头。屋里是刺鼻的霉味和汗臭,屋外是燥热的蝉鸣。而我,
正被我这辈子的亲妈刘桂芬死死按在地上,蒲扇大的巴掌一下下扇在我脸上,
嘴里骂骂咧咧:“死丫头!叫你跑!老王家出五十块钱彩礼,给你哥娶媳妇,那是看得起你!
你还敢跑?”一个满口黄牙、浑身汗臭的老男人,正搓着手,一脸淫笑地盯着我,
他就是我妈口里的“老王家”——村西头的老光棍,王瘸子。我爹苏建国蹲在门槛上,
吧嗒吧嗒抽着旱烟,闷声说:“桂芬,别把人打坏了,卖相不好,老王头该不认了。
”我那被全家当成宝的哥哥苏卫东,则靠在墙边,一脸不耐烦地催促:“妈,你快点,
春花还等着我回话呢!”这一家子,为了五十块钱,为了给宝贝儿子娶媳妇,
就要把我这个亲生女儿、亲妹妹,推进火坑。前世在十里洋场摸爬滚打,
我苏晚卿什么阵仗没见过?但这一刻,心底的寒意,却比黄浦江的冬水还要刺骨。
我没哭没闹,只是冷冷地抬起眼,迎上王瘸子贪婪的目光。然后,我笑了,用尽全力,
从肿胀的嘴角挤出一个冰冷的、轻蔑的笑。王瘸子一愣。我那还在叫骂的妈也停了手。
全家人都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我。我用只有我和王瘸子能听到的声音,轻轻说:“王大伯,
五十块钱,买我这么一个不听话的,三天两头就得往娘家跑,你还得好吃好喝伺候我爹妈,
不然他们就来闹你。这笔买卖,你亏大了。”他脸上的淫笑,瞬间僵住。1“你个死丫头,
胡说八道什么!”刘桂芬没听清我说什么,但看王瘸子脸色不对,顿时急了,
扬手又要打下来。我猛地一偏头,躲开了。“妈,”我开口,声音沙哑,却异常平静,
“我没胡说,我是在帮王大伯算账。”我强撑着从地上坐起来,无视脸颊**辣的疼,
目光直直地看向王瘸子,口齿清晰,逻辑分明:“王大伯,你算算,五十块钱,不少了,
够你一个人好吃好喝过好几年。可你要是买了我,这五十块就进了我哥的口袋,
给你当牛做马的却是我。我这个人,从小就懒,肩不能扛手不能提,你娶回去,
还得你伺候我。”“再说了,”我扫了一眼我爹妈贪婪的脸,“这钱你今天给了,
明天他们看你家米缸满了,又会来要;后天看你家下蛋的母鸡肥了,又会上门来抓。
你这是娶媳妇吗?你这是花钱请了三个祖宗回去供着!这买卖,划算吗?”一番话,
像一盆冷水,把王瘸子从头浇到脚。他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精明和忌惮。他是个老光棍,
不是个傻子。他穷了一辈子,那五十块钱是他全部的家当,自然要花在刀刃上。
“你……你胡说!”我爹苏建国终于坐不住了,把烟杆在门槛上磕了磕,站起来冲我吼,
“我们怎么会去老王家要东西!你个不孝女!”“对啊!你嫁出去了就是泼出去的水,
我们才不管你!”刘桂芬也急忙撇清关系。我冷笑一声。“是吗?”我看向王瘸子,
“王大伯,你信吗?”王瘸子浑浊的眼珠转了转,看看我爹妈那副做贼心虚的样子,
又看看我这张虽然瘦弱但眼神却异常锐利的脸,心里那杆秤瞬间就倾斜了。他怕了。
怕自己倾家荡产,最后落个人财两空。“那个……建国兄弟,弟妹,”王瘸子搓着手,
往后退了一步,干笑着说,“我看晚卿这丫头……性子烈,怕是跟我合不来。这门亲事,
要不……就算了吧?”“什么?!”刘桂芬第一个尖叫起来,“王大哥,你可不能变卦啊!
咱们都说好了的!彩礼我都跟春花家说了!”“就是啊,老王!”苏建国也急了,
“一个丫头片子的话,你怎么能信!”“我信!”王瘸子突然拔高了声音,梗着脖子喊,
“我就信她!这丫头说得对,我不能花钱买个祖宗回去!这亲,不结了!”说完,
他像是怕我爹妈扑上来似的,一瘸一拐地跑了,速度比兔子还快。屋子里,瞬间死寂。
2“你个丧门星!赔钱货!”死寂过后,刘桂芬的怒火彻底爆发了。她像一头发疯的母狮,
朝我扑了过来,那架势恨不得把我生吞活剥。“我打死你这个搅家精!我打死你!”这一次,
我没有坐以待毙。就在她的手快要落到我身上时,我猛地从地上窜起来,冲到墙角,
抄起了那把劈柴用的斧子。冰冷的斧刃横在我胸前,我用尽全身力气,
嘶声力竭地吼道:“你再过来一步,我就劈了自己!我死了,看你拿什么给你儿子换媳妇!
”刘桂芬被我这副不要命的样子吓住了,硬生生停在原地,满脸的不可置信。
苏建国和苏卫东也惊呆了。在他们眼里,
我苏晚卿一直是个逆来顺受、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受气包。
他们何曾见过我如此刚烈决绝的一面?“你……你敢!”刘桂芬嘴唇哆嗦着。
“你看我敢不敢!”我举着斧子,一步步向后退,直到后背抵住冰冷的土墙,“反正都是死,
与其被你们卖了,被老光棍折磨死,还不如现在就给自己一个痛快!我死了,一了百了!
你们也别想拿到一分钱!”“晚卿!你把斧子放下!”苏建国终于反应过来,
声音里带着一丝慌乱,“有话好好说,别做傻事!”“对啊,妹妹,
”一直冷眼旁观的苏卫东也开了口,语气里满是虚伪的关切,“你这是干什么?
咱们是一家人,有什么不能商量的?”一家人?我听到这三个字,只觉得无比讽刺。“商量?
怎么商量?”我冷笑,眼泪却不争气地流了下来。这不是懦弱,
而是这具身体残留的、对亲情的最后一点悲鸣。“是商量着把我卖五十块,还是六十块?
是商量着把我打死,还是把我饿死,好给你们省口粮?”“我告诉你们!”我抹了一把脸,
眼神重新变得狠厉,“从今天起,我的命是我自己的!谁也别想再卖我!再有下一次,
这把斧子,不是对着我自己,就是对着你们!”我的话,像一把锤子,狠狠砸在他们心上。
他们怕了。不是怕我伤害他们,而是怕我这个“商品”彻底损坏,让他们血本无归。
这就是人性。当你软弱可欺时,他们是狼;当你亮出獠牙时,他们就成了羊。3僵持了许久,
刘桂芬终于败下阵来。她一**坐在地上,开始拍着大腿嚎啕大哭。“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养了这么个讨债鬼!卫东的婚事可怎么办啊!春花家说了,没五十块彩礼,这婚就不结了啊!
”苏建国蹲在一旁,愁眉苦脸地猛抽旱烟。苏卫东则急得团团转,嘴里不停念叨:“怎么办?
这可怎么办?”看着他们这副样子,我心里没有半分同情,只有冰冷的算计。我知道,
光靠威胁是没用的。我必须给他们一个新的、更大的诱饵,才能彻底掌控这个家。
我放下斧子,走到床边,从那破烂的枕头底下,摸索了半天。这是原主苏晚卿藏东西的地方。
前世,我苏晚卿有个习惯,喜欢把贴身的金饰藏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没想到,
这个习惯也被带到了这辈子。我的指尖,触到了一个冰凉坚硬的物体。我把它掏了出来。
那是一根小小的金条。是我前世戴在脖子上的一款吊坠,造型独特,分量不轻。
当那抹灿烂的金色出现在昏暗的土坯房里时,哭声、叹气声、踱步声,戛然而止。
刘桂芬、苏建国、苏卫东,三个人的眼睛,像被磁铁吸引的铁屑,
死死地钉在了我手心那根小金条上。他们的呼吸,瞬间变得粗重。“金……金子?
”刘桂芬的声音都在发抖,她连滚带爬地过来,想从我手里抢。我手一缩,让她扑了个空。
“你哪来的金子?”苏建国也红了眼,声音嘶哑地问。“你们别管我从哪来的。
”我将金条紧紧攥在手心,冷冷地看着他们,“我只问你们,这东西,值不值五十块钱?
”何止五十块!在如今这个年代,黄金是有价无市的硬通货。这一小根金条,别说五十,
就是换五百块钱,都有人抢着要。“值!值!”刘桂芬点头如捣蒜,眼睛里冒着绿光,
“晚卿啊,我的好女儿,你快把这个给妈,妈去给你哥换彩礼!”“是啊,妹妹!
”苏卫东也谄媚地凑了上来,“你真是哥的好妹妹!哥以后一定对你好!
”我看着他们瞬间转变的嘴脸,心中冷笑。“想要?”我晃了晃手里的金条,“可以。
但从今天起,这个家,我说了算。”4“什么?”我的话,让我爹妈和哥哥都愣住了。
“你说了算?你一个丫头片子,凭什么?”刘桂芬下意识地反驳。“就凭这个。”我摊开手,
金灿灿的光芒刺得他们眼睛都眯了起来,“或者,你们也可以选择像刚才那样,把我绑起来,
继续找人卖了我。看看是五十块钱来得快,还是这根金条能让你们下半辈子吃穿不愁。
”这是**裸的阳谋。我把选择权交给了他们,但答案只有一个。在绝对的利益面前,
所谓的“纲常伦理”、“一家之主”统统不堪一击。苏建国沉默了。
他死死盯着我手里的金条,喉结上下滚动,烟瘾似乎都忘了。刘桂芬也不哭了,
眼神里满是挣扎和贪婪。只有苏卫东,这个被惯坏了的草包,还在嚷嚷:“苏晚卿,
你别太过分!我才是这个家唯一的儿子!”“儿子?”我讥讽地看着他,“儿子能当饭吃?
还是能给你变出彩礼来?”我把金条在指尖抛了抛,动作轻佻,却带着致命的诱惑力。
“听我的,别说一个李春花,以后十个八个,都随你挑。不听我的,”我手一收,
将金条揣进怀里,“你们就守着这间破屋子,继续做你们传宗接代的美梦吧。”我的话,
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好!”苏建国猛地一拍大腿,像是下了什么天大的决心,
“我答应你!从今天起,家里的事,你说了算!”“当家的!”刘桂芬急了。“你闭嘴!
”苏建国狠狠瞪了她一眼,“你想一辈子都这么穷下去吗?你想卫东一辈子都打光棍吗?
”刘桂芬不说话了,默认了。苏卫东张了张嘴,想反驳,却在看到苏建国杀人般的眼神后,
乖乖闭上了嘴。我知道,这个家的权力交接,在这一刻,正式完成了。不是靠亲情,
不是靠伦理,而是靠一根冰冷坚硬的金条。这很可悲,但也很真实。这就是我苏晚卿,
在前世的商场上,学到的第一课——人性,永远趋利。5掌控了家庭的绝对话语权,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善我们一家人的伙食。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我这副瘦弱的身躯,
风一吹就倒,根本撑不起我脑子里的宏伟蓝图。我让刘桂芬去镇上的黑市,
用我剪下来的一小块金子,换了钱和票,买回了白面、大米,还有一块肥得流油的五花肉。
当那锅飘着油花的红烧肉炖在灶上,香气弥漫了整个院子时,
苏卫东的哈喇子都快流到地上了。刘桂芬和苏建国也是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围着灶台直打转。吃饭的时候,我立下了新的规矩。“从今天起,家里的活,大家分摊。
”我夹了一块最大的肉,放进自己碗里,无视了苏卫东渴望的眼神,“妈负责做饭洗衣,
爸负责劈柴挑水。至于你,”我看向苏卫东,“地里的活,你一个人全包了。”“凭什么!
”苏卫东立刻炸毛了,“我是男人,怎么能干那些活!”“就凭肉是我买的。
”我慢条斯理地咬了一口肥瘦相间的五花肉,油香瞬间在口腔里炸开,“不想干,可以。
从明天起,你继续喝你的玉米糊糊。”苏卫东的脸涨成了猪肝色。
他看看自己碗里清汤寡水的野菜,再看看我碗里堆成小山的红烧肉,最终,屈辱地低下了头。
刘桂芬想说什么,被苏建国一个眼神给瞪了回去。这个家,开始按照我的规则运转了。
他们或许心里不服,但只要利益的缰绳还攥在我手里,他们就只能乖乖听话。吃饱喝足,
我开始思考下一步的计划。坐吃山空不是我的风格。那根金条是我的启动资金,
也是我最后的底牌,绝不能轻易动用。我需要一个能持续产生现金流的项目。七零年代,
物资匮乏,百废待兴。只要脑子活泛,到处都是商机。我躺在床上,闭上眼,
脑子里飞速运转。肥皂?蜡烛?还是……突然,我睁开了眼。我想到了一个绝佳的主意。
我们村,背靠大山。山上有一种特殊的藤蔓,坚韧又柔软,村里人偶尔会砍来编筐编篓,
但都做得很粗糙,卖不上价钱。但在前世,
我见过用类似材质编织的草帽、手提包、甚至小家具,在国外的奢侈品店里,能卖出天价。
我需要人手,需要一个懂得基本编织技巧,又能被我完全掌控的“教头”。我的目光,
落在了正在院子里洗衣服的刘桂芬身上。6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
我就把睡得正香的全家人都叫了起来。“干什么啊……天塌下来了?”苏卫东蒙着头,
不耐烦地嘟囔。我直接一盆冷水泼在了他的被子上。“啊!”他尖叫着跳了起来,
像只被踩了尾巴的猫。刘桂芬和苏建国也吓醒了,惊愕地看着我。“都给我起来!
”我冷着脸,不带一丝感情,“爸,卫东,上山,按照我画的样子,砍这种藤蔓回来,
要嫩的,有韧性的。妈,你去把村里手最巧的几个婶子大娘都叫来,就说我请她们帮忙,
有好处。”我的命令不容置疑。苏卫东虽然满心怨气,但在苏建国和冰冷现实的双重压力下,
只能骂骂咧咧地扛着砍刀出了门。刘桂芬则一脸疑惑:“晚卿,你这是要干啥?请人来帮忙,
咱家哪有东西招待?”“让你去就去,哪那么多废话。”我拿出一小把昨天换来的水果糖,
“给她们每人发两颗,就说活干好了,还有肉吃。”一听到“肉”字,刘桂芬的眼睛都亮了,
什么疑虑都抛到了九霄云外,脚下生风地跑了出去。很快,院子里就聚了五六个村里的妇女。
她们都是平日里爱嚼舌根,但手里活计确实不错的。看着刘桂芬发到手里的水果糖,
一个个都笑得合不拢嘴,同时又好奇地打量着我,
不知道我这个“鬼门关”里走了一遭的丫头,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人到齐了,
藤蔓也砍回来了,堆在院子里像座小山。我没多废话,直接拿起一根藤蔓,
用随身带着的小刀熟练地处理掉外皮和毛刺,然后用温水浸泡。我的动作行云流水,
没有一丝多余。在场的所有人都看呆了。她们也会处理藤蔓,但都是用手硬撕,用牙硬咬,
哪见过这么精细讲究的法子。藤蔓处理好后,我开始起底编织。我的手,
仿佛有了自己的记忆。前世为了打入欧洲上流社会的圈子,我特意学过各种手工技艺,
其中就包括法式藤编。那双弹钢琴、签合同的手,此刻在藤蔓间翻飞,经纬交错,
一个精致的、带着漂亮花纹的篮子底部,就在众人目瞪口呆中迅速成型。
这和我自小所见的那些粗制滥造的筐子、篮子,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东西。
“天哪……晚卿这丫头,是中邪了还是被神仙点化了?这手艺……”“这编出来的东西,
也太好看了吧?”妇女们窃窃私语,眼神里充满了震惊和羡慕。就连苏建国和苏卫东,
也张大了嘴巴,忘了手里的活。我抬起头,迎上他们的目光,淡淡地说:“都看明白了?
这就是我要你们做的东西。妈,你负责教她们最基础的编法,只要编出平整的藤片就行。
谁编得最好最快,今天中午,多分一块肉。”重赏之下,必有勇妇。“肉”这个字,
比任何慷慨激昂的动员都管用。整个院子,瞬间变成了一个热火朝天的手工车间。7三天后,
我们赶制出了第一批“产品”——五个大小不一,但都编织精巧的藤编手提包。
它们不像村里人用的菜篮子,而是带着一种洋气的、我说不清道不明的“时髦感”。
最精致的那个,我还用剩下的红色布条,在提手上打了个漂亮的蝴蝶结。看着这些手提包,
刘桂芬和苏建国眼睛都直了,翻来覆去地看,满脸的难以置信。“卿……卿啊,
这玩意儿……真能卖钱?”刘桂芬小心翼翼地问。“能不能卖,去了就知道。
”我挑出那个最别致的,对苏卫东说,“走,跟我去一趟县城。”苏卫东一百个不情愿,
但在我的威逼和苏建国“让你去你就去”的呵斥下,
还是推着家里那辆破旧的二八大杠自行车,载着我往县城去了。几十里的土路,
颠得我**都快开花了。但前世再大的苦我都吃过,这点颠簸算不了什么。到了县城,
我没有去供销社,也没去自由市场。那些地方,没人会欣赏我的“艺术品”。我的目标,
是县里唯一的工厂——红星纺织厂。这个年代,能进工厂当工人,是无上的光荣。
而工厂领导的家属,自然是县城里消费能力和审美水平最高的一批人。
我和苏卫东守在纺织厂大门口。苏卫东一脸不耐烦,觉得我在这里等是白费功夫。我没理他,
只是静静地观察着进出的人。下午下班时分,
一个穿着的确良白衬衫、留着齐耳短发的中年女人走了出来。她神态倨傲,
手里拎着一个老旧的布袋子,眉头微蹙,似乎对这袋子很不满意。就是她了!
我立刻迎了上去,脸上挂着恰到好处的、腼腆又真诚的笑容。“阿姨,您好。
”那女人瞥了我一眼,没作声,显然没把我这个乡下丫头放在眼里。我也不恼,
直接将手里的藤编包递到她面前:“阿姨,您看,这是我们家自己编的手提包,独一份的,
保证您走在街上,绝不会跟人撞样。”女人的目光,落在了那个藤编包上。
当她看到那精巧的编织,别致的款式,尤其是那个灵动的红色蝴蝶结时,
眼睛里闪过一丝惊艳。“这……这是你编的?”她有些难以置信。“是啊,”我点点头,
顺势把包塞到她手里,“阿姨您看,夏天用正好,透气又轻便,比布袋子洋气多了。
您拎着去上班,同事们肯定都得羡慕您。”女人把包拿在手里,左看右看,越看越喜欢。
她这种身份的人,最在意的就是“面子”和“与众不同”。这个包,完美地戳中了她的需求。
“多少钱?”她终于开口问。我伸出五个手指头。“五毛?”她问。我摇摇头。“五块?!
”她旁边的苏卫东先叫了出来,一脸“你疯了”的表情。五块钱,
都够一个壮劳力干半个月的活了!我没理会苏卫东,只是微笑着看着那个女人。
女人也愣住了。五块钱,确实不是个小数目。但她摸着那光滑的藤条,
看着那无可挑剔的手工,犹豫了。我趁热打铁:“阿姨,这可是纯手工的,费时费力。
全县城,不,可能全省都找不出第二个。您今天买了,就是独一份的体面。五块钱,
买个独一无二,值!”“独一无二”四个字,彻底击中了她的心。她一咬牙,
从口袋里掏出钱夹,数了五张崭新的一元纸币递给我:“好,我要了!”拿着那五块钱,
我第一次在这个时代,感受到了凭自己本事赚钱的快乐。苏卫东在旁边,已经彻底傻眼了。
他看着我手里的钱,又看看那个女人喜滋滋拎着包离去的背影,
感觉自己的世界观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一个他眼里的“破篮子”,竟然真的卖了五块钱?
8回到村里,我把那五块钱拍在桌子上时,刘桂芬和苏建国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天爷啊!真……真卖了五块?”刘桂芬的声音都在颤抖。“这比抢钱还快啊!
”苏建国喃喃自语。我看着他们震惊的样子,心里清楚,从这一刻起,我在这个家的地位,
才算是真正用“实力”稳固了下来。“这只是开始。”我环视着他们,
一字一句地说出了我的计划,“我们要扩大生产。爸,你和卫东负责上山砍藤,
保证原料供应。妈,你继续当你的教头,监督那些婶子大娘干活,保证质量。记住,
我们做的不是篮子,是艺术品,一点瑕疵都不能有!”“从今天起,我们实行计件工资。
”我抛出了一个重磅炸弹,“每编好一个合格的包底,记五分工分。编好一个完整的包,
记两毛钱。干得越多,拿得越多。月底,我统一用粮食或者钱结算。”“计件工资?
”“工分?”这些新名词,他们听得一愣一愣的,
但“干得多拿得多”和“粮食、钱”这几个字,他们是听懂了。苏卫东的眼睛里,
第一次燃起了名为“干劲”的火焰。如果砍藤能换钱,那这活儿,似乎也没那么难以忍受了。
刘桂芬更是激动得满脸通红。她不仅自己能挣钱,还能管着一帮人,
这让她第一次感觉自己成了个“人物”。我的家庭作坊,就这样正式开张了。消息传出去,
整个村子都轰动了。给苏家丫头干活,不仅有糖吃,干好了还有钱拿?
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一开始还有人观望,但当第一个发薪日,我当着全村人的面,
给手脚最麻利的王家婶子发了三块钱“工资”时,所有人都疯了。三块钱!
顶得上一个壮劳力大半个月的收入了!第二天,想来我这儿干活的妇女,
差点把我家门槛都给踏破了。我趁机提高了门槛,只招手最巧、最听话的。人多了,
管理也得跟上。我把刘桂芬提拔为“车间主任”,专门负责质检和纪律。
又让我爹苏建国当“后勤部长”,负责原料和运输。苏卫东成了唯一的“苦力”,
每天负责最累的砍藤和搬运活。他虽然怨言不断,但每次拿到我给他的“零花钱”时,
嘴都能咧到耳根去。我们家的小院,成了全村最热闹的地方。妇女们一边干活,
一边说说笑笑,气氛热烈又和谐。我成了她们口中的“晚卿老板”,
一个能带着她们赚钱的能人。而我,则开始思考更长远的事情。家庭作坊的模式,终究太小。
我要的,是一个真正的“工厂”,一个能在这个时代掀起波澜的“商业帝国”。9树大招风。
我的“藤编厂”搞得热火朝天,自然也引来了村干部的注意。这天下午,村支书赵老根,
板着一张黑脸,背着手,走进了我家院子。院子里正在干活的妇女们看到他,
都吓得停下了手里的活,噤若寒蝉。“都干什么呢?啊?不好好下地挣工分,
聚在这里搞这些乱七八糟的,是想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吗?”赵老根声音洪亮,带着一股官威。
“资本主义尾巴”这顶大帽子扣下来,所有人的脸都白了。这在当年,
可是个能要人命的罪名。刘桂芬吓得腿都软了,赶紧凑上去解释:“赵……赵书记,
我们没……我们就是闲着没事,编着玩儿的……”“编着玩儿?”赵老根冷哼一声,
指着院子里堆成一堆的藤编包,“编着玩儿能编出这么多?苏晚卿!你给我出来!
”我正在屋里设计新的图样,听到声音,不慌不忙地走了出去。“赵书记,您找我?
”我脸上带着微笑,看不出丝毫的紧张。“苏晚卿!”赵老根一字一顿,眼神严厉,
“你年纪不大,胆子不小啊!竟敢私底下组织社员搞生产,还发钱!你这是想干什么?
想挖社会主义墙角吗?”我没有被他的气势吓倒,反而笑得更灿烂了。“赵书记,您误会了。
”我迎着他的目光,不卑不亢,“我不是在挖社会主义墙角,
我这是在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啊。”“哦?”赵老根显然不信,嘴角挂着一丝讥讽,
“你倒是说说,怎么个添砖加瓦法?”“赵书记,您看,”我指着院子里的妇女们,
“婶子大娘们,白天出工挣工分,一点没耽误集体的生产。晚上有点空闲时间,
我带着大家做点手工活,赚点零花钱,改善改善生活,这有错吗?
”“这能让家家户户的孩子多吃口饭,多穿件衣裳,
不也是在响应国家‘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吗?”“至于钱……”我话锋一转,
“我发的不是工资,是‘劳动补助’。而且,我早就想好了。我们赚来的钱,
不能光想着自己。”我顿了顿,抛出了我的杀手锏。“我决定,我们藤编厂每卖出一个包,
就拿出一毛钱,上交到村里的公共账户上!这笔钱,可以用来给村里买拖拉机,
可以用来修缮小学,让孩子们有个宽敞的教室读书。赵书记,您说,
我这算不算是为集体做贡献?”我的话,让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赵老根那张黑脸,
也露出了惊讶的表情。他本来是兴师问罪来的,没想到我不仅把自己的行为说得冠冕堂皇,
还主动提出要给村里“上贡”。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如果村里真能靠这个多一笔收入,那他这个村支书的政绩,可就大大地写上了一笔!
到时候去公社开会,他脸上都有光!他的脸色,瞬间由阴转晴。“咳咳,”他清了清嗓子,
语气缓和了不少,“你这个想法……倒是有点意思。不过,
这事儿不合规矩……”“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嘛。”我笑着给他递过去一个台阶,
“咱们这是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再说了,我们这叫‘社员互助生产小组’,是在您的领导下,
为壮大集体经济做出的有益尝试。功劳簿上,您是第一位!”一顶高帽子送过去,
赵老根彻底被我拿捏了。他背着手,在院子里踱了两圈,最后停下来,
一脸严肃地宣布:“嗯,晚卿同志的觉悟很高嘛!这种一心为公,一心为集体的精神,
值得表扬!大家要向她学习!”他大手一挥:“你们这个‘互助生产小组’,我批准了!
以后就由我来当你们的指导员,大家要好好干,多为集体做贡献!”一场足以致命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