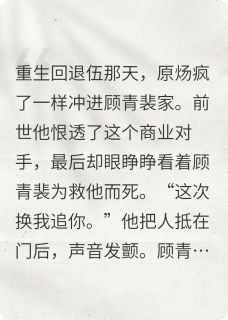晨曦微露,城市尚未完全苏醒。一层薄薄的、近乎透明的灰蓝色天光,透过巨大的落地窗,
悄无声息地漫进宽敞的客厅,驱散了夜的浓稠,将那些极简线条的家具轮廓温柔地勾勒出来。
原炀猛地睁开眼。不是惊醒,而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属于军人的警觉。
意识从深沉的睡眠中瞬间抽离,清晰得如同被冰水浇过。他几乎是弹坐起来,动作利落干脆,
没有发出丝毫声响。迷彩作训服皱巴巴地贴在身上,带着汗水和尘土混合的味道。
他下意识地抬手,用力搓了把脸,试图驱散残留的睡意,
指尖触碰到眼睑下粗糙的皮肤和细微的胡茬。目光第一时间,带着一种近乎本能的焦灼,
扫向通往二楼的旋转楼梯。安静。楼梯上空无一人,只有光线在光滑的木质扶手上静静流淌。
楼上主卧的方向,也是一片沉寂。顾青裴……还没醒?
这个念头让原炀紧绷的心弦稍微松弛了一丁点,但紧接着,
一种更强烈的冲动攫住了他——他需要做点什么。做点……顾青裴需要的事情。
前世那些冰冷的记忆碎片里,顾青裴苍白的脸色、紧抿的唇线、以及最后那滩刺目的猩红,
都像针一样扎在他的神经上。目光下意识地投向客厅尽头,
那扇半掩着的、通向厨房的磨砂玻璃门。一个模糊而急切的念头在脑海里成型——他记得,
顾青裴的胃……不太好。前世在那些你死我活的商战间隙,他偶尔会看到顾青裴皱着眉,
不动声色地按着胃部,脸色比平时更白几分。厨房。对,厨房。像被无形的线牵引着,
原炀放轻脚步,无声无息地走向厨房。推开那扇磨砂玻璃门,
一股属于崭新不锈钢和高级橱柜的、微凉的金属气味扑面而来。厨房很大,设计感十足,
各种嵌入式电器闪烁着低调的金属光泽,一尘不染,干净得像从未开过火的样板间。
原炀高大的身影闯入这片冰冷的现代空间,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他环顾四周,
目光带着一种审视战场般的锐利,最终落在那台巨大的、镜面般的双开门冰箱上。他走过去,
拉开沉重的冰箱门。冷气瞬间涌出。里面……很空。只有几瓶昂贵的进口矿泉水,
几盒包装精致的有机牛奶和酸奶,几颗孤零零的柠檬,
还有几盒贴着外文标签、看起来像是沙拉的东西。食材?几乎没有。
像一个单身精英应付生活的速食补给站。原炀的眉头拧紧了。果然……还是这样。
前世他派人调查顾青裴的生活习惯,就知道这人忙起来根本不顾身体,饮食极不规律。
冰冷的牛奶,寡淡的沙拉……难怪胃会坏掉。一股混杂着心疼和懊恼的情绪堵在胸口。
他必须做点什么。立刻。关上冰箱门,他的目光扫过旁边储物柜。打开其中一个,
里面整齐码放着未开封的米面油盐酱醋茶,包装簇新,像是买来当装饰品的。谢天谢地,
基础的调味料还有。他又打开另一个稍小的柜子。眼睛倏地一亮。角落里,
安静地躺着一个浅褐色的、带着藤编提手的砂锅。崭新的,标签都没撕。就是它了!
原炀毫不犹豫地拿出砂锅,动作带着一种找到目标的果断。他拧开水龙头,
冰冷的水流冲刷着砂锅内壁,发出哗哗的声响。他洗得很仔细,
手指用力地摩挲着陶土粗糙的质感,像是在进行某种仪式。洗好锅,他重新打开冰箱,
拿出那几盒牛奶,又挑了一颗柠檬,动作麻利地冲洗干净。接着,
他翻找出那袋未开封的珍珠米,撕开包装,舀出小半碗米粒。米粒在灯光下晶莹剔透。
他把米倒入砂锅,注入清水,手指探进去,轻轻搓洗着米粒。水流带着乳白色的淀粉淌下。
这个动作他做得有些生疏,前世养尊处优,厨房离他太远。但此刻,他全神贯注,
眼神专注得像在拆解一枚最精密的炸弹。淘好的米粒铺在锅底,加入没过米两指节的清水。
原炀小心翼翼地把砂锅放在光洁的嵌入式电磁炉灶台上,按下开关,选择了小火。
蓝色的火苗无声地舔舐着锅底。做完这一切,他并没有离开。他就那么直挺挺地站在灶台前,
微微低着头,目光一瞬不瞬地、近乎贪婪地注视着那口小小的砂锅。蓝色的火苗在锅底跳跃,
映亮了他半边棱角分明的侧脸,
也映亮了他眼底深沉的、化不开的专注和一种近乎虔诚的期待。时间在寂静中缓缓流淌。
厨房里只有砂锅受热后发出的、极其微弱的“滋滋”声,
以及水汽开始升腾的、几乎听不见的“咕嘟”声。米粒的清香,
混合着陶土被加热后特有的、朴实的土腥气,渐渐在空气中弥漫开来。原炀保持着那个姿势,
像一尊守护在神龛前的石像。他所有的感官都聚焦在那口小小的砂锅上,等待着水开,
等待着米粒翻滚,等待着……那碗能暖到顾青裴胃里的粥。
仿佛这就是此刻他生命里最重要、最神圣的使命。
---顾青裴是被一阵极其细微、却又持续不断的窸窣声惊醒的。意识从深沉的睡眠中浮起,
带着宿醉般的沉重。他习惯性地伸手摸向床头柜,
指尖触碰到冰凉的电子钟屏幕——才刚过六点。厚重的遮光窗帘缝隙里,
只透进一线极其微弱的、属于黎明的灰白。这么早?他蹙起眉,凝神细听。
那声音……不是来自卧室外,而是楼下。一种……极其轻微的、像是刻意放轻的脚步声?
还有……某种器皿被轻轻挪动的、几乎难以察觉的磕碰声?原炀!这个名字瞬间撞入脑海,
驱散了残存的睡意。顾青裴猛地睁开眼。
昨晚那场混乱的、带着巨大冲击力的记忆碎片瞬间回笼——失控的拥抱,滚烫的眼泪,
语无伦次的疯话……还有那个执拗地留在沙发上的身影。
一股难以言喻的烦躁混合着警惕瞬间攫住了他。那家伙在干什么?
大清早的……难道还没疯够?顾青裴掀开丝被,动作利落地起身。
冰凉的丝质睡衣贴在皮肤上,激起一阵细微的寒意。他没有开灯,
借着窗帘缝隙透进来的那点微光,无声地走到门边,轻轻拧开房门。走廊里一片昏暗寂静。
楼下客厅也静悄悄的,沙发的位置笼罩在阴影里,看不清是否有人。但那细微的声音,
变得更加清晰了。它来自……厨房的方向。顾青裴的心沉了下去。一种不好的预感攫住了他。
他放轻脚步,像一只优雅而警惕的猫,悄无声息地走下旋转楼梯。
鞋底踩在冰凉的木质台阶上,没有发出丝毫声响。客厅里空无一人。
清晨的微光给那些昂贵的家具蒙上了一层冷清的灰调。
空气中……似乎飘荡着一丝极其微弱的、陌生的气味?不是香薰,也不是咖啡,
是一种……淡淡的、带着暖意的谷物清香?
他的目光锁定在那扇半掩着的、通往厨房的磨砂玻璃门上。门缝里透出一点暖黄色的灯光。
那窸窣声,就是从门后传来的。顾青裴屏住呼吸,一步一步靠近。他的眉头紧锁,
眼神冰冷锐利。他倒要看看,这个原炀,大清早在他的厨房里搞什么鬼!他停在门边,
没有立刻推门。透过磨砂玻璃,只能看到一个模糊而高大的轮廓在里面晃动。
那动作……似乎是在灶台前忙碌着什么?顾青裴伸出手,指尖冰凉,轻轻推开了那扇门。
磨砂玻璃门无声地向内滑开。厨房里明亮而温暖。顶灯和嵌入式的氛围灯都开着,
将这片冰冷的现代空间照得亮如白昼。顾青裴的目光瞬间定格在灶台前那个高大的背影上。
是原炀。他背对着门口,微微弓着腰,整个人几乎伏在灶台上。
身上还是那件皱巴巴、沾着尘土的迷彩作训服,袖子被随意地挽到了手肘,
露出小臂上流畅紧实的肌肉线条。他一手拿着一个白瓷勺子,
另一只手小心翼翼地护着灶台上那个浅褐色的、带着藤编提手的砂锅。
锅里正“咕嘟咕嘟”地冒着细密的气泡,升腾起白色的水汽,
带着浓郁的米粥香气弥漫在整个厨房。原炀正专注地做着什么——他舀起小半勺粥,
动作笨拙得近乎小心翼翼,像是生怕洒出来一滴。然后,他微微侧过头,
将勺子凑近自己的唇边,嘟起嘴,鼓起腮帮子,对着那勺滚烫的粥,用力地、认真地吹气。
“呼——呼——”他吹得很卖力,额前垂落的几缕碎发随着他的动作轻轻晃动。
灯光清晰地勾勒出他专注的侧脸轮廓,高挺的鼻梁,紧抿的唇线,
还有那长长的、此刻微微垂下的眼睫,在眼睑下方投下一小片扇形的阴影。那神态,
褪去了所有的桀骜和锋芒,只剩下一种近乎笨拙的认真和一种……奇异的虔诚。吹了几下,
他似乎觉得温度差不多了。然后,原炀做了一件让顾青裴瞳孔骤然收缩的事情。
他微微张开嘴,伸出舌尖,极其快速、极其小心地,在勺子边缘那一点点的粥液上,
轻轻地舔了一下。动作快得像偷食的小动物,带着一种原始的、本能的试探。舔完,
他立刻咂了咂嘴,眉头微微蹙起,像是在仔细品味着什么。
眼神里流露出一点点的困惑和不确定。接着,他放下勺子,转身去拿旁边调料架上那罐细盐。
他用指尖捻起一小撮,极其吝啬地、几乎是数着颗粒般地,撒进了那锅翻滚的粥里。
然后又拿起勺子,重复刚才的动作——舀起,吹气,再小心翼翼地伸出舌尖舔一下。
他在……尝咸淡?顾青裴整个人僵在门口,如同被一道无声的闪电劈中。
血液似乎在这一瞬间冲上头顶,又在下一秒退得干干净净,
只剩下冰凉的指尖和一片空白的脑海。眼前这幅景象带来的冲击力,
甚至超过了昨晚那个疯狂的拥抱。
死我活、骨子里刻着“原家”骄傲的原炀……那个刚退伍回来、一身煞气的原少将……此刻,
像个做错事的孩子,像个笨手笨脚的新手厨娘,穿着沾满尘土的军装,守着一锅白粥,
用舌尖小心翼翼地尝着咸淡?荒谬!太荒谬了!
荒谬到顾青裴感觉自己长久以来构筑的、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体系,都在这一刻摇摇欲坠!
他一定是还没睡醒。这绝对是一场光怪陆离的噩梦!
可那弥漫在空气里的、带着暖意的米粥香气,那“咕嘟咕嘟”的气泡声,
还有原炀那专注得近乎神圣的侧影……一切都真实得刺眼。就在这时,
原炀似乎终于觉得咸淡合适了。他满意地、轻轻地舒了一口气,紧绷的肩膀微微放松下来。
他放下勺子,伸手去拿旁边台面上一个干净的白瓷碗,准备盛粥。就在他转身拿碗的瞬间,
眼角的余光,毫无预兆地扫到了僵立在厨房门口的那道身影。时间,在这一刻被彻底冻结。
原炀的动作瞬间僵住。他手里还捏着那个白瓷碗,保持着半转身的姿势,
像一尊突然被施了定身咒的雕像。四目相对。厨房里明亮的光线毫无保留地照在两人身上。
顾青裴穿着深灰色的丝质睡衣,身形清瘦,脸色在灯光下显得有些过分的苍白,
头发带着刚睡醒的微乱。
到了极点——惊愕、难以置信、荒谬、探究、一丝不易察觉的震动……所有情绪交织在一起,
形成一片深不见底的旋涡。而原炀,穿着脏兮兮的迷彩服,袖子挽起,手里拿着碗,
脸上还残留着刚才尝粥时那点小心翼翼的认真。此刻,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里,
所有的专注和满足如同潮水般褪去,只剩下**裸的、无处遁形的惊慌失措。
像是一个正在偷藏心爱糖果的孩子,被大人抓了个正着。空气凝固了。
只有砂锅里白粥还在不知疲倦地翻滚着,发出细微的“咕嘟”声,升腾起袅袅的热气,
氤氲在两人之间。原炀的喉结艰难地滚动了一下。他看着顾青裴那双仿佛能洞穿一切的眼睛,
看着他脸上那毫不掩饰的震惊和审视。一股巨大的恐慌瞬间攫住了他。完了。被发现了。
他那些笨拙的、小心翼翼的、试图弥补的心思……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显得如此可笑,
如此……不堪。他张了张嘴,想解释什么,喉咙却像是被滚烫的粥堵住了,发不出任何声音。
捏着碗的手指因为用力而指节泛白。顾青裴的目光,
缓缓地从原炀那张写满慌乱和窘迫的脸上,移向他身后灶台上那口冒着热气的砂锅,
再移向他手里那个干净的白瓷碗。最后,
定格在他因为紧张而微微抿起的、还沾着一点点粥渍的唇上。
厨房里弥漫着一种令人窒息的沉默。终于,顾青裴向前走了一步。
丝质睡衣的下摆随着他的动作轻轻晃动。他停在距离原炀两步远的地方,目光沉沉地看着他,
声音不高,却清晰地打破了这片死寂,带着一种穿透人心的力量:“原炀,
”他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有些异常,“你到底在做什么?
”---那平静的问句像一把冰冷的解剖刀,精准地剖开了原炀所有的伪装和强撑的镇定。
他手里捏着的白瓷碗仿佛瞬间变得有千斤重,指尖的冰凉透过碗壁一直蔓延到心底。
厨房里明亮的光线此刻显得格外刺眼,将他脸上每一丝细微的慌乱和窘迫都照得无所遁形。
灶台上,砂锅里的白粥还在不知疲倦地“咕嘟咕嘟”翻滚着,升腾的热气氤氲着浓郁的米香,
这本该温馨的画面,此刻却成了他窘迫处境最讽刺的背景。
顾青裴就站在他面前两步远的地方。丝质的深灰色睡衣衬得他肤色越发白皙,
清晨微乱的发丝垂落额角,减弱了几分平日的锐利,
却让那双眼睛里的探究和审视显得更加深不见底。他没有催促,只是静静地看着他,
那目光沉甸甸的,带着一种洞悉一切的穿透力,
让原炀感觉自己像个被剥光了丢在聚光灯下的囚徒。
“我……”原炀的喉咙像是被砂纸狠狠磨过,干涩发紧,挤出的声音嘶哑难听。
他下意识地想后退,脚跟却抵在了冰冷的橱柜边缘,退无可退。慌乱之下,
他几乎是条件反射般地抬起手,想将那个暴露了他笨拙行径的白瓷碗藏到身后,
动作仓促又可笑。“哐当!”一声清脆刺耳的碎裂声骤然响起!碗从他僵硬的手指间滑脱,
砸在光洁如镜的黑色大理石地砖上,瞬间四分五裂!白色的碎瓷片像炸开的烟花,飞溅开来,
有几片甚至弹跳到了顾青裴的拖鞋边。原炀的身体猛地一颤,
像是被那碎裂声狠狠抽了一鞭子。他僵在原地,
看着地上那摊狼藉的碎片和泼洒开的一小片粥渍,脸色瞬间褪尽血色,变得惨白。
巨大的挫败感和无地自容的狼狈感如同冰冷的潮水,瞬间将他淹没。
他像个做错了天大事情的孩子,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嘴唇翕动着,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只有胸膛在剧烈地起伏。顾青裴的目光扫过地上的碎片和粥渍,
又落回原炀那张惨白、写满惊惶和绝望的脸上。
昨晚那个疯狂的、带着巨大力量拥抱他的男人,
和眼前这个因为打碎一个碗而失魂落魄、仿佛天塌地陷的男人,反差之大,
让顾青裴的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了一下,传来一阵陌生的、尖锐的刺痛感。
这不是演戏。没有任何一个演员,
能把这种源自灵魂深处的、巨大的恐慌和无措演得如此逼真。
厨房里只剩下砂锅翻滚的“咕嘟”声,以及原炀粗重压抑的呼吸声。那呼吸声里,
似乎带上了一丝极力压抑的、破碎的哽咽。顾青裴闭了闭眼,再睁开时,
眼底深处翻涌的惊涛骇浪似乎被强行压下,只余下一片深沉的、带着探究的平静。
他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转身,走到角落的储物柜前,打开门,拿出扫帚和簸箕。然后,
他走回那片狼藉旁边,弯下腰,动作熟练而安静地开始清理地上的碎瓷片和粥渍。
他清理得很仔细,动作不疾不徐,甚至带着一种奇异的安抚人心的节奏感。
扫帚摩擦地面的沙沙声,瓷片被扫入簸箕的轻响,在寂静的厨房里格外清晰。
原炀僵立在原地,像个等待最终审判的囚徒,看着顾青裴清瘦的背影。每一次弯腰,
每一次清扫,都像一把小锤子,轻轻敲打在他紧绷到极致的神经上。那无声的清理,
比任何质问和斥责都更让他感到煎熬和……无地自容。终于,地上的狼藉被清理干净。
顾青裴直起身,将扫帚和簸箕放回角落。他转过身,重新面对原炀。
厨房里弥漫着浓郁的米粥香气,气氛却凝重得如同铅块。“粥,”顾青裴终于再次开口,
声音依旧平静,听不出喜怒,目光却锐利如刀,
直直刺向原炀那双布满血丝、此刻盛满恐慌的眼睛,“是为我做的?”他的语气不是疑问,
而是陈述。原炀的身体再次剧烈地颤抖了一下。他猛地低下头,
避开了顾青裴那仿佛能洞穿灵魂的目光。喉咙里像是堵着一团浸透了苦水的棉絮,又酸又胀。
他用力地点了点头,下巴几乎要戳到胸口,动作幅度大得带着一种自毁般的绝望。那姿态,
卑微到了尘埃里。“为什么?”顾青裴向前逼近一步,声音不高,
却带着一种不容回避的压迫感,清晰地敲打在原炀的耳膜上,“原炀,告诉我。
为什么做这些?”他的目光紧紧锁着原炀低垂的头颅,像是要穿透那层坚硬的头骨,
看清里面隐藏的所有秘密,“昨晚的疯话,那个莫名其妙的拥抱,还有现在……这锅粥?
”他顿了顿,语气加重,每一个字都像重锤落下:“别再用那些‘追我’的鬼话搪塞。
我要听真话。”最后三个字,他说得异常清晰,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命令口吻。
厨房里的空气仿佛被抽干了。米粥的香气依旧弥漫,却变得粘稠而沉重。原炀死死地低着头,
肩膀无法控制地剧烈耸动起来。他紧咬着牙关,齿根因为过度用力而传来清晰的酸痛感,
试图阻止那即将冲破喉咙的呜咽。他不敢抬头,不敢看顾青裴的眼睛,
他怕在那双眼睛里看到厌恶,看到鄙夷,看到对他“疯病”的确认。真话?告诉他什么真话?
告诉他,我带着前世的记忆回来了?告诉你,我亲眼看着你为了推开我,
被失控的大货车撞得支离破碎?告诉你,我抱着你冰冷的身体,看着你的血流干,
却无能为力?告诉你,那些我恨入骨髓的争斗,最后换来的……是你的命?
那些画面像烧红的烙铁,狠狠烫在他的神经上。巨大的痛苦和恐惧如同海啸般将他吞没。
尾的疯子……他会害怕……他会逃开……“我……”原炀的喉咙里终于挤出一点破碎的音节,
带着浓重的、无法抑制的鼻音,“我……我不能说……”声音嘶哑颤抖,
每一个字都像是从血淋淋的伤口里挤出来的,充满了巨大的痛苦和绝望的哀求。“不能说?
”顾青裴的眉头紧紧锁死,眼神锐利如冰锥,“原炀,看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