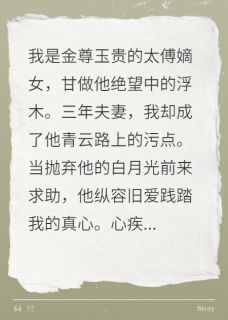我是金尊玉贵的太傅嫡女,甘做他绝望中的浮木。三年夫妻,我却成了他青云路上的污点。
当抛弃他的白月光前来求助,他纵容旧爱践踏我的真心。心疾缠身,咳血不止,
我选择以最决绝的方式“死去”。灵堂白幡飘摇,权倾朝野的男人凝视着空棺,
如疯如魔:“林晚意!天涯海角,碧落黄泉,你生是我的人,死——也只能是我的鬼!
”1、风雪送衣深冬的风雪抽打在脸上,刀割似的疼。我的怀里捂着食盒,
站在尚书府衙门的侧门前。旁边的锦书抱着大包袱,里面是沈砚冬日用的暖炉、常看的书,
还有我熬了几夜为他做的狐裘。锦书冻得发抖,朝着门房喊:“劳烦通报,
夫人来给大人送些东西。”那门房上下打量着我,嗤笑一声:“大人有令,今日有贵客,
谁来都不许进。请回吧!”锦书气得想上前跟他理论,我按住她的胳膊,看向门房:“小哥,
大人许久未归家了。天寒,我来送些冬衣。烦请通传一声。”“冬衣”二字似乎戳动了他。
他这才撇撇嘴:“等着。”在寒风里站了足有一个时辰,门终于又开了。
门房下巴扬起:“行了,进去吧。别冲撞了贵客。”他目光扫过我的脸,低声嘟囔。
“我们大人貌比潘安,
了这么个普通女子......”“还是那位侯夫人天姿国色......”心口猛地一刺,
步履蹒跚地跨过门槛。一进院子,暖意扑面而来,地龙烧得正旺。正屋门开着,
里面传出女子娇柔的笑语和沈砚低沉温和的回应。我一眼就看见了那个赤金錾花的暖手炉。
去年他忙于公务生了冻疮,我心疼坏了,专门花重金请宫中老匠打的。而现在捧着它的,
是永昌侯夫人萧玉柔。她容色倾城,眉眼间带着慵懒的倨傲,正笑盈盈看着他。“砚哥哥,
你就帮帮我嘛,那继子要是承袭了爵位,定会为难我孤儿寡母……”沈砚坐在书案后,
深紫官袍衬得他俊美矜贵,眉宇间是我从未见过的柔和。他无奈地摇摇头:“玉柔,
侯府家事,我如何插手?”“我不管!”萧玉柔撅起红唇,“你不帮我,以后再也不理你了!
”“好了好了,”他连忙道,语气里竟有一丝纵容,“怕了你了。此事…我替你周旋。
”我站在门口,像被人迎面泼了盆冰水。半年前,我那唯一的表弟想进国子监,
哪怕只是个旁听的名额,我求他看在我早逝的爹娘份上帮帮忙。他当时怎么说的?
“国子监是朝廷重地,岂能徇私?林晚意,你该懂规矩。”规矩?原来他的规矩,
只对我一个人讲。我轻咳一声,两人同时转头。
沈砚脸上的温和瞬间褪得干干净净:“你来做什么?”萧玉柔瞥了我一眼,嘴角勾着轻蔑,
连起身都懒,只微微颔首。“给你送些定胜糕。”我把食盒往前递了递。沈砚扫了眼食盒,
目光没在我身上多停片刻:“玉柔今早没吃早膳,给她吧。”我抱着食盒的手猛地一紧。
他连萧玉柔没吃早膳都知道?“是。”我掀开盒盖,端出来送到萧玉柔面前。她眼皮都没抬,
拈起一块尝了尝,眼睛亮了亮,转头对沈砚笑道:“还是你最懂我,我就爱吃这个。
”我浑身一僵。原来,他爱吃的定胜糕,从来都是她偏爱的口味。“没别的事,我先回去了。
”暖阁里的热气焐不热我浑身的冷。我再也待不住,只想赶紧逃离。沈砚“嗯”了一声,
没再看我。跨出门槛的瞬间,喉咙里一阵腥甜涌上来。我没忍住,侧身咳出一口血来,
滴在雪地里,红得刺目。2、旧情难断永昌侯夫人萧玉柔,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
漂亮到当年的永昌候不惜气死发妻也要娶她进门。而那时候,萧玉柔是沈砚的未婚妻。
沈砚虽然是当朝探花,但却出生寒门,尽管两人情深义重,但在永昌候这样的权贵面前,
根本不是对手。沈砚从清贵的翰林院修撰被罢黜为九品县令。萧玉柔成了永昌侯的续弦,
嫁进了侯府。然而永昌候虽然娶了美人,却没享受到几年。不过三年,永昌候就因病暴毙。
只留下萧玉柔和几个月大的幼儿,独自面对恨她入骨的侯府嫡长子。不过她也是幸运的,
不过短短三年,沈砚已经从九品县令坐到了吏部尚书的高位上。而他,
能如此快速升迁的原因,除了他本人的才华外,是因为我的父亲,前任太傅。
在萧玉柔大婚那日,沈砚拦住了我的马车。他知道,自从在父亲的书房里见过他之后,
我就痴恋于他。尽管我一直自卑于自己平凡的容貌,从未逾举。但他是何等聪慧之人,
一下子就看穿了我的心思。从前,他不屑一顾。如今,我成了他的救命稻草。
我知道他不爱我,但我甘之如饴。能够成为他的妻子,是我梦寐以求的幸福。那时候的我,
天真的以为,只要我爱他、敬他、不惜一切帮他,总有一天,他也会爱我三分。洞房那日,
喝得酩酊大醉的沈砚抱着我,强势地闯入我的花径。他人在我身上摩挲,
嘴里却一遍又一遍的叫着萧玉柔的名字......3、心疾难医回到宅院,刚转过游廊,
就飘来春桃和秋纹的声音。是沈砚房里最得脸的那两个婢女。“……昨儿去书房打扫,
书架最上层全是萧夫人的画像!”“谁都知道当年我们大人跟侯夫人情深义重,
要不是永昌侯,我们的主母肯定是容貌才华都冠绝京城的侯夫人!”“听说啊,
那死去的林太傅为了让自家女儿得偿所愿,暗地里也推了一把呢!”“嗡”的一声,
我怀里的食盒差点脱手。父亲?我那位教我“立身需正,待人需诚”的父亲?
他会为了让我嫁得心上人,用这样阴私的手段?锦书在旁边气得发抖,
攥着我的胳膊想冲上去理论,我却轻轻按住了她的手。“可不是嘛,
”春桃幸灾乐祸的声音又飘来,“如今永昌侯死了,明眼人都看出我们大人心情好了很多。
林夫人?不过是占着个正妻的名头罢了,大人多久没进她那院了?”“是啊,论样貌、手段,
她连萧夫人半分都及不上。也就仗着厨艺好点,对大人百依百顺,
可男人哪里会真的稀罕这个?”指尖冰凉,比外面的风雪还冷。想反驳的话堵在喉头。
想说父亲绝非那样的人,想说沈砚也曾有过片刻温和,
想说自己不是她们口中那等不堪……可话到嘴边,却只剩一片疲惫。反驳又能如何呢?
沈砚的冷漠是真的,自己在这府里活得像个影子,也是真的。我回到了冷清的院子。
锦喉咙里熟悉的腥甜又涌上来,我咳得撕心裂肺。帕子展开,那抹红刺得我眼睛生疼。
“夫人!”锦书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去…请王太医。”我喘着气,声音嘶哑,“悄悄的。
”王太医来得很快,他是看着我长大的,曾是父亲的座上宾。他搭着我的脉,眉头越锁越紧。
我的心也跟着沉下去。“大**,”他收回手,叹道,“您这心疾…郁结过深,劳损太过,
已是沉疴…药石…恐难回天。”他后面的话我没听清,只觉得心口疼得麻木。
掌心的烫伤**辣的,是做糕点时烫到的。真蠢。4、温柔假象深夜,门轴“吱呀”一声。
沈砚回来了,带着一身寒气和淡淡的酒气。他竟然来了我的院子,而不是书房。
“怎么还没睡?”他声音有点哑,目光落在我裹着帕子的手上,“手怎么了?”“没事。
”我想缩回手,却被他一把抓住手腕。他皱着眉,粗鲁地扯开帕子,露出红肿起泡的掌心。
“蠢。”他低斥一声,语气是惯常的不耐烦,却转身去拿了药箱。我僵在原地,
看着他难得低垂的眉眼,小心翼翼地用药膏涂上来。动作很生涩,
带着他自己都没察觉的轻柔。这点微末的“温柔”,猛地扎破了我强撑的平静。
眼泪毫无预兆地砸下来,落在他手背上。他手一顿,抬起头,眼里有瞬间的错愕。“哭什么?
”他声音放软了些,“很疼?”我拼命摇头,哽咽得说不出话。不是因为疼。
是因为他这点施舍般的关怀,让我堆积多年的委屈,瞬间崩塌溃堤。他叹了口气,
有些笨拙地把我揽进怀里。“好了,别哭了。方才是我心烦,说话重了。”他生硬地安抚,
继续替我涂药。这片刻的温存像偷来的。**着他,听着他沉稳的心跳,明知是虚幻,
还是忍不住沉溺。“为什么…心烦?”我哑着嗓子,明知故问。“朝堂上的事,
说了你也不懂。”那点柔和立刻被不耐取代。我闭上嘴,不敢再问。药涂完了。他放下药膏,
我下意识抽回手,心里空落落的。他却没走,反而把我按进床榻里,从后面环住我。
后背贴着他温热的胸膛,很温暖。“别动。”他声音低沉下去,带着警告,“只是抱一下。
”我僵硬地靠着他,一动不敢动。他的呼吸喷在我颈侧,有些烫。
“夫君…今日那位侯府夫人…”沈砚手上动作一顿,语气瞬间变得冷硬:“故人而已。
朝堂之事,莫要多问。”我鼓起最后勇气:“夫君…你可曾…爱我?
”回应我的是长久的沉默,和沈砚抽离的手。我压下心里的酸涩,
声音沙哑:“若有一日…我走了,你会难过吗?”沈砚嗤笑:“走?离开尚书府,
离开我沈砚的庇护,你这金尊玉贵的太傅**,能去哪里?”他起身,
头也不回地走向了书房,只留下一句“若真想走,记得告诉我一声。”也好。这样,
就真的…不必再有任何留恋了。5、决意离去我心里那点残存的希望,完全消失了。
心口那片空茫的疼,反而奇异地平复了。也好。这样也好。至少,我能选择结束的方式。
不再是沈砚眼中屈辱的“污点”,不再是尚书府里被拒之门外的“夫人”。
我要干干净净地离开,以林晚意的身份,而不是沈砚的附属品。“锦书。”锦书红着眼,
担忧地靠近:“夫人?”“整理我的私房,留下一部分,只带最贵重的,还有银票和地契。
”感谢沈砚对我的不在乎,他根本不知道我到底有多少私产。而现在这些私产,
足以让我最后的日子过得富足。也可以让我的锦书后半生有所依靠。锦书猛地抬头,
眼中先是惊愕,随即爆发出惊喜的笑容。她用力点头:“奴婢明白!”我知道她懂。
她从小跟着我,比任何人都清楚我在这府里咽下了多少委屈。接下来的日子,沈砚依旧不归,
或回来也视我如无物。这给了我绝佳的机会。锦书是我的手,我的眼。她借着采买,
悄悄联络上京郊庄子的老管事。那庄子,是父亲临终前偷偷塞给我的,连沈砚都不知道。
老管事是林家的老人,信得过。“告诉忠叔,”我低声吩咐锦书,“收拾出最僻静的院子,
请王太医推荐一个口风紧的医女过去候着。要快,要隐秘。”锦书领命而去。
最难的是王太医。我再次请他过府“诊脉”,屏退了所有人。“王伯,”我用了旧称,
声音很轻却决绝,“晚意想请您…帮我最后一场。”他看着我,浑浊的老眼里满是痛惜,
最终化为一声沉重的叹息。“大**…您想如何?”“我需要一个契机,”我盯着他,
“一场‘突发心疾,药石罔效’的急症。在所有人面前。”“庄子和后续,我已安排。
只差一个‘病逝’的由头。”王太医手指颤抖:“老夫…明白了。药,我来配。
只是…大**,这药服下,症状极凶险,如心疾暴发,痛苦非常,您需得撑住。”“我知道。
”我平静地点头。再痛,能痛过这三年吗?“您只需确保,脉象无破绽。
”他郑重地收起印信:“老夫以林家旧谊起誓,必护您最后一程。”最大的难题解决了。
我开始清理痕迹。那些偷偷写给沈砚的信笺,
那些收集的关于他喜好的零碎笔记…在炭盆里化为灰烬。火光跳跃,映着我毫无波澜的脸。
烧掉的,是我愚蠢的过去。锦书动作麻利。值钱又不显眼的首饰、母亲的遗物,
房产银票…被打成一个小小的包袱。沈砚送的东西,一件不带。它们和他一样,
都是冰冷的枷锁。我甚至开始“安排后事”。在沈砚难得在府用晚膳时,
我状似无意地提起:“我给你新做了一件雀金裘,放在箱笼里那。库房里那对羊脂玉瓶,
是给三月后忠勇侯家老太君的七十寿礼。”他拿着筷子的手顿了顿,抬眼看了我一下,
眉头微蹙,似乎觉得我有些反常。但很快,那点微澜就被漠然取代。他只“嗯”了一声,
算是知道了,再无下文。也好。他越不在意,我的计划越安全。日子在表面的平静下,
暗流汹涌地滑过。锦书带回消息,庄子已备好,医女就位。王太医也秘密递了话,药已配妥。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静静等待着,等待着那个合理的死亡时刻。心口那片空茫之地,
竟生出一丝奇异的期待。6、宴席惊变丞相府宴席的喧嚣像隔着一层厚厚的琉璃。
丝竹管弦,衣香鬓影,觥筹交错。我坐在沈砚下首,像个精致的摆设。心口的闷痛如影随形,
王太医给的药丸,就藏在我袖袋深处。然后,她来了。萧玉柔一身素锦,却难掩容光,
在永昌侯继子不善的注视下,袅袅婷婷地走向沈砚的席位。她手中捧着一只白玉酒壶,
声音哀婉:“沈大人,先夫在时,常念及与您昔日同窗之谊。如今他新丧,侯府风雨飘摇,
妾身…斗胆敬您一杯,望您念及旧情…”她眼波流转,意有所指地扫过我,“…帮衬一二。
”席间瞬间安静下来。无数道目光,或好奇或鄙夷,钉子般扎在我身上。
沈砚的背脊绷得笔直。他沉默着,没看萧玉柔,也没看我。萧玉柔的指尖微微发颤,
似乎承受不住那白玉酒壶的重量,身子一软,竟直直朝着沈砚的方向倒去!“小心!
”几乎是同时,沈砚猛地起身,长臂一伸,稳稳扶住了她的腰肢,将她半揽在怀里。
动作快得…几乎是本能。“多谢沈大人…”萧玉柔依在他臂弯里,抬起头,眼中水光潋滟,
楚楚可怜。沈砚扶着她站稳,手却没有立刻收回。他低头看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