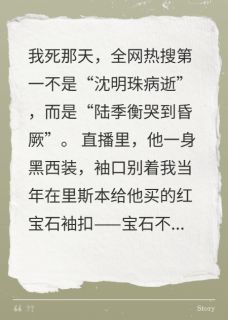我死那天,全网热搜第一不是“沈明珠病逝”,而是“陆季衡哭到昏厥”。直播里,
他一身黑西装,袖口别着我当年在里斯本给他买的红宝石袖扣——宝石不大,
镜头几次切特写都没对焦成功。直播间的弹幕刷了屏:“陆总好深情,
豪门里这么深情还这么帅的真是不多。
”“果然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啊”“袖扣是不是血钻?”“好像是红宝石,
他夫人送他的订婚礼物。”“哇,
好悲情好浪漫““只有我注意到墓碑上没写‘爱妻’吗?”“也没写陆总名字,
他们豪门不是最在乎这些吗?”这些弹幕在我棺材上空飘来飘去,像漫天的纸钱飞舞。
仅有的一两声质疑,也在陆季衡宣布终身不会再娶后,闭了麦。“永不再娶?
那余若薇算什么?”“算外室。
”这两条评论被若干条盛赞陆季衡多金又深情的弹幕迅速压过,媒体发文:现代童话闭幕,
钻石王老五封心锁爱。葬礼过后,陆氏股价又上新高。想起弥留之际,
二哥问我还有什么心愿未了。我疲惫地摇了摇头。他也是年纪上来了,若是以前,
肯定要嘲弄着问我后不后悔,而不是像现在,拄着拐杖,红着眼眶哆嗦着嘴唇看着我。
其实他以前问过我:“沈明珠,你敢保证你以后不会后悔?
”25岁的沈明珠斩钉截铁:“我一定要嫁给他,绝不后悔。”但后面他不再问了。一开始,
是我确实过得幸福,而后面,他不用问我,亦知道,我确实后悔了。如果有来世,
我不愿嫁给陆季衡。2但我没料到我居然没有来世。我死后没去天堂,也没去地狱。
我被拘在了老宅。“夫人确实命里旺夫。”初听到这句话时,我们刚结婚,
他请人来摆办公室风水。我笑着点点他的手臂:“听到没?还不对我好点儿?
”他搂过我的肩:“我待你还不够好?再好便只能供起来喽!”现下确实是供起来了,
他要我死后也旺他。他不经常来老宅,刘妈为了宅子里有生气,常年开着电视。新闻里,
:船王目送明珠号港口启航2.3亿拍下初遇旧址:陆董抽柚木地板回家重温故梦陆氏登顶!
股市创纪录,无冕之王诞生!每当听到这样的新闻,刘妈便来擦我照片,
我看着她下撇的嘴角,都想劝她:别擦了,擦到反光,镜框都要掉漆了。我最后的五年,
是刘妈陪我过的。她见过我切除大半个胃以后的辗转难眠,
见过我吃什么吐什么最后瘦成一把枯骨只能坐在轮椅上度过余生。见过陆季衡坐在我病床前,
平静地告诉我:“明珠,我不能当一辈子和尚,家大业大,总要人打理。
”她甚至替我接过不知哪个女星的电话:“你老公根本不爱你!
你占着陆太太的位置有什么用?你个黄脸婆怎么还不去死?”刘妈挂了电话,
搂住刚吃过药的我,带着鼻音话道:“太太,先生不能这样对你。
”我抚了抚她的背:“说给我听就行了,别让旁人听到了。”“下次忍不住想说什么,
就去擦擦桌子。”她家里不孝子孙几个,着实不能失去这份工作。不过那个女星说错了,
不是我要占着陆太太的位置,是陆季衡不愿放我自由,他陆季衡,只能丧偶,不能离婚。
我是他功勋碑的第一块砖,是他从穷小子到5000亿商业帝国最硬的踏脚石。
“凤凰男”的名号已被他洗刷殆尽,他不会再给自己贴上一个忘恩负义的标签。更何况,
他真的信我旺他。毕竟,我说我不愿再和他有牵扯,墓碑上不愿刻“陆季衡之妻”他不同意,
但风水先生说生人名刻死人碑上不吉,他立马同意墓碑上只刻“沈明珠之墓”几个字。
陆氏公关对外却是这样说的:陆先生尊重太太的意愿,在成为陆太太和一个母亲之外,
更是她自己,是沈明珠。所以宁愿被世人误解,也愿成全夫人。在大环境为妻冠夫姓的港城,
他做到如此地步,若我不知真相,亦会为这一份敬重感叹。我死后,
他成了全城最痴情的男人。3再次睁眼,我眼前一片耀眼的白光,
是闪光灯在此起彼伏地亮起。我尚未回过神,便听到陆季衡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明珠,
你愿意嫁给我吗?”我低头,看见27岁的陆季衡半跪在面前,举起钻戒盒递于我手边。
怎么?鬼也会做梦吗?我有点恍神,扫了眼四周,
这梦未免也太真实:这是陆季衡那年为了娶我,新置的宅子,水晶灯从三楼的屋顶垂下,
周围觥筹交错,第一次暖宅酒会,他请了全城媒体见证,向我求婚。
周围的一圈记者都很兴奋,毕竟世人都爱看穷小子逆袭娶千金,而这千金为了等他,
耗到了28岁,拒绝了所有追求者,都不肯旁嫁。在众人的期待里,我笑了笑,俯下身,
扯下那两颗红宝石袖扣,站直身子,居高临下地盯着陆季衡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道:“我。
不。愿。意。”全场安静了片刻,瞬间一片哗然。后退几步,躲开陆季衡要去拉我的手,
拿起旁边香槟塔的一杯酒,我转向记者,遥遥举杯,一饮而尽后,笑得眉眼弯弯,
再说了一遍:“我说,我不愿意。”我奔出陆宅,将满室的喧闹丢在身后。求婚是头条,
拒婚也是头条,你说对吧?4“你这是在胡闹!”父亲将茶杯重重地顿在桌子上,
“不让你嫁的时候偏要嫁!拿自己的珠宝细软倒贴着给人做本金,好不容易扶起来了,
有点出息了,你跟我说你不嫁了???”我寻摸到父亲身后,
给他边按肩边说道:“我要嫁的时候,你拦着,偏不让我嫁。现在我听你的话不嫁了,
你干嘛非得逼着我嫁?”父亲气得吹胡子瞪眼,手往后一挥,欸嘿,没打着。
母亲亦在旁边苦口婆心地劝:“明珠,你今年是28,不是18。
你认为你还有那么多选择吗?”我忍不住笑出声,真好啊,我是28,不是38,
更不是48。真好啊,一夜过后,自己居然还在,本以为只是在梦里放肆一回,没想到,
是像刘妈手机里放的那些短剧一样,重生了。母亲嗔怪地瞪我一眼:“你是失心疯了不成?
““等季衡上门来,给个台阶便下了,报纸上写成那样,你让他着实没脸面。
”我绕到他俩面前跪下,郑重说到:“爸,妈,女儿没有失心疯,也不是在开玩笑,
我真不愿意嫁给陆季衡了,我俩之前没有婚约,现下他生意蒸蒸日上,
也说不了我沈家嫌贫爱富。若有些许流言,也只是对我,我承受得了。”母亲握住我的手,
担忧地问:“是他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吗?”我摇了摇头,总不能说,
他现在没做对不起我的事,但以后会做。“爸,妈,以前是我想岔了,
我不愿再将我的一生赌在婚姻上,他生意再好,也是他陆家的生意,我待他再好,等他发达,
靠女人发家便是他洗刷不掉的耻辱。”“我不愿再靠他人,我想自己试试。
“5父母终究是没有拗过我。推开客厅的门,二哥塞给我一份报纸后,朝我竖起了大拇指。
“我不愿意!新晋纺织新贵惨遭拒婚!高龄千金另觅新欢?“报纸上,
陆季衡向我求婚的照片被做了撕裂的特效铺满整个版头。我笑着将报纸甩到一边,
拉过二哥:“别说这些有的没的,你账上有多少钱?“我没有在家里等陆季衡上门。
而是跑到商标注册署,赶在陆季衡之前,
érolaPreciosaLine“”明珠船务“”白茶花航运“全部注册。
办事员抬头:“**,这些名字很抢手。”我笑:“所以我先来。”“明珠,
“陆季衡在回家的路上堵我,”我等了你一天。“他站在我面前,衣冠楚楚,清俊如裁,
端的是好样貌。思绪又飘回以前:“沈**,我等了你一天,想把这朵玫瑰送给你。“当初,
他连续三个月在我上下学的路上等我,也不失礼,送上些小玩意儿就走。
我便是被他的好样貌,和金石为开的赤诚打动。父亲曾问我:“你看上他什么?
“我说:“我看上他对我好。”父亲说,对你好,是最靠不住的东西。可惜,我死了一遍,
才明白。陆季衡眼眶发红,眼睛里没有愤怒,只有不解与委屈:“是我做错了什么吗?
“高位者示弱,若是不谙世事的女仔看到,定会心疼心软。而我不会,我的心古井无波,
平静的水面下却填满了欲喷涌而出的愤怒。“你一定要站在这里说吗?“我看了下四周,
”又想上头条?“私人会所里,我递给他一张名片:“沈明珠,
PérolaPreciosaLine董事。谈生意可以,谈感情免了。
”他攥紧名片,指节发白。6我向陆季衡要回了当初给他的投资。他现在事业起步,
抽得出现金,城府还未深,尚要脸面,七天之内,连本带息的划到我账上。
我从大哥、二哥手里各拿了笔钱,但还是手头紧,某天夜里,却发现床头柜上放了张存单,
母亲不知道我是不是一时兴起,更不敢相信从未经商的女儿能挣到钱,明知可能是打水漂,
却把多年的体己送我做登山梯。亦如当年,她撞见陆季衡带余若薇参加酒会,
全然不顾身份给了她一耳光:“陆季衡,我沈家再不济,
也轮不到你带着外面的女人踩我女儿的脸!”陆季衡护住余若薇回道:“伯母,生意场上,
讲的是实力,不是辈分。”那时沈氏已经势微,大哥病逝,二哥只知画画,父亲身体不好,
家里生意要仰陆氏鼻息,我卧病床上,全然不知。三天后,沈氏的单子被全面叫停。
码头仓库的货柜一夜之间贴上封条,银行电话打不通,合作方纷纷退单。
沈家像被抽掉地基的老楼,嘎吱一声就要倾塌。
母亲找到陆季衡:“你要以什么身份来逼长辈弯腰?沈氏大不了破产,但我敢担保,
以后你陆季衡忘恩负义的名声传遍中外名流,陆氏在港城再也做不了航运生意!
”陆季衡冲到我病床旁,全然不顾母亲要瞒着我的心情,跟我说道:“明珠,
你现在这个样子,我不能做一辈子和尚,家大业大,是需要应酬的,一张富豪榜上看下来,
谁不是这样呢?你劝劝岳母,让她别闹了,这样对我们和沈氏都好。”他说完转身便走,
全然不顾我在身后气到吐血。醒转后,我才知他养在外面的那人是余若薇。
结婚五周年的舞会上,不到20岁的少女向并肩而立的我俩提起裙摆行礼,
我欣赏她青春懵懂,天真可爱,却没想到身边人的见异思迁,原来早有预兆。
7陆季衡喝醉了在我楼下发酒疯,声音被雨幕撕得七零八落:“明珠,这是为什么啊?明珠!
”“我哪里做错了我改还不行吗?”我打电话给警司把人拖走,我很忙,
忙到尚没时间去应对前世的对错。我用200万现金加承担500万债务的方式,
从广府海事法院手里拍下一条1.2万吨旧杂货船——法院只求“有人接盘,
别炸在我手里”。我把船身刷成深绿,船首刻白茶花,给它取名“明珠号“。平安夜,
汽笛长鸣,我穿男装站甲板剪彩,明珠号的旗帜被海风吹得猎猎作响,这次,
换我目送它启航。第二天报纸头条:港府第一美人不做阔太,要做船王?消息一出,
整座港府像被泼了冰可乐,嗤嗤作响:“她脑子进水了吧?放着总督府的舞会不跳,
跑去跟一群晒得乌漆嘛黑的船员混?““听说还要自己上船验舱,我的天,
那味道……香奈儿五号都遮不住。““女仔买船,同买手袋一样——三分钟热度。风浪一起,
她就晓得海不是镜,是刀。““我押十蚊,半年内她把嫁妆赔光,收山做少奶奶!
“……深夜,我端着酒杯站在阳台上,海风把裙摆吹得像一面反叛的旗。
二哥端着酒杯和我轻碰一下,问:”全城都在等你失败,你怕吗?
”我抬眼望向远方黑得发蓝的海面,声音轻得像刀锋划开丝绸:“等他们笑完,
这片海就改姓沈了。“8不到两年,老爷子去打高尔夫,
被老友调笑:“令千金真是不得了哦,同一艘船,周一挂港府旗跑白埔—长滨线,
周三改挂巴拿马旗跑江雄—洛杉矶线。
海关关员看着AIS轨迹直挠头:‘这船怎么国籍一天一变?
’“老爷子笑得骄傲:“这叫合法的多重身份。”几乎同一时间,深水埗的福海航运旧楼里,
谈判桌却像台风眼。福海航运的老董事长洪坤把老花镜摘了又戴,
最后重重往桌上一拍:“沈**,5000万,三条船加一个壳,我亏到贴地!
再加500万,当我给老伙计们的遣散费。”我把钢笔帽轻轻旋开,声音不高,
却刚好盖过空调嗡鸣:“洪伯,账不是这么算。
”我推过去一份折得方正的旧报纸:【福海航运停牌前收盘价0.16元,
市值仅4800万,负债1.2亿,银行已发清盘备忘。】“您再拖一个月,
连壳都会被银行拆成废铁。”我指尖在“负债1.2亿”上敲两下,像敲一记锣。
“5000万,我替您把债清干净,员工照领薪水,三条船继续跑——只是改姓沈。
”洪坤攥着报纸,手背青筋暴起。您老人家爱面子,我给您里子——交易完成当天,
福海的名字保留在船首。”洪坤抬头,看见对面姑娘眼底澄亮,像无风无浪的海,
却映得出暗涌。他忽然明白:这不是砍价,是救命的缆绳。“啪”——老人把印章重重落下,
哑声一句:“成交。以后福海……拜托沈船王。”我起身,礼貌颔首,像对长辈,
也像对手下败将。转身时,秘书递来电话:“沈**,港交所上市科刚批了反向收购通函,
股票明天复牌,新简称:明珠航运。”我“嗯”了一声,抬眼望向窗外,
维多利亚港的灯火正一盏盏亮起,像有人替我提前庆功。9总督府的圣诞舞会,
我作为商界新星出席。前世收到的,大多是邀舞的手,如今,杯口低我一寸,
名片顺着杯壁悄悄滑到我指尖。我笑着应酬完毕,一抬头,便看见舞池边站立的余若薇。
她穿了袭天青色的礼裙,贴身的布料,笼住少女刚发育好的身体,更衬出不盈一握的腰肢。
原来这么早,她便被她那个机会主义者舅父绑上缎带,推到名利场上,待价而沽。
前世母亲和陆季衡闹过一场后,他说他家大业大,需要交际,正大光明的把余若薇迎进了门。
陆季衡觉得让余若薇避开我,把她安排在了莲岛,便是给了我天大的体面。
我如把头埋在沙中的鸵鸟,不去看,不去听。我唯一的儿子澄观即将大学毕业,
奔赴大好前程,我不能表现出怨怼,让他和父亲生怨成仇。圣诞那日,
我一直在等澄观的电话,他和女友毕业旅行,说要去里斯本看看。老宅的日子仿佛被拉长,
电话铃始终没有响起。我在客厅等到睡着,恍惚间听得下人在门外议论:“二太太真是心狠。
”我悚然惊醒,到老宅后第一次主动给陆季衡打电话:“澄观给你打电话没有?
”他那边似是有记者在场,说忙,含糊过两句便挂了电话。第二日,老宅里没看到报纸。
我心生警觉,发现下人都在有意无意避开我的视线。刘妈哄我:“太太,我推你去花园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