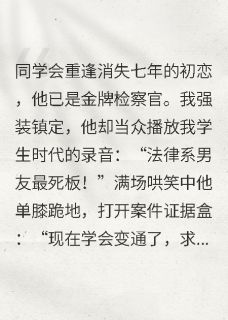同学会重逢消失七年的初恋,他已是金牌检察官。我强装镇定,
他却当众播放我学生时代的录音:“法律系男友最死板!”满场哄笑中他单膝跪地,
打开案件证据盒:“现在学会变通了,求教吗?”银手镯折射冷光那刻,
我瞥见他无名指上未消的戒痕。突然想起今早收到的婚礼请柬——新娘是我闺蜜。七天后,
他主诉的惊天贪腐案庭审现场。我作为被告辩护律师起身:“反对!
公诉人刻意隐匿关键物证。”举起他当年送我的瑞士军刀:“这把真凶遗留的凶器,
沈检察官七年前就见过。”旁听席上,闺蜜手中的婚礼请柬飘然落地。---碎裂的声响,
清脆得如同骨头折断,瞬间刺穿了宴会厅里觥筹交错的虚伪乐章。指间一空,
盛着琥珀色液体的威士忌杯,在众目睽睽之下亲吻冰冷的大理石地面,粉身碎骨。
碎片如同炸开的冰凌,四散飞溅,混合着浓烈辛辣的酒液,在我脚边蜿蜒流淌,
反射着天花板上巨型水晶吊灯无数个切割面的冷光,形成一片狼狈而刺目的狼藉。
冰凉的液体溅上**的脚踝,那微不足道的凉意,却像一条阴冷的毒蛇,
顺着皮肤一路蜿蜒啮咬,瞬间冻结了我的血液和心跳。
两千五百多个日夜堆砌起来的、摇摇欲坠的遗忘堡垒,就在这一声猝不及防的脆响里,
轰然崩塌,扬起呛人的、名为“过去”的尘埃。这里是母校法学院的百年庆典宴会厅。
金碧辉煌,衣香鬓影。空气里弥漫着昂贵雪茄、陈年佳酿和一种名为“权势”的无形亢奋。
法官、律师、检察官、昔日同窗,高谈阔论,追忆往昔峥嵘,展望未来宏图。
笑声、碰杯声、刻意压低的恭维声,汇成一股喧嚣的声浪。然而,就在杯子碎裂的刹那,
这声浪仿佛被一道无形的屏障瞬间隔绝,只剩下嗡嗡的、令人烦躁的杂音在耳际盘旋。
周遭的空气骤然变得粘稠,如同凝固的、令人窒息的蜜糖,
每一次呼吸都牵扯着沉重的滞涩感。目光所及之处,人群如同摩西分海般,
自动裂开一道缝隙。那些或熟悉或陌生的面孔上,带着惊愕、好奇、探究,
甚至一丝不易察觉的幸灾乐祸。而我,林晚,就站在这缝隙的尽头,
像一个被命运突兀地推到聚光灯下的小丑,脚边是那摊象征着失态与狼狈的罪证。
指尖下意识地蜷缩,指甲深深陷进掌心柔软的皮肉,带来一阵尖锐而熟悉的痛楚。
这痛感像一根细针,勉强刺破混沌。躲开?逃?念头刚起就被掐灭。太迟了。
就在这令人窒息的死寂边缘,在那道裂开的人墙尽头,他出现了。沈叙。
不再是记忆中那个穿着洗得发白、袖口磨出毛边的旧夹克,头发被风吹得有些凌乱,
抱着厚厚的《刑法学》穿梭在图书馆和模拟法庭之间的青涩少年。时间,或者更准确地说,
是权力与地位,将他淬炼得锋利而冰冷。剪裁精良、质感厚重的藏蓝色检察官制服,
妥帖地包裹着他挺拔如松的身形,肩章上的银色徽记在灯光下折射出冷硬的光芒。
灯光落在他轮廓分明的侧脸上,挺直的鼻梁,紧抿的薄唇,下颌线清晰得如同刀刻斧凿,
镀上一层不容侵犯的威严。他微微侧着头,
正专注地听着身旁一位头发花白、德高望重的老法官说着什么,
唇边挂着一丝恰到好处的、礼貌而疏离的浅笑,既显得谦逊,
又透着一股无形的、拒人千里的距离感。镁光灯如同嗅到血腥味的鲨鱼,迅速追随着他。
记者们的话筒争先恐后地递到近前,快门声此起彼伏。他从容地应对着,姿态沉稳,
举手投足间带着一种久居上位、洞悉一切的掌控感。世界喧嚣地围着他转,
他是毋庸置疑的焦点,是今夜这场司法盛宴的中心。
七年前那个沉默寡言、眼中只有法条与正义准绳的法律系天才,
已然蜕变成手握权柄、令人生畏的“铁面检察官”。而我,
像一个被遗忘在时光角落的、不合时宜的残局,狼狈地站在自己制造的狼藉旁。
巨大的落差感如同冰冷的潮水,瞬间将我淹没。就在我几乎要被这无形的压力碾碎时,
沈叙的目光,毫无预兆地穿透了攒动的人头和炫目的闪光灯,
精准地、像法庭上锁定关键证人的鹰隼般,捕捉到了我。那双眼睛,
依旧深邃得像不见底的寒潭,只是沉淀了太多我无法解读、也不敢解读的暗涌。没有惊讶,
没有久别重逢的波澜,甚至没有一丝一毫的温度。那眼神平静得像结了冰的湖面,深不见底,
只是淡淡地、不带任何情绪地在我脸上停留了不到一秒,便漠然地移开了。
仿佛我只是背景里一件无关紧要的摆设,一件刚刚制造了点噪音、需要被清理的障碍物。
他甚至没有停顿,依旧对那位老法官微微颔首,唇角的弧度纹丝未动。随即,
他在众人簇拥下,步履沉稳从容,径直朝我……不,是朝我这个方向的主席台走去。
擦肩而过的瞬间,衣袂带起的微弱气流拂过我**的手臂,
比清晰的、属于他的清冽气息——那是他学生时代惯用的、带着淡淡松木和书卷气的须后水,
如今混合了某种更冷冽、更陌生的金属和纸张的味道。这熟悉又陌生的气息,
像一把淬了毒的钥匙,猛地捅开了记忆的锁孔。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而冰冷的手狠狠攥住,
骤然缩紧,尖锐的痛楚瞬间蔓延。脚下意识地后退半步,试图拉开距离,
高跟鞋细细的后跟却不偏不倚踩在一块滑腻的玻璃碎片上,身体瞬间失衡,向后栽倒!完了。
绝望地闭上眼睛。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只温热干燥的手掌,
稳稳地、有力地托住了我的手肘。力道不大,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支撑感。惊惶地睁开眼。
不是他。是大学时一个关系尚可、如今在律所混得不错的男同学,周正。
他脸上带着真诚的关切:“林晚?没事吧?”他扶稳我,看了看那片狼藉,“小心玻璃。
脸色这么差?”“谢…谢谢。”我借着他的力道勉强站稳,声音干涩。
目光却不受控制地穿过人群缝隙,投向那个已然走上主席台、被光芒笼罩的背影。
沈叙的背影挺拔如松,检察官制服的肩线笔直冷硬。他从容地接过话筒。“各位尊敬的师长,
亲爱的校友同仁,晚上好。”他的声音透过顶级音响传遍大厅,低沉,醇厚,
带着一种经过岁月沉淀的、沉稳的穿透力,瞬间压下了全场的嘈杂,也扼住了我脆弱的神经。
“非常荣幸,能在母校百年华诞之际,回到这片培育了无数法律人信仰与理想的沃土。
”台下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尤其是我们法学院那几桌。他微微颔首致意,
脸上是无可挑剔的、掌控全局的表情。我强迫自己移开视线,低下头。
掌心被指甲掐出的印痕,深得几乎渗血。“……今晚,看到许多熟悉的面孔,
也看到许多在各自领域捍卫法律尊严的新星,心中感慨良多。”沈叙的声音平稳地继续,
“尤其看到我们法学院的同窗们。当年在模拟法庭争得面红耳赤,在图书馆熬通宵背法条,
被导师的‘苏格拉底式诘问’逼到墙角的日子,想必大家都记忆犹新吧?
”台下响起一片会心的笑声。“那时候啊,”他话锋似乎一转,带着点追忆的口吻,
唇角的弧度加深些许。他的目光状似无意地扫过台下。最终,如同精准的探照灯,穿透人群,
牢牢地定格在我身上。那眼神深处,带着一种近乎残忍的了然和一丝冰冷的戏谑。
“还常常能听到一些来自‘内部’的、非常‘犀利’的评价。”我的心跳,骤然漏跳一拍,
随即疯狂擂动!一股冰冷刺骨的寒意,从脚底板猛地窜起,瞬间席卷四肢百骸!
血液冲上头顶,又在下一秒褪得干干净净,只剩下冰冷的麻木和一片空白的恐惧。
他要做什么?!只见沈叙慢条斯理地从制服内袋里,掏出一个银色的、极其小巧精致的U盘。
动作从容不迫,优雅得像在展示一件关键物证。“说来也巧,”他对着话筒,
声音染上一点奇异的、磁性的笑意,目光却如同冰冷的锁链,牢牢锁着我,
像猎人欣赏着猎物徒劳的挣扎,“整理旧案卷宗时,
无意中发现了一点学生时代的‘珍贵记录’。”他刻意加重了“珍贵”二字。他顿了一顿,
视线扫过全场。整个宴会厅落针可闻。“一段录音。”他轻轻吐出这四个字,清晰无比,
如同法官落下法槌。我的大脑“嗡”的一声巨响,彻底空白!
那个午后……阳光刺眼……自习室角落……我对着好友小慧,
因为前夜沈叙又一次因为辩论队训练失约而情绪激动地吐槽……录音?!他怎么可能?!
什么时候?!恐惧如同冰冷的藤蔓,缠绕住脖颈。“放出来,”沈叙的声音轻飘飘的,
带着事不关己的残忍随意,“权当给各位助助兴,也让大家回味一下……青春的热烈。
”他唇角的笑意加深,带着冰冷的嘲弄,手指精准地按下了控制键。
下一秒——一个带着浓重鼻音、极度不满的年轻女声,在顶级的环绕立体声音响里,
无比清晰、毫无保留地炸响:“啊——气死我了!沈叙那个榆木疙瘩!死脑筋!
昨晚说好了一起去看新上映那部浪漫电影的!结果呢?电话不接,信息不回!又放我鸽子!
凌晨一点!他抱着一堆刚复印好的、还带着油墨味儿的辩论稿,
顶着一双熬得通红的眼睛冲到我宿舍楼下!说什么‘刚结束训练,第一时间就想见你’?哈!
”录音里,当年的我,声音因愤怒拔高,带着颤抖:“见个鬼啊!宿舍阿姨都锁门了!
电影早散场了!他就只会傻乎乎地站在楼下那盏破路灯底下,举着那几张破稿子!稿子!
稿子能当饭吃吗?能当电影看吗?浪漫?懂不懂什么叫浪漫啊!
跟一个法律系的书呆子讲浪漫简直是对牛弹琴!
法律系男友是这个世界上最死板、最不解风情的生物!没有之一!我林晚要是再信他的鬼话,
我就是小狗!汪汪汪!”录音戛然而止。死寂。绝对的死寂。时间被按下了暂停键。
几秒钟后——“噗嗤!”第一声憋不住的笑声响起。紧接着,像是点燃了引信,
整个宴会厅瞬间被山呼海啸般的哄笑声、口哨声和议论声彻底淹没!“哈哈哈哈!太真实了!
”“**!无情吐槽!”“法律系男友集体中枪!”“沈检!被嫌弃得很彻底啊!
”“这妹子当年够虎!实名制吐槽?”无数道目光,带着毫不掩饰的笑意、探究和戏谑,
像密集的、滚烫的箭矢射向我!脸颊火烧火燎,耳朵嗡嗡作响,血液奔流冲撞!
我像被剥光了衣服扔在聚光灯下!脚下那摊冰冷的酒渍和碎玻璃,仿佛变成了滚烫的岩浆!
就在这巨大的声浪中,一道沉稳的脚步声,穿透喧嚣,一步一步,朝我走来。
笑声议论声诡异地低了下去,直至寂静。所有的目光,追随着那个从主席台走下来的身影。
沈叙。他脸上没有半分不悦或尴尬。相反,那深邃的眼眸深处,
似乎燃着一种奇异的、灼人的亮光。他无视话筒和镜头,穿过自动分开的人群。
他一步步走到我面前。距离近得我能看清他制服领口一丝不苟的扣子,
看清他额角那道几乎看不见的浅淡疤痕——那是大二模拟法庭对抗时,
为了护住差点被对方激动辩手撞倒的我,他挡在我身前被桌角磕伤的。
近得能感受到他身上散发出的、混合着松木冷香和强大压迫感的气息。
他高大的身影完全笼罩了我。下一秒,在几百双眼睛的注视下,在死寂的宴会厅里,沈叙,
这位声名赫赫的金牌检察官,做出了让所有人瞠目结舌的举动——他毫无预兆地,单膝跪地。
动作流畅,姿态带着一种石破天惊的决然。笔挺的制服裤膝盖处,压在了冰冷光洁的地板上。
他微微仰头,下颌线绷紧。目光如同深不见底的寒潭,
牢牢锁住我因极度震惊、羞耻而失焦的瞳孔。那眼神复杂难辨,糅杂着专注、冰冷的审视,
还有一丝近乎疯狂的锋芒。他抬起右手。一个标准的、银灰色的金属案件证据保管箱,
静静地躺在他骨节分明、干净修长的手掌中。箱子侧面印着醒目的检徽。“咔哒。
”一声轻响,在死寂的空气中格外清晰。箱盖弹开。没有璀璨的戒指。
箱内黑色的丝绒衬垫上,静静地躺着一副冰冷、闪着金属寒光的——银手镯。
旁边还有一张折叠整齐的、印着检徽的《权利义务告知书》。
整个宴会厅爆发出一阵压抑不住的、巨大的抽气声和惊呼!闪光灯疯狂亮起!
沈叙的声音在混乱的惊呼和炫目的闪光中响起,不高,却清晰地穿透一切嘈杂,
带着奇异的沙哑和不容置疑的力量:“林晚。”他叫我的名字,字正腔圆。“现在,
”他顿了顿,唇角勾起一个极浅、却清晰的弧度,那笑意未达眼底,反而让眼眸更加幽暗。
“学会一点变通了。”他稳稳地举着那装着冰冷手镯的证据箱,目光灼灼,一字一顿,
清晰地问道:“求教吗?”银光与请柬时间凝固。空气不再流动。
世界被压缩成眼前这个单膝跪地的男人,和他掌中那副在辉煌灯火下闪着森然寒光的银手镯。
那冷光像无数根冰针,狠狠扎进眼底,带来尖锐的痛楚。荒谬感和尖锐的讽刺,
如同冰水混合着玻璃渣,狠狠灌进喉咙!求教?用这种方式?!在这众目睽睽之下,
用一段羞辱我的录音做前奏,再奉上一副象征逮捕和罪名的银手镯?!
冰冷的愤怒和被彻底愚弄的悲凉瞬间攫住了我!指甲更深地掐进掌心!我要开口!
戳破这虚伪的表演!视线却猛地凝固在他举着证据箱的左手——无名指根部。那里。
一道极淡、却异常清晰、无法忽视的白色环状痕迹,
如同一个刚刚褪去不久、带着余温的烙印,顽固地印在指根的皮肤上。痕迹很新,
边缘泛着一点微红,周围的皮肤颜色尚未完全恢复一致。戒痕。新鲜的戒痕。呼吸彻底停滞。
心脏像是被冰冷的铁手狠狠攥住,猛地向下沉坠!今早。
邮箱里那封静静躺着的、设计精美绝伦的电子请柬。纯白底色,烫金花体字,
精致的法槌与玫瑰缠绕的边框。点开。新娘的名字:苏蔓。
我最信任的、大学四年形影不离、分享所有秘密和心事的闺蜜苏蔓。
那个总爱亲昵地挽着我的胳膊,甜甜地叫我“晚晚”,信誓旦旦说要做彼此伴娘的苏蔓。
新郎的名字……我死死盯着沈叙无名指上那道刺眼的白色印记,
再缓缓移向他那张近在咫尺、英俊却冰冷如雕塑的脸。请柬上那个华丽流畅的花体字签名,
如同烧红的烙铁,猛地烫在我的视网膜上!新郎:沈叙。原来如此。
原来这就是他的“变通”。一场盛大的、面向所有观众的羞辱仪式。
原来这就是他所谓的“求教”。用一副冰冷的手镯和一个屈尊纡贵的下跪姿态,
将我的尊严彻底踩在脚下。原来这道新鲜的戒痕,和邮箱里那封刺眼的请柬,
才是他送给我真正的“礼物”。一个响亮的耳光。一场公开处刑。血液彻底冷却,
凝固在血管里。支撑站立的力气被瞬间抽空。“呵……”一声极轻、极短的气音,
从紧咬的牙关中逸出。我的身体先于意识做出了反应。在几百道惊愕的目光聚焦下,
在沈叙维持着那个荒诞姿势的画面中,在无数闪光灯疯狂的闪烁里——我猛地后退一步。
高跟鞋的细跟狠狠踩过地上的玻璃碎片,发出刺耳的摩擦声。然后,我转过身。
挺直僵硬如旗帜的脊背。拨开身前呆若木鸡的人群,
朝着宴会厅那两扇沉重的、通往外面黑暗世界的大门,一步一步,头也不回地走去。身后,
死寂被打破。更大的惊呼声、议论声如同海啸般爆发!“她走了?!”“拒绝了?!
”“沈检还跪着呢!”“手镯?!这什么意思?!”闪光灯更加疯狂!所有的喧嚣,
都被我抛在脑后。厚重的雕花大门被拉开,深秋夜晚凛冽的寒风,如同冰水混合着针尖,
呼啸着灌入!冷。冷得刺骨。冷得连眼泪都冻结。灰烬中的刀锋冲出那扇金色牢笼,
冰冷的夜风如同耳光抽打在脸上。高跟鞋敲击在空旷的回廊上,发出孤寂的回响。
身后宴会厅的喧嚣,像一场荒诞剧的尾声。我拐进通往酒店后花园的僻静走廊。灯光昏暗,
空气里是清洁剂和陈旧的味道。我需要黑暗。扶着冰冷的墙壁,弯下腰,剧烈的呛咳。
胃里翻江倒海,干呕着,却什么也吐不出来,只有灼烧的痛楚和冰冷的泪水汹涌滚落。
屈辱、愤怒、被背叛的剧痛、荒谬感……无数毒虫啃噬神经。苏蔓甜美的笑脸,
沈叙冰冷审视的目光,疯狂交织撕扯。那个三人世界,只有我像个傻子站在舞台中央。
不知过了多久,颤抖才稍稍平复。直起身,用冰冷的手背抹去泪水。摸索手机,
屏幕亮起惨白的光。叫车。手指颤抖着输入目的地——我那狭小却安全的出租屋。
等待接单的提示音在寂静中格外清晰。时间煎熬。一阵刻意放轻却急促的高跟鞋声由远及近。
我的心猛地一沉,屏住呼吸,缩进阴影。脚步声停在拐角。
一个刻意压低、带着得意和假惺惺关切的女声响起:“晚晚?是你吗?林晚?”是苏蔓。
血液瞬间冻结。僵硬地转身。她站在那里,穿着一身奢华的酒红色礼服,妆容精致,
头发一丝不苟。与我的狼狈形成残忍对比。她看着我,那双曾经盛满“真诚”的大眼睛里,
此刻闪烁着胜利者的光芒和戏谑。“真的是你!”她故作惊讶地轻呼,快步走来,
带着一阵浓郁的、我熟悉的香水味——我送她的生日礼物。“天哪,晚晚,
你怎么躲这儿来了?脸色这么难看?刚才里面……可真是惊天动地啊!”语气夸张,
眼神像探照灯。“沈叙他……”她顿了顿,做出为难羞涩的表情,伸出左手,
刻意缓慢地撩了一下耳边碎发。无名指上,
一枚硕大的、设计繁复的钻戒在昏暗灯光下折射出刺眼光芒!“他就是太认真了,你知道的,
检察官嘛,职业病,有时候表达方式比较……特别。你别往心里去。”语气充满施舍感。
愤怒像岩浆在冰下奔涌。“求教?”苏蔓忽然轻笑,笑声冰冷。她凑近一步,
用只有我们能听到的声音,带着恶毒的甜蜜:“晚晚,你觉得,他刚才是在向你‘求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