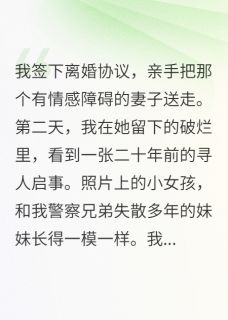我签下离婚协议,亲手把那个有情感障碍的妻子送走。第二天,我在她留下的破烂里,
看到一张二十年前的寻人启事。照片上的小女孩,
和我警察兄弟失散多年的妹妹长得一模一样。我疯了。我亲手抛弃的,
是他找了半辈子的家人,也是我余生都赎不完的罪。01离婚协议书上的油墨还未干透。
柳拂衣的字迹,和她的人一样,清瘦,带着一种刻入骨髓的疏离。我叫顾思齐。是她的前夫。
“都清点好了?”我问,声音听不出情绪。律师点点头:“顾总,
柳**已经把所有属于她的私人物品都带走了。”“所有?”“是的,
除了一些……您母亲当初添置的东西,她一样没动。”我环顾这栋空旷的别墅。
这里曾经是我们的家。现在,它只是一个装满昂贵家具的牢笼。空气里,
似乎还残留着她身上清冷的皂角香。我亲手把她推了出去。用最冷静的口吻,
说着最残忍的话。“拂衣,我们不合适。”“你的世界太小了,
小到只能装下你自己和你那些刺绣。”“我需要一个能站在我身边的妻子,
而不是一个需要我照顾的孩子。”她当时只是安静地听着。没有哭,没有闹。
甚至没有一丝波澜。她只是抬起那双过分干净的眼睛,轻声问:“签在哪里?”那一刻,
我感觉自己像一拳打在棉花上。无力,且可笑。我以为我会感到解脱。
像是卸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可当那扇门在她身后关上的瞬间,窒息感铺天盖地而来。
**在门上,听着她的脚步声渐行渐远。直到再也听不见。那个晚上,我没有回卧室。
就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了一夜。我告诉自己,这是正确的决定。我给了她一大笔钱,
足够她下半辈子衣食无忧,专心做她那些不被世人理解的艺术。我放她自由。也放过我自己。
可为什么,我的心会这么空。空得像被人生生剜掉了一块。柳拂衣的工作室,
我曾无数次踏入,又无数次失望地走出。满屋子的绣绷、丝线、半成品。她的作品,
主题永远是破碎。一朵被撕裂的莲花。一只断了翅膀的蝴蝶。一轮碎成两半的月亮。
我曾轻蔑地称之为“病态的美学”。“拂衣,绣点喜庆的东西,我母亲快过生日了。
”她沉默着,指尖的针停在半空。“绣不了。”她说。“什么叫绣不了?
”我的火气“蹭”地就上来了,“你是刺绣艺术家,让你绣个‘寿’字都绣不了?
”“我的针,只会绣碎掉的东西。”她的声音很轻,却像一根针,扎进我的心脏。现在,
这栋房子里再也没有那些“碎掉的东西”了。干净,整洁,符合我一贯的审美。也冰冷得,
像一座坟墓。02第二天,我让家政来做深度清洁。“顾先生,
这个箱子……是柳**忘了吗?”家政阿姨指着阁楼角落里一个蒙尘的纸箱。很旧了,
边缘都已磨损。不像是柳拂衣的风格。她有洁癖,东西永远一尘不染。我走过去,打开纸箱。
里面是一些更旧的东西。一本卷了角的《安徒生童话》。一个掉漆的木头小鸟。
还有几件洗得发白、明显不合身的旧童装。最底下,压着一块手帕。蓝印花布的,
上面用拙劣的针法绣着一幅图。图案很奇怪,像是某种图腾的一半,残缺不全。我皱了皱眉。
这些破烂,她留着做什么?手机响了。是我母亲,舒雅言。“阿齐,离了?”“嗯。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如释重负的叹息。“离了好,那种女人,根本配不上我们顾家。
”“整天阴沉沉的,跟个鬼似的,看着就晦气!”“妈。”我的声音冷了下来,
“她现在已经不是您的儿媳了,请您尊重她。”“哟,你还心疼了?我告诉你顾思齐,
你可别犯糊涂想什么复合!我费了多大劲才把她弄走,你要是……”“我还有会。
”我直接挂了电话。胸口一阵烦闷。当初,就是我妈一次又一次的挑剔和指责,
将柳拂衣逼得越来越沉默。而我,选择了视而不见。我以为我是为了家庭和睦。现在想来,
不过是懦弱的借口。我把手帕捏在手里,那粗糙的布料硌着掌心。我为什么要留下这个箱子?
也许,这是她唯一没有带走的东西。是她故意留下的,还是真的忘了?
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在我心底蔓延。我拿出手机,想给她打个电话。翻到她的号码,
指尖悬停在屏幕上,却迟迟按不下去。说什么呢?问她是不是忘了拿一箱破烂?
她大概只会用那种毫无波澜的语气回我一句“不要了,扔掉吧”。自取其辱。
我将手机扔回沙发,拿起车钥匙。我需要透透气。驱车在城市里漫无目的地游荡。霓虹闪烁,
车水马龙。这曾是我最引以为傲的商业帝国。我在这里呼风唤雨,无所不能。可现在,
我却像个找不到家的流浪汉。最后,车停在了一家酒吧门口。我拨通了林疏影的电话。
“出来喝酒。”林疏影是我的发小,市局刑侦队的队长。也是我唯一能说几句心里话的朋友。
03酒吧里光影迷离,重金属音乐震耳欲聋。林疏影来的时候,我已经喝了半瓶威士忌。
“怎么了?公司破产了?”他拉开椅子坐下,给自己倒了杯酒。“比破产还严重。
”我扯了扯嘴角,笑得比哭还难看,“我离婚了。”林疏影举杯的动作一顿。他看着我,
眼神复杂。“你……想好了?”“是她想好了。”“顾思齐,你摸着良心说,这桩婚事,
你对得起她吗?”我沉默。良心?我的良心早就被日复一日的争吵和冷战磨没了。
“她那种性格,你知道的,像块捂不热的冰。”我给自己找着借口。“你捂过吗?
”林疏影一针见血,“你除了要求她、改变她,你试着去理解过她吗?”我被问得哑口无言。
是啊。我只觉得她的孤僻和敏感是负担。却从未想过,那层厚厚的冰壳下面,
包裹着的是什么。“算了,都过去了。”我仰头灌下一大口酒,辛辣的液体灼烧着喉咙。
“你今天找我来,就是为了说这个?”林疏行显然不信。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块手帕,
扔在桌上。“这个,你看看。”他拿起手帕,借着昏暗的灯光仔细端详。“蓝印花布,
老东西了。这绣工……很生涩,像小孩绣的。”“你看这图案,认得吗?
”他摇摇头:“没见过,像个残片。怎么了?”“柳拂衣的。”我说,
“在她小时候的杂物箱里翻出来的。”“一个女人,身边只留着几件破烂童装和一块破手帕,
你不觉得奇怪吗?”林疏影的表情严肃起来。作为警察的职业敏感让他察觉到了什么。
“她的过去,你知道多少?”“几乎为零。”我苦笑,“她说她是孤儿,在福利院长大。
再多问,她就不说了。”我们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只有酒杯碰撞的声音,清脆又空洞。
林疏影忽然从口袋里拿出手机,点开一张照片递给我。“你看看这个。
”那是一张翻拍的旧照片,已经泛黄。照片上,是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
约莫四五岁的样子。眉眼弯弯,笑得很甜。
但那双眼睛……那双过分干净、清澈得不见一丝杂质的眼睛。和柳拂衣,如出一辙。
我的心脏,漏跳了一拍。04“这是……?”我的声音有些发干。“我妹妹。
”林疏影的声音很低,带着压抑了二十年的痛楚。“二十年前,在家门口被人抱走了。
”“我爸妈找了她一辈子,直到去世都没闭上眼。”“这些年,我只要一有空,
就会翻看各地的失踪人口档案,但凡有一点点像的,我都会去核实。”“可一次又一次,
都是失望。”他划动手机屏幕,屏幕上出现了一张更清晰的图。是一份手写的寻人启事。
【寻人:林拂衣,女,5岁,于1998年6月12日下午在家门口失踪。身穿白色连衣裙,
左手手腕处有一颗小红痣。失踪时身上带有一块蓝印花布手帕,
上面绣有林家特有的半边‘云纹’图案……】半边……云纹……我像被一道惊雷劈中。
浑身的血液在瞬间凝固。我猛地抢过桌上的那块手帕,双手颤抖地将它展开。那拙劣的针脚,
那残缺的图案……分明就是寻人启事上描述的,半边“云纹”!柳拂衣。林拂衣。原来,
她不是没有姓氏。是她忘了。不,是偷走她人生的人,让她忘了。“疏影……”我张了张嘴,
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喉咙里像是堵了一团火。“怎么了?”林疏影看着我煞白的脸,
察觉到了不对劲。我抓起车钥匙,疯了一样冲出酒吧。“顾思齐!你去哪儿!”我听不见。
我的世界里只剩下嗡嗡的耳鸣声。和那张寻人启事上,刺眼的文字。
【左手手腕处有一颗小红痣。】我见过。我当然见过!无数个夜里,我握着她的手腕入睡。
那颗小小的红痣,像一滴凝固的血,烙在白皙的皮肤上。我曾开玩笑说,
这是她上辈子的情人留下的印记。她只是沉默地抽回手,用衣袖盖住。
我当时只觉得她不解风情。原来,那是她刻在骨子里的伤疤和恐惧。车子在公路上疾驰,
我闯了无数个红灯。我冲回顾家别墅,冲上阁楼,在那个蒙尘的纸箱里疯狂翻找。终于,
我在一本童话书的夹页里,找到了。一张小小的、一寸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小女孩,
和林疏影手机里的,是同一个人。照片背后,用铅笔歪歪扭扭地写着两个字。拂衣。
我瘫坐在地上,巨大的悔恨和恐慌将我淹没。我做了什么?我到底做了什么?
我把一个在黑暗里独自挣扎了二十年的女孩,又一次推入了深渊。她的孤僻,她的敏感,
她的不安全感。她作品里所有破碎的意象。她对家庭这个词汇本能的恐惧。一切,
都有了答案。而我,这个自诩爱她的丈夫,却用“不理解”这把刀,给了她最深的一击。
我拿起手机,颤抖着拨通了林疏影的电话。“疏影。”我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
“我……我想,我找到**妹了。”05林疏影赶到的时候,我正像个傻子一样,
坐在阁楼的地板上。手里紧紧攥着那张照片和那块手帕。他看到我手里的东西,
整个人都僵住了。他一步一步走过来,从我手里接过那张薄薄的照片。他的手,
抖得比我还厉害。一个在枪林弹雨中都面不改色的刑警队长,此刻,眼眶红得像要滴出血来。
“是她……是小七……”他喃喃自语,声音哽咽。“小七是她的小名。”我们相对无言,
空气中只剩下两个男人沉重的呼吸声。许久,林疏影抬起头,布满血丝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
“她人呢?”“我们……离婚了。”我艰难地吐出这几个字。林疏影的拳头,
没有任何预兆地挥了过来。我没有躲。结结实实地挨了这一拳。嘴角瞬间破裂,
血腥味在口腔里蔓延。“顾思齐!”他揪着我的衣领,怒吼道,“**就是个**!
”“是,我是**。”我没有反驳。他骂得对。“我要见她。”林疏影松开我,
声音恢复了一丝冷静,却冷得像冰。我从地上爬起来,擦掉嘴角的血。“我带你去。
”柳拂衣的新住处,是一个很老旧的小区。没有电梯,楼道里堆满了杂物,
墙壁上满是小孩子的涂鸦。和她之前住的别墅,天差地别。我的心,又被狠狠刺了一下。
我们站在一扇掉漆的木门前。我抬起手,却怎么也敲不下去。我害怕。
我害怕看到她那双没有任何情绪的眼睛。林疏影推开我,自己敲了敲门。咚,咚,咚。
每一声,都像敲在我的心上。门开了。柳拂衣穿着一件宽大的白色T恤,头发随意地挽着,
露出一截清瘦脆弱的脖颈。她看到我,愣了一下。随即,目光落在我身后的林疏影身上。
她的眼神里,第一次出现了除了疏离之外的情绪。是……茫然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戒备。
“拂衣……”林疏影的声音在发抖,他向前走了一步。柳拂衣本能地向后退去,
身体紧紧贴在门框上。“你是谁?”她问。林疏影举起手里的照片:“小七,
你不记得我了吗?我是哥哥啊!”“哥哥?”柳拂衣重复着这个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