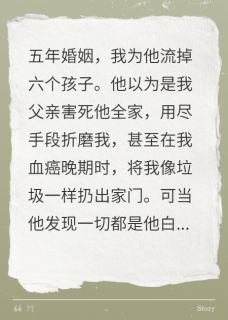五年婚姻,我为他流掉六个孩子。他以为是我父亲害死他全家,用尽手段折磨我,
甚至在我血癌晚期时,将我像垃圾一样扔出家门。可当他发现一切都是他白月光的阴谋,
当他知道自己恨错了人时,我已经签下了死亡协议。他跪在雪地里求我原谅,追悔莫及!
1戚砚臣一脚踹开偏院房门时,我正蜷缩在冰冷的床榻上,小腹传来一阵阵撕裂般的绞痛。
「滚起来。」他居高临下地站着,名贵的衬衫袖口一丝不苟,看我的眼神,
像在看一摊发臭的淤泥。我被他硬生生从床上拽起,力气之大,
让刚经历过一场浩劫的身体狠狠砸在地板上。他眸光闪烁,似乎有那么一瞬间的迟疑,
可当他视线扫过我裙摆下渗出的暗红时,那点迟疑瞬间化为浓得化不开的厌恶。「沈知馡,
你真脏。」我抬起头,嘴里满是苦涩。脏?就在昨天,他那位天真烂漫的小师妹楚灵,
挽着他的手臂,用清脆的声音说:「砚臣哥,都说四个月大的紫河车做药引,
最能调理宫寒呢。你说,是也不是?」戚砚臣当时是怎么笑的?他甚至没看我一眼,
只是温柔地拨开楚灵额前的一缕碎发,语气宠溺到令人作呕。「那还不简单?现成的一个,
用了便是。」我跪在地上,抓着他的裤腿,求他,求他不要。「砚臣,
那是我们的孩子……已经成型了啊!」回应我的,是一碗由他亲手端来的,
黑漆漆的「化胎汤」。我的孩子,我那四个月大、已经会用轻微的胎动回应我的孩子,
就这么无声无息地,成了别人固本培元的一味药引。我的心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
痛到无法呼吸。我深吸一口气,压下所有的情绪,
用一种自己都感到陌生的平静声音说:「我会起来。你走吧。」戚砚臣似乎很意外我的顺从,
锐利的眼神在我脸上逡巡。我扯出一个笑,大概比哭还难看。反正我就要死了,
没必要在最后这点日子里,再和他两看相厌。我们曾经……那么用力地爱过。
我与戚砚臣一同在戚家长大,我是戚家收养的孤女。整个少年时代,
我都像个小尾巴一样跟在他身后,大言不惭地宣布:「戚砚臣,以后我长大了,
是要进你们戚家祠堂的。」我以为那会是真的。可在我父亲,那个我同样视为亲人的养父,
为了钱,将戚家祖传的独门秘方卖给对家时,一切都毁了。戚家因此生产出大批毒药,
声誉尽毁,而戚砚臣的母亲和妹妹,就是死于那批流入市场的毒药。一夜之间,
他从天之骄子,变成了背负血海深仇的复仇者。也是从那一晚起,他不再叫我「馡馡」。
他捏着我的下巴,眼神猩红地告诉我:「沈知馡,你和你那个爹,都欠我们戚家。
我要你用一辈子来偿还。」后来,他成了戚家的新任掌门人,手段狠戾,重振家业。
所有人都说他清冷禁欲,多少豪门千金想攀附,他眼皮都不抬一下。所有人都以为,
他娶我这个罪人之女,是爱到了骨子里。只有我知道,这五年的婚姻,
是一场漫长的、不见天日的赎罪。2医生来过,沉默地给我换了药,
临走前欲言又止地看了我一眼。我知道他想劝我接受治疗。我的血癌已经到了晚期,
本想为了孩子,拼一把。可孩子没了,我活下去的念想,也就断了。我拒绝了化疗。五年里,
我怀了六次,每一次,戚砚臣都用最冷酷的方式,亲手夺走孩子的性命。他说:「沈知馡,
你不配生下戚家的血脉。」可我分明在他眼底,看到过一闪而逝的痛苦。
那些他被噩梦惊醒的深夜,他会无意识地抱紧我,
呓语般地重复着:「馡馡……为什么会这样……」「我多想……可我不能……你父亲……」
「我亲手杀了我的孩子……我怎么……配得到幸福……」那时候,我会抱着他,
像抱着一个迷路的孩子。我们都被困在这场血仇里,谁也无法解脱。门外传来脚步声,
是戚家的老管家。他面无表情地传达戚砚臣的命令:「夫人,先生让您去一趟西边的药房,
为楚灵**熬制固元汤。」我的身体晃了一下。亲手打了我的孩子,
再让我去为那个“受益人”熬药补身。戚砚臣折磨人的手段,总是这么诛心。西边药房里,
名贵的药材码放得整整齐齐。几个年轻的学徒见到我,都低下头,眼神里混杂着怜悯与鄙夷。
「她怎么还有脸来这儿啊?要是我,早就一根白绫了断了。」「嘘……小声点,
先生还留着她,自然有先生的用处。」我充耳不闻,走到药柜前,熟练地取出一支百年老参。
手刚碰到人参,一个娇俏的身影就出现在门口。「姐姐,」楚灵笑盈盈地走进来,
「砚臣哥心疼你,怕你累着,特意让我过来看看。」她说着,很自然地从我手中拿过食盒,
打开盖子,一股浓郁的鸡汤香味瞬间弥漫开来。她故作歉疚地看着我,「哎呀,
姐姐你昨天才小产,今天还要为我费心,我心里真过意不去。」
我看着她眼中一闪而过的得意,只平静地说道:「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话音刚落,
戚砚臣也走了进来,他的目光在楚灵身上停留,化为一汪柔水:「她没为难你吧?」
楚灵立刻摇头,乖巧得像只兔子:「没有的,姐姐对我很好。我还想把这个送给姐姐呢。」
说着,她从脖子上解下一个用红绳系着的血玉吊坠,递到我面前。那块玉,通体温润,
中心一点红光,像一滴鲜活的血。「砚臣哥说了,这玉能安神。我想姐姐刚没了孩子,
比我更需要它。」楚灵见戚砚臣已经走到内室去接电话,脸上的天真瞬间褪去,凑到我耳边,
用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见的声音,阴狠地低语:「姐姐,你还不知道吧?你昏迷之后,
砚臣哥嫌那摊血晦气,就……收集了起来。」我的心脏猛地一缩。「我不过是开玩笑说,
血玉用至亲之人的血来养,会更有灵性。你猜怎么着?」她晃了晃手中的吊坠,
笑容残忍又恶毒,「砚臣哥就把你那没成形儿子的胎血,全喂给了这块玉。」「姐姐你看,
这玉是不是……比以前更红润,更漂亮了?」3我死死地盯着那块玉,血液似乎在瞬间凝固,
又在下一秒疯狂沸腾。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死了,连最后一滴血,都不能安宁。
竟被他们……当成了养玉的污物!「把它给我。」我的声音沙哑得不像自己。
我猛地伸手去夺,楚灵尖叫一声,顺势向后倒去,手中的食盒“哐当”一声摔在地上,
滚烫的鸡汤泼了她一身,狼狈不堪。听到动静,戚砚臣一个箭步冲了出来。「沈知馡,
谁让你推她的!」他厉声质问,眼里的怒火几乎要将我烧成灰烬。果然,又是这样。
楚灵已经缩回他怀里,哭得梨花带雨,「砚臣哥,不怪姐姐,都怪我……」
「我本想把这块玉送给姐姐,毕竟……里面养着姐姐孩子的血,也算是个念想,
一定会保佑她的。」「可姐姐不信我,上来就打我,说是我害死了她的孩子,
要让我偿命……我昨天真的不是故意的……」听着楚灵一句句颠倒黑白的哭诉,
戚砚臣的脸色阴沉得能滴出水。而我的世界里,只剩下那块血红色的玉。「给我。」
戚砚臣皱起眉,看向我时,眼神里有一丝复杂的动摇。楚灵立刻将那块玉塞到他手里,
抽噎着说:「砚臣哥,你快把它给姐姐,只要姐姐能消气……」我伸出手,
指尖几乎就要触碰到那根红绳。戚砚臣却猛地攥紧,将玉收了回去。「你有气,冲我来。」
他的声音冷得像冰,「孩子是我决定不要的,与楚灵无关。」「她好心将这东西给你,
你倒学会恩将仇报了?沈家的家教,就是让你像条疯狗一样乱咬人吗?」「这个孽种,
要不是你瞒着,我根本不会让他活过一个月!」说着,他攥着那块玉,
大步走到药房门口的青石台阶前,当着我的面,高高扬起了手。「不——!」
我撕心裂肺地喊道。他却毫不犹豫地,狠狠将那块血玉砸向坚硬的石阶!“啪!
”一声清脆的爆裂声,血玉四分五裂,那抹刺目的红色,瞬间化为齑粉。
孩子……我最后的念想,没了。我瘫跪在地上,双目猩红地瞪着戚砚臣:「戚砚臣,
那是我们的孩子啊!」他的身形微不可查地僵了一下,眼里闪过一丝不忍。我却像疯了一样,
不顾一切地扑了过去,跪在冰冷的石阶上,用颤抖的、被碎瓷划破的手,
去徒劳地收拢那些混杂在尘土里的红色粉末。我的孩子……「疯够了没有!」
戚砚臣扣住我的手腕,想把我拖起来。我拼命挣扎:「你放开我!你把孩子还给我!还给我!
」炽热的太阳照在身上,我却感觉不到一丝暖意,浑身冰冷,视野开始发黑。我知道,
我的身体已经到了极限。就在我快要失去意识的最后一刻,我倔强地看着他,
一字一句地问:「戚砚,你的心……难道就不会痛吗?」终于,再也撑不住,我身子一软,
彻底倒了下去。戚砚臣一把将我抱入怀中。我听到他前所未有的焦急嘶吼:「沈知馡!来人!
叫医生!」4昏沉中,我做了一个很长的梦。梦里我们还没反目,在戚家的药田里,
他手把手地教我辨认草药。阳光暖暖的,他从背后抱着我,下巴抵在我的头顶。
他说:「馡馡,你闻,这味『合欢』,香气能解忧。」
我笑着问他:「那什么能解你我的忧呢?」他将我抱得更紧,低声说:「有你在,我便无忧。
」……我猛地惊醒,脸上已是一片冰凉的泪痕。原来从一开始,就错了。强行捆绑在一起,
只剩下互相折磨。戚砚臣听到动静,推门而入,见我醒来,大步流星地走到床边,
一把将我拥入怀里。「馡馡,你怎么样了。」这一声久违的“馡馡”,让我瞬间红了眼眶。
他总是这样,一边用最残忍的方式伤害我,
一边又在不经意间流露出那点可怜的、不合时宜的爱意。孩子死了,
如果我也死了……他会不会有一丝一毫的后悔?不,我要让他恨我一辈子,只有恨,
才能让他好好活着。「戚砚臣。」我推开他,平静地开口,「我们互相折磨了五年,够了。」
「我们和离吧。」这几个字,像最锋利的刀,狠狠刺进了他的心脏。他紧紧攥住我的肩膀,
力道大得几乎要捏碎我的骨头,怒吼道:「和离?你凭什么说和离!」「沈知馡,
为了离开我,你现在连这种手段都用上了?你以为假装寻死觅活,我就会放过你?」
我抬起头,迎上他暴怒的目光。「戚砚臣,我已经……不爱你了。」我撒了谎,
用尽全身力气,「放过我吧,也放过你自己。」他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
突然癫狂地大笑起来。「不爱我?」笑声戛然而止,他咬牙切齿地说道:「无论你爱不爱,
这辈子你都别想离开戚家!你和你父亲欠下的债,你用命都还不清!」「和离,你休想!」
说着,他突然将我死死按在床上。我看着他猩红的双眼,心沉了下去。
他从床头柜端起一碗黑漆漆的药,粗暴地捏开我的下颌。「你不是身子弱吗?
不就是想要个孩子做筹码吗?」「沈知馡,我给你!」他狰狞地低吼,「我亲自给你调理,
让你能继续给我生,继续给我偿还!」冰冷苦涩的药汁被野蛮地灌进我的喉咙,
呛得我剧烈咳嗽。我拼命挣扎,推拒着他。他却发了狠,一只手死死禁锢着我,
另一只手把整碗药都灌了下去。直到我身下的床单,开始沁出一片触目惊心的红。
他才像被烫到一样,猛地松开手。「怎么会……」他看着我嘴角的药渍和不断涌出的鲜血,
眼神里第一次露出了真正的惊慌。「医生!医生!快来!」他冲着门外大喊,
声音里带着他自己都没察觉到的颤抖。我的血越流越多,染红了他的手,
炙热得像是要将他灼伤。眼泪从他眼眶里滚落,滴在我的脸上。「馡馡,你不会有事的,
一定不会……」「医生马上就来了,你撑住,求你撑住……」我伸出手,
轻轻抹掉他脸上的泪,笑了。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戚砚臣的眼泪。「戚砚臣,
」我的意识开始涣散,「我好……困……」空气中,除了浓重的中药味,
还有一丝淡淡的、铁锈般的甜香。是我的血。5急救室的红灯,像一枚烙铁,
灼烧着戚砚臣的眼睛。他靠在冰冷的墙壁上,五年前的记忆如潮水般涌来。那年,
也是在这条走廊,他等来了母亲和妹妹的死讯。如今,他又站在这里,
等待着沈知馡的生死判决。门开了。满身疲惫的医生摘下口罩,看到戚砚臣,眼里没有恭敬,
只有毫不掩饰的愤怒和鄙夷。「戚先生,你是想让她死吗?」戚砚臣攥紧拳头,
下颌线绷得死紧。「化胎汤是烈**狼之药,她刚流产,身体本就亏空到了极致,
你怎么敢……你怎么敢再用那种东西灌她!」医生几乎是指着他的鼻子在骂,「五年,
六次流产!你是铁了心要她的命!」他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纸,狠狠甩在戚砚臣的胸口。
「自己看!晚期血癌!三个月前就确诊了!我让她住院化疗,她为了保住这个孩子,
死活不肯!现在孩子没了,她自己也……」“血癌晚期”四个字,像晴天霹雳,
将戚砚臣劈得魂飞魄散。他抓着那张诊断书,第一反应不是悲伤,而是荒谬和暴怒。
为了离开我……她居然连这种弥天大谎都敢撒?这是她精心设计好的,
一场逼他就范的苦肉计!这时,楚灵提着一个保温壶,柔弱地走了过来,
「砚臣哥……姐姐她怎么样了?都怪我,我不该拿那块玉**她……」
她看到戚砚臣手里的诊断书,故作惊讶地捂住了嘴,“啊”了一声,
「这个……姐姐不是说……」「说什么?」戚砚臣猛地抬头,像抓住救命稻草的溺水者。
楚灵立刻一副说错话的样子,慌忙摆手,「没什么没什么……我就是有一次,
无意中看到姐姐和李医生见面,听到姐姐说什么『只要装得像』、『您放心,
他一定会信的』之类的话……我当时以为姐姐只是想……想让砚臣哥你多心疼她一点,
我真不知道会这么严重……」这句话,像最后一根稻草,
彻底压垮了戚砚臣心里那点微末的动摇。原来如此。所有的巧合都串联起来了。
她绝望地提出和离,她恰到好处地咳血,
她让医生伪造了一份足以以假乱真的诊断书……全都是为了逃离他。好,好得很。
他眼底的慌乱被滔天的怒火取代,他转身,一脚踹开病房的门。沈知馡刚被护士扶着躺下,
脸上没有一丝血色,像一朵即将凋零的白山茶。他一步步走到床前,将那张诊断书揉成一团,
狠狠砸在她脸上,俯身,冰冷的手指死死掐住她脆弱的脖颈。「沈知馡,你告诉我。」
他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每个字都带着血腥味。「为了离开我,你连自己的命,
都舍得拿来演戏?」沈知馡连呼吸都变得困难,她看着他,看着他眼里的疯狂与不信,
连解释的力气都没有了。她只是慢慢地、凄凉地笑了起来。6她的笑,
比任何辩解都更刺痛戚砚臣。那笑里没有阴谋得逞的得意,只有一片沉寂的、浩瀚的绝望。
「把她给我扔出去!」他失控地咆哮。保镖冲了进来,将虚弱的沈知馡架起来,
连同那张沾着她血迹的床单,一同扔出了戚家大门,
扔回了她父母留下的那栋早已破败不堪的老宅。戚砚臣站在二楼的窗前,冷冷地看着这一切,
直到那辆车消失在视野尽头。可他心里非但没有复仇的**,反而空得像一个黑洞。
他终究还是不放心。一个电话打给了自己的助理:「找人盯着她,
再给我把城里所有肿瘤科的医生资料,以及姓沈的女病人的所有病历,全部查一遍!
挖地三尺也要查清楚!」而被抛弃的沈知馡,回到这栋充满灰尘的老宅后,
却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她要死了,终于可以解脱了。她撑着墙壁,
一步步走到母亲的房间,打开那个落满灰尘的旧药箱。里面没有名贵的药材,
只有母亲生前留下的,一本本泛黄的笔记和一些用牛皮纸包好的药方。母亲是个温婉的女人,
也是戚家上一代里,医术最高明的女人。沈知馡抚摸着母亲清秀的字迹,
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温暖的午后。就在这时,戚砚臣正坐在办公室里,
一沓沓的文件被送到他面前。一家、两家、三家……全市所有权威医院的诊断记录,
每一次的化验单,每一次主治医师签名的化疗建议书,
甚至还有沈知馡用自己那张可怜的积蓄卡,
缴付检查费用的单据……所有证据都指向同一个结论——她的病,是真的。不是演戏。
不是苦肉计。是他……亲手把一个癌症晚期的病人,从医院的病床上拽下来,灌下虎狼之药,
再像扔垃圾一样,将她扔了出去。“轰”的一声,戚砚臣脑子里有什么东西彻底炸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