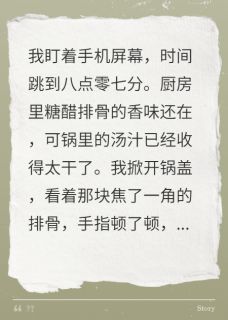飞机降落在临梧,这座小城的温暖与宁静很快包裹了我和腹中的小生命。在临梧安顿下来后,我找了份工作,努力生活。孩子出生后,为了给他更好的生活,我开了一家名为“念甜”的蛋糕店。
清晨六点,天光刚透进玻璃橱窗,我把遮光帘往上拉了半截。店门还没开,操作台上的打蛋器、刮刀、量勺都擦得发亮,像在等一个仪式的开始。
“念甜”开张第五年,每天的节奏早已刻进骨头里。
我正准备把今早第一批舒芙蕾放进烤箱,头顶的灯忽地闪了一下,接着整间店陷入黑暗。
停电了。
我眉头一跳,手没停,转身拉开操作台下方的柜子,拖出那个用了五年的移动储能箱。外壳有些发黄,边角还贴着沈小宝去年用卡通胶带补的星星贴纸。我插上电源线,按下启动键,冷藏柜的指示灯慢慢亮起来。
还好,温度没掉太多。
“妈妈?”楼上传来小家伙的声音,带着刚醒的鼻音,“又黑了?”
“嗯,电跳了。”我仰头冲楼上说,“宝宝去穿衣服,今天要早点去幼儿园。”
脚步声咚咚咚地响起来,不一会儿,沈小宝探出小脑袋,穿着恐龙图案的睡衣,头发翘着一撮呆毛。“我帮你记啦,”他站在楼梯口,一本正经,“今天要修电路。”
我笑了下,伸手揉了揉他的头,“真乖。”
他噔噔跑下来,踮脚够到操作台,拿起蜡笔在便签纸上画起来。我一边调面糊一边瞄了一眼——画的是我和他,手拉手站在一个歪歪扭扭的蛋糕上,头顶写着三个字:家。
底下还有一行小字:“妈妈+我+蛋糕=家”。
我喉咙动了动,没说话,只把那张纸揭下来,贴在了收银台最显眼的角落。
这店刚开那年,连张像样的桌子都没有,我抱着刚满月的他,在厨房角落搭了个简易婴儿床。那时候,我只知道不能倒下,因为他是我唯一要养活的人。现在,他成了我每天睁眼就想看到的脸。
七点二十分,第一批订单打包好,我推开店门,把“营业中”的牌子翻过来。阳光斜斜地铺在门口的石板路上,几片梧桐叶被风卷着打转。
“年年!”隔壁花店的李姐探出头,“今天舒芙蕾有抹茶的吗?老顾客要两份。”
“有,刚出炉。”我把袋子递过去,“趁热吃。”
她接过,压低声音:“你家小宝真是个小大人,昨天放学自己跑来取蛋糕,说‘妈妈忙,我来’,那小身板提着保温箱,看得我心都化了。”
我笑了笑,没接话。
孩子从小就懂事得让人心疼。别的小孩哭着要妈妈抱,他从三岁起就学会了轻手轻脚地给我端水,看我打哈欠,会自己爬上床盖好被子,说“妈妈睡吧,宝宝不吵”。
八点整,我牵着他往幼儿园走。路上他突然停下,仰头看我:“妈妈,老师今天说,要填‘爸爸妈妈一起做的事’。”
我脚步一顿。
“我没填。”他拽紧我的手,“我说,我妈妈一个人就能做所有事。”
我蹲下来,平视他眼睛:“那老师怎么说?”
“她说……孩子需要爸爸。”他声音低下去,睫毛扑闪,“可是,我有爸爸啊。”
我指尖微微发紧。
他仰起脸,眼神亮得像晨光里的露珠:“他在天上,保护你。”
我鼻尖一酸,但没让情绪露出来。只是轻轻摸了摸他的额头,说:“嗯,他是超级英雄。”
他笑了,蹦跳着往前走:“那我就是小英雄!”
我跟在后面,看着他小小的背影,心里像被什么轻轻撞了一下。
中午打烊前,王叔来了。
他是常客,退休工人,爱喝酒,总在下午三点左右晃进来,点一块芝士蛋糕,坐到打烊。今天他来得早,脸上泛着酒气。
“年年啊,”他坐下,笑呵呵,“一个人撑这店,不容易吧?”
我擦着柜台,淡淡应了句:“还行。”
“我说,你也该考虑考虑了。”他端起茶杯,眼神意味深长,“找个伴儿,至少有人接送孩子,晚上能搭把手。”
我手上的动作没停,语气依旧平:“谢谢王叔关心,但我儿子有爹。”
他一愣,“啊?哪个?我咋不知道?”
我抬眼,直视他:“坟头草都三米高了。”
空气静了一瞬。
王叔尴尬地咳嗽两声,正要说什么,厨房门猛地被推开。
沈小宝举着沾满奶油的刮刀冲出来,站上高脚凳,小脸严肃:“王叔!我妈说了,要找也得找会做提拉米苏的!你行吗?”
王叔张了张嘴。
“而且!”小家伙叉腰,“我爸是超级英雄,才不会让别人抢位置!”
店里几个客人噗嗤笑出声。王叔脸一阵红一阵白,端起杯子一饮而尽,嘟囔了句“开个玩笑嘛”,拎起蛋糕走了。
门铃叮当一响,人没了影。
我转身想训他,却见他正踮脚把一张纸贴在玻璃柜侧面——是张手绘的告示,歪歪扭扭写着:“本店老板已有丈夫,是超级英雄,禁止介绍对象。违者罚吃十块无糖蛋糕。”
我扶额:“谁让你贴的?”
“我自己写的!”他仰着小脸,眼睛亮晶晶,“我要保护妈妈。”
我蹲下来,把他搂进怀里。他身上有奶香和阳光的味道,心跳贴着我的胸口,又快又稳。
“宝宝……”我轻声说,“你才是妈妈的英雄。”
他搂紧我的脖子,小声说:“妈妈不哭,我长大了,我能挡在你前面。”
我没哭。五年了,眼泪早就干了。
可那一刻,我真觉得,我这个当妈的,不是在养一个孩子,而是在和一个小战士并肩作战。
下午四点,电工老陈来了。
他检查完线路,摇头:“老房子线路老化,你们这排商铺都这样。我给你换几根线,但最好还是申请增容。”
“要多久?”
“最快明天下午。”
我点头,“麻烦您了。”
他临走前看了眼墙上的价目表,“你这店,全靠口碑撑着吧?没宣传,没团购,连个二维码都是手写的。”
“客人吃得开心,就够了。”我说。
他笑了一声,“也是,有些人开店,不是为了赚大钱,是为了活得踏实。”
门关上,店里安静下来。
我走到收银台前,看着那张“妈妈+我+蛋糕=家”的便签纸。阳光斜照进来,纸角微微卷起,字迹被镀上一层金边。
沈小宝趴在地上拼乐高,嘴里哼着幼儿园教的儿歌。
我拿起抹布,开始擦桌椅。每一张椅子都坐过不同的人——有独来独往的老人,有偷偷约会的学生,有带着孩子来的单亲妈妈。她们总在临走时说:“年年,你这儿让人安心。”
是啊,这间小店,不是什么大事业,但它是我们母子的堡垒。
五点四十分,夕阳把街道染成橘色。
我挂上“今日已打烊”的牌子,反锁店门。沈小宝背着小书包站在我旁边,手里攥着一块没吃完的曲奇。
“妈妈,明天还要修电吗?”他仰头问我。
“嗯,修好了就再也不怕黑了。”
他点点头,突然踮起脚,把那块曲奇塞进我嘴里,“那我先给你充电。”
我咬了一口,甜味在舌尖化开。
他牵起我的手,晃了晃,“走啦,回家。”
我们沿着石板路往回走,影子被拉得很长。路过一家新开的奶茶店,门口贴着招聘启事,上面写着“月入过万,包住”。
我没看第二眼。
走到楼下,他忽然停下,指着二楼阳台晾着的两件衣服——我的白衬衫和他的蓝色小卫衣,在晚风里轻轻摆动。
“妈妈,”他仰着脸,认真地说,“我们家的衣服,也晒到太阳了。”
我低头看他,风吹起他额前的碎发。
他笑了,露出缺了颗门牙的豁口,“你看,我们什么都有了。”
我捏了捏他的手,正要说话——
他突然挣脱我,转身跑回店里。
我愣住,追到门口,看见他踮着脚,把那张“禁止介绍对象”的告示重新贴正,还用指甲压了压边角,确保它不会被风吹走。
然后他跑回来,牵起我的手,仰头说:
“妈妈,下次谁敢说你一个人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