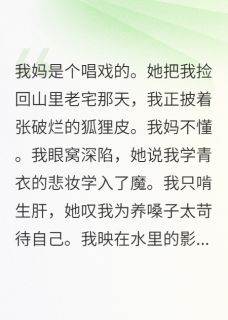我妈是个唱戏的。她把我捡回山里老宅那天,我正披着张破烂的狐狸皮。我妈不懂。
我眼窝深陷,她说我学青衣的悲妆学入了魔。我只啃生肝,她叹我为养嗓子太苛待自己。
我映在水里的影子是狐狸,她说山里水波乱,照不清人影。后来,村里来了个道士,
说要替天行道。我妈横刀立马,提着她那杆唱《破洪州》的浑铁枪,挡在我身前。
“这是我闺女,我这辈子最得意的一出戏。”“谁敢动她一根汗毛,先问过我穆桂英!
”1我妈林书琴找到我时,我正躲在后山的竹林里。身上那张人皮又旧又薄,风一吹就打颤。
我抱着一只刚掐死的野鸡,正准备享用。“安然,你这孩子,跟妈玩捉迷藏,
也不知道多穿件衣裳?”我妈的声音还是那么亮,穿透竹林,震得我耳朵嗡嗡响。
她拨开挡路的竹子,快步走到我面前,一把脱下自己的外套披在我身上。“城里剧团不景气,
也不至于让你穿成这样回来啊。”我喉咙里发出嗬嗬的怪声,张嘴就想咬她。她眼疾手快,
从兜里掏出一块梨膏糖,精准地塞进我嘴里。“又闹脾气,嗓子不要了?回家,
妈给你炖了川贝雪梨。”她拉着我的手往家走。我步履僵硬,被她拽得一个趔趄。
嘴里的糖块硌得我牙疼。路过村口的王屠夫,他看见我,吓得手里的杀猪刀都掉在了地上。
我妈还扭头冲他笑。“老王,吓着了吧?我家安然这是在体验角色呢,疯疯癫癫的,别介意。
”回到家,我妈把我按在堂屋的太师椅上。她打来一盆热水,仔仔细细给我擦脸。
我的皮肤干得像纸,透着一股死气沉沉的灰白。“瞧瞧你这妆化的,
演《窦娥冤》也不用这么下本钱吧?脸都搓掉皮了。
”她轻轻揭下我脸颊边翘起的一小块人皮,嘴里啧啧称奇。“这人皮面具做得可真够逼真的,
就是这胶水不行,都开裂了。”我猛地张开嘴,露出尖利的牙齿。
我妈顺手从桌上的果盘里拿起一个苹果,塞了进去。“饿了就说,别跟妈置气。
”她拿起一把黄杨木梳,想给我梳头。手碰到我后颈,那里的人皮已经完全裂开,
露出底下灰色的绒毛。她愣了一下。“这……这道具做得,毛都缝上去了。安然啊,
你跟妈说实话,你是不是接了《聊斋》的戏?演狐狸精?”她摸着那撮软毛,
眼神里满是赞叹。“现在的戏班子,真是舍得下血本。”晚上吃饭,我妈做了一桌子菜。
我闻着那油烟味就犯恶心,一筷子都没动,眼睛死死盯着挂在房梁上的那块腊肉。
我妈顺着我的视线看过去,叹了口气。“知道了,知道了,要吃生肉养嗓子。
”她踩着凳子把腊肉取下来,切了一大块生的给我。“吃吧,吃吧,
别把自个儿的身子弄垮了。”夜里,我身体里的饥饿感像火一样烧。我悄悄溜出房门,
想去村里找点活物。我妈拿着一根齐眉棍,把我堵在了院子里。“大半夜不睡觉,又去练功?
你这身子骨经得起这么折腾吗?”她不知从哪儿找来一根红绸带,把我绑在了床腿上。
“今晚哪儿也不许去,给我在床上好好睡觉。”红绸带上有她唱戏时开过光的朱砂,
烫得我皮肤滋滋作响。我动弹不得,只能眼睁睁看着天亮。2.第二天一大早。
王屠夫的儿子阿牛跑来敲门,脸吓得煞白:”林阿姨,不好了!山里来了个道士,
说咱们村里有妖怪!”我妈正在给我缝补那张破损的人皮。她用的是唱戏时绣凤袍的金丝线,
一针一线,密密匝匝。“胡说八道什么呢,哪来的妖怪。”她头也不抬。
“是不是又偷看你爹藏起来的画本子了?”“我说的都是真的!那道士可神了,
拿着一把桃木剑,说妖气就在……就在……”阿牛指着我,我正隔着窗户对他咧嘴笑。
我妈一巴掌拍在我后脑勺上:”没大没小,叫阿牛哥。”我发出一声尖啸,
阿牛吓得一**坐在地上。我妈还在那儿絮叨。“这孩子,从城里回来就爱跟人开玩笑。
我正给她补戏服呢,你看这手艺,远看跟真皮似的。”阿牛连滚爬带地跑了。
我妈天天逼着我喝符水,她说那是清热降火的凉茶。她还在我房间里点上檀香,
说能静心安神。那味道呛得我头晕眼花,却也真的让我安分了不少。末世,哦不,
是我变成这样的第七天。村子里的鸡鸭开始莫名其妙地失踪。
我妈照常去后山打理她的那片小菜园,我跟在她身后。那些循着味儿想靠近我的山间野兽,
一见到我,就夹着尾巴逃走了。“安然,来,帮妈把这块地翻一翻。
”我妈指着一块板结的土地。我伸出爪子,几下就把地刨得松松垮垮。“哎哟,
你这指甲该剪了,都快赶上熊爪子了。”她抓过我的手,拿出指甲刀,咔嚓咔嚓剪了起来。
剪秃了的爪子让我很不适应。中午回家,我妈把新摘的青菜炒得香喷喷的。
又从地窖里拿出一块血淋淋的生肝放在我面前。“慢点吃,没人跟你抢。
”她看着我风卷残云的样子,眼神里满是心疼。“你这孩子,在外面到底受了多大的罪,
吃相跟几百年没见过荤腥一样。”3.直到那个年轻的道士找上门来。他叫陈宇,眉清目秀,
一身洗得发白的青布道袍。他看见我,脸色瞬间变得凝重:”大娘,你女儿身上妖气冲天。
”我妈正在院子里给我吊嗓子,闻言柳眉一竖。“什么妖气不妖气的,我闺女那是台风,
懂不懂?角儿都这样。”“可她印堂发黑,眼露凶光!”“那是烟熏妆,现在城里流行这个。
”“她走路悄无声息,脚不沾尘!”“那是练的台步,身段轻盈。
”陈宇被我妈怼得哑口无言,他从怀里掏出一张黄色的符纸,想贴到我额头上。
我妈抄起晾衣服的竹竿就冲了上去。“谁敢动我闺女!”她一套枪法使得出神入化,
竹竿在她手里变成了银枪,把陈宇打得连连后退。陈宇没办法,只好在村口安顿下来。
他发现我妈种的菜远近闻名,吃了能强身健体,比他画的符管用。更不好意思赶我们走了。
每天都有村民来换蔬菜。我妈用一篮子青菜换了半扇猪肉。用一筐萝卜换了一袋精盐。
用一把韭菜换了一坛女儿红。女儿红不是必需品,我妈还是换了,她说我体寒,
喝点酒能暖身子。陈宇不死心,天天来劝。“林大娘,您女儿真的不是普通人,她很危险。
”我妈往我嘴里塞了一瓣橘子。“胡说,我闺女乖着呢,她怎么没害我?
”“可是……”我妈眼睛一瞪。“可是什么可是,我家安然好着呢,她不可能是妖怪。
”日子就这么过着,直到有一天。王屠夫家新买的小猪仔丢了,
有人说看见一个黑影蹿进了我家的院子。全村的人拿着锄头扁担把我们家围了个水泄不通。
“把那妖怪交出来!不然连你家房子一起烧了!”他们声嘶力竭地喊着。我妈把我护在身后,
手里攥着那把切菜的刀。“这是我闺女!她不是妖怪!你们要赶她走,俺也跟着走!
”“她是妖怪啊林书琴!”“放屁。”我妈气得浑身发抖。“俺家安然才不是你们说的怪物!
她就是爱美,就是敬业,就是……就是……”她卡壳了,回头看我。我正蹲在门槛上,
专心致志地用指甲刮着地上的青苔,对外面的骚动充耳不闻。所有人都沉默了。
我妈突然想起了什么,从戏服箱子里翻出一件金光闪闪的佛衣,披在我身上:”你们看,
都说妖怪怕佛光,俺闺女不怕!”那佛衣上绣满了梵文,像烙铁一样烫着我的皮肤,
我疼得龇牙咧嘴,但还是站在原地,一步没动。陈宇推了推鼻梁上不存在的眼镜。“大娘,
佛衣确实能镇压邪祟,但这只是传说,没有任何典籍记载所有的妖都怕佛衣,
说不定你女儿是特例呢。你看看她那样子,她哪里像个人?别自欺欺人了……”“闭嘴。
”我妈又从头上拔下几根银簪,对着我的头顶就扎了下去,急于证明我还是个人。
“这是俺家祖传的针法,专治癔症,俺肯定能把她治好。”说来也怪,那几针下去。
我混沌的脑子清明了一瞬。我张开嘴,发出了一个含混不清的音节:“妈……”我妈愣住了,
随即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滚落下来。“听见没,俺闺女会叫妈,妖怪会叫妈吗?
”村民们面面相觑。最终叹了口气,三三两两地散去了。陈宇临走前,
偷偷塞给我妈一本泛黄的线装书。“《镇妖集》,您……有空看看。
”4.我妈没看那本《镇妖集》。她把书垫了桌脚,
然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给我“治病”上。她每天逼着我练功,压腿,下腰,跑圆场。
我僵硬的四肢在她的“悉心指导”下,居然真的柔软了不少。她还教我唱戏。“来,安然,
跟着妈唱,‘我本是卧龙岗上散淡的人’……”我张开嘴,发出的却是野兽般的嘶吼。
她也不气馁,一遍遍地教。“气沉丹田,声音要从嗓子眼儿里出来,要圆润,要亮。
”我学不会,急得用爪子挠墙,在墙上留下了几道深深的抓痕。她看到了,不惊反喜。“哟,
这指力,演武生准能成角儿。”村里平静了一段时间,但暗流仍在涌动。
王屠夫家的猪仔再也没找回来,他看我家的眼神一天比一天怨毒。村民们虽然嘴上不说,
但都绕着我家走。只有陈宇,还隔三差五地来。他不提妖怪的事,只跟我妈聊些戏文典故。
我妈引他为知己,时常留他吃饭。饭桌上,他总是有意无意地把一些浸过朱砂的筷子递给我。
我闻到那味道就犯恶心,碰都不碰。我妈就说我挑食,把筷子抢过去自己用。“你这孩子,
怎么这么娇气,筷子还分人?”陈宇的试探一次次失败,脸上的表情也越来越凝重。
我知道他在怀疑我,我也在警惕他。这个男人身上有种让我很不舒服的气息,干净,纯粹,
像正午的太阳,让我无所遁形。一天,我妈去镇上赶集,留我一个人在家。陈宇又来了。
他没有进门,只是站在院子外,静静地看着我。“你到底是什么东西?”他问。我没理他,
继续啃我的生肉。“你这样留在她身边,迟早会害了她。”我啃肉的动作停顿了一下。
他见有反应,继续说:“你身上的妖气越来越重,已经快压制不住了。等到月圆之夜,
你会彻底失去理智,到时候,第一个受害的,就是你最亲近的人。”我猛地抬起头,
冲他龇出了牙。他叹了口气,从怀里拿出一个小小的香囊。“这是安神香,
用百草之王混合雄黄制成,你戴在身上,或许能帮你压制心魔。
”他把香囊放在门口的石墩上,转身走了。我盯着那个香囊,犹豫了很久。最终,
还是没有去拿。我妈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她给我带了城里最有名的烧鸡。“安然,
快来尝尝,这家的烧鸡,皮脆肉嫩,香得很。”我闻到那股熟肉的香味,胃里一阵翻江倒海。
我妈看我没反应,自己撕了个鸡腿,咬了一口。“真香。你不吃,妈可就都吃了。
”她吃得很慢,一边吃,一边用余光瞟我。我看到她眼底一闪而过的失落。那一刻,
我心里某个地方,像是被针扎了一下。5.村里的气氛越来越诡异。
家家户户门口都挂上了桃木剑和八卦镜。连王屠夫都在他家猪圈的门上贴满了黄符。
我妈对此嗤之以鼻。“一群没见识的,搞得跟唱大戏一样。”她照旧拉着我在院子里练功,
唱戏,仿佛外面的一切都与我们无关。但她的眉头,却越锁越紧。她开始失眠,
半夜常常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对着月亮发呆。我知道,她在害怕。不是怕我,是怕那些村民。
怕他们会伤害我。陈宇来的次数更勤了。他不再跟我妈聊戏文,
而是开始讲一些他在外游历时听到的,关于人与妖的故事。有书生与狐女的爱恋,
有道士与蛇妖的纠缠。每个故事的结局,都是悲剧。我妈听得入了神,时而叹息,时而落泪。
“你说,那些妖怪,是不是也不想害人?”她问陈宇。陈宇沉默了片刻,说:“心有善念,
人妖无异。心存恶根,人亦是妖。”我妈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那天之后,
她开始偷偷看那本被她用来垫桌脚的《镇妖集》。她看得很快,常常一看就是一整夜。
书页被她翻得卷了边。我不知道她看懂了多少,只知道她房间里的檀香味,
变成了浓烈刺鼻的艾草味。她还开始在我的饭菜里加一些奇怪的东西。
有时候是磨成粉的朱砂,有时候是切成末的桃木屑。我吃了之后,浑身燥热,
五脏六腑都像是在燃烧。我开始反抗,不再吃她给的任何东西。我们陷入了冷战。她不逼我,
只是每天把饭菜做好,放在我面前,然后自己坐在一旁,默默地看着我。她的眼神里,
有心疼,有无奈,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坚定。我饿得眼冒金星,身体里的**在疯狂叫嚣。
好几次,我都差点忍不住扑向她。但一对上她那双清澈又固执的眼睛,我心里的那头野兽,
就偃旗息鼓了。僵持了三天。我终于妥协了。我端起那碗混着朱砂的肉羹,一口气喝了下去。
灼烧感从喉咙一直蔓延到胃里。我疼得在地上打滚,发出了痛苦的哀嚎。我妈冲过来抱住我,
眼泪大颗大颗地掉下来,落在我的脸上,比朱砂还要烫。“安然,妈知道你难受,再忍一忍,
很快就好了,很快就好了……”她在我耳边,一遍遍地重复着这句话。像是在安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