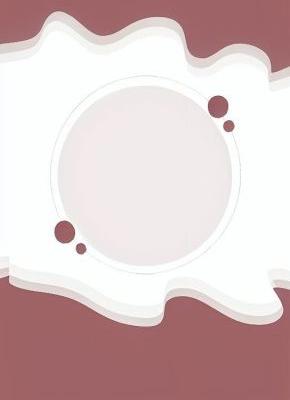为了家族,我代替哥哥穿上男装去参军长枪刺入血肉的触感,我已经习惯了。
金属摩擦骨骼的声音,我也习惯了。温热的鲜血溅在脸颊上,带着死亡的腥气,
我甚至已经能面无表情地用手背擦去。在这里,我叫苏烈。一个在北境战场上靠着杀敌军功,
从新兵蛋子爬到百夫长的狠角色。三年前,我叫苏锦。是苏家那个以绣工闻名,
柔顺温婉的二女儿。“阿烈,小心!”战友的一声爆喝将我从短暂的失神中拉回。
我下意识地侧身,一支淬毒的冷箭擦着我的铁甲飞过,深深钉入我身后的木桩,
箭羽兀自嗡嗡作响。我眼神一寒,反手抽出腰间的短刀,看准偷袭的敌军百夫长,
如猎豹般扑了过去。刀光掠过,一颗头颅冲天而起。鲜血喷涌,染红了我脚下的黑土地。
周围的喧嚣似乎在这一刻静止了。敌军看着他们倒下的头领,士气瞬间崩溃。
我方的士兵则爆发出震天的欢呼。“苏百夫长威武!
”我面无表情地将短刀在尸体的衣服上擦干净,收回刀鞘。转身,对着我的兵,
声音嘶哑而冰冷:“打扫战场,清点伤亡。”这就是我的日常。血与火,生与死。
每当夜深人静,我卸下满是血污的盔甲,抚摸着胸口层层缠绕的束胸白布,
那种尖锐的疼痛才会提醒我,我到底是谁。我是苏锦。我的哥哥苏明章,是苏家唯一的男丁,
是我们全家的希望。他自幼体弱多病,却才华横溢,十六岁就中了秀才,
所有人都说他将来必定是状元之才,光耀门楣。三年前,北境战事吃紧,朝廷强行征兵。
每个有男丁的家庭,必须出一个。征兵的文书送到家里那天,爹娘一夜白头。
哥哥更是当场咳血,晕了过去。大夫说,他这身子骨,别说上战场,
就是去军营的路都走不到一半。我们家,要绝后了。那天晚上,娘拉着我的手,
哭得肝肠寸断。“锦儿,我的锦儿,你哥哥要是去了,就是要他的命啊!我们苏家,
就全完了啊!”爹,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跪在我面前,老泪纵横。“锦儿,爹对不起你,
爹没用。可你哥哥……他不能死,他要是死了,我怎么去见苏家的列祖列宗?
”哥哥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如纸,拉着我的衣袖,气若游丝:“妹妹,若有来世,
哥哥做牛做马报答你……”我看着他们。我的爹,我的娘,我的哥哥。
我们是血脉相连的一家人。于是,我剪掉了及腰的长发,穿上了哥哥的衣服,
用锅底灰抹黑了脸,束紧了胸。我对着铜镜里的那个陌生少年,一字一句地说:“从今天起,
我叫苏烈。”我代替哥哥,走进了那个吞噬人命的军营。临走前,娘抱着我,
将一个油纸包塞进我怀里。“烈儿,这是娘给你做的点心,路上吃。家里你放心,
我们会照顾好自己的。你在军中,一定要保重,我们……我们等你回来。
”哥哥则送给我他最珍爱的一方砚台,“妹妹……不,苏烈。此去,万事小心。
哥哥会在家日夜为你祈祷,等你凯旋,哥哥亲自为你接风洗尘。”我走了。
带着全家的希望和嘱托,踏上了这条九死一生的路。军营的日子,比我想象的苦一百倍。
每天的操练都像要扒掉一层皮。我和一群男人一起摸爬滚打,吃的食物粗糙得划嗓子。
晚上几十个臭烘烘的男人挤在一个大通铺,鼾声、梦话、磨牙声此起彼伏。我不敢多喝水,
怕起夜暴露身份。我不敢和任何人走得太近,怕被发现女儿身。我不敢生病,不敢受伤,
不敢在任何人面前流露出丝毫的软弱。因为我不是苏锦,我是苏烈。
我是我们苏家唯一的“男丁”。刚开始的半年,我几乎每天都在绝望的边缘挣扎。好几次,
我都想干脆死在战场上,一了百了。但家里的信,是我唯一的支撑。每隔一个月,
我都能收到一封家书。娘在信里说,家里一切都好,让我不要挂念。她又给我做了新棉衣,
托商队给我捎来,让我天冷了记得加衣。爹在信里说,我寄回家的军饷都收到了,
他用这些钱给哥哥请了最好的大夫调理身子,哥哥的病已经大有好转,都能下床读书了。
他还骄傲地说,邻里乡亲都夸他养了个好儿子,将来必定封侯拜将。哥哥的信总是最长的。
他会和我分享他最近读了什么书,有什么心得。他会告诉我城里又开了哪家新铺子,
发生了什么趣闻。他字里行行都充满了对我的关切和担忧。“阿烈吾弟,见字如面。
闻北境风雪愈寒,弟是否衣单?切记保重身体,万勿逞强。兄在家中,日夜温书,
不敢有丝毫懈怠,只盼早日考取功名,让你我兄弟二人,共同光耀我苏家门楣。
家中一切安好,勿念。父母康健,唯对你甚是思念。万望吾弟,早日凯旋。
”每次读着哥哥的信,感受着他那熟悉的、隽秀的字迹,
我就觉得身上所有的伤痛和疲惫都消失了。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为了他们,
我必须活下去。不但要活下去,还要活得比所有人都好。我要挣军功,我要升官,
我要让我苏家,成为谁也不敢小觑的存在。抱着这个信念,我变了。我变得比男人还狠。
冲锋,我永远在第一个。杀敌,我永远杀得最多。别人不敢接的任务,我接。
别人不敢打的硬仗,我打。我身上添了无数的伤疤,最重的一次,
一支箭矢离我的心脏只差半寸。军医都说我没救了,可我在昏迷了三天三夜后,
硬是又睁开了眼睛。所有人都说,苏烈这个人,命硬,心更狠。我用三年的时间,
用无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换来了百夫长的职位。我手下管着一百号兄弟,
每个月有十两银子的军饷。除了留下一点生活所需,剩下的我全都寄回了家。
我想象着爹娘收到银子时欣慰的笑容,想象着哥哥可以用这些钱买更多珍贵的书籍,
请更好的大夫。我甚至开始幻想,等战争结束,我脱下这身军装,恢复女儿身。
或许朝廷会念在我的功劳上,不对我们家降罪。到那时,哥哥应该已经高中,
我们家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家了。我就求爹娘,给我找个普通人家嫁了,
安安稳稳地过完下半辈子。每当想到这里,刀口舔血的日子,似乎也多了几分甜意。我以为,
这样的日子会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直到张三的到来。张三是我们同乡,
比我晚一年被征召入伍。他被分配到了别的营,我们很少能见到。这次打了胜仗,
我们营和他们营一起负责押送战俘。休息的时候,他凑了过来,递给我一个水囊。“苏头儿,
喝口水。你刚才真猛,一个人干掉一个百夫长!”他脸上满是崇拜。我点点头,接过水囊。
他挠了挠头,有些不好意思地问:“苏头儿,我听口音,你也是咱们临江城的人吧?
”我心中一凛,含糊地“嗯”了一声。“哎呀,那可真是太巧了!”张三兴奋起来,
“说不定咱们还认识呢!我家就住城南,你家呢?”“城北。”我言简意赅,不想多谈。
“城北啊……”张三想了想,“苏头儿你姓苏,城北的苏家……我想起来了!
是不是那个出了个神童秀才的苏家?叫苏明章的?”我的心猛地一跳,
握着水囊的手不自觉地收紧了。“听说过。”我淡淡地回答。“何止是听说过啊!
”张三一脸羡慕,“那苏秀才可真是咱们临江城的骄傲!人长得白白净净,跟个仙人似的,
学问又好。而且啊,他命还好!”“命好?”我皱了皱眉。“是啊!”张三压低了声音,
像是在说什么秘密,“三年前征兵,本来征的是他。结果人家苏家有办法,
不知道使了什么手段,硬是让他免了兵役。听说啊,是花了大价钱,找了个替死鬼。
”我的血液,在刹那间,似乎停止了流动。替死鬼?我看着张三,
喉咙干涩得厉害:“什么……替死鬼?”“就是找个人替他来当兵呗。”张三说得理所当然,
“有钱人家都这么干。不过苏家藏得深,没人知道那个替死鬼是谁。反正啊,
苏秀才就这么留下来了。人家现在过得可滋润了!”“滋润?”我的声音有些发抖。
“那可不!”张三的语气里满是藏不住的嫉妒,“人家苏秀才,
去年就娶了咱们临江城第一美人,柳家的千金柳若雪!那嫁妆,十里红妆,
把整个临江城都给轰动了!”柳……若……雪……这个名字像一把烧红的烙铁,
狠狠地烫在了我的心上。柳若雪,我曾经最好的闺中密友。我们一起长大,无话不谈。
我曾偷偷告诉她,我心悦我们书院的夫子。她也曾娇羞地对我说,
她觉得我哥哥是全天下最好的男子。我还曾笑着答应她,等将来哥哥高中,
我就求爹娘去柳家提亲,让她做我的嫂子。原来,她真的做了我的嫂子。
在我代替她心心念念的男人,在北境的冰天雪地里,用命去搏一个未来的时候。“而且啊,
”张三还在喋喋不休,“苏家这两年不知道走了什么运,发了大财。
在城里又是买地又是盖房,听说还给苏秀才捐了个官,现在人家是正儿八经的官老爷了!
前两个月,他媳妇还给他生了个大胖小子!啧啧,真是人生赢家啊!”我感觉不到冷,
也感觉不到疼。我只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我身体里,碎了。碎得彻彻底底,
连一片完整的都找不到了。我脑海里回响起娘撕心裂肺的哭喊:“锦儿,你哥哥要是去了,
就是要他的命啊!”回响起爹老泪纵横的哀求:“锦儿,爹对不起你,爹没用!
”回响起哥哥气若游丝的承诺:“妹妹,若有来世,
哥哥做牛做马报答你……”好一个体弱多病!好一个全家的希望!好一个做牛做马的报答!
原来,从头到尾,我才是那个最大的笑话。我不是苏家的英雄,我只是苏家花钱都懒得花,
直接推出去的……替死鬼。他们用我的命,换来了我哥哥的锦绣前程,娶妻生子,官运亨通。
他们用我从死人堆里刨出来的军饷,在家里盖新房,买新地,过着富足安逸的生活。而我呢?
我在这里,人不人鬼不鬼地活着。我身上这十几道深可见骨的伤疤,
我每天晚上都会被噩梦惊醒的恐惧,
我为了隐藏身份所承受的所有非人的折磨……在他们眼里,这一切,是不是都理所应当?
因为我只是个女儿。女儿,就是用来牺牲的。“苏头儿?苏头儿?你怎么了?脸怎么这么白?
”张三的声音将我拉回现实。我看着他,忽然笑了。那笑容,一定比这北境的寒风还要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