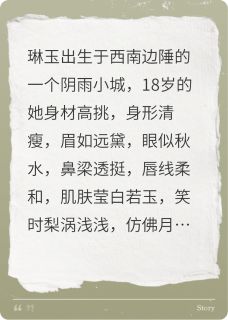琳玉出生于西南边陲的一个阴雨小城,18岁的她身材高挑,身形清瘦,眉如远黛,
眼似秋水,鼻梁透挺,唇线柔和,肌肤莹白若玉,笑时梨涡浅浅,仿佛月光下初绽的昙花,
清丽中带着几分不染尘埃的纯净。在人大图书馆三楼靠窗的位置,
琳玉第三次捡起掉在地上的笔时,终于抬头瞪了眼斜前方的男生。江逾白正假装翻书,
指缝却漏出半张脸,见她看过来,立刻把书竖得笔直,耳根却红了。琳玉忍不住弯了弯嘴角。
作为连续多年霸占光荣榜首位的校花,递情书的、堵走廊的男生她见得多了,
却第一次遇见这样的——每天雷打不动坐在她斜前方,不说话,不递东西,
就安安静静地看书,偶尔被她抓包偷看,会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似的立刻弹回去。
那天她抱着一摞厚重的专业书,在楼梯转角差点摔倒,是江逾白冲过来稳稳托住了书脊。
他手掌很热,指尖擦过她的手背时,两人都顿了顿。“谢谢。”她抬头,才发现他很高,
白T恤洗得有些发白,眼镜片后的眼睛亮得惊人。“不、不客气。”他说话有点结巴,
放下书就想走,却被她叫住。“你是不是……经常在三楼看书?”他猛地回头,
像是没想到她会主动搭话,点了点头,耳朵又红了。后来他们开始一起占座。
琳玉发现江逾白不像看起来那么木讷,他解物理题时手指翻飞,讲起宇宙星系时眼睛里有光,
会在她熬夜赶论文时默默递来热牛奶,也会在她被篮球队长堵着告白时,假装路过,
轻轻喊她:“琳玉,老师找你。”篮球赛决赛那天,琳玉被朋友拉去看。江逾白是替补,
穿着印着号码的球衣坐在场边,和平时安安静静的样子判若两人。中场休息时,
他突然朝观众席望过来,目光精准地落在她身上,然后红着脸,从口袋里摸出颗大白兔奶糖,
笨拙地朝她挥了挥。全场都在欢呼,没人注意到角落里的这一幕。
琳玉却觉得心脏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下,砰砰直跳。毕业那天,大家在校门口互相拥抱告别。
江逾白站在人群外,手里捏着个信封,几次想走过来,都被喧闹的人潮挡了回去。
琳玉主动走到他面前:“江逾白,你是不是有话想跟我说?”他愣了愣,把信封塞给她,
转身就跑,跑了两步又停下,背对着她喊:“我、我考去你填的城市了!”信封里没有情书,
只有一沓厚厚的便利贴。
在图书馆随手写的便签——算错的公式、突然冒出来的灵感、甚至是抱怨天气太热的碎碎念,
不知被他什么时候收了去,每张后面都补了一行小字。最后一张便利贴上,
她画了只歪歪扭扭的兔子,旁边是他的字迹:“这只兔子,能不能允许我追?”琳玉抬头时,
夕阳正落在江逾白身上,他还站在原地,紧张得像等待宣判的学生。她忽然笑出声,
朝他挥了挥手里的便利贴:“不用追啦,我在这儿等你很久了。”风穿过人群,
掀起她的裙摆,也吹动了少年终于敢直视过来的、盛满星光的眼睛。原来有些喜欢,
从不需要轰轰烈烈,就像图书馆的阳光,悄无声息,却早已铺满了整个青春。
琳玉发现江逾白的微信头像暗下去时,办公室的时钟刚跳过凌晨一点。
她面前的电脑屏幕还亮着,PPT里的方案改到第三十七版,**在血液里失效,
只剩下太阳穴突突的疼。手机震了震,是江逾白发来的:“还没忙完?我炖了汤,
放保温箱里了。”琳玉盯着那行字发了会儿呆。三个月前,他们还挤在出租屋的小沙发上,
分享同一份外卖,吐槽老板画的饼比月亮还圆。那时江逾白刚进研究所,
她在广告公司做助理,下班路上会绕去买串糖葫芦,你一口我一口,把晚风都吃得甜丝丝的。
变化是从琳玉接下那个美妆项目开始的。客户要求三天出全案,她连续熬了两个通宵,
回家时江逾白已经去上班,保温盒里的粥结了层皮。有天凌晨她终于拖着疲惫的身子到家,
推开门,看见江逾白坐在黑暗里,客厅的灯被他按得只剩盏小夜灯。
“你到底还要忙到什么时候?”他的声音有点哑,“上周说好去看的电影,票都过期了。
”琳玉脱高跟鞋的动作顿了顿。她想解释项目有多重要,解释这是她转正后的第一个大单子,
可话到嘴边,只剩句没力气的“对不起”。那天晚上,他们背对着背睡,中间隔着的空隙,
像突然裂开的河。这天,客户公司的项目总监送琳玉到楼下,绅士地替她开车门。
这一幕恰好被来接她的江逾白看见。他没说话,只是攥着方向盘的手青筋直跳,
一路沉默地开回家。“他只是送我回来。”琳玉试图解释。“是吗?”江逾白扯了扯嘴角,
“你们部门团建,他为什么单独送你?琳玉,你现在接触的人,和以前不一样了。
”琳玉忽然觉得很累。她想起大学时,江逾白在图书馆替她占座,
会细心地在她常喝的矿泉水瓶上贴张小纸条,写着“少喝冰的”。那时他看她的眼神,
满是纯粹的欢喜,从不会有这样带着刺的怀疑。“江逾白,”她声音发颤,
“你觉得我变成什么样了?”“我不知道。”他别过脸,“我只知道,
你现在聊的KPI、转化率,我听不懂。你加班的深夜,我守着空房子,也等不到你。
”那天他们吵到最后,江逾白摔门去了书房。琳玉坐在空荡荡的客厅,
看着茶几上那本他们大学时一起做的相册——毕业照里,她穿着学士服,江逾白站在旁边,
手里举着颗大白兔奶糖,笑得像个傻子。她忽然想起项目启动会上,
总监拍着她的肩说:“小玉,这个项目做好了,年底就能升主管。”那时她心里雀跃,
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江逾白。可后来的忙碌里,她连告诉他的时间都没有。凌晨三点,
琳玉终于改完方案。她走到书房门口,看见江逾白趴在桌上睡着了,手边摊着他的实验报告,
旁边放着她之前随口说想吃的草莓,已经洗干净,颗颗饱满。她轻轻走过去,替他盖上毯子。
月光从窗帘缝里钻进来,落在他眼下的乌青上——她才想起,他最近也在赶一个重要的实验,
常常在实验室待到半夜。第二天早上,琳玉没去公司。她把江逾白叫醒,
拉着他去了他们大学旁的那条小吃街。还是那家麻辣烫店,老板笑着问:“还是老样子?
微辣,多放醋?”琳玉点头,转头看江逾白。他眼眶有点红,低声说:“对不起,
昨天我不该怀疑你。”“我也有错。”琳玉搅着碗里的粉丝,“我太想做好工作,
把你忽略了。其实每次加班到深夜,看见你发的消息,我都特别想立刻回家。
”江逾白握住她的手,指尖带着实验室消毒水的味道,却很暖:“我也该理解你。
你不是变了,是在往前走。只是我……有点怕追不上。”“傻瓜。”琳玉笑起来,
像大学时那样,捏了捏他的脸,“我们可以一起走啊。你教我看你的实验数据,
我跟你说我的客户有多难缠,好不好?”麻辣烫冒着热气,把两人的眼镜片都熏得模糊。
远处传来学校的下课铃,像极了他们曾经一起听过的无数个午后。后来,
琳玉的方案顺利通过,庆功宴上她提前离场,江逾白在楼下等她,手里提着刚买的糖葫芦。
琳玉的名字出现在总监晋升名单上那天,办公室的打印机刚好卡纸。她蹲在地上拆硒鼓,
高跟鞋跟陷进地毯的纹路里,身后忽然传来一声低沉的笑。“需要帮忙吗?
”顾衍站在逆光里,西装袖口挽到小臂,露出的腕表在日光灯下泛着冷光。
他是集团空降的副总裁,也是这次晋升评审的终级决策人。琳玉站起身时,
闻到他身上清冽的雪松味,和江逾白身上常年的皂角香截然不同。“谢谢顾总,
我自己来就好。”她指尖还沾着墨粉,下意识地往白衬衫后摆蹭了蹭。
顾衍的目光落在她泛红的耳尖上,没说话,只是弯腰拾起她掉在地上的工牌。
照片上的琳玉还是刚入职时的样子,扎着高马尾,笑起来露出两颗小虎牙,
和此刻穿着修身西装、眼神锐利的她判若两人。“三年从助理做到总监,
”他把工牌别回她领口,指尖有意无意擦过她的锁骨,“琳玉,你比简历上写的更有意思。
”琳玉往后退了半步,避开那道带着压迫感的视线。她想起早上出门时,
江逾白在煎蛋锅前跟她挥手:“晚上庆祝,我订了那家你爱吃的日料。
”那时阳光正落在他发梢,暖得像他们合租屋里那盏旧台灯。
升职后的第一个项目就由顾衍亲自牵头。加班成了常态,顾衍的车总是准时等在公司楼下。
他从不开收音机,车厢里只有两人浅淡的呼吸声,琳玉盯着窗外掠过的霓虹,
总想起江逾白骑着电动车带她穿过晚高峰的样子,风里都是烤红薯的甜香。
“江逾白又来接你?”一次加班到深夜,顾衍忽然开口,
目光扫过楼下那个裹着厚外套的身影。江逾白手里捧着个保温杯,在寒风里跺着脚,
像株倔强的冬青。琳玉没应声,拉开车门时被顾衍抓住手腕。他的掌心温热,
力道却不容抗拒:“琳玉,你该站在更高的地方。”那晚江逾白递过来的热汤还冒着热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