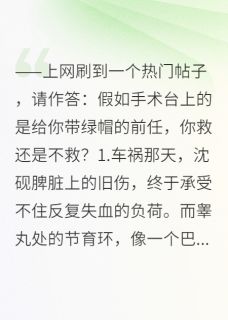——上网刷到一个热门帖子,请作答:假如手术台上的是给你带绿帽的前任,你救还是不救?
1.车祸那天,沈砚脾脏上的旧伤,终于承受不住反复失血的负荷。而睾丸处的节育环,
像一个巴掌,扇的我头脑蒙蒙的,撕开了最后的伪装。抢救室里,
他意识模糊时喊的“小糖果”,不是林向晚,而是林见棠。我是林见棠,
现在是抢救沈砚的医生,而我的妹妹,是林向晚。至于沈砚,是我的前男友,
我妹妹的未婚夫。她想起沈砚当时信誓旦旦的承诺,“我给自己盖下了小糖果的戳,
把我赔给小糖果一辈子。”当时的他,眉眼含笑,仿佛就是一辈子。可他忘了,糖果会融化,
血会凝固,谎言会氧化成锈。凌晨零点零一分,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在耳膜里炸成四拍。
E-A-D-G,和当年医学院解剖室那架跑调的钢琴同一个调性。
......2.2020年暮春,下午4:20,实验楼303。
百叶窗把阳光切成手术刀片,一条一条落在松木固定板上,像碘伏泡过的琥珀。我,研0,
第一次穿白大褂,下摆拖地。沈砚,研2,传说中“用手术刀削苹果皮都不会断”的男人。
实验对象:一只2.3kg新西兰白兔,耳缘静脉比我的未来都清晰。
沈砚的右手握刀,左手把兔耳往后梳——那动作像在给他家布偶猫顺毛。“别怕,很快。
”口罩闷住嗓音,薄荷牙膏味顺着缝隙飘出来。我捏着镊子,棉球在碘伏里“咚”一声。
下一秒,刀片划开颈部皮肤,兔子突然暴起。塑料固定带“咔”——断了。
颈静脉像被拉满的弓,“啪”地弹在刀口上。血喷出来,细密,赤红,
逆光像一罐打翻的朱砂星屑。我愣在原地。沈砚已经把我整个人按进怀里。左臂横在我眼前,
袖口溅满血点,像雪地里提前开的早梅。“别看。”他的心跳透过两层薄薄的布料,
直接砸在我鼓膜:咚、咚、咚。世界静音,只剩三拍心跳,
和窗外钢琴社在练《梦中的婚礼》。我抬头,看见他金丝眼镜边缘被光割出细碎虹彩。
睫毛在镜片后投下一小片阴影,像停了一只黑蝶。他抬手,无菌手套的指腹蹭过我眼尾,
擦掉那粒血珠。滑石粉蹭在皮肤上,微凉,发痒。“吓傻了?”他笑,牙齿白得晃眼,
像把春天嚼碎后吐出的第一缕风。然后,声音低下来,像在宣布实验结论:“小糖果,
以后我们每天都这样并肩,好不好?”我点头,鼻尖撞到他胸口,
闻到淡淡的薰衣草柔顺剂味。那一刻,我以为“以后”是一条无限延伸的光带。后来才明白,
那其实是他提前写好的实验步骤,而我,不在计划之内。
......3.护士报病情的声音像除颤仪放电——“患者沈砚,28岁,车祸,
血压60/40,心率150,疑脾破裂!”我手指一抖,
蓝色橡皮筋“啪”地弹在腕骨,勒出一道苍白的月蚀。下一秒,平车撞门进来。白炽灯底,
沈砚半敞手术衣,锁骨窝里那粒青柠色糖果纹身一闪——三年过去,糖纸依旧鲜亮,
像把凝固的汽水。......4.记忆瞬间倒退。器材室,灯管滋啦作响。
我把他按在门板,消毒棉片贴上锁骨,冰得他打了一个激灵。“别怕,是我送你的生日礼物。
”纹身枪“嗒嗒嗒”落下,他额头抵着我,呼吸混着草莓汽水味。“小糖果专属,
”少年声音嚣张又认真,“以后谁碰我,就给她看——我早被预定了。”5.如今,
那颗糖被唇角涌出的血珠一分为二:一半倔强地亮着;一半被血糊掉,再也看不清。
像极了我们——**干净净,什么标记都没留;他却把一句玩笑话刻进皮肤,再用一生去疼。
6.那天,实验楼外,老教授的小女儿在学钢琴。那天她弹的正是《梦中的婚礼》。
旋律顺着走廊瓷砖的缝隙溜进来,像一条透明的丝线,把我们一圈一圈缠住。
沈砚忽然放下持针钳,摘下手套。“听——”他闭眼,指尖在空气中轻敲节拍。
阳光落在他睫毛上,金色绒毛随着呼吸起伏。他轻声数:“一小节四拍,
第一拍永远落在心上。”我鬼使神差地接下去:“G大调,右手八度,左手琶音。”他睁眼,
眸子里盛着整个夏天的树影:“对,就像我们。”“一个主刀,一个辅助,缺一拍都会乱。
”老师从门外经过,打趣:“医学生最浪漫的爱情,就该像你们这样。”沈砚笑得肩膀轻颤,
一把搂过我的肩。白大褂袖口蹭在一起,发出簌簌的摩擦声。“老师,我和我家小糖果,
天生一对!”他的声音清亮,像刚开启的苏打气泡,一路噼啪噼啪地炸进我耳蜗深处。
......7.带沈砚见家长那天是小年。旧城区不许放炮,空气里却全是硝糖的焦甜。
我提着两袋稻香村点心,沈砚抱着一箱车厘子,并肩站在四合院门口。
门楣上父亲手写的春联墨迹未干:“杏林春暖千秋盛,橘井泉香万世传。
”横批是“悬壶济世”,笔锋利落,像一把柳叶刀。沈砚今天穿了件墨黑羊绒大衣,
领口别着一枚极细的银杏领针——那是我去年拿奖学金给他买的。
他呼出的白气在冷空里结成小霜,又被风吹碎。我伸手替他理了理围巾,指尖碰到他喉结,
他下意识滚动,像吞咽下一口紧张。“怕?”“怕。”他老实承认,
“怕你爸把脉把出我心律不齐。”我笑,刚想安慰,门吱呀开了。母亲系着枣红围裙,
袖口沾着面粉,像雪里落梅。她先看见我,再看见沈砚,眼睛弯成月牙:“小沈吧?快进来,
手炉刚添炭。”父亲端坐在藤椅,膝头摊一本《伤寒论》,金丝镜后的目光从书沿上方探出,
像X光。沈砚立刻把箱子举到胸前,声音绷得笔直:“伯父,车厘子,智利空运,低温冷链。
”父亲“嗯”了一声,指关节在桌面轻敲三下——那是他诊脉时计算心率的习惯。
“哒哒哒——”一串脚步声从楼上滚下来。林向晚顶着玫瑰棕卷发,
草莓睡衣的毛边蹭过扶手,发出静电的噼啪。她停在最后一级台阶,歪头冲沈砚笑,
声音脆生生:“姐夫?”沈砚耳根瞬间红透,像被辣椒水呛了。
我瞥见他锁骨窝里那粒糖果纹身,青柠色,边缘已随时间褪成雾蓝。林向晚顺着我的视线,
也看见了那粒糖果。她眼睛亮了一下,像小孩子看见橱窗里最后一颗糖——不是喜欢,
是盘算。八仙桌摆得满满当当:母亲做的糖醋里脊泛着琥珀光,
父亲炖的当归黄芪鸡在砂锅里咕嘟咕嘟。我坐沈砚左边,林向晚坐他正对面。
她拿筷子戳着米饭,忽然开口:“姐夫,听说你Rh阴性?稀有血型啊。
”沈砚正给父亲倒花雕,手腕一抖,酒液差点洒出。父亲抬眼:“哦?那和我们家晚晚一样。
”我夹了一筷子里脊到沈砚碗里,轻声:“先吃饭,血型待会儿聊。”林向晚撅嘴,
筷子尖在桌面画圈,一圈又一圈,像在计算血量。饭后,母亲让我去厨房切橙子。
我蹲在碗柜前,听见客厅传来棋子落盘的清脆声——父亲拉着沈砚下围棋。
身后门被轻轻带上。林向晚闪进来,草莓睡衣的毛边蹭过我的小腿,痒得像羽毛。“姐,
”她压低声音,却压不住兴奋,“他真的好帅啊,像之前见过的一个大哥哥。
”我皱眉:“怎么了?”她咬着糖葫芦的竹签,声音含糊:“我不是说过了吗?之前,
我还不在这里的时候......”我心里“咯噔”一下,刀尖在橙皮上划歪,
橙汁溅到袖口,像一滴突兀的血。夜里十一点,客人散了。父亲送沈砚到门口,
塞给他一盒自制固元膏:“熬夜伤身,配热牛奶。”沈砚双手接过,
像接一份郑重其事的医嘱。我送他去巷口打车。月光落在青石板路上,像撒了一层碎盐。
他忽然停住,转身把我按进怀里,下巴抵着我头顶:“你爸好像……喜欢我。
”声音里带着不确定的雀跃。我把脸埋进他围巾,闻到淡淡的檀香皂味:“嗯,我妈也喜欢。
”顿了顿,我补了一句,“晚晚也是。”他笑,胸腔震动:“晚晚?她叫我姐夫叫得挺顺口。
”我们都没发现,厨房那扇门后,妹妹眼里闪过的光,不是崇拜,是猎人看见猎物的光。
那天之后,沈砚成了我家的常客。父亲教他写春联,母亲教他炖药膳。
林向晚每次都会坐在他旁边,托着腮,数他锁骨上的糖果有几条纹路。直到很久以后,
我才知道——她数的从来不是纹路,是血型的刻度。而那个冬夜的小巷,
月光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影子尽头,沈砚牵着我的手,掌心滚烫。我们都不知道,
就在我们身后,另一道影子悄悄跟了出来——草莓睡衣的裙摆扫过青石板,
像一片不肯落地的糖霜。......8.“林见棠!发什么呆!”主任的吼声像电击,
我瞬间回神。无影灯下,沈砚的脸近乎透明——静脉蓝得像泡皱的地图。
睫毛上嵌着挡风玻璃碎碴,冷光折射,把急救室顶灯拆成七色,落在他青灰的眼睑。
血先滑到内眦,停0.1秒,像在犹豫要不要蒸发。随后加速,压弯睑缘绒毛,
又倔强弹起。下一瞬,血滴坠在我虎口——烫。不是37℃,是熔铅。
皮肤0.1秒内全部毛孔起立,像草原溅火星。烫意沿桡骨狂奔,在神经末梢炸开,
我指骨一抖。接着是湿。血填进掌纹最浅那条生命线,洪水灌进干涸河床。黏稠,氧化,
暗红。像把三年裂缝缝合,又瞬间崩断。而更深的,是记忆的温度。
......9.”林医生,患者无脉电活动!“护士把除颤仪推到我手边。
我摸到电极板的金属边缘,突然想起来:大二那年做CPR考核,
沈砚故意在我耳边吹气:“下次实战,我给你当模型。”现在他真的躺成模型,胸骨柄凹陷,
像被上帝踩了一脚。我俯身按压。
“01、02、03……”心里却在想:“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的呢……”10.“咔。
”胸骨断了。断裂声像那年我摔碎他送的听诊器,塑料壳在水泥地炸开的三重奏。
第一重:”林向晚怀孕了,孩子是我的。“第二重:”但她是**妹。
“第三重:”我需要给她献血,熊猫血,只有我能救她。“我当时笑了,
指着化验单:”沈砚,你很强壮吗?演什么骑士?期末月我们一起通的宵,
身体素质你应该自己清楚。“他沉默的样子像现在——瞳孔散大,对光反射消失。
11.“静推——肾上腺素1mg!”我吼得比除颤器还响,嗓子当场裂成两瓣,
一口血涌进口罩,瞬间积成温热的铁锈小泊。没空摘。我整个人折叠着压上沈砚胸口,
左手晶体液500ml狂灌,右手一针闪电顺管而下,直插心室。
俯耳——胸骨下传来揉皱锡箔的沙沙声,室颤波细成散沙,死活聚不成一次收缩。
心电监护绿得像毒牙,锯齿一路啃屏。时间被按下1.5倍速。
我数秒:1、2、3——血氧62→58,血压60/40掉到46/30。
再一针。针头拔出时,带出一条血线,溅在我眼睫,世界瞬间红滤镜。“再来!
”我咬碎口罩里的血,声音闷成爆破音。沈砚的瞳孔在灯下缩成针尖,像在说:“林见棠,
欠你的,这次一次还清。”我回他一个更狠的按压——胸骨下陷5cm,回弹那瞬,
我把自己的心跳也按了进去。12.那一瞬,记忆被锯齿钩住,猛地倒回两年前。
——深夜图书馆。暖黄台灯把《内科学》摊开的扉页照得像一片薄脆的蜂蜜。
我趴在上面打瞌睡,口水洇湿了“心律失常”四个字。沈砚握着0.38mm的黑色签字笔,
偷偷在空白处画心电图。不是病理的锯齿,而是圆润的窦性P-QRS-T,一笔一划,
像在描摹最柔软的摇篮曲。最后一格,他画了一个小小的糖果贴纸,旁边写:“小糖果,
以后我们生个女儿,叫沈呦呦。”字迹细而倾斜,像晚风拂过柳叶。我醒来时,
那行墨迹还没干透,指尖一碰就晕开淡蓝色的尾迹,像心跳漏掉的一拍。13.如今,
同样的锯齿出现在屏幕上,却不再温柔。每一次细小的震颤,
都像那支笔在我心内膜上重重划下一刀。尖齿深入,把未出生的“沈呦呦”三个字撕成碎片。
碎片太轻,飘进肺循环,又从我的呼吸里呛出来,混在口罩的血腥里,变成一口滚烫的雾。
我听见自己的心跳隔着两层手术衣与他共振——咚、咚、咚。可他的胸腔只会以沙沙的碎响,
像冬天踩裂薄冰。那声音越来越大,大到整个手术室都变成一只空洞的鼓。
鼓面是我绷紧的耳膜,鼓槌是那根不断往下坠的肾上腺素针头。“再来1毫克!”我喊。
声音却碎成粉末,落在锯齿上,被吞得一点不剩。屏幕上的绿线依旧高高低低,像一把钝锯,
来回拉扯。每拉一次,就把“沈呦呦”往未来推远一厘米,也把我的心往过去拉回一厘米。
最后,锯齿陡然升高——又陡然跌落。一条平直的绿线横亘在屏幕上,
像那年他画完心电图后,在末尾轻轻拉长的尾笔。只是这一次,没有糖果,没有名字,
只有无限延长的空白,和空白里,我一声比一声更哑的——“再推1毫克……”“血库告急!
患者AB型,库存只剩3U!”护士的声音在头顶炸开。AB型。哈。我扯开他病号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