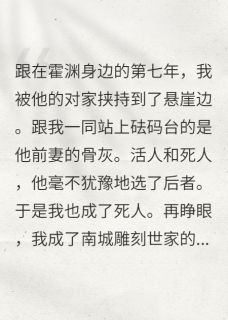跟在霍渊身边的第七年,我被他的对家挟持到了悬崖边。
跟我一同站上砝码台的是他前妻的骨灰。活人和死人,他毫不犹豫地选了后者。
于是我也成了死人。再睁眼,我成了南城雕刻世家的掌家**。
走马上任第一单就遇上了霍渊。要给他早逝的夫人刻一座等量金身。
1我望着那张自己的照片说不出话来。来人话语很客气,却又带着不容拒绝的强势。
「早就听闻骆**技艺精湛,甚至远胜于令尊,我家少夫人的事还望**多多上心。」
槽点太多,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吐槽。斟酌半天,我问:「你确定这是你家少夫人?」
霍九英俊的面上一冷,眼睛泛红,「骆**这是什么意思,我家少夫人是谁,
我难道还会弄错吗!」也是,霍九是霍家的大执事,霍渊最亲的那条狗,四分之一个当家人。
谁是少夫人他怎么会不清楚。我望着身侧神色痛苦的霍九,差点要笑出声。
又想到他那把百发百中的枪,生生憋了下去。不怪我,毕竟就在一个月前。
在我还顶着照片上那张脸时,他满眼厌恶,「我家少夫人永远只会是白恩姐,
你算个什么东西!」我怒极反笑,「我算你爹。」当初是我背着濒死的他走出了雨林,
再造之恩,可不算他爹吗?可是救他一条命,终究是比不上白恩的一个烂馒头。
让他踏踏实实护了人家十八年。想来也是,霍家人谁不是如此。我为他们剖心又剖肝,
都比不上白恩微微一笑。所以在那万丈的悬崖边,人人都紧张,
生怕白恩的骨灰有一点散到风中去。根本没人在乎,我在悬崖下摔了个稀巴烂。我敛起笑,
认真说,「没有啦,我只是想在确认一下,毕竟弄错了就也不灵了。」我贴心道,
「要不霍先生再回去确认一下。」也许是霍九发癫了呢,背着霍渊偷偷出来的。
要是霍渊发怒了,我还能逃过一劫。曾经有合作商见霍渊牵着我,凑上去喊了我一声霍太太。
差点被霍渊废了全家。用他的话来说,我算个什么东西?是啊,我算个什么东西。
我怀着这个疑问死了过去,又活了过来。再睁眼时,有人回答了我这个问题。管家热泪盈眶,
「你是我们南城雕刻世家的接班人啊,**!」什么接班人?雕刻?
我不敢置信地指了指自己,「那我也会雕刻吗?」管家竖起了大拇指,
「**的雕刻技术举世无双,堪称大家!」我眼前一黑。曾经我心血来潮,
为霍渊用萝卜雕了个百鸟朝凤。他执筷半天,吐出一句,「阿桑这技艺不错,
这鸭子戏水雕得微妙。」一旁的霍九嗤笑,「东施效颦。」我和霍渊的笑都淡了下来。
我常听下人们说,白恩最是手巧,跟天上的仙女似的。其实何必听他们说。
霍渊抚烂了那条方巾,尽管历经多年,上面的刺绣针脚依旧栩栩如生。霍九沉思半天,
点了点头,「是我考虑不周了。」我松了一口气,差点就被这王八蛋连累了。
忽然又听见霍九说,「也是,材料纯度和尺寸还得再问问少爷,不能马虎!」他冲我一鞠躬,
「多谢骆**提点了!明日再来拜访。」我无语至极。这是材料尺寸的问题吗?
这是当事人的问题!但霍九没给我机会,转身离开了。他一走,我就哭丧着脸对管家说,
「杨叔,我突然不会雕刻了。」杨叔虎躯一震,「那咋办,我都收了霍家定金了。」
我也虎躯一震。霍家行商历来有规律,谁要敢半道撂担子,赔的可不是钱这么简单了。
杨叔急得团团转,最后一拍大腿,「要不你去求求三爷?」三爷?哪个三爷,
不会是我认识的那个三爷吧?2眼前的人裹在一身绸缎中,檀香袅袅,
他美得像魏晋仙人一般。只不过这也太瘦了。比上次见面瘦太多了。我没来的及敲锣打鼓,
就被人摁着头喊了一声「三叔。」啥玩意?杨叔痛哭流涕,说上天不公,
骆家就剩我和骆长檩两个血脉了。结果一个在病床上歪歪斜斜,一个忘了当家技艺,
这可怎么活!我心里五味杂陈,曾经的死对头病的要死了,自己却要给他哭丧摔盆,
这叫什么事!骆长檩眼皮都不抬,「帮不了。」嘿,真是没有一点集体意识。我刚要说话,
杨叔就冲上前去,一个滑跪,边哭诉边掏出我刚雕得那团垃圾。骆长檩终于抬眼看我,
我心虚地摸着鼻子避开他的视线。他冷笑一声,「大哥这么多年,就教出你这么个…玩意。」
「可是,这又跟我有什么关系呢。」骆长檩是骆家养子,能力却比骆家几个兄弟还要出众。
骆老爷子一视同仁,甚至一度想将他列为继承人。骆家几位少爷自然不服,
又没有什么能力扳倒他。心一狠,就给骆长凛投了毒。自此他缠绵于病榻。
所以他留我一条命,可以说的上是仁慈了。杨叔长叹一声,都是孽,怨不得别人。
「那我去求求霍家,拒了这一单。」躺椅上的人哼笑一声,像终于来了点精神,
「霍渊那狗玩意终于死了,要刻碑了?那我乐意至极。」我&杨叔:「…」骆家三爷,
人称南城双绝。颜绝,嘴更绝。一开口就要毒死人。第一次见面,就是因为他这张嘴,
跟我结下了冤仇。杨叔摇摇头,「听说要给他们早逝的少夫人,打一座金身。」
骆长檩更来劲,「呵,这么爱,怎么不跟着白恩一起死,真是可怕得很。」
「不是先前那位白夫人,是…上月没了那位,听说叫桑榆。」
哗啦一声骆长檩从躺椅上翻了下来。他青丝散漫,眼红的像一只妖物。「哈…嗬嗬!」
他的笑混着血咳,「太好笑了。」杨叔急得要死,「三爷!三爷!你别笑了。」
我害怕地缩到一边。妈呀,几月不见,骆长檩越来越像神经病了。良久,他抬起头来,
「告诉霍渊,这单我接了。」我松了一口气,正要谢他,又见他眼刀瞟了过来。「小侄女,
你就负责给我打下手吧。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有多废物,」「你!」我正要开口,
又听见他冷飕飕地说,「要是太废物,这手就别要了吧。」行,他是大佬,我是牛马,
不敢有怨言。3第二日,霍家送来了更为详细的制定图。骆长檩没放人进门,
只要了那张真人照片。照片中,曾经的我挨着霍渊笑得没心没肺。骆长檩死死地盯着。
过了好久,他毫不犹豫地一撕,霍渊那张俊脸就成了碎片。「无关紧要的人在上面干嘛。」
霍九正要发作,却被骆长檩堵了回去,「白眼狼,你想清楚,我这小侄女手坏了,
能给你们刻的只有我了。」霍九生生憋了回去,拱手道「还望三爷多上心。」
说罢又狠狠瞪了我一眼。敲,这小王八蛋。我跟着骆长檩气冲冲地回屋,
为他铺好了一桌工具。他却久久不动。握着照片的手在微微颤抖。我悄**开溜,
「三叔累了,要不今天就这样吧。」他没说话。我作势拉开了门,
却听见他冒出一句「哈巴狗。」我脚一滑,差点摔倒。不是,骆长檩认出我来了?
回头却见他对着我那张照片冷笑。骆长檩跟我不对付,就是因为他叫我哈巴狗。我气不过,
连夜带刀撬了他的窗。却意外撞见出浴的他。长腿蜂腰,又白又…大,哎不是,又白又高。
我下意识地吹了个口哨。他气得浑身发抖,眼红脸也红。不过骆三爷到底是骆三爷。
他拉好衣裳,又客气地请我坐下来喝一杯。他人长得美,声音也如冷玉击泉一般动听。
我就被这样哄着,吃了他一杯又一杯好茶,然后迷迷糊糊忘记了自己要来干啥。直到告辞时,
骆长檩才邪恶一笑,「拜拜,小哈巴狗。」我猛然惊醒,四处找刀。可刀早就被他握在手里,
说什么都不肯还我。想起过往,我垂眸苦笑。谁能想到,再次见他,我已是换了一副躯壳。
骆长檩握着那张照片,话说得狠极了。说我咎由自取,误入歧途。真是跟狗一般。
我默不作声地听着他骂。心里在下一场大雨。是啊,别人都看得清,
我自己却傻傻纠缠了七年。七年,足够梧桐落了又盛,足够稚子长成大人。却没能让霍渊,
爱上我。耳边的怒骂一直不绝,我垂眸走了出去。入秋的南城风雨兼加,
雨水渐起在落地窗上。让我听不到怒骂里的哽咽。4早早的我就被杨叔拽起了床。
等我揉着眼睛走进工作坊时。一身唐装的骆长檩早就端坐案前。见我时,他笑哼,
「小侄女来得真早,下次不如吃了晚餐再过来吧。」我:「……」面对这尊大佛,
我不想再起事端。连忙陪着笑脸凑上前去,「三叔哪里得话,要从哪部开始,
我来给您打下手。」骆长檩不语,默默拽下了身前的红布。红布下,是一尊栩栩如生的金像。
我被震在了原地。那是一尊少女像。有着山花一般灵动的眼,和春草一般倔强的眉。
嘴角泛起的笑,能让人感到无边的暖意。那亦是我,死去的桑榆。屋里只有呼吸声。许久,
霍九的哭声响起,他的喉咙里泛起苦意。他哭,他说,「小妹,哥哥想你了。」我初入霍家,
不过十九岁。二十二岁的霍九凶得像匹狼。拽着我的手,将我扔出了门外。后面我救了他,
他才梗着头,认了我做妹妹。从此护我如眼珠。可是那天悬崖上的风太大。让我认清了现实。
我再一次被他们,像垃圾一样丢出门外。霍九一哭,骆长檩就笑了,「哎呀呀,
原来白眼狼也会流眼泪。」霍九抹了把脸,沉默者示意手下人把金身往外搬。骆长檩摔了杯,
「慢着——」霍九停了下来,「三爷还有什么吩咐?」骆家金像名气响,
不仅是因为技艺精湛。更是因为从来只接亡客单。骆家的金像,能招魂。午夜梦回,
那些未说完的遗憾,那些来不及的思念,还有机会一一倾诉。「要这金像招魂啊,规矩可多。
」霍九一瞬间肃穆,「三爷请讲。」骆长檩哑着嗓子,像个修罗,「要让那霍渊啊,
像条狗一样爬过来,再一步一叩首迎回去。」「只有这样啊,才行。」**出所料,
场面不欢而散。我扶额,「三叔你干嘛放着好好的赚钱事不赚。」他凉凉地看我一眼,
「因为我有良心。」我无语,那我死得干干净净的族人算什么。他又沉吟,「因为我有良心。
」「不像有的人,当哈巴狗就算了,还没有良心。」不是这话怎么这么熟悉。
我眼皮跳了起来,小心翼翼地问,「三叔,你说我啊?」他冷笑,「你还不配。」
我:「……」行,我自讨没趣。我正要往外走,又被他拽了回来。「功课没做想跑哪里去?」
我一缩脖子,乖乖坐回案前。他眯着眼,漫不经心地说,「先做个简单的,雕朵玉兰看看吧。
」我握着刀,深吸一口气。提刀,下手。突然又被呵断,「你是左撇子?」
我看了看我拿刀的左手,摇头。「不是啊,但是总感觉左手拿刀方便一点。」案面轻晃,
骆长檩又咳了起来。良久,他直起身,「刻吧。」又漫不经意藏起染血的手帕。完蛋了,
死对头真的要嘎了。我收回视线,专心刻起玉兰来。过了一刻钟,我终于雕出了一朵,垃圾。
骆三爷眉头紧蹙,厌恶之情溢于言表。挥了挥手,想立马赶走我这晦气玩意。
我也懂事地立马溜了。6霍九等人又上了门。听说带了比原来多三倍的酬金。
杨叔看着骆长檩,「三爷,这……」喝着茶的男人不为所动,「我记得要求我已经说过了。
耳聋是他们的问题。」骆长檩让人把霍家人哄了出去。过了许久,有又人上门登访。
杨叔不情愿地打开门。门外是一袭黑衣的霍渊。他也瘦了。可毕竟是港城叱咤多年的霍大少。
气势依旧压人。他垂者眼,温和地笑笑,「我来接桑榆回家。」我的心高高地扬了起来。
我等这句话,多久了?记不清了。从崖边等到崖底。从血热等到血凉。骆长檩沉默着。
我在心里默默回答,「太晚啦。」太晚了,霍渊。世界上已经没有桑榆了。
我与霍渊相识于一场山体滑坡。他是来登山的游客,我是被抛弃的大山学子。父母要卖了我,
为十岁的弟弟买一位童养媳。他救了我。又供我上了学。他是恩人。跟在霍渊身边那几年,
我不可抑制地动了心。霍家大少俊美无双,又能力出众。可这样一位注定是欢场上的高手,
却有着一位早逝的白月光。无数人铆足劲却再也冲不尽他的心。我也一样,
只不过我更傻一点。卯了七年,卯掉了姓名。我和他关系转变在第四年。
我和他被困在一座雪山,又恰巧两人都穿了白色羽绒服。搜救机看不到。所以我割开了手腕,
用血染了一圈标记。再睁眼时,霍渊僵坐在床前。「傻子。」他说,又说了一声,「傻子。」
却又红着眼,狠狠地吻住了我。那一刻,我觉得所有拜过的菩萨都灵验了。可是就算这样,
我的生日他还是选择去墓地。我的生日和白恩的祭日是同一天。我看着霍渊远去的背影,
喃喃道「为什么?」在霍家人嘴里,我知道了他们的过去。白恩不爱霍渊。
约了情夫要一起私奔,结果出了车祸双双离世。可是就算这样,她的祭日,
却依旧是霍渊永远的凉夜。霍姝看着失魂落魄的我,笑了。她说,有的人站在那里就赢了,
什么都不用做。在崖底彻底闭上眼那刻,我才终于又记起了这句话。回过神来,
霍渊依旧立于门前。寸步不让。骆长檩也用尽耐心,「给老子滚。」霍渊的话还在继续,
「她只是闹脾气了。肯定不舍得让我等。」「她那么爱我,我一叫她,她就眼巴巴凑上前来。
」哈。真可笑。怪不得骆长檩骂我哈巴狗。真是形象。一阵刺痛涌上我的心头,我眼睛一闭,
彻底昏了过去。再醒来时,屋内灯火昏暗。身侧人的影子在墙上投出一个熟悉的轮廓。
「桑榆,你没死对不对?」7灯火下,一人骨相立挺,眉眼凌冽。是霍姝。她没看我。
隔着一层屏风,她与那金像相顾无言。良久,她才轻笑,「他们说你碎在了悬崖底,
可我不相信。」我听着她的轻语,心中思绪飘远。霍姝是霍家上不得台面的私生女。
在奉信弱肉强食的霍家,弱小的她一度是被欺凌的对象。久而久之,
人人都说霍家出了个疯女人。谁靠近就咬谁。又臭又硬跟个男人一样。
可是直到我撞见她也会在母亲的忌日偷偷哭。也会看着美丽的首饰和衣服凝神。
后来我不厌其烦地接近她。给她过生日,陪她看病,为她装扮。我只比她大三个月,
却早已把自己当成了她的姐姐。我有些难受。可下一秒,我就被她的话拉入了冰窖。她说,
「我其实挺讨厌你的,对每个人都那么好。可是再模仿白恩姐,你也不是那抹白月光,
不过是劣质的糖纸,看着夺目,实则只让人觉得腻味。」我愣在原地。
她的白恩姐给过她什么呢?不过时刚入霍家时,看着来了月经无措惊慌的霍姝,
嫌弃至极的丢下一块卫生巾。结果跟霍九的烂馒头一样,让他们心心念念这么多年。
她张了张口,像是吐出了一个藏了很久的秘密。她眼里没有愧色,只有解脱。「你不知道吧,
其实那天是你是可以活的,因为白恩姐她根本没有死。」我睁大了瞳孔,心猛然下沉。
还有比这更可笑的事情么?本来我以为自己不过是输给了一罐骨灰,原来连这骨灰都是假的。
霍姝站在那金像面前,看不清表情。只是有些遗憾地说,「可惜忘记跟你说一声谢谢。」
眼前的场景在逐渐的崩塌、变形回过神来的我逐渐变得跟那座金像一样面无表情。
我绕过了屏风。没想到室内还有别人,霍姝脸色有一秒惊慌。发现是我,又立马恢复了淡然。
她甚至没有正眼看我,「骆**,金像我就先搬走了。」我摆了摆手,语气真诚。
「可是我三叔不是说了吗,要搬着金像,得让霍渊一步一叩首才行呀。」霍姝眯起了眼,
脸上带了几分厌恶。「骆**,你久居深闺可能不知道,我没有那么好说话。」
她又转看着那金像。「都说你们骆家的金像能招魂,可我从来都不信什么因果报应。」
我浅笑着附和。「是啊,要是有报应,应该也先报在辜负者身上,
轮回的苦干嘛要被害者来尝呢?」霍姝的背影僵直了。回过头看我的眼神近乎凶恶。
我静静地与她对望「虽然我久居深闺,可我也曾听闻前年李氏那块地,
霍**拿的好像不是那么光彩?」她彻底变了脸色。霍家谁没有秘密呢?而我刚好,
知道他们所有的秘密。霍姝离开时可谓是神情狼狈。当然,她没能带走那尊金像。
我静静地打量着那金像,不愧出自骆长檩之手。她立在那里,宛如活人。
雕刻者仿佛是它的知己至交,连它最轻微的神态都能刻画。挚爱之人推我入地狱,
最后竟是死敌为我塑像。我只觉得荒唐。在我出神时,骆长檩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我身后。
「小侄女,你在想什么?」我打量着身边这个人,依旧是苍白阴俊的面孔。明明是夏天,
身上的绸衣依旧扣到了第一颗玉扣。身体上的残缺和过于阴沉的性格,让他活得压抑又无趣。
外界曾戏谑他,是装在玉壳子里的人。我突然对这个传闻中的骆三爷,
我的死对头产生了好奇。「三叔,你这一辈子有过什么**的时刻吗?」
骆长檩冷冷打量我一眼,夜风吹起他一角绸衣。他许久没说过。我摸了摸脖子,正打算开溜。
却见他不紧不慢道,「有啊。」8骆长檩转了性子,变得爱上班了。
从前基本不见于人前的他,却时不时就在公司晃悠。杨叔语气欣慰,
「咱们骆家也是好起来了。」我握着厚厚的文件报告长叹,「好的只有他骆三爷一个人吧。」
毕竟他每天就喝喝茶,浇浇花,要么就杵着他那镶钻的手杖到处溜达。话音未落,
男人眼眸一扫,「小侄女,你好像有异议?」我连忙摆手,「不敢不敢。」骆长檩哼笑一声,
「今天放你一天假,带你去个好地方。」稀里糊涂地,我就被骆长檩拐上了车。
看着车窗外飞逝的街景,无语地问,「老板就这么旷工,不怕倒闭么?」
骆长檩随意地支着额头。「没关系,反正我是个早死的,烂摊子只会是你的。」
我看着他无所谓地样子,想起曾经与他初识。他咳着血,却还不要命地往寒潭里跳。
等我费劲巴力地把他拉起来时,他也只冷冷瞪我一眼「多管闲事。」我气得要升天。
旁人戏谑又挖苦地说,「桑**真是何苦呢?可没人敢害我们大名鼎鼎的骆三爷,
人家是自己想不开呢。」那人与同伴交换了个恶意的眼光。「何况就算想开了又能怎么办?
反正也活不长。」那些恶意与眼前漫不经心的骆长檩重合。我的心中漫起一阵异样。「三叔,
生命是很宝贵的,不要咒自己。」他不在意地与我对视,却见我眼眸认真。
沉闷的夏季空气被隔绝在窗外。车里静默一片。好久,骆长檩勾起嘴角,却移开了目光。
「知道了。」我心中微微松了一口气。却又对上他似笑非笑的眼神,「小侄女管得到是宽。」
我在心里摇了摇头,都说人心易变。可这么多年,骆长檩还是那个傲娇怪。
他带我去地方在远郊。一块平平无奇的园子,一座低低矮矮的房子。
园子里种满了稀奇古怪的植物,像是有人精心打理,又像任由它们野蛮生长。才推开门,
就有四五只猫咪围上来。它们熟稔地蹭着骆长檩的裤脚,撒娇打滚。
骆长檩轻轻地推开了它们,带我走进了那座矮矮的房子。熟悉感近乎扑面而来。
墙上贴满了守护甜心的海报,柜子里塞满了柚子糖。可我使劲想了想,
我好像没有过这样的房间。到底是在哪里见过,才会觉得如此熟悉?
这座小屋看上去平平无奇,跟矜贵的骆长檩格格不入我问他,「私闯民宅不好吧?」
骆长檩修长的手指剥开一颗柚子糖,自顾自地喂到了嘴里。
那从来端方又面无表情的男人将糖咬的嘎巴响。「想什么呢?」我疑惑极了,
「那你为什么会有这样一座小园啊?」他皮笑肉不笑,「因为请了个特别不靠谱的设计师,
上当了。」这世界上还能有让骆长檩吃亏的人,我简直要好奇死了。「谁呀?」
在他目不转睛地打量中,我居然感受到了一丝心虚。看着那些装饰,我猛然想起来,
这不是我梦中的屋子吗?我从小就有一个愿望,能有一小座属于自己的屋子,
旁边要种满奇怪的植物,柜子里要有吃不完的柚子糖。不用分给弟弟的柚子糖。可是可是,
骆长檩怎么会知道!他的眼眸沉沉,有那么一瞬间,我感觉他已经看透了我皮下的灵魂。
可他什么也没说。我也没再敢开口。突然骆长檩的电话响起。那端的管家语气焦急,
「不好了三爷,霍大少今天带人上门,强硬地搬走了金像!」9回去的路上,
骆长檩将车开得飞快。我劝他,「三叔你冷静一点。」他的眼眸冷得像冰,「你会回头吗?」
「什么……」风声太大,我没听见他的话语。他手微微一怔,然后又低问道,「我是说,
要是桑榆还活着,你觉得她会不会回头?」我望着他冷峻的侧脸,心猛然跳动起来。
重生以来,我不止问过自己一次这个问题。不甘心在崖底咽气时,
我也曾幻想过他们追悔莫及的样子。凭什么,凭什么我要被放弃?
可是当再一次呼吸到新鲜的空气时,我只感觉到庆幸。活过来的那种庆幸,
只有明白了死亡的痛苦才知道。我摇了摇头。「她不会。」没有人能替死去的桑榆原谅,
就算是现在的我也不行。骆长檩轻轻扬起了嘴角。「我想也是。」「那么现在,
我们一起去替她完成一场审判吧。」闯入霍家时,身着黑衣的霍渊静静地靠着黑暗的角落。
空气中弥漫着浓厚的血腥味和香灰的味道。骆长檩嗤笑一声,「霍狗,你要不直接去死呢?
用这些上不得台面伎俩恶心谁?」此刻我才看到。霍渊垂着的手,正鲜血淋漓。他阴鹜着脸,
再也没有了人前的稳重,语气冰冷。「骆三爷,不是说你骆家塑的金像能招魂吗?
我的桑榆怎么还不回来?」他说到后面,已满是痛恨。骆长檩笑出了声,
盯着霍渊全是血丝的眼一字一句道。「有没有可能,她生生世世都不想见你这个畜生。」
骆长檩字字诛心。如果时机不对,我简直都想给他鼓个掌。可却**得霍渊拔出了枪。
「你找死!她那么爱我,怎么可能不来见我,肯定是你使了手段。」霍九在一旁红了眼。
自此那天在崖下找到桑榆残缺的尸体之后,大哥就不对劲了。起初他没有任何异样,
甚至连一丝难过都看不出来。哪怕他跟了大哥那么久,他也不免替桑榆感到心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