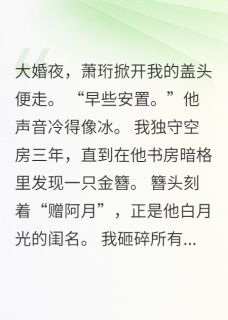大婚夜,萧珩掀开我的盖头便走。“早些安置。”他声音冷得像冰。我独守空房三年,
直到在他书房暗格里发现一只金簪。簪头刻着“赠阿月”,正是他白月光的闺名。
我砸碎所有定情信物,他却在谋逆案里护我周全。流放路上,
他浑身是血推开我:“快走!”我抱着染血的木盒逃出生天。
盒底压着张泛黄纸条:“吾妻清晚,唯愿卿如金丝雀,永困我掌中。”红烛高烧,
映得满室喜红如血。沈清晚端坐在铺着百子千孙锦被的拔步床上,
头顶沉重的赤金点翠凤冠压得她脖颈发酸,眼前只有一片晃动的、朦胧的红色。
那是她的盖头。龙凤呈祥的图案在烛光下泛着细碎的金光,
每一根丝线都缠绕着家族沉甸甸的期许,勒得她几乎喘不过气。
外面喧天的锣鼓和宾客的哄笑声隔着厚重的门板,闷闷地传进来,像隔着一层水。
她交叠放在膝上的手,指尖冰凉,掌心却沁出薄薄一层汗,
将那绣着缠枝莲的嫁衣料子洇湿了一小片。不知过了多久,
久到她几乎以为这喧嚣永不会停歇,门轴终于发出一声沉重的“吱呀”声。脚步声。沉稳,
有力,一步步踏在光洁的金砖地上,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威势,径直向她走来。
沈清晚的心猛地提到了嗓子眼,下意识地屏住了呼吸。
她能感觉到那高大的身影停在了自己面前,一股清冽的、带着淡淡松墨气息的味道笼罩下来,
并不难闻,却带着一种拒人千里的疏离。眼前骤然一亮。盖头被掀开。
烛光刺得她微微眯了下眼,才看清站在面前的男人。萧珩。她的夫君,大周朝新晋的靖安侯,
天子近臣,权倾朝野。一身大红的喜服衬得他身姿愈发挺拔如松,剑眉斜飞入鬓,鼻梁高挺,
薄唇紧抿着,勾勒出近乎冷硬的线条。烛火在他深邃的眼眸里跳跃,却映不出一丝暖意,
只有一片沉寂的、望不到底的寒潭。他看着她,目光平静无波,
像是在审视一件新得的、却并不十分合心意的器物。那眼神里没有新婚的喜悦,没有惊艳,
甚至没有一丝属于活人的温度。沈清晚脸上努力维持的、属于新嫁娘的羞怯笑容,
在他这冰水般的注视下,一点点僵硬、凝固。她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
哪怕是句“侯爷安好”,喉咙却像是被什么堵住了,干涩得发不出任何声音。
萧珩的视线在她脸上停留了不过一瞬,便漠然地移开,扫过旁边紫檀木圆桌上摆放的合卺酒。
他没有动。“早些安置。”四个字,从他薄唇中吐出,声音低沉悦耳,
却冷得像三九寒冬屋檐下挂着的冰凌,每一个音节都带着刺骨的寒意,砸在沈清晚的心上。
他甚至没有多看她一眼,仿佛掀开盖头已是完成了某种不得不为的仪式。说完,便径直转身,
大红喜服的袍角在烛光下划出一道冷冽的弧线,高大的身影毫不留恋地走向门口。
“侯爷……”沈清晚下意识地唤了一声,声音细弱蚊蚋,
带着连她自己都未曾察觉的颤抖和一丝微弱的祈求。萧珩的脚步在门口顿住,并未回头。
“明日还要入宫谢恩,早些歇息。”他背对着她,声音依旧没什么起伏,
像是在吩咐一件再平常不过的公事。然后,他抬手拉开了房门,
身影没入门外沉沉的夜色之中。“吱呀——”门被轻轻带上,隔绝了外面残留的喧嚣,
也隔绝了沈清晚最后一点微弱的希望。偌大的新房,瞬间只剩下她一个人。
红烛还在噼啪作响,跳跃的火苗将她的影子长长地投在地上,孤单得可怜。
桌上那对描金彩绘的合卺杯,并排立着,杯中的酒液澄澈,映着烛光,像两汪凝固的泪。
沈清晚维持着端坐的姿势,一动不动。过了许久,久到双腿都麻木了,
她才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松开紧握的双手。掌心那被指甲掐出的月牙形痕迹,
深得几乎要渗出血来。一滴滚烫的泪,毫无征兆地砸落在她冰凉的手背上,
洇开一小片深色的湿痕。她猛地抬手捂住嘴,将那几乎要冲口而出的呜咽死死地堵了回去。
肩膀抑制不住地颤抖起来,像寒风中一片无依的落叶。新婚夜,她的夫君,靖安侯萧珩,
掀开她的盖头,只留下四个冰冷的字,便将她一人,
丢在了这铺天盖地的、令人窒息的红色里。安置?呵。这漫漫长夜,才刚刚开始。
靖安侯府的日子,像一潭深不见底的死水。表面光鲜,内里却冰冷刺骨,毫无波澜。
沈清晚成了这偌大侯府里最精致也最寂寞的摆设。萧珩待她,
客气周全得如同对待一位远道而来、需要妥善安置的贵客。晨昏定省,他从不缺席,
只是那问候如同例行公事,眼神疏离,言语间不带丝毫暖意。用膳时,两人相对而坐,
长长的紫檀木餐桌宽得能跑马,沉默在精致的菜肴上空弥漫,只有碗筷偶尔碰撞的轻响,
敲打着令人窒息的寂静。他从不留宿在她的“清辉院”。侯府的下人们都是人精,
侯爷的态度便是他们的风向标。起初的恭敬里还带着几分试探,时日一长,
那恭敬便只剩下了表面功夫。送来的份例虽不敢克扣,但那份怠慢却如同冬日里渗骨的寒气,
无处不在。炭火总是不够暖,时令鲜果总比别处晚半日,连她院里的花草,
似乎都比别处蔫得快些。沈清晚起初还会试着去萧珩的书房送些汤水点心。那是外院的重地,
寻常人不得擅入。她端着温热的汤盅,站在那扇紧闭的、雕刻着狻猊兽首的厚重木门外,
听着里面隐约传来的、他与幕僚清客议事的声音,或是翻阅卷宗的沙沙声。鼓起勇气敲门,
回应她的总是长随萧安那张恭敬却疏离的脸。“夫人,侯爷正忙,吩咐了任何人不得打扰。
”“夫人,侯爷刚歇下,您请回吧。”“夫人……”一次,两次,
三次……那扇门从未为她打开过。汤盅里的热气渐渐散去,变得冰凉,
如同她一次次捧出去又被原样端回来的心。她不再去了。她开始学着打理自己的小院。
亲手侍弄花草,看它们在春日里抽芽,在夏日里绽放,在秋风中凋零。她临摹字帖,
抄写佛经,试图在笔墨纸砚间寻找一丝内心的平静。更多的时候,她只是坐在窗边,
看着庭院里那几竿修竹,在风中摇曳,日影一点点从东移到西。三年。一千多个日夜,
就在这无声的消磨中悄然滑过。少女时那点鲜活的憧憬和羞涩,
早已被这日复一日的冷寂打磨得黯淡无光,只剩下一种近乎麻木的平静。
她像一株被精心移栽到华美花盆里的植物,
根须却从未真正扎进这片名为“靖安侯府”的土壤。直到那个午后。
初夏的阳光透过雕花窗棂,在书房光洁的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萧珩奉旨出京巡查河道,
归期未定。偌大的侯府,似乎连空气都松懈了几分。沈清晚独自坐在萧珩的书房里。
这地方她极少来,即便来了,也只在靠窗的软榻上坐坐,从不碰他的书案。
今日是府中管事送来几本新到的账册,需她过目用印。管事放下册子便躬身退了出去,
留下她一人。书房里弥漫着熟悉的松墨冷香,混合着旧书卷特有的、干燥微尘的气息。
巨大的紫檀木书案上,笔墨纸砚摆放得一丝不苟,镇纸压着一叠尚未批阅的公文。
一切都透着主人严谨冷肃的作风。沈清晚的目光无意识地扫过书案后那排顶天立地的书架。
乌木的架子,深沉厚重,上面整齐地码放着各类典籍、卷宗,分门别类,一丝不乱。
她的视线掠过书架最底层,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那里似乎比别处颜色略深一点?
像是一块活动的挡板?鬼使神差地,她放下了手中的账册,走了过去。蹲下身,
指尖试探着在那块颜色略深的木板上轻轻一按。“咔哒。”一声极其轻微的机括声响。
那块木板竟真的向内弹开了一条缝隙!沈清晚的心猛地一跳,指尖有些发凉。她犹豫了片刻,
最终还是抵不过那强烈的好奇与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冲动,伸手轻轻拉开了那块挡板。
里面是一个小小的暗格。不大,仅能容下一掌。暗格里没有书信,没有密函,
也没有任何她预想中可能属于“秘密”的东西。只有一支簪子。一支女子的金簪。
簪身是极细的金丝绞股而成,工艺繁复精巧,在幽暗的暗格里,
依旧折射出一点微弱却不容忽视的华光。簪头并非寻常的凤凰牡丹,
而是一只振翅欲飞的金丝雀!雀鸟的形态被刻画得栩栩如生,羽毛根根分明,
小小的眼睛用两粒细小的红宝石镶嵌,灵动非凡。沈清晚的呼吸瞬间停滞了。
她颤抖着伸出手,小心翼翼地将那支金簪从暗格里取了出来。冰冷的金属触感顺着指尖蔓延,
一直凉到心底。她将簪子举到眼前,借着窗外透进来的光线,细细端详。然后,
她的目光凝固在了簪尾内侧一个极其隐蔽的位置。那里,用极其纤细的刀工,
刻着两个蝇头小字——赠阿月。阿月。这两个字像淬了剧毒的针,
猝不及防地狠狠扎进沈清晚的眼底!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骤然缩紧,
痛得她几乎无法呼吸!她认得这个名字!京城谁人不知,靖安侯萧珩年少时,
曾有一位青梅竹马的恋人,闺名便唤作“阿月”!传闻那女子出身清贵,才貌双全,
与萧珩情投意合,是京中人人艳羡的一对璧人。后来……后来似乎是那女子家中突遭变故,
香消玉殒。从此,阿月便成了萧珩心口一颗抹不去的朱砂痣,一道无人敢触碰的逆鳞!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怪不得他新婚夜弃她如敝履!怪不得他三年冷落,视她如无物!
怪不得这书房重地,连她这个明媒正娶的侯夫人都不得轻易踏足!原来这书房最隐秘的角落,
藏着的不是家国大事,不是机要文书,而是他心上白月光的一缕遗念!
一支刻着“赠阿月”的金丝雀簪!那她沈清晚算什么?一个顶着“侯夫人”名头的笑话?
一个被摆放在明面上,用以掩盖他心中那道永不愈合伤口的、可怜又可悲的替代品?!
巨大的羞辱感如同汹涌的潮水,瞬间将她淹没!三年的隐忍,三年的委屈,三年的自欺欺人,
在这一刻被这支冰冷的金簪彻底击得粉碎!“啪嗒!”金簪从她颤抖的手中滑落,
掉在冰冷坚硬的金砖地上,发出一声清脆而刺耳的声响。沈清晚踉跄着后退一步,
背脊重重撞在冰冷的书架上。她看着地上那支依旧闪耀着华光的金簪,
看着那只振翅欲飞的金丝雀,只觉得那鸟儿的眼睛,那两粒细小的红宝石,
正闪烁着讥诮而冰冷的光,像是在无声地嘲笑着她的痴傻与多余!
一股难以言喻的悲愤和绝望猛地冲上头顶!她猛地转身,
跌跌撞撞地冲出了这间让她窒息的书房!回到清辉院,沈清晚像一头被彻底激怒的困兽。
她冲进内室,目光扫过妆台上那些萧珩或是按例赏赐,
或是敷衍送来的首饰——赤金嵌宝的步摇,点翠镶珠的华盛,
羊脂白玉的镯子……每一件都价值不菲,每一件都曾被她小心翼翼地珍藏,
视作他或许有那么一丝丝在意的证明。此刻,这些华美的物件在她眼中,
都变成了最刺眼的讽刺!她扑到妆台前,
一把抓起那个最贵重的、嵌着鸽血红宝石的赤金璎珞项圈!那是她生辰时,他派人送来的。
她当时还傻傻地欢喜了许久!“骗子!全都是骗子!”她嘶哑地低吼着,用尽全身力气,
狠狠地将那项圈砸向地面!“哐当——!”沉重的金饰与坚硬的地砖猛烈撞击,
发出巨大的声响!镶嵌的宝石崩飞出去,滚落一地。赤金的项圈扭曲变形,躺在狼藉之中,
如同她此刻支离破碎的心。她还不解恨!又抓起一支白玉簪,看也不看,再次狠狠掼下!
“啪嚓!”温润的白玉应声而断,碎成几截!一件,又一件!
那些承载着她三年卑微期许和自欺欺人的“定情信物”,
在她疯狂的、带着哭腔的嘶喊和碎裂声中,化为满地狼藉的碎片和扭曲的金属!
泪水早已模糊了视线,她看不清自己砸的是什么,也感觉不到手掌被碎片划破的刺痛。
她只想毁掉这一切!毁掉这些虚假的、冰冷的、时刻提醒着她是个多余替代品的玩意儿!
当最后一件首饰也化为齑粉,沈清晚颓然跌坐在冰冷的地上,背靠着同样冰冷的床柱。
满地的碎片在透过窗棂的阳光下闪烁着刺眼的光,像无数双讥讽的眼睛盯着她。
她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胸口剧烈起伏,喉咙里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三年了。
她像个傻子一样,守着一个空壳般的婚姻,守着一个心里永远装着别人的男人。
她所有的隐忍,所有的退让,所有的期盼,都成了天底下最大的笑话!她抬起手,
看着掌心被碎片划破的伤口,鲜血混着灰尘,蜿蜒而下,滴落在她素色的裙摆上,
洇开一小朵绝望的花。也好。碎了,干净。她再也不要当那个可悲的替代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