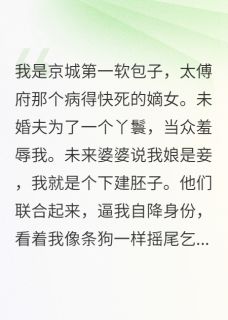我是京城第一软包子,太傅府那个病得快死的嫡女。未婚夫为了一个丫鬟,当众羞辱我。
未来婆婆说我娘是妾,我就是个下建胚子。他们联合起来,逼我自降身份,
看着我像条狗一样摇尾乞怜。我顺从地低下头,在他们以为拿捏住我的时候,
我轻轻拍了拍手。门外,黑压压的鸦卫涌入,刀锋映着他们惊恐的脸。装了二十年的兔子,
终于可以露出獠牙了。1我叫沉鸢。京城第一权臣,当朝太傅沉玄清的独女。
也是整个洛阳权贵圈里,出了名的软骨头。我那即将过门的未婚夫,虎威将军的长子裴疏,
更是深信这一点。今日,是我出阁前分府别居的第一天,我在自己的新府「听雨苑」里设宴,
请了半个京城的名流。宴会之上,丝竹悦耳,人影绰绰。
定远侯家那个不着调的小儿子喝多了,指着我身边的大丫鬟锦瑟,
非要我把她许配给他府上的一个护卫,说那护卫至今未娶,可怜得很。本是一句玩笑话,
我却也当了真。我轻声问锦瑟,可愿去侯府享福。她羞红着脸,扭扭捏捏地站了出来。
可谁曾想,那护卫一见锦瑟,脸色顿时铁青。两人竟是旧识,过去还有过一段情缘,
只是最后闹得不欢而散。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两人也不管满堂宾客,就在这庭院中央,
当着所有人的面,对骂了起来。男的骂女的嫌贫爱富,女的骂男的无能懦弱。唾沫横飞,
污言秽语不堪入耳。我皱着眉,敲了三次桌子,声音不大,但足以示警。他们却恍若未闻。
我这个主人的脸,被他们当众踩在脚下,反复碾压。最后还是定远侯看不下去,
一脚踹在自家护卫身上,命人将他拖了出去。那护卫走了,锦瑟却不依不饶,站在原地,
像个疯婆子一样继续数落着那人的不是,仿佛要将这天大的委屈,说给全天下听。
满堂的宾客,都饶有兴致地看着这场闹剧,等着看我这个主子,要如何收场。
我的脸已经烧得滚烫。「来人,」我终于失了耐心,声音冷了下去,「把她拖下去,
掌嘴二十,让她知道什么叫规矩。」一个下人,在主人的开府宴上如此撒泼,失了我的体面,
也脏了客人的眼睛,不罚她,我这公主府日后岂不成了菜市场。我的话音刚落,
一只手猛地抓住了我的手腕,力道之大,捏得我骨头生疼。是裴疏。
他不知何时走到了我的面前,一脸的怒气与鄙夷。「沉鸢!你还有没有一点同情心?」
他的声音洪亮,确保了在场每一个人都能听得清清楚楚。「一个姑娘家受了情伤,
发泄几句罢了,你就要下此毒手?你的心是石头做的吗?」他将我猛地一拉,
把我从主位上拽了起来,然后一把将哭哭啼啼的锦瑟护在身后。那架势,
仿佛我才是那个仗势欺人的恶霸,而他,是拯救弱小的英雄。满堂的视线,像无数根针,
密密麻麻地扎在我身上。他们都在看我的笑话。看我这个沉家唯一的嫡女,是如何在成婚前,
就被未来的夫君拿捏得死死的。看我为了讨好他,能卑微到什么地步。毕竟,所有人都知道,
我爱惨了裴疏。「她受了情傷,就可以不顧體面,砸我的场子?」我试图挣脱他的手,
声音都在发颤,「裴疏,这是我的府邸,她是我的丫鬟!」「你的府邸又如何?」他冷笑着,
甩开了我的手,「沉鸢,你别忘了,若没有我裴家愿意娶你,你这个空有嫡女名分的病秧子,
谁会多看一眼?收起你那可笑的架子,给锦瑟道歉!」道歉。他让我,堂堂太傅之女,
给一个当众撒泼的丫鬟,道歉。我看着他那张英俊却写满傲慢的脸,
看着他身后那个哭得梨花带雨,眼神里却藏着得意的锦瑟,一股寒气从脚底直冲天灵盖。
这些年,为了他,我学着掌管中馈,为他调配药膳,为他打理人情。
我将自己所有的骄傲与自尊都收敛起来,只为能安安稳稳地嫁给他。可我换来了什么?
换来了他在我最重要的日子里,为了另一个女人,给我最狠的一巴掌。原来在他心里,
我连一个下人都不如。周围的空气仿佛凝固了。所有人都屏息凝神,等待着我低头,
等待着我像过去无数次一样,委曲求全。我深吸一口气,压下喉间的腥甜。再抬眼时,
脸上已不见丝毫血色,只剩下一片惨白。我对上了裴疏那不耐烦的眼神,嘴唇微微颤抖着,
吐出几个字。「你说得对。」我垂下眼帘,声音轻得像一片羽毛。「是……是我小家子气了。
」裴疏的脸上露出了胜利者的微笑。我转头,对还愣着的管家吩咐道:「锦瑟姑娘累了,
扶她下去歇息,不必罚了。」满堂宾客,发出若有若无的叹息,其中夹杂着几声轻蔑的嗤笑。
裴疏满意地拍了拍我的肩膀,仿佛在安抚一只听话的宠物。他转身离去时,
没有看到我低垂的眼眸里,那一片死寂的冰冷。我静静地看着他抓过的手腕,那里,
一片刺目的红痕。裴疏。还有锦瑟。我记住你们了。2宴会不欢而散。
裴疏为了一个丫鬟当众羞辱我的事情,一夜之间传遍了洛阳。我成了全京城最大的笑话。
人人都说,我沉鸢离了裴疏,就活不下去。我把自己关在「听雨苑」,三天没有出门。
下人们都以为我伤心欲绝,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在等。等一个让所有嘲笑我的人,
都闭嘴的机会。第四天,裴疏来了。他不是一个人来的。他还带了兵部尚书的公子,
户部侍郎的侄子,还有几个洛阳城里有头有脸的世家子弟。浩浩荡荡,像来问罪。
我坐在正厅,慢条斯理地喝着茶。他一进门,便将一张纸摔在了我面前的桌子上。「签了它!
」他的语气,不是商量,是命令。我拿起那张纸,上面是娟秀的蝇头小楷,字里行间,
满是柔情蜜意。但内容,却让我笑了。这是一份「纳妾意向书」。内容是,恳请我沉鸢,
同意他裴疏,在迎娶我过门之前,先将侍女锦瑟,以贵妾之礼,抬入裴家。
理由是锦瑟姑娘温柔善良,善解人意,与裴公子情投意合,又不忍伤害未来主母,
故而左右为难,茶饭不思,日渐消瘦。裴公子不忍见其神伤,又感念我沉鸢的大度,
故请我成全。真是好一番感天动地的说辞。「裴疏,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放下那张纸,
平静地问。他冷笑一声,大马金刀地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什么意思?沉鸢,
你别揣着明白装糊涂。锦瑟跟了我,是你天大的福分。她懂事,温柔,不像你,
只会摆着一张死人脸,言语无味,空有太傅嫡女的名头。」
他身后的兵部尚主公子也帮腔道:「就是啊沉**,裴兄是什么人物?
未来是要继承虎威将军大统的。男人三妻四妾本是寻常,你作为正妻,
最要紧的就是贤惠大度。锦瑟姑娘我见过,是个美人,性子也好,提前纳了,
也能先为裴家开枝散叶嘛。」「是啊是啊,沉**,你母亲当年,不也是……」
户部侍郎的侄子话说到一半,被裴疏一个眼神制止了。但他未说完的话,像一把淬了毒的刀,
精准地捅进了我的心脏。我母亲。我母亲是父亲的妾室,生下我之后就难产而死。
这是我身上永远洗不掉的印记。也是裴疏和整个洛阳城,都认为我软弱可欺的根源。
他们觉得,一个妾生的女儿,能嫁给将军府的嫡长子,是天大的高攀。所以我必须忍,
必须让,必须像条狗一样听话。锦瑟袅袅婷婷地从裴疏身后走了出来。
她穿着一身水绿色的新衣,头上戴着我前几日才赏给她的金步摇,
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怯懦和羞涩,跪在了我面前。「**,求您成全我和公子吧。
奴婢知道自己身份卑贱,配不上公子。可奴婢与公子是真心相爱的。
奴婢愿意一辈子当牛做马,侍奉**和公子,绝无二心。」她说着,眼泪就掉了下来,
楚楚可怜的模样,确实能激起男人的保护欲。我看着她,又看了看裴疏。裴疏的眼神里,
满是催促和警告。他带来这么多人,就是要用整个上流圈子的舆论,来压垮我。逼我就范。
「你的意思是,如果我不同意,就是善妒,不贤惠了?」我轻声问。裴疏的耐心耗尽了。
他站起身,走到我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我。那眼神,像在看一只随时可以捏死的蚂蚁。
「沉鸢,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我裴家愿意娶你,看中的是你背后沉太傅的势力。
你唯一的价值,就是乖乖地当好这个联姻的棋子,为我们裴家和我父亲在朝堂上铺路。
签了它,你依旧是将军府未来的主母。若是不签……」他顿了顿,嘴角的笑意充满了残忍。
「我不介意,换一个更听话的女人来坐这个位置。」这已经是**裸的威胁了。他说,
我的价值,就是一枚棋子。原来如此。我忽然就想通了。这些年的委曲求全,小心翼翼,
在他眼中,不过是一个棋子为了保住自身价值,所做的徒劳挣扎。可笑,真是可笑。
我看着面前这张俊美却又丑陋的脸,忽然觉得无比的恶心。我拿起桌上的毛笔,蘸了蘸墨。
满屋子的人都屏住了呼吸。锦瑟的脸上露出了压抑不住的喜色。裴疏的嘴角,
勾起了满意的弧度。他以为,他赢了。我抬起手腕,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的笔尖。
他们都以为我会签下自己的名字。我确实也写了。但写的,不是「沉鸢」。
而是一个他们所有人都看不懂的符号。那是一个潦草,却又充满了杀伐之气的图腾。一只,
展翅欲飞的乌鸦。我放下笔,将那张废纸推到裴疏面前,抬起头,
冲他露出一个他从未见过的笑容。一个冰冷到极致,妖异到极致的笑容。「好啊。」
我轻声说。就在我话音落下的瞬间。「轰隆!」一声巨响。正厅厚重的实木大门,
被人从外面一脚踹得粉碎。木屑飞溅中,无数身穿黑色劲装,面戴乌鸦面具的影子,
如同鬼魅一般,涌了进来。他们手持泛着幽光的短刃,动作整齐划一,悄无声息,只一瞬间,
就将裴疏和他带来的那群酒囊饭袋,围得水泄不通。刀刃出鞘的声音,整齐得像一声惊雷。
方才还不可一世的世家公子们,瞬间面如死灰,两股战战,几乎要瘫软在地。
浓烈的血腥味和杀气,瞬间充满了整个大厅。裴疏和他带来的那群所谓的「精英」,
在这群真正的死神面前,就像一群待宰的羔羊。他惊恐地看着我,嘴唇哆嗦着,
一个字也说不出来。而我,缓缓站起身,走到他的面前。3「你……你到底是谁?」
裴疏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他引以为傲的镇定和傲慢,在绝对的死亡威胁面前,
碎得连渣都不剩。他带来的那些同伴,更是丑态百出,有人已经瘫在地上,身下一片湿濡,
散发出难闻的骚味。我没理他。我走到那群黑衣人面前。为首的一人,
摘下了脸上的乌鸦面具,露出一张冷硬如铁的脸。他单膝跪地,声音沉稳如山。「指挥使,
鸦卫一百二十人,已封锁全府,听候调遣!」指挥使。这个称呼,像一道天雷,
劈在裴疏和所有还清醒着的人的头顶。鸦卫。大周王朝最神秘,最恐怖的存在。
皇帝的直属暗卫,掌管监察百官,先斩后奏,权力滔天。传闻鸦卫的指挥使,
神龙见首不见尾,是皇帝最信任的一把刀,杀人不见血,手段酷烈。没人知道他(她)是谁,
长什么样。可现在,鸦卫的统领,竟然跪在沉鸢的面前,称她为「指挥使」。这怎么可能!
这个在他们眼中,柔弱、无能、只能依附男人才能生存的病秧子,
竟然是那个手握生杀大权的魔王?「裴疏,」我终于转过身,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那张因为恐惧而扭曲的脸,「你总说我母亲出身卑贱,
我沉鸢配不上你裴家的门楣。现在,我来告诉你答案。」我的声音很轻,却像重锤一样,
敲在每个人的心上。「我的母亲,闺名苏潋,是先帝亲封的鸦卫第一任指挥使。
我身上流着她的血,这支让整个大周都闻风丧胆的铁军,是我母亲留给我唯一的嫁妆。」
我伸出手,轻轻抚上裴疏的脸。他的身体剧烈地颤抖着,像是被毒蛇碰到。「你以为,
你算计的是一只温顺怯懦的小猫。却不知道,你亲手招惹的,是悬在整个裴家头顶上,
最锋利的一把刀。」「不……不可能……这不可能……」裴疏失神地摇着头,
显然无法接受这打败性的事实,「你骗我!沉太傅……沉太傅怎么会允许你……」「我父亲?
」我嗤笑一声,「他知不知道,很重要吗?」我的指尖划过他的嘴唇,他的眉毛,
最后停在他的眼睛上。「不过,我倒是要感谢你。」「感谢你,让我看清了你的嘴脸。」
「感谢你,给了我一个,名正言顺,清理门户的理由。」裴疏像是被抽走了所有力气,
瘫倒在地。而那个刚才还跪在我面前,演得楚楚可怜的锦瑟,早就吓得晕死过去,
像一条死狗一样趴在地上。我走到她身边,用脚尖踢了踢她。「拖出去,弄醒。」我的语气,
平淡得像是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两名鸦卫立刻上前,架起锦瑟,拖了出去。很快,
一声凄厉的惨叫传来,接着锦瑟被重新拖了回来,脸上多了几道血痕,人是醒了,
但已经吓得魂不附体,只会不停地磕头。「**饶命!**饶命啊!」我蹲下身,
捏住她的下巴,强迫她抬起头。「锦瑟,刚刚你说,你和裴公子,是真心相爱的?」
「不……不是……奴婢该死!奴婢胡说八道!是裴公子……是裴公子逼我的!」
她语无伦次地求饶,试图把所有责任都推出去。「哦?他逼你的?」我看向裴疏,「裴公子,
她说的是真的吗?」裴疏已经被吓傻了,只是呆呆地看着我,眼神空洞。我笑了。「看来,
你们两个,需要玩一个游戏,来帮我理清一下头绪了。」我站起身,对身后的鸦卫统领道。
「北风,把我的宝贝匣子,拿来。」4「是,指挥使。」叫北风的鸦卫统领,
很快捧来一个三尺长的紫檀木匣子。匣子打开,里面不是什么金银珠宝,
而是一排排泛着冷光的,小巧而精致的刑具。银针,小刀,铁钩,镊子……每一件,
都像是艺术品,却又透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寒意。在场的所有世家子弟,看到这些东西,
胃里都开始翻江倒海,有人已经忍不住吐了出来。我从匣子里,拈起一把薄如蝉翼的小刀。
刀锋在烛光下,反射出一条冰冷的光线。我走到已经瘫软如泥的锦瑟面前。「裴疏,
你不是最喜欢她这张脸吗?」我用刀尖,轻轻划过锦瑟光滑的脸蛋。「你说她比我更懂情趣,
比我更美,你为了维护她,当着半个洛阳城的面,让我下不来台。」「现在,」
我嘴角的笑意加深,「我就让你亲眼看看,这副让你神魂颠倒的皮囊,
被一片一片剥下来的时候,是怎样一副光景。」「不要!」裴疏终于找回了一点神智,
他疯狂地嘶吼起来,「沉鸢!你这个疯子!毒妇!」「嘘。」我竖起一根手指,示意他安静。
「游戏开始了,要遵守规则。」我的手很稳。刀尖刺入皮肤,没有发出一丝声音。
我挑起一小片薄薄的脸皮,血珠,瞬间就从伤口处涌了出来。「啊——!」
锦瑟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惨叫。「第一刀,」我没有理会她的尖叫,声音平静地像在说书,
「是为了惩罚你,身为我的贴身丫鬟,却吃里扒外,勾结外人。」我手腕一转,又是一刀。
这一刀,划在了她的鼻翼上。「啊!我的脸!我的脸!」锦瑟疯狂地挣扎,
却被两名鸦卫死死按住,动弹不得。「第二刀,」我继续道,「是为了惩罚你,不知尊卑,
在我的开府宴上,肆意撒泼,丢尽我的脸面。」裴疏双目赤红,状若疯狂,
他挣扎着想扑过来,却被鸦卫一脚踹在膝盖上,重重地跪倒在地。「沉鸢!你放了她!
有什么冲我来!」他声嘶力竭地喊道。我充耳不闻,慢条斯理地划下第三刀。「第三刀,
是为了惩罚你,野心勃勃,不知廉耻,妄图染指你不该碰的东西。」锦-瑟的脸上,
已经血肉模糊,分不清哪里是泪,哪里是血。她开始求饶,含混不清地喊着。
「是……是裴公子……是他让我这么做的……是他想……想通过我……打探您的……」「哦?
」我停下了手里的刀,看向裴疏,露出一个恍然大悟的表情,「原来,不止是为了美色啊。」
裴疏的脸色,瞬间惨白如纸。他意识到,我不仅要报复他个人的羞辱,
我还要……我将带血的刀尖,在锦瑟的衣服上擦了擦。「看来,我们的游戏,要升级了。」
我看着裴疏,甜甜地笑了。「我的好夫君,你说,我该怎么奖励你的‘深谋远虑’呢?」
我将小刀扔回匣子,发出「当啷」一声脆响。那声音,像是敲在每个人的心坎上。
「裴家当年,诬陷兵部左侍郎张劲谋反,致使其满门三百余口,一夜之间,尽数惨死于午门。
」我踱步到裴疏面前,用脚尖抬起他的下巴。「这件事,你父亲做得神不知鬼不觉,
连大理寺都查不出半点蛛丝马迹。可惜,他忘了,这世上,还有我们鸦卫。」裴疏的瞳孔,
因为极致的恐惧而缩成了针尖。他完了。他全家,都完了。他终于明白,我从一开始,
就不是在和他计较什么丫鬟,什么脸面。我在等,等他自己,把整个裴家,
都送到我的刀口下。「毒妇!你这个蛇蝎心肠的毒妇!」他用尽最后的力气咒骂我。
我俯下身,在他耳边轻声道。「别急。你心爱之人的痛苦,才刚刚开始。」「而你,
我的夫君,你的折磨,现在才正式拉开序幕。」5消息,比瘟疫蔓延得更快。当我带着鸦卫,
出现在「听雨苑」的那一刻起,裴家覆灭的倒计时,便已开始。一夜之间,天翻地覆。
虎威将军府被一千鸦卫围得水泄不通,连一只苍蝇都飞不出去。裴疏的父亲,
手握十万兵权的虎威大将军裴振山,还没来得及调动一兵一卒,就被从帅帐中直接拖了出来,
一身戎装,狼狈不堪。裴家的主母,平日里在贵妇圈中高高在上的将军夫人,
连同裴家上下三百多口族人,不论嫡庶,不论男女老幼,全都被押到了太傅府门前,
黑压压地跪了一地。洛阳城的老百姓,将太傅府门口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所有人都想看看,
这个一夜之间权势滔天,敢于向将军府动刀的太傅嫡女,究竟是何方神圣。
我站在太傅府的台阶上。我父亲,当朝太傅沉玄清,就站在我身边。他一生沉稳,
喜怒不形于色,此刻,脸上依旧是那副波澜不惊的模样。跪在最前面的裴振山,看到我,
眼中迸射出怨毒的光芒。他嘶吼道:「沉玄清!你教的好女儿!我裴家与你沉家联姻,
你竟暗中下此毒手!你好狠的心!」父亲没有说话。我却笑了。我缓步走下台阶,
走到他的面前。「裴将军,此言差矣。」我从北风手中,拿过一卷厚厚的卷宗,
砸在他的脸上。「第一,我与你儿子的婚约,从他逼我纳妾的那一刻起,便已作废。」
「第二,我今日抄你裴家,不是因为私怨,而是国法。」「这里面,
详细记载了你裴家三十年来,勾结外戚,私吞军饷,草菅人命,乃至通敌叛国的上百条罪状。
每一条,都证据确凿。每一条,都足够让你裴家,死上十次。」裴振山浑身一震,
脸色瞬间惨白。他看着我,像是第一次认识我。「你……你什么时候开始……」
「从你儿子第一次,在我面前流露出对鸦卫的兴趣开始。」我冷冷地打断他,「你以为,
派一个精心**过的丫鬟到我身边,就能探听到鸦卫的机密?就能窥伺到皇家的力量?
裴将军,你的野心不小,可惜,你的儿子,太蠢。」这时,一阵马蹄声传来。
人群自动分开一条道路。靖王,慕容冽,当今圣上唯一在世的亲弟弟,手握监国之权,
一身玄色王袍,骑在高头大马上,缓缓而来。他的身后,跟着一队禁军。全场,
瞬间鸦雀无声。百姓也好,跪着的裴家人也好,全都低下了头,不敢直视天家威仪。
慕容冽翻身下马,径直走到我的面前。他看都没看跪了一地的人,只是将一份明黄的圣旨,
交到我的手中。「鸢儿,陛下口谕,此事,全权交由你处置。无论结果如何,他与我,
都为你担着。」他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到每个人耳朵里。这是皇帝,在为我撑腰。
整个大周朝,最顶层的权力,都站在了我这一边。裴家,再无一丝翻盘的可能。
我缓缓展开圣旨,清亮的声音,在寂静的街道上响起,宣读着裴家累累的罪行,
以及最终的判决。「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虎威将军裴振山,心怀不轨,
结党营私……罪大恶极,罄竹难书!着,即刻将裴氏一族,主犯三十六人,押赴西市,
斩立决!其余族人,流放三千里,永世不得还朝!家产尽数充公!钦此!」宣读完毕。
裴家众人,发出了鬼哭狼嚎般的哀嚎。裴振山的老婆,那个曾经趾高气昂的将军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