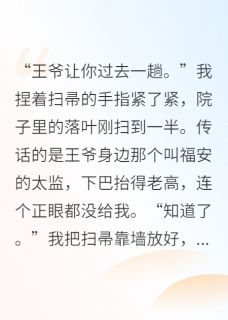那双眼睛……太不对劲了。
回到听雨轩,我那唯一的陪嫁丫鬟小桃正急得在门口转圈,见我回来,立刻扑上来,压低声音:“**!王爷没为难您吧?叫您过去干嘛呀?”
小桃是姐姐江雪的丫鬟,从小一起长大,忠心耿耿。姐姐死后,赵氏本想把她打发走,是我硬要过来的。在这深似海的王府里,小桃是我唯一能信的人。
“没事。”我走进冰冷的屋子,搓了搓冻僵的手,“就是认个脸,然后告诉我,没事别往他跟前凑。”
“啊?”小桃愣了一下,随即愤愤不平,“这算什么呀!您是正妃啊!怎么能把您丢在这破地方不闻不问?您看看这炭,送来的都是些黑炭渣子,点起来全是烟,呛死人!还有这饭菜,顿顿清汤寡水,连点油星都看不见!我去找厨房理论,那些婆子还阴阳怪气,说什么‘王妃体弱,就该吃清淡些’!”她越说越气,眼圈都红了,“**,咱们过的日子,连府里有点头脸的管事嬷嬷都不如!”
我走到窗边那张掉漆的桌子旁,拿起早上送来的早膳——一碗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糙米粥,一小碟乌漆嘛黑的咸菜。冰冷的,早就没了热气。
“正常。”我拿起筷子,夹了根咸菜放进嘴里,又咸又涩,“赵氏把我塞进来,顶了姐姐的位置,可不是让我来享福的。她巴不得我在这王府里悄无声息地烂掉,或者因为不懂规矩得罪了王爷,被直接处置了,那才干净。这样,她女儿江雨才有机会。”
“那王爷呢?王爷就任由他们这么作践您?”小桃替我委屈。
王爷?我眼前又闪过那双深不见底的眼睛。一个常年卧病、连府务都无力打理的人?呵。
“别指望他。”我放下筷子,那点咸菜实在咽不下去,“这府里,靠谁都不如靠自己。”
“靠自己?”小桃茫然地看着我,“**,咱们在这府里,人生地不熟,连月钱都被克扣得厉害,连打点下人的银子都没有,怎么靠自己啊?”
我没回答,走到床边,从那个破旧的陪嫁箱笼最底层,摸出一个小布包。打开,里面是几块碎银子,还有一支样式简单、磨得发亮的银簪子。这是我娘留给我的最后一点东西。银子很少,加起来不到十两。那簪子,是我最后的念想。
“小桃,”我把碎银子塞给她,“你去趟外院,找那个负责采买花草的王婆子。”
“找她干嘛?”小桃不解。
“打听点事。”我压低声音,“问问她,府里负责采买炭火和米粮的,是哪位管事?平日里在哪条街上哪家铺子进货?进的都是什么货?价钱几何?”
小桃更懵了:“**,您问这个做什么?”
“让你去就去。”我看着她,“记住,只打听,别多话,更别让人看出你是故意打听的。就说……就说咱们听雨轩的炭火太差,烟太大,想自己掏钱换点好的,问问路子。”
小桃虽然还是不明白,但看我神色郑重,用力点了点头:“嗯!**放心,我这就去!”
看着小桃揣着银子小跑出去的背影,我捏紧了手里那支冰冷的银簪。赵氏想让我悄无声息地死?做梦。姐姐的死,我一定要查清楚。在这之前,我得先在这吃人的王府里活下去。
活得不好,但必须活着。
小桃的银子没白花。
王婆子是个碎嘴的,又贪点小便宜。几块碎银子加上小桃刻意装出来的可怜相,很快就把话套出来了。
王府的炭火米粮采买,归内院一个姓钱的管事管。这钱管事是严嬷嬷的一个远房侄子。他常去城西“恒通商行”进货。府里主子们用的自然是上好的银霜炭和精细米面,但分到各处的,尤其是我们听雨轩这种“冷灶”,就全是下等的黑炭和发霉的陈米。
“恒通商行?”我琢磨着这个名字。京城做炭火米粮生意的大商行有好几家,“恒通”算不上顶大,但据说后台很硬。
“**,打听出来了,然后呢?”小桃问。
“然后?”我把玩着那支银簪,簪尖冰凉,“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