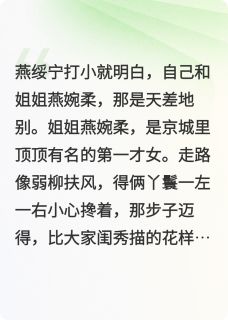燕绥宁打小就明白,自己和姐姐燕婉柔,那是天差地别。姐姐燕婉柔,
是京城里顶顶有名的第一才女。走路像弱柳扶风,得俩丫鬟一左一右小心搀着,那步子迈得,
比大家闺秀描的花样子还要精细讲究。偶尔一阵风吹过,她那纤细的腰肢便微微晃一晃,
随即抬起一只雪白纤手,轻轻按在胸口,秀眉微蹙,仿佛一口气没喘匀就能当场晕过去。
平日里不是抚琴作画,就是吟诗作对,身上的衣裳熏着最名贵的兰香,
连帕子都得用苏杭最新的软烟罗裁。京城里的贵妇**们提起来,
没有不夸一句“神仙人物”的。而她燕绥宁呢?
京城的贵妇圈里流传着另一个响当当的名号——京城第一惹祸精。
她不爱那些劳什子琴棋书画,嫌憋闷。她最爱的是爬树掏鸟窝,动作利索得像只狸猫,
常常把御史家后院那棵老槐树顶上的喜鹊窝搅得鸡飞狗跳。要么就是溜到城外护城河,
挽起裤腿跳下去摸鱼虾,一身泥点子,脸蛋晒得发红,
活脱脱一只刚从山野里蹦出来的野猴子。为了这事儿,
没少挨娘亲的训斥和爹爹恨铁不成钢的瞪眼。御史夫人好几次叉着腰在她家门外,
指着门里骂“没规矩的小泼猴”,她娘只能赔着笑脸把门关得严严实实。所以,
当那道明晃晃、沉甸甸的赐婚圣旨降下来,指名要燕家女嫁给边关守将秦牧野时,燕家上下,
从她爹娘到洒扫的粗使婆子,心里头都跟明镜儿似的——这“殊荣”,除了大**燕婉柔,
还能有谁?毕竟,传闻里那位秦将军,名声实在是不怎么美妙。说他身高八尺,
腰围也是八尺,青面獠牙,声如洪钟,一顿饭能生啖三斤带血的羊肉,
活脱脱就是个从地狱里爬出来的煞神!边关那种苦寒之地,风沙能把人脸皮子刮掉一层,
让婉柔那样的娇花去?那还不如直接拿刀子抹脖子来得痛快些。果然,圣旨前脚刚念完,
后脚,燕婉柔的绣楼里就传出了惊天动地的悲泣。她扑在娘亲怀里,哭得梨花带雨,
气若游丝:“娘啊!那等虎狼之地,女儿这般身子骨,去了……怕是活不过三日啊!娘亲,
您就眼睁睁看着女儿去送死吗?”那眼泪,跟断了线的珍珠似的,噼里啪啦往下掉,
直哭得燕夫人心肝儿都碎了。于是,在那个月黑风高、连狗都懒得叫的晚上,
燕绥宁被她亲娘,以一种近乎“打包处理”的速度,
连哄带吓地塞进了一顶临时找来的、半旧不新的红绸花轿里。“宁儿啊,
娘……娘也是没法子!”燕夫人眼圈红红的,手里攥着帕子,声音压得极低,
带着点不易察觉的颤抖,眼神躲闪着不敢看女儿那双过于清亮的眼睛,
“你姐姐她……她实在受不住那苦寒。你……你不一样!你皮糙肉厚,从小摔打惯了,抗造!
去了边关,说不定、说不定还能活得挺好!
”她飞快地把一个沉甸甸的小包袱塞进燕绥宁怀里,里头叮当作响,大概是些散碎银子,
“好孩子,为了咱们燕家……委屈你了!”花轿的帘子“唰”地一声被彻底放下,
隔绝了娘亲那张写满愧疚与无奈的脸,也隔绝了燕府那熟悉的高墙深院。
轿夫一声闷闷的“起轿——”,轿子便晃晃悠悠地被抬了起来,颠簸着离开了京城。这一路,
走了足有一个多月。路途遥远,颠簸得人骨头架子都要散了。燕绥宁开始还觉得新鲜,
撩开帘子看外面陌生的山野,没几天就腻烦了。沿途的驿站饭菜粗糙,淡得嘴里能飞出鸟来。
她实在熬不住,瞅准护卫松懈的当口,利落地翻出轿窗,溜进路旁的林子,
用包袱里藏着的弹弓打了几只倒霉的野兔山鸡。自己寻个僻静处生火烤了,
油滋滋的肉香飘散开来,馋得那几个押送的护卫直咽口水。她倒也大方,撕下大半分给他们,
堵住了他们上报的嘴。吃饱喝足,她拍拍身上的草屑灰烬,大摇大摆地回到轿子里,
继续当她的“待嫁新娘”,只是包袱里多了几块风干的兔肉当零嘴儿。
当那顶饱经风尘、颜色都有些黯淡的小红花轿,
终于摇摇晃晃地出现在边关苍凉辽阔的地平线上时,秦牧野正在尘土飞扬的校场上练兵。
日头毒辣,汗水顺着他棱角分明的下颌线滚落,砸在脚下的黄土地上,洇开一小团深色。
他身形挺拔如松,一身玄色劲装,更衬得气势迫人。手里一杆丈八长枪,正被舞得虎虎生风,
银亮的枪尖在阳光下划出一道道凌厉的弧线,破空之声尖锐刺耳。
底下操练的兵卒一个个绷紧了皮,吼声震天,不敢有丝毫懈怠。副将陈忠抹了把脸上的汗,
刚想凑近汇报点军务,眼角的余光忽然瞥见远处官道上那点突兀的红色。他定睛一看,
连忙低声提醒:“将军!您瞧,那边……好像是京城送来的……”秦牧野的动作猛地顿住。
长枪“锵”地一声拄在地上,激起一小圈尘土。他眯起深邃锐利的眼眸,
循着陈忠指的方向望去。只见一顶小小的红轿子,在漫天黄尘里,像个微不足道的红点儿,
正艰难地、慢吞吞地朝军营这边挪动。那顶轿子,在粗犷荒凉的边关背景衬托下,
显得格外扎眼,也格外脆弱。秦牧野的心,没来由地“咯噔”沉了一下。眉头下意识地拧紧,
薄唇抿成一条冷硬的直线。京城……真给他送了个风吹就倒的瓷娃娃过来?这娇滴滴的闺秀,
能在这刀口舔血的地方活几天?他心里那点本就稀薄的、对婚姻的所谓期待,
瞬间被这顶小红轿碾得粉碎,只剩下一片烦躁。轿子终于晃晃悠悠地停在了校场边缘。
尘土渐渐散去,周围操练的士兵都好奇地放慢了动作,偷偷朝这边张望。空气仿佛凝滞了,
只剩下边关特有的、带着沙砾味道的风,呼呼地刮过。一只穿着鹿皮小靴的脚,
突兀地从轿帘底下伸了出来,稳稳地踩在了粗糙的地面上。那靴子沾满了尘土,却结实得很,
绝不是闺阁**的绣花鞋。紧接着,轿帘被一只同样沾着尘土的手猛地向上一掀!
力道大得带起一阵风。一道绛红色的身影利落地从轿子里钻了出来。劲装束腰,
勾勒出纤细却蕴含力量的腰肢和笔直修长的双腿。来人背上还斜挎着个小包袱,
头发因为长途颠簸有些毛躁,随意地束在脑后,几缕碎发贴在汗湿的额角。她站定,
抬手随意地抹了一把脸,露出一张明丽张扬的面孔。一双眼睛尤其亮,像刚出窝的狼崽子,
带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野性和好奇,
毫不闪避地扫视着眼前这片陌生的军营和那些盯着她看的彪悍军汉。最后,
那双亮得惊人的眼睛,精准地锁定了校场中央那个拄着长枪、气势最盛的男人。
燕绥宁单手叉腰,下巴微扬,清脆的声音带着点长途跋涉的沙哑,
却穿透了校场上的风声和士兵们压抑的呼吸声,直直地砸了过来:“喂!你就是秦牧野?
”她上下打量了他一番,眼神挑剔,像在集市上挑牲口,末了,竟还撇了撇嘴,
语气带着点显而易见的失望,“啧,长得也不丑嘛!跟传说的青面獠牙差远了!
害我白紧张一路。”秦牧野:“……”他身后的副将陈忠,脸憋得通红,
肩膀开始可疑地剧烈抖动,赶紧低下头,死死盯着自己的靴尖,生怕一个忍不住笑出声。
周围的士兵也纷纷低下头,校场上响起一片压抑的、此起彼伏的咳嗽声。青面獠牙?
秦牧野那张线条冷硬、在边关被风霜打磨得如同岩石般的俊脸上,
肌肉几不可查地抽搐了一下。他握着枪杆的手指,下意识地收紧了几分。
按照边关这边勉强凑合的婚礼流程,天刚擦黑,
秦牧野被一群挤眉弄眼、嘻嘻哈哈的兵油子推搡着,进了那间临时布置出来的“新房”。
屋内只点着两支粗大的红烛,光线昏黄摇曳。
桌上摆着几碟冷掉的、硬邦邦的馒头和一点咸菜疙瘩,算是喜宴的“余温”。
空气里弥漫着尘土和皮革的味道,实在没什么喜庆可言。
秦牧野看着床上那个端坐的、盖着红盖头的身影,心里那点烦躁又涌了上来。
他吐出一口浊气,勉强压下,迈着沉稳的步子走过去,准备按规矩掀盖头。
手刚伸到一半——那顶红彤彤的盖头,竟自己“呼啦”一下,猛地向上飞了起来!
盖头下露出的景象,让见惯了大风大浪的秦将军,也彻底僵在了原地。
他那新鲜出炉的“夫人”,正大马金刀地盘腿坐在铺着粗布的硬板床上!
一手抓着一条烤得焦黄流油、香气四溢的羊腿,另一手正奋力撕扯着上面的肉,
腮帮子塞得鼓鼓囊囊,油光蹭亮的小嘴还在不满地嘟囔着:“饿死了!饿死了!
你们边关的喜宴怎么回事?走了几个月,就给我吃这个?净是些噎死人的破馒头!
连口热乎肉汤都没有!早知道路上那只兔子就不该分给护卫……”她一边抱怨,
一边狠狠咬下一大块羊肉,吃得那叫一个投入忘我,仿佛眼前杵着的不是她的新婚丈夫,
而是根碍眼的木头桩子。秦牧野伸出去的手,就那么尴尬地悬在了半空中。
他看着眼前这毫无闺秀仪态、吃得满嘴流油的少女,再看看桌上那几碟可怜的冷馒头,
一股荒谬感直冲头顶。他深吸一口气,压下额角突突直跳的青筋,
过她油乎乎的手和那条显然不是边关军营能烤出来的羊腿(一看就是她路上自己猎的存货),
再落到她那双依旧明亮、此刻却只顾着食物的眼睛上。他突然开口,声音低沉,带着点试探,
也带着点不易察觉的、被冒犯后的火气:“你……会射箭吗?”燕绥宁正奋力跟羊腿较劲,
闻言,动作猛地一顿。她抬起头,油亮的嘴唇还沾着肉屑,
那双狼崽子似的眼睛瞬间亮得惊人,仿佛嗅到了猎物气息。她飞快地用袖子胡乱抹了把嘴,
动作粗鲁却带着一股子利落劲儿,下巴一扬,语气满是毫不掩饰的挑衅:“嘁!百步穿杨,
小菜一碟!怎么,想比划比划?”她眼珠滴溜溜一转,
目光落在他腰间悬挂着的那把镶嵌着绿松石的精致匕首上,狡黠地勾起嘴角,“光比没意思,
敢不敢赌点彩头?就赌你腰上那把匕首!我要是赢了,它就归我!”秦牧野的嘴角,
几不可查地向上扯动了一下,像是气笑了,又像是被激起了久违的好胜心。
他深深看了她一眼,那眼神锐利得像要剥开她这身皮囊,看看里面到底装了个什么怪物。
“好。”他干脆利落地吐出一个字,转身大步流星就往外走,“校场见。输了,别哭鼻子。
”“谁哭谁是孙子!”燕绥宁三两下把剩下的羊腿肉塞进嘴里,腮帮子鼓得像只松鼠,
含糊不清地应战,跳下床就追了出去,还不忘把那条啃得精光的羊腿骨顺手丢回桌上,
发出“哐当”一声响。一刻钟后,原本该归于寂静的校场,被无数火把照得亮如白昼。
闻讯而来的将士们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个个伸长脖子,兴奋得像是过年。
新夫人进门第一天就要跟将军比箭?这可是开天辟地头一遭的大热闹!
秦牧野和燕绥宁相隔百步,各自站定。燕绥宁掂量着手里的硬弓,
那是从旁边一个看热闹的弓箭手那里临时“借”来的。她试着拉了拉弓弦,点点头,还行。
随即屏息凝神,眼神瞬间变得专注锐利,方才啃羊腿时的野性莽撞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冷酷的沉静。她动作快如闪电,三支羽箭已同时搭在弦上!“嗡——!
”弓弦剧烈震颤!三道乌光撕裂空气,带着尖锐的厉啸,如同流星赶月,直扑百步外的箭靶!
“咄!咄!咄!”三声沉闷的入靶声几乎不分先后响起!火光下,清晰可见三支白羽箭,
成品字形,整整齐齐、分毫不差地钉在红心正中!箭尾的白羽还在微微颤动!“好——!!!
”短暂的死寂后,校场上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喝彩声!士兵们激动得脸都红了。这三箭齐发,
箭箭中靶心!这准头,这力道,这胆魄!神乎其技!秦牧野眼中掠过一丝极深的讶异,
随即化为更浓烈的战意。他缓缓抽出五支箭,动作沉稳如山岳。“嗖!嗖!嗖!嗖!嗖!
”他开弓引箭的速度快到让人眼花缭乱!五支箭并非同时射出,而是一箭快过一箭,
后箭追着前箭的尾羽,连成一条笔直致命的死亡之线!每一箭都精准无比地钉入箭靶红心,
将燕绥宁那三支箭牢牢地“钉”在了靶上!最后一箭的力道更是惊人,箭头深深没入木靶,
箭杆犹自嗡嗡作响!校场再次沸腾!将军的追风连珠箭,名不虚传!
燕绥宁看着被钉死的三支箭,非但没有沮丧,反而兴奋地舔了舔嘴唇,
眼中燃起熊熊火焰:“再来!”两人你来我往,箭矢破空之声不绝于耳。燕绥宁刁钻诡异,
时而连珠,时而弧线,专射活动靶;秦牧野则稳如磐石,箭箭追魂,力道刚猛。
一时间竟斗了个旗鼓相当,难分高下。最终,两人同时射向最后一个抛上半空的陶罐。
两支箭在空中精准地碰撞在一起,“咔嚓”一声脆响,双双折断,陶罐碎片四溅。平局!
“嗷——!!!”校场上的欢呼声几乎要掀翻夜空。将士们看得热血沸腾,嗓子都喊哑了。
看向燕绥宁的目光,已从最初的惊奇变成了彻底的狂热和敬佩。秦牧野放下弓,
深深地看着火光下那个因为兴奋而双颊绯红、眼睛亮得惊人的少女。心头那点轻视和烦躁,
如同晨雾遇见烈日,顷刻间消散得无影无踪。这哪里是什么一碰就碎的瓷娃娃?
分明是一头误入狼群、却比狼更凶悍的母老虎!他走过去,解下腰间那柄镶嵌绿松石的匕首,
递到她面前,声音低沉,带着一丝他自己都未察觉的沙哑:“你赢了。
”燕绥宁毫不客气地一把抓过,爱不释手地摩挲着冰凉的刀鞘和上面漂亮的纹路,
得意地扬起下巴:“那是自然!谢啦!”夜深人静,喧嚣散尽。
秦牧野躺在临时婚房那张硬邦邦的木板床上,翻来覆去,身下的木板发出不堪重负的吱呀声。
白天校场上的激烈交锋,少女亮得灼人的眼神,
还有那三支品字形的箭矢……一幕幕在他脑海里反复回放。他本以为的新婚夜,
该是红烛摇曳,软语温存,哪怕只是相敬如宾也好。可现实呢?他微微侧头,
看向睡在外侧的身影。燕绥宁睡得正沉,
怀里紧紧抱着她那把从京城带来的、刃口雪亮的短刀。红烛微弱的光映着她酣睡的侧脸,
褪去了白天的张扬,显出几分稚气。只是……她微微张着嘴,
喉咙里发出均匀而响亮的呼噜声,一声接一声,节奏感十足,在这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
简直像军营里打雷的战鼓。秦牧野:“……”他忍了又忍,那呼噜声却像魔音灌耳,
顽强地钻进他的脑子。他试着翻个身,背对着她。没用。那声音还是无孔不入。
他烦躁地叹了口气,终于忍不住伸出手,隔着被子轻轻推了推她的肩膀。
“喂……你……”他压低声音,试图唤醒她。睡梦中的燕绥宁眉头一皱,不耐烦地咕哝一声,
手臂下意识地一甩,差点把怀里的短刀砸他脸上。她含糊不清地嘟囔,
着浓重的睡意和被打扰的暴躁:“……吵死了……再吵……砍你……”秦牧野的手僵在半空,
额角的青筋又突突跳了起来。他瞪着身边这个睡得昏天黑地、还威胁要砍他的“夫人”,
半晌,挫败地收回手,认命地躺平,睁大眼睛望着房梁上简陋的椽子。看来今晚,
注定要与这惊天地泣鬼神的呼噜声为伴了。第二天清晨,
燕绥宁是被营地里飘来的、一股难以言喻的味道给熏醒的。
那是一种混合了陈年麦麸、粗盐和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腥膻气的味道,直往人鼻子里钻。
她揉着眼睛坐起身,秦牧野早已不见踪影。循着味儿找到伙房,
眼前的景象让她眉头拧成了疙瘩。几个伙头兵正围着几口巨大的铜釜忙碌,
锅里翻滚着灰褐色的糊糊,旁边堆着些黑乎乎、硬邦邦的杂粮饼子。士兵们排着队,
面无表情地领着一碗糊糊和两个饼子,蹲在角落里默默地啃着,
脸上看不出丝毫享受食物的愉悦。“这……就吃这个?”燕绥宁凑近看了看那糊糊,
又拿起一块饼子掂了掂,硬得能当砖头使。她忍不住咂舌,“喂马都比这个强吧?
”一个年长的伙头兵认得她,苦着脸道:“夫人有所不知,边关苦寒,粮草运输艰难,
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这糊糊是豆面混了麸皮,饼子是粗粮压的,顶饿!就是味道……咳,
差了点。”燕绥宁看着士兵们麻木啃饼的样子,再看看那锅毫无食欲的糊糊,
一股无名火就拱了上来。她二话不说,撸起袖子就冲进了伙房。“起开起开!都让让!
”她拨开几个愣住的伙头兵,动作麻利得像一阵风。眼睛在堆满食材的角落里一扫,
精准地锁定了角落里挂着的、半扇被风吹得干硬的羊肉。她二话不说,
抄起旁边一把沉重的厚背砍刀,“哐哐”几下,手起刀落,
利索地将冻得硬邦邦的羊肉剁成了大小均匀的肉块。那架势,比伙头兵剁菜还要熟练几分。
“大锅!烧热水!”她一边指挥,一边飞快地翻找。姜块?有!拍碎!干瘪的野葱?有!
切段!角落里居然还发现了一小袋压得严严实实的、颜色深沉的料粉?她凑近闻了闻,
眼睛一亮:“花椒大料?好东西!”大锅里的水很快沸腾。
燕绥宁将剁好的羊肉块“哗啦”一声倒进去,血沫翻滚。她抄起大勺,撇去浮沫,
动作干净利落。接着,姜块、葱段、那一小把珍贵的大料花椒,被她一股脑儿扔进锅里。
她抢过伙头兵手里的长柄大勺,用力在锅里搅动起来,让滚烫的水流充分包裹每一块肉。
“火!大火烧滚!然后转小火,慢炖!”她抹了把额头的汗,声音清脆,
带着不容置疑的指挥感。伙头兵们面面相觑,
又不敢违逆这位昨天刚在箭术上跟将军打了个平手的“新夫人”,只得依言照做。
时间一点点过去。浓郁的、霸道的、带着奇异香料气息的肉香,
开始顽强地从那口巨大的铜釜里钻出来,先是丝丝缕缕,继而越来越浓烈,像一只无形的手,
蛮横地撕开了伙房沉闷的空气,霸道地向整个营地蔓延开去。这股前所未有的香气,
仿佛带着某种魔力。操练的士兵们动作慢了下来,鼻子不自觉地翕动。
巡逻的队伍经过伙房附近,脚步明显变得拖沓。就连几里外正在执行潜伏任务的斥候小队,
都有人忍不住悄悄咽了下口水,低声嘀咕:“操……什么味儿?这么勾魂?”终于,
熬煮了近两个时辰的羊肉汤出锅了。汤汁呈现出诱人的奶白色,上面漂浮着点点金黄的油花。
大块的羊肉炖得酥烂脱骨,沉浮在浓郁的汤里。
那股融合了肉香、姜香和香料奇异辛香的浓郁味道,简直要把人的魂儿都勾出来。
秦牧野处理完军务,刚走到中军帐附近,就被这霸道无比的香气撞了个满怀。他脚步一顿,
锐利的目光投向伙房的方向。副将陈忠早已按捺不住,喉结上下滚动,眼睛都直了。
当一碗热气腾腾、撒了把翠绿野葱花的羊肉汤端到秦牧野面前时,他面上依旧没什么表情,
只是拿起勺子,舀起一勺浓汤,吹了吹,送入口中。滚烫、香浓、醇厚。
羊肉特有的鲜味被彻底激发出来,又被姜的辛辣和香料的复合味道巧妙地包裹、提升,
没有丝毫腥膻,只有满口的丰腴满足。那炖得酥烂的羊肉,入口即化,唇齿留香。
秦牧野没说话,只是动作沉稳地一勺接一勺,很快,一碗汤见了底。他放下碗,拿起筷子,
又夹起一块羊肉,仔细地吃干净。整个过程,表情平静无波,仿佛只是在完成一项例行任务。
直到三碗羊肉汤下肚,他才放下碗筷,拿起旁边一块还算干净的布巾擦了擦嘴角,
抬眼看向旁边正抱臂站着、一脸“快夸我”表情的燕绥宁,语气平淡无波,
听不出什么情绪:“还行。”燕绥宁期待的眼神瞬间垮了下去,嘴角不满地撇了撇。还行?
就这?她辛辛苦苦折腾半天!然而,秦牧野下一句话,
却是对着旁边同样吃得满嘴油光、正意犹未尽的陈忠说的,声音不大,
却清晰地传遍了整个鸦雀无声、都在偷眼瞧这边动静的伙房:“传令下去。
以后军营伙房一应事务,由夫人全权掌管调配。任何人,不得有异议。”说完,他起身,
看也没看燕绥宁脸上瞬间绽放的、比边关落日还要灿烂的笑容,径直大步走出了伙房。
燕绥宁正式在边关军营扎下了根,并且以一种惊人的速度混得风生水起,如鱼得水。
她接管伙房后,军营的伙食水平简直是翻天覆地。那口熬煮羊肉汤的大铜釜成了她的宝贝,
她变着花样地折腾:今天炖上大锅的杂粮豆粥,里面切上细碎的腌菜末和风干的肉粒,
热气腾腾,咸香开胃;明天用粗粮面掺上野菜碎,
烙成金黄喷香的薄饼;后天又不知从哪里搞来些河鲜小鱼,熬成浓白鲜美的鱼汤。
士兵们捧着碗,脸上不再是麻木,而是久违的、对食物的满足和期待。私下里,
都开始叫她“灶神娘娘”。她不仅管饭,还闲不住。
发现军营里有一小队负责后勤和救护的女兵,箭术平平,立刻来了精神,
自告奋勇当起了教头。校场一角,常能听到她清脆的呵斥声:“肩膀沉下去!腰发力!眼神!
眼神盯死靶心!你那箭飘得跟喝醉了似的!”女兵们被她操练得叫苦不迭,却又心服口服,
箭术肉眼可见地精进。她还认得不少草药,常背着个竹篓,
拉着军医营里须发皆白的老军医进山采药。边关的山野荒凉,却藏着不少宝贝。
她能准确地指出哪里长着止血的白茅根,哪里能找到消肿的蒲公英,
甚至还能找到几株罕见的、治疗风寒有奇效的紫花地丁。老军医看她的眼神,
从最初的怀疑变成了由衷的欣赏。最惊险的一次,
是跟着一队精锐斥候去抓一个混进附近集镇的北狄探子。那探子狡猾,
眼看就要混入人群逃脱。燕绥宁二话不说,抄起旁边斥候背着的硬弓,搭箭、拉弦、瞄准,
动作一气呵成,快如闪电!“嗖——!”一支羽箭破空而去,
精准无比地擦着那探子的头皮飞过,“咄”的一声,将他用来束发的簪子连同发髻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