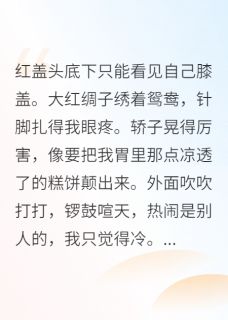红盖头底下只能看见自己膝盖。
大红绸子绣着鸳鸯,针脚扎得我眼疼。轿子晃得厉害,像要把我胃里那点凉透了的糕饼颠出来。外面吹吹打打,锣鼓喧天,热闹是别人的,我只觉得冷。
替嫁。
这两个字像冰锥子,从圣旨砸到楚家那天起,就扎在我心口上。嫡姐楚云瑶,京城第一美人,要死要活不肯嫁个瘫子王爷。爹娘舍不得眼珠子,我这个生母早逝、扔在后院长大的庶女,就成了顶包的那个。
“秋儿,这是你的造化!进了王府,你就是正经的王妃!”嫡母拍着我的手,指甲掐进我肉里,脸上堆着笑,眼里却淬着冰,“替云瑶享福去,懂吗?”
懂。怎么不懂?享一个残废王爷的福?享一个据说性情暴戾、克死三任王妃的活阎王的福?
轿子停了。喧闹声浪猛地扑进来。一只枯瘦、布满褐色斑点的手掀开轿帘,指甲缝里藏着陈年的泥垢。是王府派来的喜婆。
“王妃娘娘,请下轿。”声音嘶哑,像破锣。
我搭上那只手,冰凉刺骨。脚下是硌人的碎石子路。大红地毯从王府门口铺进去,像条淌血的路。
拜天地?没有。王爷“病弱”,一切从简。我被那喜婆半搀半拖,直接送进了洞房。
屋子很大,红烛高烧,熏得人头晕。空气里有股怪味儿,混着浓烈的药草香,底下还藏着一丝……像是东西腐烂了的甜腥气。
“王爷就在里间歇着。王妃娘娘,您……好生伺候着。”喜婆丢下话,逃也似的退出去,门“咔哒”一声落了锁。
心猛地一沉。锁门?
里间垂着厚重的帷幔,深紫色,密不透光。那怪味儿更浓了。我僵在原地,手脚冰凉。
“杵着当门神?”一个男人的声音突然响起,不高,带着久病的虚弱,却像冰渣子刮过耳膜,冷得瘆人。“过来。”
我深吸一口气,指甲掐进掌心,挪动步子。掀开帷幔。
一张巨大的紫檀木拔步床。床上半倚着个人。
这就是我的夫君,当朝七王爷,萧景夜。
烛光昏暗,映着他半张脸。苍白得没有一丝血色,薄唇抿成一条锋利的线。眼窝深陷,眼神却锐利得像淬了毒的刀子,直直刺过来。下半身盖着厚厚的锦被,纹丝不动。
他比我想象中更年轻,也更……死气沉沉。像一尊蒙尘的玉雕,美则美矣,却透着腐朽的寒意。
“楚家……胆子不小。”他扯了扯嘴角,那笑比哭还难看,“弄个丫头片子来糊弄本王?”
我腿肚子发软,扑通跪在冰冷的地砖上。“王爷明鉴!臣女……臣女……”嗓子发干,后面的话卡住了。怎么说?说我是被逼的?说楚家欺君?
“楚云瑶?”他声音里听不出喜怒。
“臣女……楚秋。”我低着头,盯着自己磨破的绣花鞋尖。
“楚秋?”他重复一遍,尾音拖长,带着点玩味,“秋天的秋?倒是个……扫落叶的命。”
这话像针,密密地扎过来。
“起来。”他命令道,“看着本王。”
我撑着地,勉强站起,膝盖生疼。抬眼撞进他深不见底的眸子里。那里没有愤怒,没有惊讶,只有一片死寂的冰原。
“本王废人一个,活死人罢了。”他语气平淡得像在说别人,“嫁进来,就是守活寡,跟守陵没两样。怕吗?”
怕。怕得要死。但怕有用吗?
“臣女……不怕。”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抖。
他嗤笑一声,极其轻微,却满是嘲弄。“不怕?那就好。从今往后,你就是这活死人墓的守墓人。”他指了指床脚一个落满灰的矮凳,“坐那儿。本王……要睡了。”
说完,他闭上眼,不再看我,仿佛多看一眼都嫌累。
我像个木头人,挪到矮凳边坐下。冰冷的木头硌着骨头。红烛噼啪爆了个灯花。外头隐隐约约的喧闹彻底没了,死一样的寂静裹上来,压得人喘不过气。只有他极其微弱、时断时续的呼吸声,证明床上躺着的是个活物。
活死人墓。他说得真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