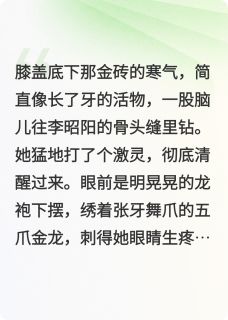膝盖底下那金砖的寒气,简直像长了牙的活物,一股脑儿往李昭阳的骨头缝里钻。
她猛地打了个激灵,彻底清醒过来。眼前是明晃晃的龙袍下摆,绣着张牙舞爪的五爪金龙,
刺得她眼睛生疼。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极其压抑的沉滞,仿佛凝固的胶水,吸一口都费劲。
她下意识地攥紧了手里的东西——触感粗糙,带着点诡异的黏腻。低头一看,
李昭阳的脑子“嗡”的一声,像被重锤狠狠砸了一下。
一张皱巴巴、边缘甚至带着干涸暗红色污渍的纸!上面歪歪扭扭爬着几行字,
墨迹被不知是水还是别的什么洇开,糊成一团。她费力地辨认:“顾郎,你若不娶我,
我便剃了头发当姑子去!”落款处,三个字触目惊心——昭阳公主。
下面还摁着一个清晰的、鲜红的手印!**?!一股凉气瞬间从脚底板窜上天灵盖,
激得她头皮发麻。电光石火间,不属于她的记忆碎片,如同被砸开的蜂巢,轰然涌入脑海!
《霸道状元的小娇妻》!
活、最后被小白花女主设计嫁给暴戾安南王、不到半年就“病逝”的炮灰女配——昭阳公主!
“李!昭!阳!”一声怒喝,如同炸雷在死寂的御书房里爆开,
震得房梁上的灰尘似乎都在簌簌往下掉。龙案后头,当今圣上,她的皇帝舅舅,
一张脸气得铁青,胡子根根倒竖,随着他粗重的喘息剧烈地抖动着,像是随时要飞离下巴。
他手指颤抖地指着她,指尖几乎要戳到她的鼻尖:“你!你堂堂天家公主!金枝玉叶!
竟…竟给新科状元写这种东西?!还…还摁血印?!皇家颜面何存!祖宗的脸都让你丢尽了!
”李昭阳僵硬地转动眼珠,看向皇帝舅舅手指的方向。
御书房那冰凉的、光可鉴人的金砖地上,离她几步远的地方,跪着另一个人。
一身簇新的状元红袍,本该是意气风发,此刻却衬得他那张脸比身下的地砖还要惨白几分,
毫无血色。他死死低着头,身体控制不住地微微发颤,仿佛下一秒就能直接厥过去。
新科状元,顾行之!原主那要死要活的对象!李昭阳的心脏像是被一只冰冷的手狠狠攥住,
又猛地提起,悬到了嗓子眼。完犊子!这不是开局即地狱吗?原主这恋爱脑晚期患者,
临了还给她挖这么大一个坑!御前递**逼婚?这跟坟头蹦迪有什么区别?按原剧情,
再过不久,那小白花女主就该闪亮登场,然后就是她被迫嫁给安南王那个变态,
香消玉殒的结局!不!绝对不行!求生的本能如同火山爆发,
瞬间压倒了所有初来乍到的茫然和惊惧。巨大的恐惧攫住了她,身体比脑子更快一步,
她猛地一个哆嗦,几乎是手脚并用地扑向地上那张沾血的纸!“撕拉——!
”清脆的裂帛声在落针可闻的御书房里显得格外刺耳。“舅舅!我错了!
”李昭阳的声音又尖又利,带着破音的嘶哑和孤注一掷的决绝,她双手并用,
疯狂地撕扯着那张承载着原主疯狂和愚蠢的“情书”,“我不喜欢他了!真的!
我一点都不喜欢顾行之了!我要退婚!现在就退!”纸屑如同惨白的雪花,
纷纷扬扬从她颤抖的指间飘落,落在冰冷的金砖上,落在她跪着的裙裾上。
时间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皇帝舅舅张着嘴,那滔天的怒火僵在脸上,像是凝固的雕塑,
只剩下胡子尖还在惯性般地微微颤动。他瞪圆了眼睛,
难以置信地看着地上那个状若疯癫的外甥女,仿佛第一次认识她。顾行之的颤抖猛地停住了,
他倏地抬起头,惨白的脸上是极致的震惊和茫然,连呼吸都似乎停滞了。他死死盯着李昭阳,
眼神复杂得像一团乱麻——惊愕、错愕、一丝不易察觉的…如释重负?还有深不见底的疑惑。
整个御书房陷入一种诡异的、令人窒息的安静。只剩下李昭阳粗重的喘息,
和纸屑落地时细微的沙沙声。“你……”皇帝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
带着浓重的狐疑和审视,他眯起眼,锐利的目光像刀子一样刮在李昭阳脸上,
“又想闹什么幺蛾子?以退为进?还是嫌朕刚才骂得不够狠?”李昭阳深吸一口气,
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她猛地挺直了腰板,抬起沾了点灰和纸屑的脸,
努力绷出一副“幡然醒悟”、“大彻大悟”的凛然表情,声音斩钉截铁:“舅舅!
昭阳以前糊涂!被猪油蒙了心!从今往后,昭阳要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她顿了顿,
用尽全身力气喊出那个在她看来无比正当、在此刻却石破天惊的理由:“我要搞事业!
为国为民!为江山社稷发光发热!婚约?那是什么玩意儿!太耽误我赚钱…啊不是,
太耽误我为国分忧了!”掷地有声!皇帝舅舅:“……”顾行之:“……”空气再次凝固。
皇帝的表情从暴怒到狐疑,再到此刻的…一种难以言喻的空白。
他像是第一次认真打量这个从小看着长大、却从未真正了解过的外甥女。顾行之则完全懵了,
搞事业?为国为民?耽误赚钱?
这还是那个为了见他一面能在宫墙外淋一夜雨、为了逼他表态敢在御前递**的昭阳公主吗?
就在这死寂的、几乎要令人窒息的安静里,李昭阳眼角的余光,
极其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丝微小的动静。在御书房最不起眼的角落里,
光线略显黯淡的雕花窗棂旁,一道颀长的身影一直安静地伫立着,仿佛融入了背景。
他穿着极为素雅的月白色常服,身姿挺拔如松,气质清冷似雪后初霁的远山。
方才那场闹剧似乎全然与他无关,他只是个沉默的旁观者。然而此刻,
就在李昭阳喊出“搞事业”三个字时,那个清冷如谪仙的男人,
唇角极其细微地、几乎难以察觉地向上弯了一下。那弧度极小,转瞬即逝,快得像幻觉。
可李昭阳确定自己看见了!那绝不是错觉!太傅谢韫!原书里顾行之最大的金大腿,
清冷孤高,不沾凡尘,连原书女主使出浑身解数都未能靠近分毫的冰山!李昭阳的心跳,
因为这惊鸿一瞥的淡笑,莫名地漏跳了一拍,随即涌上更深的警惕。这尊大神,他在笑什么?
看戏吗?还是觉得她疯了?***退婚的顺利程度,远远超出了李昭阳最乐观的想象。
皇帝舅舅被她那番“为国为民搞事业”的宣言震得半晌回不过神,又见她撕了**,
态度坚决得像是换了个人,最终半是狐疑半是疲惫地挥了挥手,算是默许。
他甚至没多问一句她打算搞什么“事业”。至于顾行之,那份急切更是溢于言表。
生怕李昭阳只是抽风,下一刻就会反悔扑上来继续纠缠。几乎是皇帝默许的旨意刚下,
当天下午,顾行之就亲自把两人的庚帖恭恭敬敬地退回了公主府,速度快得令人咋舌。
一同送来的,还有一个描金绘彩、做工精致的食盒。李昭阳的贴身大宫女春桃,
小心翼翼地捧进来,脸上带着点古怪的表情:“殿下,顾大人…呃,顾状元差人送来的,
说是…聊表心意,愿与殿下好聚好散。
”李昭阳正对着满库房的绫罗绸缎和金银珠宝发愁——这些都是原主攒下的“嫁妆”,
现在看着只觉得累赘。闻言,她挑了挑眉,走过去掀开食盒盖子。
一股甜腻的桂花香气扑面而来。食盒里,
整整齐齐码着八块晶莹剔透、点缀着金黄桂花的糕点。品相极佳,显然是精心准备的。“呵,
”李昭阳嗤笑一声,毫不掩饰脸上的讥诮,“好聚好散?
怕是巴不得这辈子都别再跟我扯上关系。”她随手拈起一块桂花糕,指尖传来温软的触感,
却只觉得腻味。原主对这味道爱得痴狂,
只因顾行之曾在某个诗会上随口赞过一句“秋日桂花,清雅宜人”。如今看来,这“心意”,
廉价又可笑。她没半点犹豫,扬手就把那块精致的糕点丢回了食盒里,
发出“啪嗒”一声轻响,对春桃道:“拿去,给御膳房后头那群野猫加餐。就说本宫赏的,
让它们也尝尝这状元郎的‘好意’。”春桃瞪大了眼,有些难以置信:“殿下?
这…这可是御香斋最好的桂花糕…”就这么喂猫?“怎么?本宫的话不管用了?
”李昭阳斜睨她一眼,语气淡淡,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势,“还是说,你也想尝尝?
”春桃一凛,连忙低下头:“奴婢不敢!奴婢这就去!”捧着那盒价值不菲的桂花糕,
脚步匆匆地退下了,心里却掀起惊涛骇浪。殿下她…真的不一样了!退婚的第二天,
李昭阳就雷厉风行地搬出了象征着尊贵与束缚的公主府。她只带了四个信得过的宫女太监,
几箱换洗衣物和书籍,以及从库房里精挑细选出来、方便变现的金银细软,轻车简从,
直奔城西空置已久的永安坊。这消息像长了翅膀,瞬间点燃了整个京城的八卦之火。
茶楼酒肆,街头巷尾,议论纷纷。“听说了吗?昭阳公主被状元郎给甩了!哭天抢地的,
连公主府都待不下去了!”“啧啧,可不是嘛!听说直接搬到城西那破落户才住的永安坊了!
那地方,又偏又旧!”“唉,到底是金枝玉叶,受不得这打击,怕是要寻短见吧?
”“谁知道呢,皇家的事,乱得很……”李昭阳坐在摇摇晃晃驶向永安坊的马车上,
听着外面隐约飘进来的议论,白眼都快翻到天灵盖了。伤心欲绝?寻短见?呵!
她李昭阳的人生字典里,从今往后就没有“为男人要死要活”这几个字!
马车在永安坊一处略显破败但还算宽敞的宅院前停下。朱漆大门斑驳,门环锈迹明显,
院墙也显露出岁月的痕迹。李昭阳跳下马车,
深吸了一口这城西带着点市井烟火和淡淡尘土味的空气,只觉得无比畅快!自由的味道!
她没理会周围探头探脑、指指点点的目光,径直走到紧闭的大门前,
从随身包袱里摸出一块早就准备好的、用墨汁写得歪歪扭扭的木牌,踮起脚,“啪”的一声,
稳稳挂在了门框的钉子上。木牌上赫然几个大字——【昭阳书局】。
下面还有一行清晰的小字:招女掌柜,月银十两,包三餐。木牌在微风中轻轻晃荡,
简陋得有些可笑,却像一个无声的宣言,砸进了围观人群的眼里。“书局?公主开书局?
”“招女掌柜?还包三餐?十两银子?疯了吧?
”“怕不是把《女诫》《女则》绣成帕子拿出来卖吧?哈哈哈!”“走走走,过几天开业,
非得来看看这热闹不可!”议论声更大了,充满了不解、嘲讽和浓浓的好奇。
李昭阳拍拍手上的灰,对身后目瞪口呆的春桃等人咧嘴一笑,露出一口小白牙:“行了,
别愣着,开工!打扫!咱们的‘事业’,就从这块破牌子开始了!
”***昭阳书局开业那天,场面之“盛大”,远超李昭阳的预期。
永安坊那条原本不算宽敞的街道,被人群挤得水泄不通。乌泱泱的脑袋攒动着,男女老少,
贩夫走卒,甚至还有不少伸着脖子看热闹的读书人。嗡嗡的议论声汇成一片嘈杂的海洋。
“挤什么挤!让让!让爷看看公主殿下能弄出什么花儿来!”“听说里面全是绣花的书?
真的假的?”“别瞎说!没看那牌子上写着‘书局’吗?肯定是卖书的!”“公主卖书?
她能看懂几本?别是拿《三字经》当宝贝卖吧?哈哈哈!”“嘘!小声点!人出来了!
”吱呀一声,那扇斑驳的朱漆大门被两个小太监从里面拉开。
李昭阳穿着一身利落的鹅黄色窄袖襦裙,头发简单地挽了个髻,只簪了一支素银簪子,
脸上脂粉未施,却神采奕奕。她站在门槛内,目光扫过门外黑压压的人群,
脸上没有丝毫怯场,反而扬起一个灿烂又带着点狡黠的笑容。“诸位父老乡亲!
”她声音清亮,穿透了嘈杂,“感谢大家伙儿捧场!今儿个我李昭阳这书局开张,
不卖绣花帕子,也不卖什么高深的之乎者也!”她故意顿了顿,吊足了所有人的胃口,
才猛地一扬手,“掀!”随着她一声令下,
覆盖在门内大堂中央巨大物件上的大红绸布“哗啦”一声被扯落!
阳光透过敞开的大门照射进去,落在那些奇特的木质框架上。瞬间,
整个现场像是被施了定身法!只见大堂中央,整齐排列着好几排造型奇特的木架子。
架子旁站着几个穿着统一干净短打的伙计。随着李昭阳一个眼神示意,
伙计们动作熟练地操作起来。他们拿起一块块排列着小方块的木板(字模),蘸了墨,
放入一个带框的板中,覆上纸张,再用一个平整的木头刷子用力一压、一刷!
“咔哒…咔哒…哗啦…”清脆而富有节奏的机械运转声响起!那些木质的框架、连杆、滚轴,
在伙计们灵巧的操作下,如同被赋予了生命,开始精密地咬合、转动、压印!
动作流畅得令人眼花缭乱。一张张雪白的纸张,如同被施了魔法,
源源不断地从机器末端吐出来!速度快得惊人!纸上清晰地印着工整的墨字!
方才还喧闹的人群,此刻死寂一片。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张大了嘴巴,
像是一群被掐住了脖子的鸭子。连那些准备看笑话的读书人,脸上的嘲讽也瞬间凝固,
化为极致的震惊!“天…天爷啊!那…那是什么仙家法宝?”“纸!好多纸!印得真快!
真清楚!”“看!印出来了!又一张!
”“这…这比那些书铺里老雕工吭哧吭哧刻半天快多了啊!”惊呼声如同潮水般,
一波高过一波,瞬间淹没了之前的嘲讽。李昭阳满意地看着众人的反应,走到第一台机器旁,
拿起一张刚刚印好、墨迹未干的纸张,高高举起,朗声道:“诸位!此乃‘活字印刷术’!
印得快,印得多,印得便宜!今日开业,首印两本书!”她指向旁边早就备好的一摞书,
“其一,《农耕指南》!教大家如何选种、育苗、防虫、堆肥,包你地里多打粮!其二,
《女则新编》!不教你怎么伺候男人,专教女子如何管家、算账、明事理、立身持家!
”她的话音刚落,人群就炸开了锅!“《农耕指南》?真能多打粮?快!给我来一本!
我爹种了一辈子地,也没书上说得明白!”“《女则新编》?管家算账?这…这能行吗?
给我家闺女也带一本!”“掌柜的!给我留一本!《农耕指南》!”“《女则新编》!
我要两本!给我家婆娘和小妹!”刚才还只是看热闹的人群,瞬间化身为抢购大军。
伙计们刚把书搬到门口临时支起的摊位上,就被一抢而空!后面的人拼命往前挤,
场面一度混乱。李昭阳早有准备,指挥着几个身强力壮的太监维持秩序,收钱找零,
忙得不可开交。“别急别急!都有!机器在印着呢!保证供应!”李昭阳嗓子都快喊哑了,
脸上却笑开了花,手里铜钱银角子叮当作响,那声音比什么仙乐都好听。就在这时,
一种奇异的感觉让她下意识地抬起头,越过攒动的人头,向人群的最后方望去。那里,
不知何时安静地站了一个人。月白色的长衫,在周遭粗布麻衣的人群中显得格外清逸出尘。
他身形挺拔,面容清俊,眉宇间仿佛凝结着终年不化的霜雪,气质疏离,
正是那位御书房角落里的“冰山”太傅——谢韫。
他手里拿着一本刚刚买到的《九章算术》翻印本,正低头看着。似乎是察觉到李昭阳的目光,
他缓缓抬起头。四目,隔着喧嚣的人群,猝然相接。李昭阳脸上的笑容微微一滞,
心头莫名一跳。这位大神怎么来了?来看她笑话?
还是来替他的“得意门生”顾行之打探敌情?谢韫的目光清冷依旧,但在那层冰霜之下,
李昭阳似乎捕捉到了一丝极其细微的、与上次御书房如出一辙的……兴味?他隔着人群,
对着李昭阳的方向,极其轻微地点了下头,算是见礼。接着,李昭阳就看到他薄唇微启,
清越而平静的声音,竟神奇地穿透了周围的嘈杂,
清晰地传到她耳边:“殿下这活字印刷之术,构思奇巧,化繁为简,利在千秋。
着实令人叹服。”不是嘲讽,不是质疑,是实实在在的……赞叹?
李昭阳心头那点警惕瞬间飙到了顶点。事出反常必有妖!这位顾行之的金大腿,
人设崩得有点厉害啊!她下意识地后退了半步,像只竖起浑身尖刺的刺猬,
语气带着十二分的戒备:“太傅过誉。怎么,您今日前来,也想买书?《九章算术》?
还是…《女则新编》?”她故意加重了后一本书名,带着点挑衅。
谢韫似乎并未察觉她的敌意,或者说,毫不在意。他垂眸看了一眼手中的书,复又抬起眼,
目光平静无波地落在李昭阳脸上,声音依旧是那种清泉击石般的冷淡调子,
说出的话却石破天惊:“书,臣已买了。不过,臣今日前来,是想与殿下谈一桩生意。
”他顿了顿,清晰地说道:“臣想买下这书局三成股,不知殿下,可愿割爱?”“???
”李昭阳脑子里瞬间塞满了巨大的问号,几乎要溢出来。
她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被太阳晒晕了,出现了幻听。买股?入股?
这位清冷孤高、不食人间烟火、据说连俸禄都懒得管的谢太傅,
居然主动提出要入股她这个刚刚开张、前途未卜的小书局?还是在这种大庭广众之下?大哥,
你的人设崩得连渣都不剩了好吗?!你真的是那个传说中连女主都搞不定的高岭之花谢韫?
李昭阳看着那张俊美却毫无表情的脸,第一次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活久见”。
***尽管李昭阳内心疯狂吐槽,对谢韫的动机充满了十万个为什么,但理智告诉她,
这桩买卖,划算!谢韫是谁?当朝太傅,清流领袖,天子近臣!
他背后代表的是庞大的人脉网络、顶尖的学术资源,以及难以估量的隐形声望。有他入股,
等于给她的书局盖上了一块金光闪闪的“免死金牌”和“品质保证章”。至于他图什么?
李昭阳暂时想不明白,索性不想。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先把眼前的好处捞到手再说!
反正她光脚不怕穿鞋的。事实证明,李昭阳这笔“买卖”做得极其明智。谢韫入股后,
带来的效应几乎是立竿见影的。首先便是订单。原本书局主要面向的是普通市民和农户,
印些实用手册。谢韫入股后的第三天,
一辆辆装饰雅致的马车便停在了永安坊略显寒酸的巷口。
下来的是国子监的博士、翰林院的学士,甚至还有几位在文坛德高望重的老先生。
他们或拿着书单,或带着自己的诗文手稿,指名要找“谢太傅入股的书局”印书。
清流名士的圈子被悄然撬动,订单量瞬间翻了几番。其次,便是技术上的“意外之喜”。
书局里那几台宝贝活字印刷机,在李昭阳看来已经是跨时代的发明,但毕竟是初期版本,
问题不少。最烦人的就是卡纸。印着印着,纸张就容易在滚轴那里堆叠卡住,轻则耽误工夫,
重则撕坏印好的书页,浪费纸张墨汁,让李昭阳心疼得直抽抽。一天下午,
谢韫恰好来查看账目(虽然李昭阳严重怀疑他只是找个理由来看看他的“投资”)。
他安静地站在一台正在运转的机器旁,看着伙计皱着眉,又一次小心翼翼地处理卡住的纸张。
他看得很专注,清冷的眸光在那复杂的木质结构上缓缓移动,仿佛在拆解其中的奥秘。
看了约莫一刻钟,就在李昭阳准备招呼他喝茶时,谢韫忽然转身,
对旁边一个正在用竹片削东西的小学徒道:“竹片,给我。”小学徒一愣,
傻乎乎地把手里削了一半的竹片递了过去。只见谢韫接过那半片竹片,
又从工具箱里拿起一把小刻刀。他修长的手指异常稳定,刻刀在他手中如同有了生命,
在坚硬的竹片上飞快地切削、打磨。动作行云流水,带着一种奇特的韵律感,
完全不似他平日执笔批阅奏章的模样。李昭阳和伙计们都看呆了。不过盏茶功夫,
几个小巧玲珑、边缘打磨得极为光滑、带着精密锯齿的小圆轮出现在谢韫掌心。
他走到那台卡纸的机器旁,蹲下身,仔细观察了一下滚轴连接处的结构。然后,
他拿起其中一个竹片小齿轮,对着一个位置比划了一下,
又用小刻刀在木轴上极其精准地刻出几个浅浅的凹槽。接着,他拿起另一个略大些的竹齿轮,
套在相邻的另一根轴上。两个竹齿轮的齿牙,严丝合缝地咬合在了一起。“试试。
”谢韫站起身,用他那清冷无波的声线吩咐道,顺手拿起旁边一块干净的布巾,
慢条斯理地擦拭着沾了竹屑的手指。伙计将信将疑地重新放纸、刷墨、启动机器。
“咔哒…咔哒…哗啦…”机器运转起来。这一次,纸张如同被无形的丝线牵引着,
无比顺畅地通过滚轴,再也没有出现一丝卡顿!运转得丝滑无比,
简直像后世广告里说的“纵享丝滑”!“天!神了!”伙计惊喜地叫出声。
李昭阳看得目瞪口呆,嘴巴微张,好半天才找回自己的声音,
带着浓浓的不可思议:“太傅…您…您还懂木匠活?”谢韫擦干净手,将布巾叠好放在一旁,
闻言,眼皮都没抬一下,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略懂。
”李昭阳:“……”略懂?您管这叫略懂?!这手艺,放现代至少是个八级钳工!
她感觉自己对这位冰山太傅的认知,再次被刷新了。后来,
她才从一些旧日宫人的闲谈中拼凑出一点信息。原来这位“略懂”的太傅,
年少时曾在工部观政三年,并非只读圣贤书。据说宫里那座用来计时的巨大铜漏,
计时不准的问题,就是他当年改良解决的。有了这位“技术入股”的大神坐镇,
书局的运转效率和质量都提升了一大截。李昭阳数着账面上日益增长的数字,
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事业”带来的踏实感和成就感。腰包鼓了,胆子也壮了。
李昭阳那颗“搞大事”的心又开始蠢蠢欲动。书局后院原本堆满了杂物和备用木料,
地方不小。李昭阳大手一挥,让人清理出来,简单粉刷修葺,购置了桌椅板凳,
挂了块新牌子——【昭阳女学】。她的目标很明确:专教女子读书识字,基础算账,
管家理事。不求培养什么才女,只求让她们多懂些道理,多掌握些安身立命的本事,
别一辈子只围着锅台和男人转。“读书明理,算账管家,是立身的本事!学了,
至少能看懂契约,算清账目,管好自己的嫁妆体己,将来在婆家腰杆子也能挺直些!
”李昭阳站在简陋的讲台上,
被家人送来、或好奇或怯生生的女孩子(大多是书局雇员的女儿或附近家境尚可的商户女),
侃侃而谈,话语直白又充满鼓动性。然而,这消息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巨石,
瞬间掀起了滔天巨浪。最先炸锅的是朝堂。“荒谬!简直是荒谬绝伦!”御史台的王老大人,
须发皆白,此刻气得胡子直抖,在朝会上捶胸顿足,
痛心疾首地指着李昭阳(她因书局和农具改良之功,被特旨允许列席旁听),
声音洪亮得能掀翻太和殿的屋顶,“女子无才便是德!此乃古训!公主殿下开什么女学?
教女子读书算账?抛头露面,成何体统!此风一开,牝鸡司晨,阴阳颠倒,纲常败坏!
有伤风化!有辱斯文!老臣恳请陛下,即刻下旨,查封此等祸乱之所!
”唾沫星子几乎要喷到李昭阳脸上。满朝文武,不少人纷纷点头附和,
看向李昭阳的目光充满了不赞同和鄙夷。连皇帝舅舅都皱紧了眉头,
显然也觉得她这步子迈得太大、太出格。李昭阳站在大殿中央,
承受着四面八方或质疑或谴责的目光,脊背却挺得笔直。她早有准备。“王大人,
”她不慌不忙地开口,声音清越,压过了朝堂上的嗡嗡议论,“您老说女子读书有伤风化?
那请问,何为风化?”不等王御史反驳,她直接朝殿外喊道:“春桃!
”早已等候在殿外的春桃,立刻捧着一本厚厚的册子快步进来,恭敬地递给李昭阳。
李昭阳接过册子,刷拉一声翻开,高高举起,朗声道:“这是我昭阳女学首批十六位女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