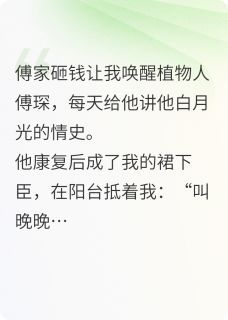傅家砸钱让我唤醒植物人傅琛,每天给他讲他白月光的情史。我坐在床边讲得投入,
突然对上他睁开的眼睛:“你声音很像她,但故事都是编的。”他康复后成了我的裙下臣,
在阳台抵着我:“叫晚晚,我的晚晚。”直到白月光婚礼请柬寄来,
他揉皱扔进海里:“晦气。”我笑着递上孕检单,
却被他掐住下巴:“你以为怀个野种就能取代她?”海水淹没我时,妹妹短信亮起:“姐,
医生说我的手术费……”傅琛后来疯了一样翻我的包,掉出本密码日记。
最后一页贴着他车祸前**我的照片:“找到她了,可怎么让她不逃?
”暴雨像是谁在天上撕开个口子,不要命地往下倒。
林晚晚费力地撑着一把被风吹得变了形的伞,另一只手紧紧攥着身边男人的手臂。
傅琛的步子迈得大,带着大病初愈的疏离和一种她看不透的烦躁。雨水冰冷地钻进她的后颈,
冻得她骨头发僵。黑色的迈巴赫安静地停在医院门口,像一头蛰伏的巨兽。
侍者恭敬地拉开车门,傅琛几乎是拖着林晚晚把她塞了进去。车内空间宽大奢华,
隔绝了外面喧嚣的暴雨和寒意,暖气丝丝缕缕地渗入毛孔,
却驱不散林晚晚心里沉甸甸的冰渣。傅琛重重地摔进真皮座椅,
湿透的昂贵衬衫贴着他宽阔紧实的肩背。他闭着眼,紧皱的眉头如同刀刻。林晚晚抽出纸巾,
习惯性地探身想替他擦掉发梢的水珠。指尖还未触及,
那双紧闭了整整五年、方才在病房里搅动起一片惊天波澜的眼睛,倏地睁开了。
漆黑的瞳孔深处没有一丝劫后余生的庆幸或虚弱,
只有纯粹的、淬了冰的审视和一股令人胆寒的戾气。那眼神像无形的冰锥,
精准地穿透雨声和车内的暖意,直扎在林晚晚僵硬的手指上,冻得她血液都停了一瞬。
她仓促地收回手,指尖蜷在微冷的掌心,用力到指尖发白。
车子在傅家那栋森严如同堡垒的临海别墅前停下。下车时,
一阵更加猛烈的横风卷着雨鞭狠狠抽来。傅琛忽然伸出手臂,用一种不由分说的霸道姿态,
将几乎要被风掀倒的林晚晚一把揽进怀里,用自己的身躯充当屏障。
冰冷湿透的布料紧紧贴着她单薄的家居服,
他胸膛的起伏隔着两层湿透的衣料清晰地传递过来,带着一种陌生的、滚烫的温度。
林晚晚的身体瞬间绷成了一张拉满的弓,纤细而脆弱。别墅大厅璀璨的水晶吊灯,
像无数只冰冷的眼睛,照亮傅家那些早已得到消息、垂手肃立的管家佣人惊疑揣测的脸。
时间仿佛凝滞了一秒,每一道打量的目光都像带着细小的倒钩,无声地刮擦着她敏感的神经。
他臂弯传来的滚烫力道和这无处不在的注目礼,让她恍惚间像是置身于一场光怪陆离的噩梦。
“都下去。”傅琛的声音不高,却清晰地穿透雨声,带着不容抗拒的威压。众人如蒙大赦,
迅速无声地退散,偌大的客厅瞬间只剩下窗外无尽的雨啸,
还有两人彼此交缠又被放大得过分清晰的呼吸。傅琛终于松开了她,
动作随意得像丢开一件不再需要、沾了污渍的工具。林晚晚踉跄一步才站稳,
脸颊的热度还未完全褪去,心却像失了重般直往下坠。她抬起眼,撞入傅琛的视线里。
他正漫不经心地、一根一根地解开自己衬衫袖口湿透的宝石纽扣,
露出一截苍白却肌理清晰的小臂。他的目光扫过她苍白的脸颊、微微发抖的嘴唇,
最终落在她潮湿卷曲的发梢上。那眼神,专注得让人心慌。蓦地,他低笑出声,
薄唇勾起一个毫无温度的、近乎邪气的弧度。长臂倏然一伸,带着未散的水汽,
骨节分明的手指猝不及防地擒住了林晚晚小巧的下颌。力道不轻,带着一种绝对的掌控欲,
强迫她仰头直视他深渊般的眼。“以后……”他的气息扑近,
带着一丝雨后松针的冷冽和她看不懂的玩味,拂过她的耳廓和颈侧敏弱的皮肤,
激得她浑身颤栗,“叫我傅琛。”林晚晚的心跳几乎停滞。
那两个字——傅琛——像一个古老的、被封印的禁忌字符,沉重地压在她的舌尖上。
过去五年,她只在文件末尾、合同签名处见过这两个凛冽锐利的字迹。更多时候,
她在他的私人领域里,扮演的角色需要一个更为亲昵的称呼。
和那叠厚厚的、写着冷酷条例的协议所赋予的名字……曾是她无数个深夜里辗转挣扎的枷锁,
也曾在某个连自己都快要骗过的恍惚瞬间,成为她卑微依恋里的唯一支点。
此刻这突如其来的转变,像骤然崩断的琴弦,割得她心口一阵锐痛。他让她称呼他的名字,
是终于……要把那层可悲的薄纸彻底捅破,让她彻底认清自己是谁了吗?
看着她的瞳孔因为惊惧而一点点放大,像受困小鹿湿漉漉的眼,傅琛唇角的弧度更深了几分,
带着一丝近乎残忍的欣赏。他慢条斯理地俯下身,鼻尖几乎要碰到她冰凉的额头,
声音压得更低,如同情人间的耳语,却淬着危险的毒液:“乖,现在就叫一声。
傅琛……我的名字。”滚烫的气息拂过她的皮肤,像烙铁一样烫人。
林晚晚只觉得空气都成了粘稠的岩浆,每一次呼吸都灼痛她的喉咙。
被他指尖钳制的地方隐隐作痛,下巴被迫抬起的角度让她脆弱的脖颈暴露无遗。
在那双如同猎食者锁定了孱弱猎物般的目光注视下,
一股从未有过的、令人窒息的恐惧感扼住了她的呼吸。五年。
整整五年她守在这座金色牢笼里,用另一个女人的身份和名字,
对着他沉睡的躯壳讲述另一个女人的爱与恨。她熟悉他紧闭的眉眼弧度,
记得他每一次微弱的呼吸频率,甚至比他自己的家人更敏锐地察觉过他指腹的温度变化。
她看着他一点点被各种顶尖仪器和名贵药物维系着生命,
如同隔着玻璃窗观看一件精美却遥不可及的藏品。她像一个虔诚又蹩脚的演员,
日复一日地念诵着不属于自己的剧本,连名字都是偷来的。那五年的光阴,
连自己都不敢细究的疲惫和某些隐秘疯狂的期待……在此刻傅琛清醒的、全然陌生的凝视里,
在“傅琛”这两个字沉沉压下的瞬间,轰然碎裂。心脏在胸腔里鼓噪,撞得肋骨生疼,
却奇异地冷静下来。好。清醒也好。是该结束了。林晚晚迎着他冰冷戏谑的目光,
唇瓣微微颤动。那个名字像是粗粝的沙砾,艰难地从喉咙深处碾磨着升起。
“傅……”她张开口,声音低哑破碎,如同在寒风中战栗的羽毛。“……琛。
”就在“琛”字艰难吐出的刹那,那个滚烫的、带着水汽与绝对力量的怀抱骤然收紧,
将她剩余的音节全部扼杀在齿间!天旋地转!傅琛猛地低下头,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强悍姿态,
滚烫的、带着惩罚意味的唇重重地压了下来,带着一种蛮横的掠夺气息,
吞噬了她所有的挣扎与呜咽,也彻底堵死了她试图保持清醒与界限的所有可能性。
没有一丝温柔,纯粹的征服和标记。窗外,狂风撕扯着巨浪,狠狠撞在临海的礁石上,
摔得粉身碎骨,发出沉闷而绝望的轰响。夜色浓稠,黏腻地糊在巨大的落地窗上,
只有远处的灯塔光柱,像一把钝刀,缓慢地切割着无边的黑暗海面。
林晚晚蜷在宽大得令人心慌的沙发角落,抱着一本看了一半的旧书,
视线毫无焦距地落在窗外那片令人心悸的墨黑海上。书房方向的门被无声推开,
沉稳的脚步踏在昂贵的地毯上,悄无声息。是傅琛。她下意识地想要收紧膝盖,
脊背无声地绷紧,像一只受惊后试图将自己缩进硬壳里的软体生物。
然而那脚步声径自朝她而来。巨大的影子笼罩下来,
带着刚沐浴过的薄荷冷冽气息和他身上独有的、压迫性的气场。
身体被一只强健的手臂从沙发里毫不费力地捞起,落入一个坚实而滚烫的怀抱。
林晚晚惊呼一声,书“啪”地掉在地毯上。傅琛抱着她,如同抱着一个轻盈的洋娃娃,
几步就走到了整面墙的落地玻璃前。冰冷的玻璃贴着她**在睡裙外的后背皮肤,
冻得她一个激灵。窗外,无星无月的墨海翻涌着,发出低沉而原始的咆哮,
仿佛某种蛰伏的巨兽。傅琛滚烫坚实的胸膛紧贴着她的后背,形成冰与火交织的囚笼。
他一只手穿过她的腋下,轻而易举地将她整个身体向上托了托,让她双脚离地,
被迫完全倚靠在他身上。下颌被他另一只带着薄茧的大手捏住,
力道霸道又不容抗拒地将她的脸转了过去。客厅顶灯的光线被他高大的身形遮蔽了大半,
黑暗中只剩下玻璃反射出两人模糊交缠的轮廓。
他那双在晦暗光线下显得更加幽邃难测的眼睛紧紧攫住她,
里面燃烧着一种**裸的、近乎要将她拆吃入腹的原始欲望,
还有某种……混乱扭曲的情感漩涡。“看清楚了?”他的声音贴着她的耳根响起,
低沉得如同深渊的低鸣,每一个字都带着温热的气流钻进她的耳膜,
激起一阵难以抑制的酥麻和战栗,“外面是什么?是海,吃人的海。
没有我……”他收紧在她腰间的手臂,滚烫的掌心透过薄薄的衣料烙在她皮肤上,
“你跳下去,连个泡沫都不会有。”他低下头,滚烫的唇贴着她冰凉的耳廓皮肤摩擦着,
带着一种残忍的亲昵,声音喑哑而执拗,像个霸道的孩子:“叫晚晚……我的晚晚。
”那重复的命令,在此时此地,更像一种偏执的诅咒。海潮的轰鸣声似乎更大了些,
潮气仿佛渗进了骨头缝里。林晚晚能清晰听到自己牙齿磕碰的细微声响。
她努力想从他滚烫的桎梏中汲取一点力量站直,嘴唇抖动着。“晚……”她闭上眼,
声音细若蚊呐,如同濒死的蝉鸣。“晚……”她屈服了,用那个他指定的、偷来的名字,
换来片刻喘息的苟且。傅琛似乎满意了。低笑一声,带着一丝得逞的畅快,
他轻易地将她翻了过来,冰凉的玻璃瞬间变成一种尖锐的刺骨寒意抵着脊骨。
没给她丝毫适应的时间,带着掠夺性质的吻再次狠狠落下,如同窗外不知疲倦拍岸的海浪,
凶猛、混乱、不容反抗,仿佛要将她和这片令人窒息的海域一起卷入旋涡,彻底吞噬殆尽。
咸涩的味道……是他的吻?还是她咬破唇瓣流出的血?
抑或根本就是窗外那片大海倒灌了进来?
客厅里只剩下水晶吊灯冰冷的光线和中央空调送风沉闷的嗡嗡声。
那封红色的请柬静静地躺在光可鉴人的天然大理石茶几上,像一块不小心溅落的凝固鲜血,
刺得眼睛生疼。林晚晚坐在宽大的沙发边缘,指尖冰凉,如同浸在雪水里。
她看着傅琛一步步从楼上走下来。他刚沐浴过,黑发微湿,穿着质地精良的深灰色丝绒睡袍,
身上带着清爽的薄荷须后水气息,
与昨夜那个将她抵在冰冷玻璃上如同捕食者般啃噬的男人判若两人。
他只是淡淡扫了一眼那封突兀的红色,仿佛看见什么无关紧要、甚至有点碍眼的尘埃,
脚步没有丝毫停顿。他径直走到那扇巨大的观景窗边,窗外是晴朗碧空下波光粼粼的海面,
一片虚假的平静祥和。他甚至没有回头,只伸出骨节分明、带着长期上位者惯性的手,
随意地捻起那张喜帖。林晚晚的心悬到了嗓子眼,那红色在她视野里无声地燃烧着。
她是知道的!协议里的核心条款,关于那位叫叶清澜的白月光**的一切动向,
都被监控、被定期汇报。傅琛沉睡时,那些报告总是放在他枕边最新的财经杂志下面,
她收拾病房时曾无意瞥见过一次,纸张崭新,印着某个安保公司冷酷的Logo。
可他醒来后,这报告就彻底消失了。叶清澜这个名字连同她过往的一切,在傅琛的世界里,
也一同消失了?像一个被强行擦除的字符?傅琛背对着她,微微侧身。
窗外天光勾勒出他过分清晰冷硬的侧脸线条,
连他颀长指间夹着的那抹艳红都成了背景板上微不足道的一点油彩。
他鼻子里发出一声极轻、极冷的哼笑,如同冰屑落入沉寂的湖面,激不起一丝真实的涟漪,
只有刻骨的鄙夷与彻底的无关痛痒。修长的手指倏然张开。
那封承载着别人一生中可能最重要的幸福邀约的红帖,像一个被主人厌弃的玩具,
被随意地从敞开的巨大窗口抛了出去。它被强劲的海风猛地吹卷起来,打着旋儿,
如同蹁跹却失去控制的血蝶,只挣扎了短短一瞬,
便朝着下方礁石嶙峋的墨蓝色海面直直坠落,
眨眼间被一个翻涌起的浪头“哗啦”一声吞没得无影无踪。傅琛缓缓转过身。
阳光透过巨幅玻璃,在他身后铺开一片明亮的背景板,
却将他沉在阴影里的正面衬得更加深邃莫测,如同立在光明与黑暗的交界处。
他看向沙发上的林晚晚,唇角似乎向上弯了一下,但那弧度太淡太快,
几乎让人以为是光影的错觉。“脏东西,晦气。”他说,声音不高,没什么情绪的起伏,
平静得像在陈述“今天天气不错”。但每一个字都像淬了剧毒的冰针,
精准地扎入林晚晚早已千疮百孔的心脏深处,引发一阵隐秘而剧烈的、濒死般的抽搐。
他擦掉了属于叶清澜的痕迹。那么,对于他此刻口中这个“我的晚晚”……他想要的,
究竟是什么呢?是补偿,是寻找替身的延续,还是一场更为扭曲的自我证明?
空气里仿佛还残留着喜帖上印刷油墨那若有似无的味道,
混合着窗外飘进来的、带着咸腥气的海风,形成一种令人作呕的混合物。
林晚晚看着傅琛朝她走近的身影,巨大的落地窗外是晴空万里、碧海无垠,阳光灿烂得讽刺,
却暖不进这冰冷囚笼的半分角落。他越是表现得无谓,那片吞噬了喜帖的冰冷海域,
就越像是对她未来命运的某种无声预告和嘲弄。是时候了。她不能再做一头待宰的羔羊,
被命运推着走。她必须亮出她仅有的、可能根本不堪一击的底牌。“恭喜。
”林晚晚的声音很轻,像一片羽毛掠过死寂的湖面。她的脸上甚至挤出了一丝苍白的微笑,
迎着傅琛莫测的目光,她伸手探进睡袍宽大的口袋里——几天前,
她就将那张薄薄的纸片贴身藏在这里,像藏着一件足以烫穿皮肉的秘密武器。
指尖触到折叠起的纸张边缘。那是医生递给她时眼中复杂的恭喜与叹息。
薄薄的纸在她颤抖的指间被展开,发出细微的窸窣声。她能感觉到自己掌心冰凉一片,
却烫得吓人。她努力维持着脸上那丝脆弱的、几乎快要撑不住的笑。她将纸轻轻抬起,
朝着傅琛的方向,目光带着孤注一掷的决绝,死死锁住他的眼睛:“或许,是双喜临门?
”那张孕检单的白纸,在明亮的光线下显得有些刺眼。
上面清晰的“早孕”字样以及一个初步估算的、象征着新生萌芽的小小孕周,
如同烙印般醒目。客厅里陷入了死一样的寂静。时间被无限拉长,每一秒都凝滞得沉重如铅。
窗外的海鸟发出悠长的鸣叫,尖锐地划破宁静的空气。
傅琛的脚步停在距离她几步之遥的地方。
他脸上那点或许是真实、更可能是虚假的暖色瞬间荡然无存,如同退潮般消失得干干净净,
露出底下冰冷坚硬、毫无温度的石礁本色。他深黑的眼眸骤然收缩,
像猛兽锁定了猎物最后垂死的挣扎,
瞳孔深处炸裂开一股席卷一切的黑色风暴——那是被冒犯、被欺骗、被愚弄的惊怒,
还有一种更为纯粹恐怖的毁灭欲!他猛地跨步上前,动作快得带起了残影。
林晚晚只觉得手腕被一只铁钳般的大手狠狠攥住,剧痛钻心,仿佛骨头都要被捏碎。
那张孕检单像一片失去依托的残叶,从她剧痛而无法控制的手中飘落,无声地滑落在地毯上。
下一刻,强劲凶狠的力量攫住她的下颌骨。傅琛的手指冰冷如铁,带着能把骨头捏碎的力道,
逼着她抬头,被迫与他对视。那张英俊绝伦的脸,此刻在她仰视的视野里扭曲变形,
成为地狱判官的冷酷塑像。咫尺之遥,他的呼吸滚烫地喷在她脸上,
眼中的烈焰足以将她焚毁成灰烬。
“哈……”一声短促、冰冷、毫无笑意的嗤笑从他紧抿的薄唇间挤出来,如同毒蛇吐信,
“林晚晚,”他每一个字都像是淬了寒冰的重锤,狠狠砸落,“你真让我恶心!
”冰冷的视线像探照灯,直白地扫过她依旧平坦的小腹,
眼神里没有一丝对这个可能存在的“生命”的温情或错愕,
只有极致的鄙夷和深重的、看透一切的嘲弄。“你以为……”他一字一顿,字字清晰入骨,
带着摧枯拉朽的力量,“在我这里,怀上个不知哪里来的野种,就能取代她了?
就能在我傅家安身立命了?”“野种!”“取代她?”“恶心!”每一个词,
都如同一柄淬毒的重锤,精准无比地砸向林晚晚心口最脆弱、最不敢直视的地方。
那里早已血肉模糊,此刻又被砸得骨头渣子四溅。取代谁?
那个正沉浸在盛大婚礼幸福里的白月光叶清澜?
还是那个傅琛五年来唯一记得要寻找的、车祸前的那个神秘女子?
那张密码日记本里照片上的人?那五年里卑微的、被精心扮演又痛苦挣扎的影子?
那个偷来的名字下的自己?混乱的念头如同沸腾的泥浆,搅动着她濒临崩溃的神经。
巨大的耻辱和灭顶般的绝望像是冰冷的海水,瞬间没顶而来!傅琛的目光如同淬毒的箭镞,
每一寸扫视都像是在凌迟她的尊严。她感到一阵灭顶的窒息和冰冷的恐惧席卷全身。不!
不是这样的!她想尖叫,想辩驳,想把这五年积攒的委屈和不敢言说的痛苦一股脑倾泻而出!
可喉咙像是被最狠戾的咒语死死堵住,任凭她怎样挣扎,也发不出一丝像样的声音,
只有胸腔里如同破旧风箱般拉出沉重的、破碎的嘶鸣。她所有的力气都被抽干了,
被他掌中传来的绝对力量,被那比窗外怒海更加冰冷的眼神冻结。
她像一个被抽离了所有骨骼和意志的提线木偶,失去力气支撑,无法挣扎,无法呼喊,
只能任由傅琛钳制着她,像拖着一具没有生命的破败玩偶,
毫无怜惜地朝着通向露台的玻璃门走去。玻璃门被他粗暴地拉开,发出巨大的摩擦声响。
更加狂暴的海风如同挣脱牢笼的巨兽,裹挟着浓重的、冰冷的咸腥气劈头盖脸地砸了进来,
瞬间吹乱了林晚晚的长发,拍打在脸上如同无数细小的耳光。外面,
是傅家别墅那视野绝佳、同时也距离底下嶙峋礁石和狂暴大海最近的观景露台。
墨蓝色的海水在阳光照不到的角落翻涌出白沫,狠狠撞在黑色的礁石上,
发出巨大沉闷、如同远古巨兽咆哮的轰鸣,溅起几层楼高的惨白水花!
露台上的风如同无数条冰冷的鞭子,疯狂抽打着林晚晚单薄的睡裙,
将布料紧紧裹贴在她身上,勾勒出无助的轮廓。海水咆哮的轰鸣声震耳欲聋,
如同地狱之门在脚下洞开。她被这股巨大的力量拽到冰冷的金属栏杆边,
傅琛紧扣着她小臂的手没有丝毫放松,那力道像是要嵌进她的骨头里。“看啊!
”他冰寒刺骨的声音穿透风暴,带着一种残酷的审判意味,
将她的脸更近地压向那冰冷的栏杆,“好好看看!”下方,距离露台数十米的高度,
是嶙峋狰狞的黑色礁石群。每一次浪潮涌来,都带着雷霆万钧之力狠狠撞上去,
在坚硬的礁石表面撞得粉身碎骨,溅起冲天的、混杂着泡沫的惨白水沫!
那声音如同成千上万吨的石头在海底摩擦滚动,沉重、原始、充满了毁灭性的力量,
敲打着人的耳膜和心脏,仿佛要将这悬崖连根拔起一同拖入深海!汹涌的海水永不停歇,
像一张巨口,深不见底。林晚晚浑身抖得如同风中残烛,牙齿不停地磕碰着,
发出细碎绝望的颤音。死亡的阴影如此清晰迫近,冰冷的海腥气灌满了她的鼻腔。
傅琛强健的身体紧紧贴在她背后,不是庇护,而是禁锢。
他的薄唇贴在林晚晚被狂风吹乱的鬓角边,每一个字都如同冰锥凿进她的耳蜗:“林晚晚,
你拿什么跟她比?拿你这颗恶毒愚蠢的心?”钳制着她的手臂骤然松开,
巨大的推力从背后传来!林晚晚如同断线的风筝,身体被一股蛮横的力量猛地推向前,
失去平衡!恐惧的尖叫卡死在喉咙深处。她双手在求生本能下胡乱地向前抓去,
死死地抠住了露台最外延那冰凉光滑、湿漉漉的金属栏杆边缘!整个身体悬空!身下,
就是那张开巨口、喧嚣沸腾着等待吞噬一切的深渊之海!狂暴的风卷着她散乱的长发,
猎猎作响。咸涩冰冷的海水气息混杂着死亡的恐惧,无孔不入地钻进她的每一个毛孔。
她像个风干的标本,死死吊在栏杆之外,纤细得仿佛下一秒就会被风暴撕碎的手指,
因过度用力而指节惨白。心脏在胸腔里疯了一样狂跳,每一次搏动都沉重地撞向喉头,
带来濒死的窒息感。血液在四肢百骸逆流、冻结。“傅琛!”破碎的声音终于挤出牙缝,
带着泣血的颤抖和绝望,“你**!”没有回应。露台栏杆的冰冷顺着指尖蔓延到四肢百骸。
悬空的双腿仿佛踏在虚无的空气里,身下是震耳欲聋的深渊咆哮。她不敢回头,
身后那人的气息如同跗骨之蛆,冰冷的杀意几乎要凝成实体。求生本能战胜了肢体的僵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