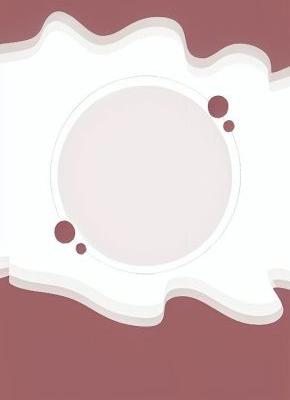三万块,我成了村里那个“鬼”果园的新主人。据说那地方以前是片乱葬岗,阴气很重,
谁沾手谁倒霉。我正准备刨掉老果树种新的,一锄头下去,却挖出了个密封的罐子。
我好奇地打开一看,差点当场晕过去。小小的罐子里,竟然塞满了东西。
01我抱着那个沉甸甸的陶罐,心脏在胸腔里擂鼓。风吹过老旧的门框,发出呜呜的声响,
像是无数只手在抓挠。我猛地回身,死死关上大门,再把窗户一扇扇关严实,
用布条塞住缝隙,直到屋里暗得只剩下呼吸声。汗水浸透了我的后背,
衣服黏糊糊地贴在黝黑的皮肤上。我把陶罐放在那张掉漆的方桌上,手抖得厉害。
罐口用黄泥和桐油封得死死的,透着一股陈旧的土腥味。我找来一把菜刀,
沿着罐口的缝隙一点点地撬,心跳声盖过了一切。“咔哒”一声轻响,封泥裂开了一道缝。
一股古朴、深沉的气息扑面而来。我深吸一口气,猛地掀开盖子。屋内的昏暗中,
一抹温润的光晕散开。罐子里,塞满了大大小小的玉佩。龙形的,凤纹的,蝉状的,
每一块都雕工精美,线条流畅,在微弱的光线下泛着油脂般的光泽。
这不是什么普通的玩意儿。我颤抖着手,从中拿起一块环形的玉佩。玉质温润细腻,
入手微凉,表面刻着细密的谷纹,透着一股来自遥远年代的庄重气息。我的呼吸几乎停滞了。
我把所有玉佩小心翼翼地倒在桌上,一件件地看,脑子里一片空白。
强压着几乎要冲破喉咙的狂喜,我摸出那部用了好几年的旧手机,屏幕上还有几道裂纹。
信号时断时续,我举着手机在屋里转了好几个圈,才勉强连上网。汉代古玉佩。图片。
搜索结果跳出来的一瞬间,我的眼睛死死盯住屏幕。那些博物馆里的藏品,
那些拍卖会上的天价珍宝,和我桌上的这些东西,何其相似。价值惊人。
这四个字像一道惊雷,在我脑中炸开。我不是那个穷得叮当响,
只能花三万块承包凶地的陈默了。我发财了。这个认知让我浑身发抖,不是因为冷,
而是极度的兴奋和一种难以言喻的恐惧。财不露白。这个道理,我爹从小就念叨。
我猛地站起来,把所有玉佩重新装回罐子,盖上盖子。这件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一个也不行。就在这时,门口传来一阵轻微的脚步声,接着是探头探脑的影子。“阿默,
在家吗?”是堂哥陈强的声音,黏腻得像条蛇。我心脏猛地一缩,
几乎是下意识地把陶罐塞进了桌子底下。我清了清嗓子,
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和平时一样木讷。“在呢,哥,有事?”我拉开门栓,
刺眼的阳光让我眯起了眼。陈强就站在门口,脸上挂着那种假惺惺的笑,
一双小眼睛却不着痕迹地往我屋里瞟。“没事,就看看你。那果园怎么样了?动工没?
”他的视线在我沾着新鲜泥土的裤腿上停了一秒。“刚开始,土太硬了,不好弄。
”**在门框上,挡住他的视线,语气平淡。“那地方邪性,你可得小心点。”他一边说,
一边又想往里瞅,“别挖出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我的心沉了下去。
他就像闻到血腥味的苍蝇,这么快就凑上来了。“能有啥,一堆破石头烂树根。
”我打了个哈欠,装出疲惫的样子,“哥你要是没事,我得再睡会儿,累死了。
”我直接下了逐客令。陈强脸上的笑僵了一下,随即又恢复了原样,“行,那你歇着。
有啥事就跟哥说,别客气。”他转身走了,但我能感觉到,他那双眼睛还在我背后。
我关上门,背靠着门板,大口喘气。不行,放在这里太不安全了。等到夜深人静,
我摸出那把用了多年的锄头,在我那张破木板床下,开始一下一下地挖。泥土被我刨开,
挖出一个半米深的坑。我把那个陶罐用几层塑料布包好,郑重地放进去,
再把土一层层填回去,踩实,最后把床板移回原位。做完这一切,我躺在床上,
睁着眼睛看着漆黑的屋顶。床下是能改变我一生的财富。窗外是虎视眈眈的豺狼。这一夜,
我辗转难眠。02天刚蒙蒙亮,院子里的鸡叫了第一声,我就听到了院门被推开的嘎吱声。
来得真快。我闭上眼,继续装睡。“阿默啊,起了没?大娘给你送早饭来了。
”大伯母那尖细的嗓音,像锥子一样扎进我的耳朵。我慢吞吞地爬起来,打开门,
一股浓重的劣质香水味扑面而来。大伯母提着个篮子,脸上堆满了菊花般的褶子,
热情得让我反胃。“哎呀,看你这孩子,一个人过日子就是不行,脸都瘦尖了。”她说着,
硬是挤进了屋里,一双眼睛像雷达一样四处扫射。“大娘,我没事,吃得惯。”我低着头,
声音闷闷的。她把篮子放在桌上,里面是两个干巴巴的馒头和一碟咸菜。“快吃,趁热。
”她殷勤地把馒头递给我,一**坐在我床边,那床板发出一声不堪重负的呻b吟。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阿默啊,你那果园……昨天动工,没发现啥吧?
”她状似不经意地问,手还在床板上拍了拍。我啃了一口馒头,硬得硌牙。“没呢,土不好,
石头太多,我正愁这三万块本钱啥时候能回来。”我叹了口气,
把一个穷困潦倒、愁眉不展的年轻人演得活灵活现。“哎,年轻人别急,慢慢来嘛。
”话音刚落,陈强也跟了进来,像个影子。“我就说那地方不行,纯粹是扔钱。
”他靠在门框上,语带嘲讽,“爸妈当年就说,那块地以前是乱葬岗,邪门得很,
小心挖出什么白骨啊、破罐子之类的,不吉利。”他特意加重了“破罐子”三个字。
我心里冷笑,这母子俩一唱一和,戏演得真不错。“那也没办法,便宜啊。”我继续装傻,
脸上全是苦涩,“除了那地方,我哪还有钱承包别的。”我把所有的失落和无奈都写在脸上,
每一个细微的表情都在告诉他们:我就是个倒霉蛋。大伯母和陈强对视了一眼,
眼神里带着不易察觉的得意。他们似乎相信了。“行了,那你慢慢弄吧,别太累着。
”大伯母站起身,目的达到,准备离开。“有啥解决不了的困难,就找你大伯和你哥,
咱们是一家人。”她临走前,还不忘补上一句虚伪的客套。我木然地点点头,
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眼神瞬间变得冰冷。一家人?我爸妈刚走那会儿,
他们是怎么霸占我家的田地,又是怎么把抚恤金“借”走不还的?这一笔笔账,
我可都记着呢。他们前脚刚走,我后脚就把那两个馒头扔给了院子里的土狗。狗闻了闻,
嫌弃地刨开土埋了。我不能坐以待毙。这罐子里的东西,是真是假,到底值多少钱,
我必须尽快弄清楚。我回到屋里,重新挖开暗格,
从罐子里挑了一块最小、最不起眼的蝉形玉佩。它看起来最普通,
玉质也似乎不如其他的温润。我用布小心包好,揣进最贴身的内袋里。必须去城里一趟。
找个真正懂行的人,给我一个答案。03最早一班去市里的班车,
车厢里弥漫着汗味和尘土味。我缩在角落,手一直紧紧按着胸口的内袋,
那块玉佩的轮廓硌着我的皮肤,却让我感到心安。两个小时的颠簸后,
我终于站在了市里最大的古玩市场门口。这里人声鼎沸,到处都是地摊和店铺,真假难辨。
我不敢去那些看起来富丽堂皇的大店,怕被当成肥羊宰。我绕着市场走了两圈,
最后选了一家门面很小,看起来毫不起眼的铺子。老板是个戴着金链子的胖子,
正翘着二郎腿喝茶。“老板,看个东西。”我压低声音,
小心翼翼地把用布包着的玉佩递过去。他懒洋洋地掀起眼皮,接过玉佩,只用两根手指捏着,
对着光瞥了一眼。“仿的。”他把玉佩扔回柜台上,发出一声脆响。我的心猛地一沉。
“现代机雕,做旧手法都不到家。小兄弟,喜欢这个我这儿多的是,五十块钱一个,随便挑。
”他的语气里充满了轻蔑。“不可能!”我下意识地反驳。“嘿,你这小孩,
我吃这行饭二十年了,还能看走眼?”他嗤笑一声,“不信你到别家问问,看有谁收。
”我捏紧了那块玉佩,狼狈地走出了店铺。阳光刺眼,我的脑子嗡嗡作响。
难道……真的是我空欢喜一场?那些在网上看到的图片,那些天价的数字,都只是我的幻想?
我不信。我不信我爹妈留给我的运气会这么差。我咬了咬牙,横下心,
走向市场里最大的一家店,“聚宝阁”。店里的装修古色古香,
一个穿着长衫的老师傅正坐在太师椅上,手持一个放大镜,端详着一枚铜钱。我深吸一口气,
走了过去。“老师傅,您能帮我看看这个吗?”我把玉佩双手奉上,
声音因为紧张而有些沙哑。老师傅抬起头,看了我一眼,他那双眼睛虽然有些浑浊,
却透着一股精明。他没说话,接过玉佩,从抽屉里拿出一副老花镜戴上,
又拿起了那个放大镜。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的心悬在半空中。老师傅看得极其仔细,
从雕工到沁色,再到孔洞的痕迹,每一处都不放过。许久,他才放下放大镜,
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他抬头看着我,眼神里带着惊讶和郑重。“小伙子,这东西,
你从哪儿得来的?”我的心狂跳起来。“祖……祖上传下来的。”我胡乱编了个理由。
老师傅点了点头,似乎并不想追根究底。“这是汉代的和田白玉,典型的游丝毛雕工艺,
包浆自然,沁色入骨,是真品。”真品!这两个字像烟花一样在我脑海里炸开,
巨大的狂喜瞬间淹没了我。“那……那它值多少钱?”我颤声问道。老师傅摇了摇头,
“这东西不好估价。它的价值,不仅仅是金钱。我建议你,如果想出手,
去找正规的拍卖行或者鉴定机构。不要在外面轻易示人。”他把玉佩还给我,
意味深长地补充了一句:“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小伙子,你好自为之。
”我握着那块滚烫的玉佩,郑重地向老师傅鞠了一躬。走出聚宝阁,我感觉自己像踩在云端。
一切都是真的。我真的挖到了宝藏。回村的路上,我心情激动,反复回味着老师傅的话。
班车在村口停下,我刚下车,一个身影就迎了过来。是陈强。
他像一根桩子一样杵在村口那棵大槐树下,脸上挂着皮笑肉不笑的表情。“阿默,回来了?
去城里干嘛了啊,这么久?”我心头一紧,所有的喜悦瞬间冷却,只剩下冰冷的警惕。
他居然在这里等我。04“地里缺肥料,去城里看看。”我面不改色地撒谎,
拍了拍裤腿上的灰。我的手上空空如也,这个动作显得格外刻意。
陈强的视线在我身上扫了一圈,像是在搜寻什么,最后停留在我空空如也的手上。“买肥料?
肥料呢?”他的语气里充满了怀疑。“问了几家,太贵了,没舍得买。
”我露出一副囊中羞涩的无奈表情,叹了口气,“寻思着还是先多用点力气,把地翻好再说。
”陈强半信半疑地盯着我,似乎想从我脸上找出破绽。我的表情坦然得没有波澜,
眼神里只有贫穷带来的麻木。他最终什么也没看出来,只能悻悻地说:“你就是死脑筋,
那破地有什么好弄的。”我没再理他,径直往家的方向走。背后的那道目光,如芒在背。
事情很快就朝着我最不希望的方向发展了。第二天,村里的风向就变了。“听说了吗?
陈默在他那果园里挖到宝贝了!”“可不是嘛,有人看见他昨天偷偷摸摸去了城里,
肯定是去销赃了!”“那块地本来就邪乎,指不定是哪个大官的墓,这小子发大财了!
”谣言像插上了翅膀,一夜之间飞遍了整个村子。大伯一家就是这股风的源头,
他们添油加醋,把我说成了一个得了横财就六亲不认的白眼狼。村里人看我的眼神彻底变了。
以前是同情和可怜,现在是**裸的羡慕、嫉妒,还有毫不掩饰的贪婪。我家的门槛,
突然之间就热闹了起来。“阿默啊,我是你三姑奶,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呢。
最近手头有点紧,你先借我两万块周转周转?”“小默,你二舅家的孩子要结婚,
彩礼还差五万,你看……”那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一个个都冒了出来,
脸上挂着虚伪的笑,嘴里说着感人肺腑的陈年旧事,最终的目的都是一个字:钱。
我家的那扇破木门,仿佛成了一个许愿池。我对所有人都只有一个回答。“没有。
”“都是谣言,我哪有钱。”“我要是有钱,还住这破屋子?”我指着漏雨的屋顶,
指着墙角的裂缝,一遍遍地哭穷。我的态度越是坚决,他们眼里的怀疑就越是浓重。
他们不相信,或者说,是不愿意相信我还是那个穷光蛋陈默。
流言蜚语把我推到了全村人的对立面。我走在路上,总能感觉到背后指指点点。
那种被孤立、被觊觎的压力,像一张无形的大网,把我牢牢罩住。
我看清了这帮所谓的亲戚邻里,在利益面前,那点可怜的温情,薄得像一张纸。
愤怒在我的胸口燃烧,但我只能死死压抑着。我越是烦躁,就越是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现在还不是翻脸的时候。05终于,最不想看到的一幕还是发生了。陈强带着大伯,
直接一脚踹开了我的院门。“陈默,你给我出来!”陈强的声音嚣张跋扈,像是来抄家。
我放下手里的锄头,慢慢从屋里走出来,眼神平静地看着他们。大伯**,挺着个啤酒肚,
一脸的理所当然。“阿默,我们也不跟你绕弯子了。”大伯一开口,就给我定了罪,
“你承包的那块果园,下面是我们陈家的祖坟。你在祖坟上挖出来的东西,理应是我们家的。
”我的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祖坟?真是天大的笑话。“大伯,饭可以乱吃,
话不能乱说。”我拿出早就准备好的承包合同,在他们面前展开,“白纸黑字,
村委会盖了章的。这块地的使用权现在归我,我在我承包的地里干活,
挖出什么都和你家没关系。”“你放屁!”陈强直接爆了粗口,“那下面埋的是我太爷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