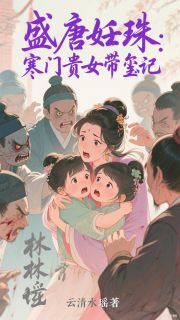月儿那场惊心动魄的高热,如同淬炼的烈火,虽险险渡过,
却耗尽了林琬本就所剩无几的元气。她卧床休养了数日,脸色依旧苍白,但那双眼睛,
却沉淀下更深的沉静与决绝。那袋来自波斯邸的银钱,不再仅仅是财富,
更是沉甸甸的责任和必须抓住的生机。她不能再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更不能将身家性命寄托于贵人的一时垂青。建立自己的根基,刻不容缓。村尾,
靠近西山溪流下游处,有一处废弃多年的染坊。几间破败的土坯房,屋顶塌了大半,
院子里杂草丛生,一口巨大的、早已干涸结满青苔的染缸歪斜在角落,
几根腐朽的木架散落一地,空气中仿佛还残留着经年累月的劣质染料和霉变的混合气味。
这里荒僻、破败,却也足够隐蔽,远离村中喧嚣。林琬看中了这里。
她用波斯邸订单的大部分利润,加上康萨陀那张能把死人说活的嘴,
以极低的价格从村里盘下了这片废墟。钱花出去时,张二郎看着那白花花的银子,
心疼得直抽抽,嘴唇哆嗦着想说些什么,
但想起月儿病中林琬那拼命的模样和那句“我能做啥”,终究是咽了回去,默默扛起了锄头。
清理、修缮、改造,是异常艰苦的过程。康萨陀发挥了他“百事通”的本事,
不知从哪里淘换来一些旧木料、瓦片和工具。
张二郎仿佛要将那夜未能护住女儿的愧疚和力量都发泄出来,沉默地挥汗如雨,
清理废墟、修补墙壁、搭建简易棚顶,手上磨出了血泡也浑然不觉。林琬拖着病体,
亲自规划:最大的一间房改造成蒸馏工坊,需要砌灶台、安置蒸馏器具(她画了图,
让康萨陀找铁匠定制了几口特殊的铜锅和冷凝管);一间稍小的作为净花处理间,
需砌水槽、搭晾架;最角落一间干燥通风的,作为分装储藏室。人手是关键。
林琬深知保密的重要性。她没有大张旗鼓,
康萨陀暗中留意村里手脚麻利、家世清白(最好是有难处、需要这份活计养家糊口)的妇人。
最终选定了三人:周娘子:三十出头,手脚极其麻利,丈夫前年进山采药摔断了腿,
干不了重活,家里两个孩子嗷嗷待哺,生活困顿。李婶:四十许,沉默寡言,
但做事极其细致认真,早年守寡,独自拉扯一个病弱的儿子。
春桃:正是村口那位曾给林琬送过一碗糙米粥的瞎眼阿婆的儿媳。二十多岁,眉目清秀,
眼神清澈,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坚韧。阿婆的儿子去年被征了徭役,生死不明,
婆媳俩相依为命,日子过得紧巴巴。林琬记得那碗粥的情分,也看中春桃的干净和那份沉静。
林琬亲自与三人签下了保密契约。契约由康萨陀执笔,
措辞严谨(得益于他早年混迹市井的见识),不仅要求她们对作坊内所见所闻守口如瓶,
更明确规定了泄密的严厉惩罚——十倍赔偿工钱,并送官究办。三人按了手印,
神色都带着敬畏和感激。林琬给的工钱,足够她们养家糊口。
(林琬亲自带她们辨认西山野山矾花的最佳采摘期和部位)、净花(去杂叶、清洗、阴干)。
·春桃:心思最细,
负责蒸馏环节的辅助(看火、添水、记录时间)和最后的分装入瓶、封口。
核心的蒸馏配比、冷凝控制、最后的品质检验和香露的最终提纯(这一步她始终亲力亲为)。
·张二郎:负责重体力活(挑水、劈柴、搬运原料和成品)、以及最重要的——守门。
小小的“琬记香露坊”,在深秋的寒风中,于这片废弃的染坊废墟上,悄然运转起来。
蒸馏铜锅第一次冒出带着奇异冷香的白汽时,林琬站在氤氲的雾气中,
苍白的脸上终于露出一丝如释重负的疲惫笑意。这是她的根基,是她和孩子们未来的希望。
然而,利益的甜香,如同滴入水中的鲜血,很快引来了嗅着腥味而来的鲨鱼。
作坊运作不到半月,麻烦就找上了门。这日午后,张二郎正蹲在作坊院门口,
笨拙地用新买的斧头劈着柴火。几个流里流气的身影晃荡着走了过来,
为首的是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尖嘴猴腮,脸上长着几颗显眼的癞痢,
正是里正王老栓那个游手好闲、横行乡里的独子——王癞子。
他身后跟着两个同样歪瓜裂枣的跟班。王癞子一脚踹开虚掩的院门,大摇大摆地走进来,
三角眼贪婪地扫视着已经初具规模的作坊,最后落在正在分装香露的林琬身上,
嘿嘿一笑:“哟呵。林寡妇,行啊。不声不响弄出这么大个摊子?
发财了也不跟乡里乡亲打个招呼?”林琬放下手中的瓷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