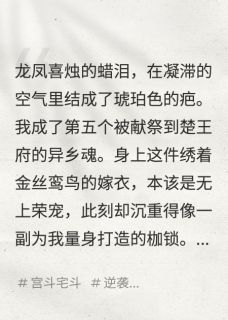龙凤喜烛的蜡泪,在凝滞的空气里结成了琥珀色的疤。
我成了第五个被献祭到楚王府的异乡魂。身上这件绣着金丝鸾鸟的嫁衣,本该是无上荣宠,
此刻却沉重得像一副为我量身打造的枷锁。婚房对面,我的夫君,楚王赵弈,
正用一种打量待宰牲畜的眼神,将我从发梢到指尖,一寸寸地凌迟。
他修长的指节叩击着紫檀木桌面,那不紧不慢的“笃、笃”声,
成了我生命沙漏里最后的流沙。“天赋人权,生而平等。你以为然否?”他终于开口,
嗓音平直得没有任何情绪,像是在问一句“风从何来”。我的心跳,在那一瞬被攥停了。
血液倒灌回心脏,又在刹那间凝成冰,刺得四肢百骸一片森寒。这不是问题,
这是一道催命符,专为我,或者说,专为“我们”这类人所设下的终极考验。
指甲深深嵌入掌心,我借着那点刺痛强迫自己找回知觉,将视线垂落在地,用一种近乎谄媚,
独属于这个时代的卑微语气,颤抖着回话:“王爷……妾身……妾身愚昧。自幼所学,
唯有君臣之纲、父子之道、夫妇之义。世间万物,皆有尊卑,各安其位,方得长久。
”赵弈的面容隐在烛火的阴影里,看不真切。那双幽深的眸子,静得像一潭千年寒渊,
我这颗试探的石子投进去,连一丝涟漪都未曾惊动。他对我的答案不置可否,
仿佛只是随手拨开了路边一丛碍事的荆棘,接着问了下一个。“盘尼西林、水龙吟,此二物,
你可有耳闻?”冷汗,已经将我的中衣彻底浸湿。这些仿佛镌刻在我们灵魂深处的名词,
从他口中吐出,却带着一股铁锈般的血腥味。我几乎是本能地猛力摇头,将内心的惊涛骇浪,
悉数化作恰如其分的茫然与无辜:“求王爷恕罪,妾身……闻所未闻,不知是何等珍宝。
”他沉默了下来。时间被拉得很长,长到我几乎能听见自己颈骨因恐惧而发出的“咯咯”声。
就在我以为下一秒便会有人进来将我拖走时,一段轻佻而不成调的旋律,
从他削薄的唇间哼了出来。
“两只老虎跑得快......”那是我曾单曲循环过无数个夜晚的,属于另一个世界的歌。
我赖以伪装的一切,在那一刻,轰然崩塌。他不是在审问,他是在验尸。验证我这具躯壳里,
装的究竟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古董,还是一个会给他带来天**烦的“新魂”。“可曾听过?
”他问,语气平淡,却胜过千钧。我调动了全身所有残存的力气,
才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不至于抖得太厉害:“……许是……乡间俚语编成的小调,
妾身……只会唱些采茶的歌谣。”“是么。”赵弈终于起身。
烛光将他颀长的身影拉扯成一头蓄势待发的墨色猛兽,投在墙壁上,几乎将我完全吞噬。
他没有再施舍我一个眼神,仅是淡漠地朝门外吩咐:“送她去清芷院。往后,叫她安守本分。
”那一夜,红烛燃尽,清辉满地,我睁着眼,直到天明。次日,我顶着一双堪比硕果的眼袋,
跟在引路侍女身后,去给王府真正的主子们请安。正妃沈若华,凤仪天成,端庄威严,
她淡淡地受了我一拜,便让我坐于末席。而另一位侧妃柳氏,
则毫不避讳地将我从头到脚细细打量,那目光黏腻如蛇信,所到之处,
激起我一身的鸡皮疙瘩。“妹妹这般绝色,想来必有不凡之处,也难怪王爷会动心。
”柳贵人轻轻拨弄着茶盏的浮沫,声音甜得发腻,话里却藏着钩子。我慌忙起身,
将姿态放得更低:“贵人过誉了,妾身蒲柳之姿,萤火之光,怎敢与各位姐姐的日月争辉。
”“哦?是吗?”柳贵人掩唇轻笑,那笑声在过分安静的厅堂里,显得格外尖利。
“妹妹可千万别学前头那几位,总觉得自己是天选之人,与这世道格格不入。你猜,
她们最后都怎么样了?”她似乎找到了极有趣的乐子,用一种分享秘闻,
令人毛骨悚然的口吻,开始细数这座华美牢笼里的亡魂:“第一个啊,性子最烈。
进府当晚,就对王爷高谈阔论,说什么‘女子不应是附庸,应有自己的天地’,
还说我们这些姐妹,都是被圈养的金丝雀。王爷呢,最喜欢清静。第二天,
她就在后湖的荷花深处,找到了永恒的安宁。”我的指尖一颤,滚烫的茶水泼在了手背上,
我却浑然不觉。柳贵人饶有兴致地欣赏着我的失态,继续说道:“第二个呢,
倒是是个聪明的,想走实用路子。她不知从哪弄来一张方子,说是能点石成金,
造出坚不可摧的城墙。可王爷觉得,一个深闺女子,懂得比朝中重臣还多,这份聪明,
比敌国的千军万马还可怕。后来呀,她那颗装满了奇思妙想的脑袋,
就成了城墙上最坚固的一部分。”“至于第三个嘛,”她故意顿了顿,像是在回味一道珍馐,
“她给王爷唱了支曲儿,那调子,据说闻所未闻,靡丽动人。可惜啊,
王府里一个喂马的奴才,也会哼那么两句。王爷最恨旁人觊觎他的东西,尤其是女人。当晚,
她就被赏给了府里的护卫们,听说,歌声比那曲子还动人。”每一个字,
都像一根烧红的铁钉,被她笑吟吟地,钉进我的骨头里。柳贵人终于放下茶盏,
目光若有似无地瞟向一直沉默不语的正妃沈若华,笑道:“最可惜的,还是第四位。
她懂的可真多,又是什么轮耕法,又是什么新式农具,恨不得把天都翻过来。
可正妃姐姐说得对,祖宗之法,乃国之根基,岂容动摇?一杯御赐的毒酒,
也算是王爷全了她最后的体面。”说完,她终于将视线转回我身上,那双潋滟的美眸里,
满是猫捉老鼠般的怜悯与嘲弄。“所以啊,林妹妹,”她柔声道,像在传授什么金玉良言,
“在这王府里,最要紧的,不是脑子,也不是脸蛋。”“是听话。
”第二章:棋盘上的棋子柳贵人那句淬了毒的“听话”,像一根无形的绣花针,
还扎在我耳膜深处,嗡嗡作响。我彻底成了一具被抽去灵魂的提线木偶,由侍女杏儿牵引着,
麻木地挪向下一处请安的殿宇——太妃的祥云堂。人未至,声先闻。一阵极力压抑的咳嗽声,
从堂内深处飘了出来,那声音细得像风中残羽,却又沉甸甸地,敲在每一个途经者的心坎上。
“姐姐这凤体,当真是比江南的丝绸还金贵。晨风才起了那么一丝丝,就咳成了这副模样,
这要是让外人听了去,还不得以为是谁胆大包天,给姐姐气受了呢?
”柳贵人那甜腻而尖锐的嗓音再次响起,像一把淬了蜜的刀子,精准地刺向那咳嗽声的源头。
我顺势抬眼,望见了一位身着月白素裙的女子。她正以一方素帕掩唇,
眉心凝聚着一抹怎么也化不开的愁绪。想必,她就是传说中那位集万千宠爱于一身,
却也集万千嫉恨于一身的侧妃,苏晚意。她的美,是一种濒临破碎,带着凄婉病意的绝色,
美得让人心惊,总觉得下一刻,她便会化作青烟,就此散去。“妹妹又拿我取笑了,
是我这身子不争气罢了。”苏晚意轻声应答,即便是被如此露骨地挑衅,
她的声音依然温润如玉,听不出一丝火气。“哼,不争气的,何止是身子。
”柳贵人冷哼一声,目光像两道实质的冰棱,毫不避讳地刮过苏晚意平坦无波的小腹。
这是一场无声,发生在锦绣堆里的凌迟。我垂下头,用尽全力让自己缩成一团影子,
一根柱子,一幅挂在墙上不会呼吸的背景。在这张巨大的棋盘上,
我不过是一枚刚刚被摆上来,无足轻重,却又随时可能被当作弃子牺牲掉的兵卒。“好了,
都是自家姐妹,往后还要朝夕相处,都少说两句吧。”正妃沈若华终于开口。
她的声音和她的人一样,沉稳端方,听不出半分喜怒,却带着不容置喙的威严。
“王爷最重府里的规矩,若让下人们听了去,嚼舌根子,成何体统。”她端坐于主位,
凤眼微抬,淡淡的目光扫过全场。方才还气焰嚣张的柳贵人立刻像被掐住了脖子的孔雀,
悻悻然地收起了所有翎羽。沈若华,是这座后院绝对的执法者,是秩序的化身,她的话,
便是圣旨。她朝我微微颔首,算是认了脸,那眼神疏离而公允,像在清点一本账册,
而不是在审视一个活生生的人。就在这份冰冷的宁静中,一缕浓郁的檀香随着珠帘的晃动,
悄然渗入。一位身着深色福字锦衣,发髻上只插着一支朴素玉簪的妇人,在侍女的搀扶下,
缓步从内堂走出。她便是这王府的根,楚王之母,当今太妃。“都来啦。
”太妃脸上挂着慈和安详的笑意,仿佛一位再寻常不过的邻家祖母。
她的目光温和地在我们每个人脸上转了一圈,最后,落在了我的身上。
“这便是新入府的林丫头吧?瞧着是个安静本分的,好,甚好。”我连忙起身,
规规矩矩地行了大礼。“坐,快坐下,在我这老婆子跟前,不必如此拘束。”她摆了摆手,
目光又转向苏晚意,语气里满是疼惜:“晚意啊,身子可好些了?
我叫御膳房给你炖了上好的血燕,你可得盯着人,按时喝了才行。”话锋一转,
她又看向柳贵人:“明月也是,你这孩子,就是火气太盛,仔细伤了肝气。
”她像一个完美的大家长,对每一个小辈都关怀备至,面面俱到,滴水不漏。然而,
当她的目光再次回到我身上时,那份温和却让我感到了一种泰山压顶般的窒息。“林丫头啊,
”她轻声细语,像在说什么体己话,“你年轻,身子骨瞧着也结实。要早些为王爷开枝散叶,
这才是一个女人安身立命的根本。王爷子嗣单薄,我这老婆子,
可就日日夜夜盼着能早些抱上孙儿了。”一句“开枝散叶”,轻飘飘的,却像一座无形的山,
狠狠压在了我的脊梁上。我眼角的余光瞥见,柳贵人的嘴角勾起一抹毫不掩饰的讥讽,
而苏晚意的脸色,似乎又白了三分。从祥云堂活着出来,我才终于敢大口喘气。
回到那座偏僻冷清的清芷院,杏儿为我奉上凉茶,在我身边踌躇了许久,才终于咬了咬牙,
将声音压得像蚊子哼:“主子……您今日,应当是瞧出来了吧?”我点点头,
端起茶杯一饮而尽,试图用那冰凉的茶水,来浇灭我心底翻腾的寒意。杏儿轻叹一声,
那口气里,有同情,有无奈,更有身处此间的无力感:“咱们王爷,那心尖尖上的人,
从始至终,都只有苏侧妃一个。”她见我没有打断,
便说得更深了些:“奴婢听府里的老人说,王爷曾有一位早逝的青梅竹马,是他的亲表妹。
而苏侧妃的容貌身段,与那位表**,有着七八分的相像。”原来如此。这份滔天的宠爱,
不是源于爱情,而是源于一个逝去之人的影子。苏晚意,不过是个替身。“王爷对苏侧妃,
那真是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天底下但凡有点好东西,都流水似的往她院里搬。
千年的人参,万年的灵芝,都当饭食似的给她吊着那一口气。可也正因为如此,
”杏儿的声音压得更低了,“她就成了所有人的眼中钉,肉中刺。正妃娘娘面上再大度,
心里哪能舒坦?柳贵人就更不必说了,她父亲可是手握重兵的大将军,她自视甚高,
哪里咽得下这口气?”“所以啊,苏侧妃看似风光无限,实则日日都在刀尖上行走。她活得,
比我们这些做奴婢的,还累。”我放下茶杯,指尖一片冰凉。一个活在影子里的替身,
一个骄横跋扈的将军之女,一个深不可测的铁腕正妃,
还有一个用慈爱催着所有人“开枝散叶”的太妃。这盘棋,杀机四伏。而我,
以及我那四位已经化为尘土的前辈,在这盘棋局里,又算什么角色呢?
是为了**苏晚意而存在的棋子?还是为了平衡各方势力而丢出的炮灰?我不敢再想下去了。
每多想一层,离地狱便更近一步。第三章:风平浪静下的暗涌我用日复一日的顺从,
为自己织出了一件名为“安分”的隐身衣。日子,竟真的滑入了一段诡异的死寂。
我将自己活成了一道可有可无的背景:晨昏定省时,是绝不多言的木雕;狭路相逢时,
是永远垂首的石像;独处清芷院时,是连呼吸都怕惊动尘埃的影子。
柳明月似乎也终于厌倦了向一块顽石投掷她那些无处发泄的怒火,
除了偶尔投来几道轻蔑如施舍的目光,倒也懒得再寻我的麻烦。
我就像一只学会了装死的猎物,蜷缩在安全的角落,不求饱腹,但求无祸。
只要能这样安静地、不被记起地活着,就好。然而,我忘了,在这座王府里,
命运从不由自己书写。有时候,哪怕只是一阵无心的风,都能将你这片落叶,
吹到烈火的中央。变故发生在太妃的寿宴上。那是一次再寻常不过的家宴,席间觥筹交错,
笑语晏晏。酒过三巡,王爷赵弈却不知为何,忽起雅兴,要考校一下在座女眷的才学。
正妃沈若华的诗,雍容大气,一如其人;柳明月的画,浓墨重彩,艳丽张扬;而侧妃苏晚意,
仅仅是素手抚了一曲《秋风词》,便引得王爷凝神静听,久久不语。轮到我时,
我只说自己愚笨粗鄙,仅识得几个字,妄图蒙混过去。可在王爷那不容拒绝的示意下,
我还是被“请”到了案前。我提着笔,手腕刻意放松,写下一首最浅白不过的祝寿打油诗。
我藏起了前世苦练十几年的笔锋,将每一个字都写得稚拙笨重,像孩童初学的涂鸦。
就在我暗自松了口气,以为终于可以退下时,赵弈却忽然离席,踱步至我身后。他俯下身,
一股清冷的龙涎香瞬间将我笼罩。他的目光,没有在我那谄媚的诗句上停留分毫,
而是像一把探针,精准地落在了我刻意隐藏,某一划的收尾处。
那是一种极其专注、又带着一丝穿透时空的审视,仿佛在透过我这副皮囊,
辨认着另一个早已腐朽的灵魂。“你的字,倒有几分……”他低声自语,话未说尽,
却已成功地让满座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我能清晰地感觉到,柳明月那道目光,
瞬间化为实质的芒刺,狠狠扎在了我的背上。赵弈没有再说下去,
只是随手从腰间解下一支通体莹润的白玉簪,甚至没有亲手递给我,
而是直接交予了我身旁的内侍。“赏她了。”那声音云淡风轻,却像一道晴天霹雳,
在我头顶轰然炸开。我跪在冰冷的地面上,双手因为极度的恐惧而剧烈颤抖,接过那支玉簪。
它触手冰凉,却烫得我几乎要立刻将它甩开。这不是赏赐,这是一道画在我额上的催命符。
从那天起,我用卑微换来的那点平静,被彻底撕碎。“哟,林妹妹,
这就戴上王爷赏的簪子了?果然是人要衣装,佛要金装,这么一衬,倒也真有几分狐媚样了。
”次日请安,柳明月笑吟吟地拦住我的去路,那涂着丹蔻的指甲,几乎要戳到我的脸上。
我慌忙垂下头,声音抖得不成样子:“贵人说笑了,妾身……妾身不敢。”“不敢?
我看你敢得很!”她脸色一变,声色俱厉,“苏姐姐身子抱恙,你倒会见缝插针,
学了她那点楚楚可怜的风骨去勾引王爷!真是好手段,好心机!
”“妾身没有……”“还敢顶嘴!”她话音未落,一记耳光已狠狠扇了过来。
我被打得偏过头去,半边脸颊瞬间麻木,随后便是火烧火燎的痛。但我没有哭,也没有辩解,
更没有去捂脸,只是立刻跪倒在地,将头深深地磕下去,一遍遍重复:“妾身知错,
请贵人息怒。妾身知错,请贵人息怒。”这,仅仅是个开始。接下来的日子,
我的份例被无故克扣,送来的饭菜永远是残羹冷炙。我被罚在没有炭火的佛堂抄写经文,
一抄就是整夜,直到手指冻得无法执笔。清芷院的炭火总是不翼而飞,在滴水成冰的冬夜里,
我只能将所有被褥裹在身上,像一只濒死的雏鸟,瑟瑟发抖。我成了柳明月情绪的便溺之所,
一个可以随意打骂的出气筒。我将自己缩得更小,变得更加卑微。远远见到她的仪仗,
我会主动躲进假山后;她开口斥责,我便立刻跪下认错;她降下惩罚,我便默默承受一切。
我用最彻底的顺从,来坐实自己“懦弱无能”的标签,我赌她会觉得,
反复欺凌一个毫无反抗能力的软骨头,是一件极其乏味的事。在这场无声的凌虐中,
正妃沈若华永远是那个最高高在上的看客。她端坐在她的权力之巅,
冷眼看着我们这些妾室的争斗,就像看一场与她毫不相干,热闹的猴戏。
而唯一给过我一丝暖意的,竟是苏晚意。有一次,柳明月罚我在庭院的雪地里跪了两个时辰。
当晚,我的膝盖便高高肿起,痛入骨髓。夜深人静时,苏晚意的贴身侍女却像个幽灵般,
悄悄潜入了清芷院,送来一小瓶成色极好的活血化瘀药膏。“我们主子说,
让林主子好生受着,莫要落下病根。”侍女将药膏塞进我冰冷的手中,低声传话,“她还说,
妹妹,忍一忍,就过去了。”我握着那瓶还带着旁人体温的药膏,心中五味杂陈,一片冰凉。
她是真的出于善良,还是……在庆幸,终于有另一个人,可以为她分担柳明月的炮火了?
在这座王府里,或许连善意,都带着精密的算计。我谁也不敢信。
第四章:喜孕与杀机那份虚假的平静,是被一声清脆的瓷器碎裂声,彻底击穿的。彼时,
在太妃的祥云堂里,时间仿佛已经凝固。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目光像无数根钉子,
死死地钉在那个跪伏于地、为苏晚意请脉的老太医身上。空气黏稠得几乎能拧出水来,
每一秒的等待,都是一场无声的煎熬。“如何?”楚王赵弈的声音划破了死寂,那里面,
竟带着一丝连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绷紧到极致的颤抖。老太医花白的胡须剧烈地抖动了一下,
他收回三指,随即以一种近乎献祭的姿态,将整个身体深深叩拜下去,
声音洪亮得足以震落屋梁上的尘埃:“恭喜王爷!贺喜王爷!苏侧妃……已有一月身孕!
”“啪!”柳明月手中的粉彩茶盏,应声落地,摔成了一地无法挽回的碎片。
滚烫的茶水溅湿了她华丽的裙摆,她却像被抽走了魂魄般浑然不觉,
一张向来美艳逼人的脸庞,在刹那间血色尽褪,惨白如纸。而楚王赵弈,
在经历了短暂到几乎不存在的怔忡后,那张万年冰封的脸上,竟爆发出一种我从未见过,
近乎癫狂的灼热光芒。他一把挥开身边所有侍从,三步并作两步冲到苏晚意身边,
小心翼翼地将她从榻上扶起,那动作,虔诚得仿佛在对待一件触之即碎的稀世琉璃。“晚意!
你听到了吗?我们……”他紧紧攥住她的手,眼中的狂喜几乎要将她点燃,“我们有孩子了!
”“王爷……”苏晚意的眼眶一红,泪水便不受控制地滚落,那泪水中,不知藏着几分喜悦,
又藏着几分惊惧。“从今日起,”赵弈猛然转身,目光如利剑般扫过满屋神色各异的女人,
下达了不容置喙的铁令,“侧妃免去所有请安,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
踏入她的院子半步!她若少了一根头发,本王要你们所有人都陪葬!”这句话,掷地有声,
像一块巨石砸入死水深潭。激起的,却不是喜悦的涟漪,而是冰冷刺骨的杀意。
我看到柳明月的指甲,已深深嵌入掌心,几乎要掐出血来。而主位上的正妃沈若华,
脸上依旧挂着无可挑剔的得体微笑,只是那笑意,像一层精美的冰雕,
没有一丝温度能抵达眼底。最先打破这份诡谲的是太妃。她满面红光地走上前,
亲热地拉住苏晚意的手,慈爱地轻轻拍着:“好孩子,我的好孩子!
你可真是我们赵家的大功臣!快,快坐下,可千万不能累着我的乖孙儿。
”她转头对身边的管事嬷嬷吩咐道,
声音里满是藏不住的喜悦:“立刻把我私库里那支最老的千年人参,
还有所有能叫上名号的补品,全都送到侧妃院里去!记住了,从今往后,侧妃的一日三餐,
都必须由我亲自过问!”太妃的关怀无微不至,那份热络,却像一条华美的锦被,
让人感到一种甜蜜的窒息。王府的气氛,从这一天起,彻底变了。表面上,风平浪静,
一片祥和。太妃每日嘘寒问暖,赏赐如流水般涌入苏晚意的庭院。
王爷更是将那方小小的院落围得如铁桶一般,别说一个人,便是一只苍蝇都休想飞进去。
柳明月像一只被拔了利爪的猛虎,再也不敢明着寻衅。只是每次请安,
她望着苏晚意空出来的那个座位时,眼神都阴鸷得能滴出毒汁。她不再找我的麻烦,
因为她所有的恨意,都有了一个更清晰、更具体的靶心。而正妃沈若华,
则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交口称赞的“贤德”之事。她亲自带着自己的女儿赵灵犀,
前往京郊最负盛名的护国寺,为苏晚意腹中的胎儿斋戒祈福,一去便是三日。消息传回王府,
人人都称颂正妃宽厚大度,母仪天下。可只有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假象。这座王府,
变成了一个巨大,精致的舞台。每个人都戴上了最完美的假面,
全情投入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温柔,慈爱,嫉妒,贤惠的……她们的台词无可挑剔,
她们的表情滴水不漏。然而,当我独自走在王府幽深的迴廊下,却能清晰地感觉到,
空气中那股紧绷到极致,一触即发的气息。侍女们走路的脚步都轻了,说话的声音都低了,
每个人的眼神都在惊惶地闪躲,生怕自己会成为那根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杀机,
就蛰伏在那些虚伪的笑容与温存的问候背后。一场足以将所有人吞噬的风暴,
正在无声地酝酿。而苏晚意腹中那个尚未成形的孩子,就是这场风暴的风眼。
他(她)的每一次心跳,都在为这座金碧辉煌的牢笼,敲响倒计时的丧钟。
第五章:血染的香囊那把最终杀人的刀,是以一份天真为鞘,用一双稚嫩的手,
亲自递出来的。正妃沈若华的女儿,年仅十岁的赵灵犀郡主,
亲手绣了一个针脚歪歪扭扭的鸳鸯戏水香囊,作为礼物,送到了苏晚意的枕边。
“听闻苏娘娘近来夜里总睡不安稳,这是灵犀为娘娘求来的心意。
”小郡主仰着一张纯洁无瑕的脸蛋,声音清脆得像一串风中的银铃,“里头的香料,
都是母亲大人亲自去寺里开过光,挑选的上好安神香,能让娘娘和未出世的弟弟睡个好觉。
”苏晚意看着那针脚虽稚拙,却充满童趣的香囊,眼眶瞬间就红了。她将那份礼物视若珍宝,
亲手挂在了床头最显眼的位置。她甚至还在我们前去探望时,
满脸幸福地笑着说:“还是正妃姐姐最是细心,灵犀这孩子,也真是贴心,像个小暖炉似的。
”当时,在场的每一个人,都由衷地赞叹着郡主的孝心与正妃的贤德大度。没有人能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