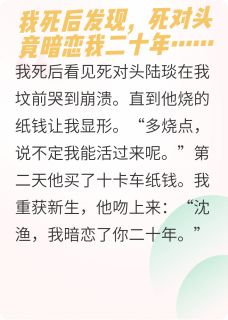我死后看见死对头陆琰在我坟前哭到崩溃。直到他烧的纸钱让我能在梦里显形。“多烧点,
说不定我能活过来呢。”我开玩笑。第二天他买了十卡车纸钱堆满山头。火焰中我重获新生,
他赤红着眼吻上来:“沈渔,我暗恋了你二十年...”1雨水像是天被捅了个窟窿,
没头没脑地往下泼,砸在冰冷的墓碑上,噼啪作响。墓碑上嵌着的黑白照片里,是我,沈渔。
照片里的我嘴角还挂着那副混不吝的弧度,像是在嘲笑这狗屁倒灶的人间,
更像是在嘲笑此刻跪在泥水里,哭得像个傻子的陆琰。他那身名贵的西装早就糊满了泥浆,
精心打理过的头发被雨水浇透,狼狈地贴在额角。那张平日里对着我,
不是冷笑就是刻薄讥讽的俊脸,这会儿被一种近乎崩溃的绝望扯得变了形。
雨水混着眼泪鼻涕糊了一脸,要多难看有多难看。我飘在自己坟头上头,冷眼瞅着,
心头的邪火噌噌往上蹿。“陆琰,**演戏演上瘾了是吧?
”我冲着他那张涕泪横流的脸吼,声音当然只有风能听见,“咱俩从穿开裆裤就开始掐,
幼儿园抢积木,小学争小红花,中学打架一块儿蹲局子,大学抢项目抢到双双在校长室罚站!
你忘了?我咽气那天,你丫还拉了一卡车鞭炮在殡仪馆门口放得震天响,
就差举个‘热烈庆祝沈渔归西’的横幅满街跑了!现在搁这儿哭坟?哭给鬼看呢?
装什么兄弟情深!”这戏码也太投入了,投入得我想凝聚个实体,一脚把他踹泥坑里去。
陆琰听不见我的咒骂。他猛地俯下身,额头一下又一下,重重地磕在坚硬冰冷的墓碑底座上,
“咚”、“咚”的闷响,听着都疼。鲜红的血丝立刻从额角渗出来,混着泥水往下淌。“操!
”我惊得魂体都晃了晃。这孙子……来真的?他抬起头,
雨水冲刷着他脸上蜿蜒的血痕和泥污。那双平时看人总带着三分讥诮七分凉薄的眼睛,
这会儿空洞得吓人,像两口被绝望彻底淘干了的枯井。他死死盯着墓碑上我的照片,
嘴唇哆嗦着,喃喃自语,
不该…不该是这样的……沈渔……你怎么能……怎么能……”后面的话被更凶猛的呜咽吞了。
他像个被全世界扔下的孩子,蜷在冰冷的墓碑前,肩膀抖得筛糠似的,雨水无情地浇着。
我飘着,那股被背叛的火气莫名其妙地消了大半,
只剩下一种毛骨悚然的荒谬感和一丝……连自己都不愿承认的酸涩。演得太真了,
真得让我心里发毛。就在这时,陆琰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
手忙脚乱地去掏他那湿透的西装口袋。哆嗦着掏出个被雨水泡得软塌塌的烟盒,
又摸出个同样湿淋淋的纯金打火机。啪嗒,啪嗒,火石艰难地擦了几下,终于,
一小簇微弱的火苗在暴雨里顽强地亮了起来,跳动着,随时要灭。他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
胡乱地从旁边一个同样湿透的黑色大塑料袋里,
扯出一大把惨白粗糙的黄纸——烧给死人的冥钱。
他笨拙地把那一大沓纸凑向那点随时会灭的小火苗。“别费劲了!”我飘在旁边嗤笑,
“这么大的雨,点得着才有鬼……”话音还没落,怪事发生了。
那簇小火苗竟然真的舔上了黄纸的边儿,顽强地烧了起来,橘红色的光在灰暗的雨幕里跳动,
映着陆琰那张被雨水、泪水、血水糊得乱七八糟的脸。一股难以言喻的暖流,像最醇厚的酒,
猛地灌进我虚无的魂体。那感觉太清晰了,清晰得我浑身一震,
仿佛冻僵的四肢百骸瞬间泡进了温泉里,每一个“细胞”都在满足地**。
原本轻飘飘、随时会被风吹散的意识,也像是被什么东西锚定了,
前所未有的踏实感裹住了我。我惊愕地低头“看”着自己半透明的手掌,
那被雨水穿透的虚影,似乎……真的凝实了那么极其微弱的一丝?虽然还是虚,但那点变化,
实实在在!2陆琰浑然不觉,只是死死盯着那堆在暴雨里艰难燃烧、冒着滚滚浓烟的纸钱。
火苗被雨水打压着,微弱得很,浓烟呛得他直咳嗽,眼睛熏得通红,泪流得更凶。
但他不管不顾,像着了魔,机械地从湿透的袋子里掏出更多的纸钱,
拼命往那堆小小的火焰上塞,哪怕只让它旺一点点。
“烧……多烧点……沈渔……”他语无伦次地哽咽着,嗓子哑得厉害,
“你收着……都收着……别在下面……受委屈……”浓烟呛得他快背过气,
手上的动作却越来越快,越来越疯。每投入一把新的纸钱,
我都能清晰地感觉到一股更强的暖流注入我的“身体”,那份凝实感像被反复锻打的铁,
正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变得坚固、沉重。一个荒谬绝伦、却又带着致命诱惑的念头,
像藤蔓一样死死缠上我的意识——这孙子烧的纸钱,**是我的“口粮”!接下来的日子,
我成了陆琰梦里的钉子户。这发现简直让我乐疯了,一种恶作剧般的兴奋冲淡了死亡的阴霾。
第一次成功入梦是在他烧完纸的第三晚。在他那个大得离谱、装修得跟冰窖似的书房里。
他趴在巨大的红木书桌上睡着了,眉头锁得死紧,眼下乌青一片。我攒了半天劲,
才勉强把自己那半透明的影子投射在他书桌对面那张贵得离谱的意大利真皮沙发上。
我跷着二郎腿,努力摆出最欠揍的姿势,冲他吹了个无声的口哨。陆琰在梦里似乎有感应,
猛地抬起头。当他的视线聚焦在我身上时,那双深眼睛骤然瞪大,
瞳孔里清清楚楚映着我半透明、跷着腿的影子。他像是被无形的巨锤砸中了,
整个人从椅子上弹起来,带倒了身后的椅子,刺耳的摩擦声在梦里都那么真切。
“沈……沈渔?!”他的声音抖得不成调,充满了难以置信的惊骇,脸唰一下白得吓人。
我咧嘴一笑,故意让笑容显得阴森森的,朝他挥挥手。可惜,动作一大,魂体立刻不稳,
像信号不良的电视画面一样剧烈闪烁起来,边缘模糊。
陆琰脸上的惊骇瞬间被一种更强烈的、近乎疯魔的急切取代。他踉跄着扑过来,伸出手,
想抓住我闪烁的影子。手指毫无阻碍地穿过了我虚影的手臂,抓了个空。“别走!
”他嘶吼着,声音里是快崩溃的绝望,“沈渔!告诉我!告诉我怎么才能留住你?!
”看着他失魂落魄、痛不欲生的样子,一股说不清的滋味涌上来。妈的,这王八蛋,
恨我的时候是真恨,现在……这又算怎么回事?戏精附体?还是脑子进水了?
心里那点恶趣味占了上风。我稳住闪烁的魂体,凑近他,用一种飘忽又十足戏谑的语气,
在他耳边低语,
确保每个字都烙进他的梦:“纸钱……多烧点……说不定……”我故意拉长了调子,
像讲个荒诞的笑话,“……我还能活过来呢?嗯?”说完,魂力耗尽,
我的影子像被风吹散的烟,瞬间没了。只留下陆琰僵在原地,脸上交织着狂喜和更深的绝望,
像个被巨大希望砸懵又怕一切是假的可怜虫。后来几次入梦,我变着法儿骚扰他。
有时在他公司顶层的落地窗前,外面是璀璨夜景,我飘在他身后,
对着玻璃映出的影子做鬼脸;有时在他空旷的卧室,他躺在床上,我就蹲在床头柜上,
用虚影手指去戳他紧皱的眉头。每次出现,我都只说一两句话,主题永远不变:烧纸,
越多越好。3“喂,陆大总裁,手头紧啊?烧那么点够谁塞牙缝?火力不足啊兄弟!
”我飘在他昂贵的波斯地毯上吐槽。“啧,今天这叠金元宝成色不行啊,
下面通货膨胀懂不懂?得加量!”我抱着手臂,一脸嫌弃地评着他刚烧完的那堆灰烬。
“陆琰,你是不是不行?烧个纸都磨磨唧唧!”我故意激他。陆琰的反应一次比一次邪乎。
从最初的震惊狂喜,到后来的急切追问,再到最后,他变得沉默又偏执。每次在梦里看见我,
他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就像饿狼锁定了猎物,死死盯着我,
里面翻涌着我看不懂的、浓稠化不开的东西。他不再试着碰我,也不问怎么留下我。
他只是看着我,用那种要把我魂儿吸进去的眼神,然后在我消失前,哑着嗓子,
一遍遍重复:“等着……沈渔……你等着……”他那眼神看得我后背发凉,
总觉得这家伙的精神头儿在往一个极其邪门的方向一路狂奔。但能凝实体的诱惑太大了,
像毒瘾,沾过一次就戒不掉。每一次纸钱烧起来的暖流,
都让我离那个“活过来”的荒诞念头更近一步。直到那天晚上,我又摸进他梦里。
地点还是那书房,气氛却变了天。陆琰没坐书桌后,而是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背对着我。
窗外是沉沉的夜。我刚凝出虚影,他就猛地转过身。月光打在他瘦得脱形的侧脸上,
眼窝深陷,下巴胡茬凌乱,整个人透着股快烧干的疲惫,只有那双眼睛,亮得瘆人,
里面烧着一种豁出去的、孤注一掷的疯劲儿。“沈渔。”他开口,嗓子哑得像砂纸磨过,
却带着种奇异的平静,平静得让人心慌,“明天。”“嗯?”我被他这没头没脑的话弄懵了。
他往前走了一步,月光照亮了他脸上近乎虔诚的决绝。他死死盯着我虚幻的眼睛,一字一顿,
每个字都像从骨头缝里挤出来,带着滚烫的烙印:“明天,你来。”“来什么?去哪儿?
”我皱眉,被他这状态搞得有点发毛。他不解释,只是重复着,眼神偏执得吓人:“明天!
等着我!一定要来!沈渔!”那眼神里的疯狂和执念太冲了,冲得我这鬼魂都心惊肉跳。
我刚想追问,魂力耗尽,视野瞬间模糊。在彻底消失前,
我好像看到他嘴角扯了一下……近乎狰狞的、豁出去了的弧度。4第二天傍晚,
残阳像血泼在城郊那座孤零零的山头上。风刮得邪乎,卷起尘土和枯叶呜呜叫,
像无数冤魂在哭。我飘在自己墓碑上头,心里七上八下。
陆琰昨天梦里那副“明天见生死”的鬼样子,总觉得要出大事。这神经病,
该不会搞什么邪门歪道吧?就在夕阳快沉进地平线那会儿,山下闹腾起来了。不是一辆车,
也不是几辆车。是轰鸣。地在抖。一条由重型卡车组成的铁龙,咆哮着,像醒了的远古巨兽,
顺着盘山公路往上爬。一辆、两辆、十辆……整整十辆巨大的、满载的红色解放卡车,
喷着黑烟,引擎的吼声撕破了山野的寂静,惊得鸟雀乱飞。
车队最终停在山腰一片开阔的坡地,离我坟地不远。车门砰砰响,
跳下来几十个穿着工装、戴安全帽的壮汉,动作麻利得像支军队。他们沉默着,
在工头指挥下,开始卸货。卸下来的东西,让飘着的我,魂儿差点当场吓散。纸钱!
全是纸钱!不是那种糙了吧唧的黄纸,
是印着硕大“天地银行”、面额动辄“壹佰億”、“伍佰億”的豪华版冥币,
一捆捆用塑料膜包得严实,像巨大的金砖。还有成箱成箱金灿灿的“金元宝”,
叠得整整齐齐的“别墅”、“跑车”、“游艇”纸扎,
甚至有几匹扎得活灵活现、几乎等身高的“骏马”!十辆巨卡的货斗被掏空了。
卸下来的纸钱和祭品,堆满了整个山坡,像座山!金灿灿的“钱”,花花绿绿的“财产”,
在夕阳余晖下反着光,荒诞又刺眼,形成一片散发着浓重油墨和浆糊味的“金山”!
陆琰从领头卡车的副驾驶下来。一身纯黑修身风衣,衬得脸更白,眼下乌青浓得像挨了揍。
几天不见,人瘦脱了相,风衣穿在身上空荡荡的。但他站得笔直,背脊像根宁折不弯的钢钎。
山风吹乱了他额前的碎发,露出那双眼睛——里面烧着种近乎病态的、豁出去了的火,
疯狂、执拗,还有一丝……孤注一掷的绝望。他无视那些搬运工,
也无视这能让人眼珠子掉出来的“金山”。目光穿透了空间,
死死地、牢牢地钉在我墓碑的方向。那眼神,像穿过了生死的界限,
直接钉在了我飘荡的魂儿上!“开始。”他薄唇微动,声音不大,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绝,
穿透风声和引擎的余音。工头立刻抄起对讲机吼了几句。几十个工人迅速动起来,
他们不是像往常那样小堆小堆地烧,而是……泼汽油!刺鼻的汽油味瞬间冲进鼻子。
大量的汽油泼在那座纸钱祭品堆成的山上。几个工人拿着长柄点火器,
分散在“金山”几个角。陆琰还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像块黑色的礁石。目光,自始至终,
没离开过我墓碑的方向。眼神里的火,快化成实质了。“点火!”工头一声令下。嗤——!
数道火舌几乎同时从“金山”的不同角落窜起!火焰撞上汽油,像饿兽见了鲜肉,轰然爆燃!
轰!!!一声沉闷的巨响!不是鞭炮,是火焰瞬间吞掉巨量东西的怒吼!十卡车纸钱同时烧,
产生的热和光,像颗小太阳砸在了山坡上!“卧……槽……”我飘在墓碑上头,
魂体被那瞬间爆发的、排山倒海般的能量彻底淹了!这不再是涓涓细流,不再是温乎气儿!
这是山崩海啸!是恒星爆炸般的能量!比以往任何一次都磅礴亿万倍的“暖流”,
带着烧化一切的灼热和让人魂儿发抖的生命力,像决堤的灭世洪水,
蛮横地灌进我虚无的魂体!“呃啊——!
”一种无法形容的、魂儿被硬生生撕开又粗暴捏合的剧痛席卷了我!
仿佛每一个“粒子”都在尖叫着被粉碎,
下一秒又被那狂暴的能量强行捏合、锻造、压上重量!我再也飘不住了!
像颗被无形大手狠狠砸向地面的石头,猛地往下坠!砰!!!一声闷响!不是砸在软泥上,
是狠狠撞上了一块硬邦邦、冰凉的东西——我的墓碑!剧痛!
真实的、刺骨的、属于肉身的剧痛,瞬间从后背炸开,窜遍全身!
“嘶……”我倒抽一口冷气,这久违的、活人的痛感,让我脑子一片空白。
灰尘和呛人的烟味猛地灌进鼻子,呛得我直咳嗽:“咳!咳咳咳!”嗓子干得发紧,
每喘一口气都带着灼痛。我下意识抬手,想去揉撞疼的后背,
指尖却先碰到了冰冷、粗糙的石头面儿——墓碑的背面。手指的触感……温热、实在,
带着细微的纹路和生命搏动的脉搏!不再是虚无的穿透!不再是冰凉的空气!是……真身!
5我猛地低头。夕阳最后一缕光,穿过漫天飞舞、像黑雪似的纸灰,落在我摊开的手掌上。
皮肤是健康的暖色,指甲盖透着淡淡的粉,掌心的纹路清清楚楚。
不再是半透明的、随时会散的虚影!我……活了?我真……活了?!
心脏在腔子里疯了一样地擂,咚咚咚,像要撞开肋骨蹦出来!血在血管里奔流,
发出久违的、让人发晕的轰鸣!后背撞墓碑的钝痛,吸进烟尘的呛咳,
被热浪烤的灼烧感……所有活人的知觉,像潮水一样涌回来,瞬间淹了我!狂喜?惊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