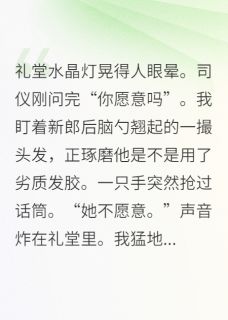江肆在医院观察了两天。确定没有大碍才出院。额角的纱布拆掉了。留下一道浅浅的痂。
像一枚小小的勋章。出院那天。他没回公寓。直接让司机把车开到了……民政局?
我看着车窗外那栋熟悉的建筑。傻眼了。“你……干嘛?”“领证。”他答得理所当然。
侧过头看我。眼神灼灼。带着一种“你休想再跑”的霸道。“怎么?想反悔?
”他指了指自己额角那道新鲜的痂。“阮朝暮。”“救命之恩。”“以身相许。
”“天经地义。”我被他这强盗逻辑气笑了。“谁答应你以身相许了?”“你亲我了。
”他理直气壮。“亲一下就要领证?”“不然呢?”他挑眉,凑近一点,
温热的气息拂过我的耳廓,声音压低,带着蛊惑,“难道……你想白嫖?”“江肆!
”我脸腾地红了。他低低地笑起来。胸腔震动。愉悦而满足。然后。他收敛了玩笑的神色。
目光变得认真而深沉。像静谧的深海。“朝暮。”他叫我的名字。不再是连名带姓。
带着一种珍而重之的温柔。“我知道。”“太快了。”“你还有很多不确定。”“没关系。
”他伸出手。干燥温暖的掌心。包裹住我有些冰凉的手。十指紧扣。力道坚定。
“我们有一辈子的时间。”“你可以慢慢想。”“慢慢看。”“慢慢确定。
”“看我是不是……”他顿了顿。眼底漾开细碎的光。像揉进了星辰。“真的值得你托付。
”“下辈子。”“下下辈子。”他的声音不高。却像带着千钧的重量。一字一句。
稳稳地落在我的心上。我看着他的眼睛。看着那道浅浅的疤痕。
看着里面盛满的、毫无保留的温柔与坚定。心口被一种巨大的、温暖的、踏实的情绪填满。
满得快要溢出来。那些关于重生匪夷所思的疑惑。关于未来的不确定。
关于二十一年“死对头”身份的微妙。在这一刻。似乎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眼前这个人。
在礼堂里把我从悬崖边拉回。在风雨中为我筑起堡垒。在生死一线间毫不犹豫挡在我身前。
用最笨拙也最赤诚的方式。把一颗滚烫的心。剖开。捧到了我面前。我反手。
更用力地回握住他的手。指尖传递着同样的力量。然后。我拉开车门。跳下车。
站在民政局门口明媚的阳光下。朝他伸出手。脸上扬起一个灿烂的、毫无阴霾的笑容。
“江肆。”“还等什么?”“进去啊!”“下辈子下下辈子太长。
”“这辈子……”“我预订了!”他看着我伸出的手。看着我脸上的笑容。愣了一下。随即。
那深邃的眼眸里。爆发出璀璨夺目的光彩。像沉寂的火山。终于喷涌出最炽热的熔岩。
他大步跨下车。长腿一迈。三两步就走到我面前。没有去握我的手。而是直接张开双臂。
将我整个人。紧紧地。用力地。拥入怀中!力道大得像是要把我揉进他的骨血里。
他身上清冽的冷松气息。混合着阳光的味道。瞬间将我包围。温暖。而坚实。“好。
”他低沉的声音。带着难以抑制的激动和颤抖。响在我的耳畔。像最郑重的誓言。“这辈子。
”“下辈子。”“下下辈子。”“你都是我的。”“阮朝暮。”“我的。”他松开怀抱。
却依旧紧紧握着我的手。十指紧扣。掌心相贴。滚烫的温度。一路蔓延到心底。他拉着我。
转身。大步流星。朝着民政局那扇象征着幸福与承诺的大门。走去。阳光在我们身后。
洒落一地碎金。我微微侧过头。看着他线条冷硬却无比柔和的侧脸。
看着他眼底跳跃的、毫不掩饰的喜悦和光芒。看着我们紧紧交握、仿佛永远不会分开的手。
心口。被一种前所未有的、饱满的、踏实的幸福感。充盈着。死对头?重生?娶我回家?
管他呢。重要的是。此刻。他牵着我的手。走向我们的未来。走向属于我们的。朝朝暮暮。
两本崭新的红本本。被工作人员微笑着递出来。钢印鲜红。照片上。我们头挨着头。
他嘴角噙着一丝得逞的笑。我眼里盛满了光。江肆一把抢过属于他的那本。
像抢到了什么稀世珍宝。翻开来。指尖摩挲着照片。又小心翼翼地。
揣进了贴近胸口的内袋里。还用力按了按。仿佛这样。就真的把我揣进了心里。“走了。
”他重新牵起我的手。指腹在我手背上无意识地摩挲着。带着薄茧。有点痒。“回家。
”“回哪个家?”我故意问。“我们的家。”他答得斩钉截铁。拉着我。
脚步轻快得像是要飞起来。刚走出民政局大门。刺眼的闪光灯毫无预兆地亮成一片!
五六个扛着长枪短炮的记者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瞬间围堵上来!话筒几乎要戳到我们脸上!
“江先生!阮**!恭喜二位!请问你们真的是在阮**与赵先生婚礼当天相识相恋的吗?
”“有传闻说你们是商业联姻,是为了对抗赵明轩和王海洋的阴谋,是真的吗?”“阮**!
赵明轩先生昨天公开指控您婚内出轨江先生,转移财产,您有什么要回应的吗?”“江先生!
听说您动用家族势力对赵家赶尽杀绝,是否属实?”尖锐的问题。像淬了毒的刀子。
劈头盖脸砸过来。带着窥探隐私的恶意和煽动性。江肆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
眼神骤然变得冰冷锋利。像出鞘的寒刃。他把我往身后一拉。用自己高大的身躯。
严严实实地挡住那些刺眼的镜头和咄咄逼人的话筒。“让开。”他开口。声音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