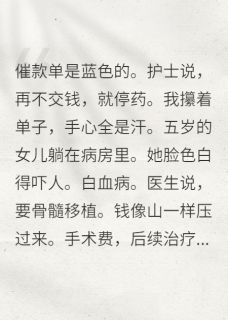催款单是蓝色的。护士说,再不交钱,就停药。我攥着单子,手心全是汗。
五岁的女儿躺在病房里。她脸色白得吓人。白血病。医生说,要骨髓移植。
钱像山一样压过来。手术费,后续治疗费。我把能卖的都卖了。老家那点破房子,
值不了几个钱。积蓄像水一样流干。电视挂在医院走廊顶上。声音嗡嗡响。本地新闻。
镜头晃得厉害。一家24小时便利店。招牌旧了,缺了个角。抢劫案。
一个男人死死护着收银机。头发很短,全白了。像落了一层厚厚的雪。镜头扫过他的脸。
一道疤,从眉骨划到颧骨。很深。我手里的塑料杯子掉在地上。水溅了一裤腿。是他。陈砚。
我的前夫。那个我以为这辈子再也不会见到的人。他头发全白了。五年。才五年。
他老了二十岁。护士催缴费的声音还在耳朵边响。电视里,警察带走了劫匪。
记者把话筒戳到陈砚面前。他低着头,摆手。手指关节粗大,手背上也有疤。
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工服。便利店的名字印在胸口。很小一家店。心脏跳得像要炸开。
女儿在里面躺着,等着钱救命。他在这里。就在这个城市。像个最普通的打工老头。
他怎么会在这里?他怎么会变成这样?我猛地站起来。催款单在我手里捏成一团。
汗浸透了纸。我知道那家便利店。在城西。一个很旧的小区外面。我冲进病房。女儿睡着了。
小脸陷在枕头里,呼吸很轻。我摸了摸她的额头。有点烫。时间不多了。我亲了亲她的脸。
很轻。怕吵醒她。转身跑出医院。风很大。刮在脸上生疼。我招手拦了辆出租车。“城西,
惠民小区旁边那个便利店。”司机从后视镜看我。我眼睛大概很红。他没说话,踩了油门。
车子开得飞快。窗外的楼房向后倒。五年前的事,也像这些楼一样,压过来。
压得我喘不过气。我叫安今朝。安是安定的安,今朝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今朝。我妈说,
这名儿好,活在当下。可我的当下,曾经全是陈砚。陈砚不是活在当下的人。他要掌控一切。
掌控我。嫁给他时,我才二十一。他家有钱。很有钱。他爸是开厂的。陈砚接手后,
生意做得更大。他长得也好。个子高,眉眼深。很多女人喜欢他。我以为我走了大运。
新婚头几个月,像泡在蜜罐里。他对我很好。要什么给什么。珠宝,衣服,包包。
堆满衣帽间。他说我穿什么都好看。他喜欢带我出去。应酬,聚会。把我圈在他手臂里。
像展示一件珍贵的收藏品。慢慢地,变了味。“今朝,手机给我看看。”他靠在床头,
刚洗完澡,头发湿漉漉的。语气随意,像在说天气。我正刷着朋友圈。愣了一下。
“看我手机干嘛?”他笑了笑。伸手拿过去。“随便看看。查查岗。”手指划拉着屏幕。
翻我的聊天记录。翻我的相册。每一个联系人,每一张照片。他看得很仔细。我有点不舒服。
像被人扒光了衣服。“有什么好看的。”我想抢回来。他手一抬,躲开了。
“看看我老婆跟谁聊天,不行?”他还在笑。眼神却没什么温度。后来,这成了习惯。
我的手机,在他那里没有秘密。他给我装定位。随时能知道我在哪。家里的保姆,司机。
都是他的眼睛。“太太,先生问您中午和谁吃饭了?”保姆一边擦桌子,一边问。
眼睛没看我。“一个大学同学,女的。”我切着水果。刀有点钝。“先生问,叫什么名字?
在哪儿吃的?”保姆停下动作。看着我。水果汁黏在手上。我报了个名字。报了个餐厅。
心往下沉。像掉进冰窟窿。一点自由都没有。喘不过气。我提过。吵过。闹过。“陈砚,
我不是犯人!”我把他的茶杯摔在地上。瓷片飞溅。褐色的茶水洇湿了地毯。他坐在沙发上。
眼皮都没抬一下。慢条斯理地擦着他的金丝眼镜。“今朝,外面很乱。我是为你好。保护你。
”他把眼镜重新戴上。镜片后的眼睛看着我。平静,不容置疑。
“你只需要待在我看得见的地方。乖乖的。”“保护?”我气得浑身发抖,“你这是监视!
是控制!”他站起身。走近我。高大的影子笼罩下来。带来压迫感。“控制?
”他捏住我的下巴。力道不轻。“你是我的妻子。我的。明白吗?”他的气息喷在我脸上。
热的。带着一种偏执的占有欲。“你的一切,都是我的。包括你的行踪,你的时间,
你这个人。”他低头,在我嘴唇上咬了一口。不重,但带着警告。“别再说这种话。
也别想着离开。你离不开的。”那次之后,我彻底明白了。他不会改。我在他心里,
就是个漂亮的物件。得摆在他眼皮底下。按他的心意活着。我想逃。这个念头像野草,疯长。
但陈砚看得太紧。他的势力太大。我娘家没人。我妈早没了。爸是个赌鬼,
拿了陈砚一大笔钱,早不知道跑哪去了。没人能帮我。逃,硬逃是找死。得让他彻底放手。
让他以为我死了。这个念头冒出来的时候,我自己都吓了一跳。太疯狂。
但像黑暗里的一道光。唯一的生路。我开始偷偷攒钱。现金。不多。几百几百地藏。
塞在旧书里,塞在废弃的化妆盒夹层。我不敢动卡。他查得到流水。也不敢联系任何人。
风险太大。我变得格外“乖”。顺从他的一切要求。他喜欢我穿什么,我就穿什么。
他让我陪他去哪,我就去哪。不再看手机。不再提任何朋友。像一只被驯服的金丝雀。
窝在他打造的笼子里。他好像很满意。眼神里的审视少了些。放松了些警惕。
机会来得猝不及防。他要去国外谈一笔大生意。半个月。这是他第一次长时间离开。
保姆张妈老家有事,请假回去了。新来的保姆还没到岗。
家里只剩下我和一个不住家的钟点工。天赐良机。那几天,我心跳得厉害。像揣了个兔子。
面上还得装平静。计划在脑子里过了无数遍。我选了一条盘山公路。去邻市必经之路。弯多,
坡陡。监控少。容易出“意外”。那天下午,天气阴沉。预报说有雨。
我开着自己那辆红色小跑车。车是陈砚买的。他说红色衬我。车里,
放着我提前准备好的东西。几件我的衣服。一个旧包。包里塞了点零钱,
一张不记名的超市卡。最重要的,是我手腕上常年戴着的那个翡翠镯子。水头很好,
陈砚奶奶给的。算是传家宝。他一直盯着,我几乎从不离身。我把镯子褪下来。
小心地放在副驾驶座上。一个显眼的位置。深吸一口气。踩下油门。车子像一道红色的箭,
射向盘山公路。雨点开始砸下来。噼里啪啦打在挡风玻璃上。雨刮器疯狂地左右摇摆。
视线有些模糊。心脏在胸腔里狂跳。几乎要撞出来。握着方向盘的手全是汗。滑腻腻的。
这条路我开过几次。熟悉每一个弯道。前面就是最险的那个急弯。一边是山壁,
一边是陡峭的悬崖。没有护栏。就是这里。我猛踩油门。引擎发出轰鸣。车子像失控的野兽,
冲向悬崖边的弯道。速度太快。轮胎在湿滑的路面上尖叫。失重感猛地袭来。
身体被狠狠甩向车门。头磕在玻璃上。嗡的一声。天旋地转。车子翻滚着。
金属扭曲的声音刺耳极了。玻璃碎裂。世界颠倒。我死死护住头。蜷缩在驾驶座。
剧痛从身体各处传来。温热的血顺着额角流下。腥咸的味道。车子终于停下。四轮朝天。
我挂在安全带上。血糊住了眼睛。雨水混合着血水,流进嘴里。咸的,涩的。
我艰难地解开安全带。身体重重地摔在变形的车顶上。疼得眼前发黑。用尽全身力气。
我从破碎的车窗爬出去。冰冷的雨水瞬间浇透全身。伤口被**得**辣地疼。我跌跌撞撞,
滚进旁边浓密的灌木丛里。荆棘划破了皮肤。顾不上疼。死死趴着。屏住呼吸。
警笛声由远及近。红蓝的光在雨幕中闪烁。脚步声。人声。有人在喊:“车里没人!”“找!
快找!”“下面是悬崖!太深了!雨太大!”我听到他们在我头顶的公路边呼喊。
手电筒的光柱在雨夜里胡乱扫射。有几束光掠过我藏身的灌木丛。我把自己缩得更紧。
脸埋在冰冷的泥水里。一动不动。“找到一个包!还有……镯子碎了!”有人喊。
声音在风雨里断断续续。“是陈太太的镯子!她常戴的那个!
”“完了……这掉下去……”搜寻持续了很久。雨越下越大。山崖下漆黑一片。水流湍急。
他们最终放弃了。认定我连人带车摔下了悬崖。尸骨无存。我在湿冷的灌木丛里趴着。
直到所有声音消失。只剩下哗哗的雨声。浑身冻得麻木。伤口疼得钻心。我知道,
第一步成了。等彻底安静下来。我才敢动。咬着牙,拖着几乎散架的身体。沿着山沟,
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山下挪。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不能回头。不能被发现。
我扔掉沾满泥泞的外套。在一个废弃的桥洞下,换上准备好的旧衣服。把脸和头发弄得更脏。
天快亮时,我搭上了一辆运菜去邻市的小货车。蜷缩在满是泥巴和菜叶的车斗里。
像个真正的流浪者。司机是个沉默的中年男人。没多看我一眼。在邻市一个混乱的城中村,
我用现金租了个没窗的小单间。房东是个眼神浑浊的老太婆。没要身份证。只认钱。
我躺在那张散发着霉味的硬板床上。发起了高烧。伤口感染。浑身滚烫。疼得死去活来。
没有药。只能硬扛。那几天,脑子里昏昏沉沉。全是陈砚的脸。他愤怒的,平静的,
带着掌控欲的眼神。还有电视新闻的声音。反复播放着那场惨烈的“车祸”。
记者用夸张的语气描述着豪门太太的“香消玉殒”。镜头扫过悬崖下汹涌浑浊的河水。
扫过警察打捞上来的汽车残骸和那个装着碎镯子的证物袋。陈砚的脸出现在新闻画面里。
他刚从国外赶回来。一身昂贵的黑西装。站在雨里。脸色惨白。嘴唇紧抿着。
眼神空洞地看着那片悬崖。雨水打湿了他的头发和衣服。他像一尊没有生命的雕像。
记者的话筒递过去。他猛地抬手打掉了。动作凶狠。镜头一阵摇晃。画面切断了。那一刻,
我心里没有喜悦。只有一种冰冷的、劫后余生的虚脱。他信了。他真的以为我死了。烧退了。
伤口结了痂。留下丑陋的疤痕。我剪短了头发。染成枯黄色。戴上笨重的黑框眼镜。
在城中村的小饭馆找了个洗碗的活。老板是个刻薄的女人。工钱压得很低。活很累。
油腻腻的碗碟堆成山。热水烫得手通红。但我心里踏实。没人认识我。没人找我。我自由了。
后来,我离开了那个城市。一路向南。用攒下的那点微薄积蓄。像个幽灵一样活着。打零工。
端盘子。在服装厂踩缝纫机。日子清苦。但呼吸是顺畅的。没有无处不在的眼睛。
没有令人窒息的掌控。直到发现自己怀孕。孩子是陈砚的。离开前最后那段时间怀上的。
知道的时候,我坐在简陋的出租屋马桶上。看着验孕棒上的两条杠。浑身冰冷。
第一个念头是不要。不能留。这是他的孩子。是和他最后的、最深的联系。是隐患。
我去了医院。躺在冰冷的检查床上。医生指着B超屏幕上的一个小点。“看,有心跳了。
”那个小点微弱地跳动着。像一颗遥远的星星。眼泪毫无预兆地涌出来。怎么也止不住。
医生奇怪地看着我。我捂着脸。从指缝里看着那个跳动的小点。它是无辜的。
它选择了我做妈妈。在这个世界上,我终于不再是一个人了。我逃下了检查床。逃出了医院。
留下了她。我的女儿。我给她起名叫安晓。破晓的晓。她是我的新生,我的光。五年。
我带着晓晓,像两只迁徙的鸟。在一个又一个不起眼的小城停留。我摆过地摊。做过家政。
在超市当过收银员。日子紧巴巴的。但看着晓晓一天天长大。会笑了。会爬了。
会奶声奶气地叫“妈妈”。所有的苦都值了。陈砚的世界离我太远了。远得像上辈子的事。
我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守着我的晓晓。平静地活下去。直到晓晓突然流鼻血。止不住。
小脸煞白。送到医院。晴天霹雳。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医生的话像冰锥,扎进耳朵里。
“情况不太好。需要尽快骨髓移植。费用……前期准备加上手术,保守估计,至少八十万。
后续治疗费用另算。”八十万。一个天文数字。把我卖了也不值。我的积蓄,
在昂贵的检查和初期治疗面前,像丢进河里的石子。连个响儿都没听见。亲戚?没有。朋友?
不敢联系。借?谁能借我这么多?谁能帮我?走投无路。我想起了老家。
那个被我爸输掉、又被陈砚当初“买”下来、最后落在我名下的破房子。它还在不在?
值不值钱?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可能换点钱的东西。虽然渺茫,但我必须回去试试。
为了晓晓。刀山火海也得闯。我把晓晓托付给同病房一个信得过的护工阿姨。
买了最便宜的火车票。硬座。咣当了一夜。回到这座阔别五年、埋葬了我前半生的城市。
房子居然还在。像个垂死的老人,歪歪斜斜地立在城乡结合部。更破了。墙上爬满青苔。
门窗都烂了。里面住着几个外地拾荒的。我拿出皱巴巴的房产证。跟他们交涉。吵。闹。
最后给了他们一点钱。才把人请走。我找了家最便宜的小中介。
把房产证复印件拍在油腻的桌子上。“卖。越快越好。”中介是个秃顶男人。叼着烟。
眯着眼看房产证。“这位置……这房子……”他摇头。“不好卖啊。太偏太旧。
顶多……二十万。还得碰运气。”二十万。杯水车薪。我的心沉到谷底。像被浸在冰水里。
浑身发冷。可我没得选。二十万也是钱。能撑一阵子。“卖!尽快!”我的声音干涩嘶哑。
走出中介那间满是烟味的小屋。阳光刺眼。我头晕目眩。巨大的绝望像石头一样压着。
喘不过气。离八十万还差得远。晓晓还在医院等着。催款单像索命符。一张接着一张。
我失魂落魄地走到医院。像一具空壳。催款单又来了。护士的眼神带着同情,
更多的是公事公办。“安晓妈妈,今天必须交了。不然明天药就停了。”蓝色的单子。
像一张死亡通知。我攥着它。手指关节捏得发白。走到走廊尽头。想透口气。
抬头就看见了电视。看见了那家破旧的便利店。
看见了那个满头白发、脸上带疤、穿着廉价工服的男人。陈砚。记忆像开了闸的洪水。
瞬间冲垮我所有的伪装。五年来的小心翼翼,五年来的隐姓埋名,
在看到他满头白发的那一刻,土崩瓦解。巨大的震惊和一种难以言喻的恐慌攫住了我。
他怎么会在这里?他怎么会变成这样?像个最底层的、被生活榨干了汁水的苦力?
那个呼风唤雨的陈砚呢?女儿微弱的脸庞和催款单刺眼的蓝色在脑子里交替闪现。
像两把钝刀子,来回切割。钱。现在只有钱能救我女儿的命。
而他……他是我眼前唯一可能抓住的、能救我女儿命的稻草。尽管这根稻草,
可能带着致命的刺。出租车在“惠民便利店”门口停下。招牌缺角的地方,
露出锈迹斑斑的铁皮。玻璃门上贴着褪色的促销广告。里面亮着惨白的日光灯。
货架摆得满满当当,有点乱。我推开门。门上的感应器发出干涩的“欢迎光临”。
声音在寂静的小店里格外刺耳。他背对着门。站在收银台后面。正弯腰整理货架底层的香烟。
动作有些迟缓。那身洗得发白的蓝色工服,裹着他依旧高大的身躯。却显得空荡荡的。
曾经挺直的脊背,似乎也微微佝偻了。最刺眼的,是那头白发。短而扎眼。
像一丛被霜打透的枯草。他听到声音。直起身。转过来。时间仿佛凝固了。那张脸。
刻在我骨头里的轮廓。眉骨到颧骨那道疤,像一条狰狞的蜈蚣趴在那里。深褐色。
衬得他皮肤更显粗糙暗沉。眼窝深陷。里面的光,不再是掌控一切的锐利,
而是一种沉沉的、近乎麻木的疲惫。只有那双眼睛的形状,那紧抿的薄唇,还是陈砚。
只是被岁月和风霜,狠狠打磨过。他看到了我。瞳孔猛地一缩。像被针扎了一下。
脸上所有的肌肉瞬间绷紧。那道疤也跟着扭曲了一下。震惊。难以置信。
然后是……一种极其复杂的东西翻涌上来。太快,我看不清。是恨?是怨?还是别的什么?
他死死地盯着我。像要把我钉在原地。空气凝滞。只有冰柜压缩机发出低沉的嗡嗡声。
我喉咙发紧。干得冒火。手指掐进掌心。强迫自己往前走了一步。走到收银台前。
隔着那层冰冷的玻璃台面。“陈砚。”我的声音抖得厉害。几乎不成调。他的嘴唇动了动。
没发出声音。目光依旧锁着我。像两把冰冷的钩子。刮过我的脸,我的头发,
我身上廉价的旧外套。那眼神,像是在审视一个从地狱里爬出来的幽灵。我被他看得心慌。
几乎想掉头就跑。但兜里那张催款单,像烙铁一样烫着我的皮肤。我深吸一口气。
指甲深深掐进肉里。用尽全身力气,挤出一句话:“借我点钱。”声音干涩得像砂纸摩擦。
他像是没听清。或者是不敢相信。眉头紧紧拧在一起。那道疤显得更凶了。“你说什么?
”他终于开口。声音嘶哑。像生锈的铁片刮过石头。完全不像他以前那种低沉悦耳的嗓音。
是被烟熏坏了?还是……别的?“借我点钱。”我重复了一遍。声音稍微稳了点,
但依旧带着颤音。我不敢看他的眼睛。目光落在收银台玻璃下压着的香烟价目表上。
“我女儿……生病了。很重。需要钱救命。”说到“女儿”两个字,我的心狠狠一抽。
像被撕开一道口子。“女儿?”他重复着这两个字。声音陡然拔高。
带着一种尖锐的、难以置信的嘲讽。“安今朝,你告诉我,你死了五年。
现在像个鬼一样站在我面前,开口第一句话,是借钱?为了一个……女儿?”他的眼神变了。
震惊褪去。只剩下冰冷的、尖锐的审视和一种被彻底激怒的戾气。“你跟谁生的女儿?嗯?
这五年,你躲在哪里逍遥快活?现在孩子病了,没钱了,想起我这个前夫了?
”他猛地一拳砸在收银台上。砰的一声巨响!台面上的计算器跳了一下。我吓得一哆嗦。
本能地后退半步。心脏狂跳。“看着我!”他低吼。像一头被激怒的困兽。隔着收银台,
他身体前倾。那股压迫感又回来了。带着浓烈的烟味和一种……我说不上来的、陈腐的气息。
“告诉我!这五年!**到底在哪儿!”恐惧像藤蔓一样缠上来。勒得我窒息。我后悔了。
我不该来的。他会杀了我吗?像他曾经威胁的那样?我几乎想夺门而逃。
但晓晓苍白的小脸浮现在眼前。她细弱的声音喊着“妈妈,疼”。
那点可怜的母性压倒了恐惧。我抬起头。迎上他暴怒的目光。眼泪不受控制地涌上来。
模糊了视线。“我没死。”我哽咽着,声音破碎,“当年……车祸……是假的。我跑了。
”我豁出去了。语无伦次,只想快点结束这场煎熬。“我没办法!陈砚!你把我当犯人!
我受不了了!我只能跑!只能让你以为我死了!我才能活!”我喘着气,眼泪流进嘴里,
咸涩无比。“孩子……是你的。”最后三个字,轻得像叹息。却像一颗炸弹,投进死水。
陈砚脸上的暴怒瞬间凝固了。像一张骤然定格的恐怖面具。所有的表情都僵在那里。
瞳孔放大。死死地盯着我。像不认识我一样。那道疤在惨白的灯光下,显得格外狰狞。
“我的……孩子?”他喃喃地重复。声音飘忽。带着一种巨大的茫然和……荒谬感。
他像被抽掉了骨头,高大的身躯晃了一下。手撑在收银台上。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
他低下头。肩膀微微耸动。粗重的呼吸声在寂静的店里格外清晰。过了很久。
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再说话。他猛地抬起头。眼睛赤红。像要滴出血。那里面翻涌着太多东西。
震惊、狂怒、被欺骗的暴戾、还有一丝……极其微弱、几乎无法捕捉的痛楚?
“安今朝……”他咬着牙,每一个字都像从牙缝里挤出来,带着血腥味。
“你好……你真好……”他胸膛剧烈起伏。像拉破的风箱。“骗我你死了!
骗得我……”他哽住了。抬手狠狠抹了一把脸。手背上青筋暴起。“现在告诉我,
我有个女儿?快死了?等着我的钱救命?”他发出一声短促的、极其难听的笑。
像夜枭的啼哭。“你觉得我会信吗?嗯?你觉得我陈砚,是条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狗?!
”“她在医院!”我被他眼中的疯狂吓到,尖声打断他,“就在市儿童医院!血液科!
病房号是……”我飞快地报出信息,“她叫安晓!五岁!白血病!需要骨髓移植!八十万!
医生说要八十万!”我像倒豆子一样,语无伦次地吼出来。眼泪鼻涕糊了一脸。“你不信?
你现在就去看!去看看她!看看她那张脸!看看她像不像你!”我掏出手机。手抖得厉害。
指纹解锁好几次才成功。翻出相册。里面全是晓晓的照片。笑着的,哭着的,睡觉的,
扎着针的……我把屏幕猛地杵到他眼前。几乎要贴上他的脸。“你看!你看啊!陈砚!
你看看她!”照片上,小女孩苍白瘦弱。但那双眼睛……那微微上挑的眼角。
那紧抿的唇线……和陈砚,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尤其是生病后,小脸轮廓更清晰,
那种骨子里的相似,根本无从辩驳。陈砚的目光落在手机屏幕上。像被磁石吸住。
他的呼吸停滞了。暴怒和疯狂一点点从他脸上褪去。取而代之的,
是一种巨大的、近乎空白的茫然。他死死地盯着屏幕里那个虚弱的小女孩。
眼神剧烈地波动着。震惊、怀疑、一丝难以置信的震动……最后,
定格在一种深不见底的痛楚上。他伸出手。指尖颤抖着。似乎想去触摸屏幕里孩子的脸。
但又在半途停住。像怕碰碎了什么。他猛地闭上眼。喉结剧烈地上下滚动。
像是在吞咽着极其苦涩的东西。再睁开时,眼底赤红一片。像燃尽的灰烬。他沉默了。
死一样的沉默。只有冰柜还在嗡嗡作响。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长。
我举着手机的手酸得发抖。心悬在万丈深渊之上。终于。他动了。他什么也没说。
猛地转过身。动作有些踉跄。他弯下腰。在收银台底下摸索。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
像是在翻找什么。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他要干什么?拿刀?报警?几秒钟后,他直起身。
手里拿着一个东西。那是一个很旧的、半透明的厚塑料袋。超市买菜用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