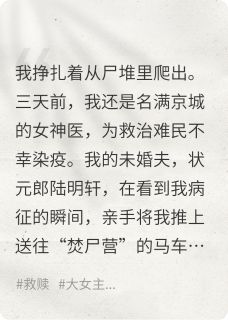乱葬岗的腐臭几乎令人窒息。玉无病挣扎着从尸堆里爬出。
更致命的是她手臂上那象征着瘟疫的黑斑。三天前,她还是名满京城的女神医,
为救治涌来的难民不幸染疫。她的未婚夫,新科状元郎何明轩,在看到她病征的瞬间,
眼神从深情变为惊恐,亲手将她推上送往“焚尸营”的马车。“为了大局,玉儿…莫怪我。
”1求生尸体的味道钻进我的鼻子,黏在喉咙口。我咳了一声,更多的腐臭涌进来。
月光惨白,照在我左臂上,那里有几块黑斑,提示我染上了瘟疫。三天前,
我还是京城里能跟阎王抢人的玉神医。何明轩,我的未婚夫,新科状元郎。
他掀开我袖子看到黑斑时,眼里的光一下就灭了,变成了最深的井。
他把我推上那辆摇摇晃晃的破马车。“玉儿…为了大局,莫怪我。
”何明轩的声音隔着布巾传进来,冷得掉冰渣。马车动了,碾过京城青石板路,
把他和他那身崭新的状元红袍丢在后面,越来越小。现在,我躺在乱葬岗的尸堆里。远处,
京城像个巨大的黑影,灯火在它肚子里明明灭灭。那里头,有琼林宴,有簪花的游街,
有他何明轩平步青云的锦绣路。我喉咙里滚出一声笑,比哭还难听。恨?那东西太轻了。
我动了动手,努力撑起自己,冰冷的烂泥覆盖着我。不能死在这里。像条野狗一样烂掉?
让何明轩高枕无忧地做他的状元郎?做梦!我咬住牙,一股腥甜涌上喉咙。我硬生生咽下去,
开始在这死人堆里一寸一寸地爬。腐肉和断骨硌着我的身体。月光照在几株歪歪扭扭的草上,
叶子边缘带着锯齿。鬼哭藤。剧毒,碰一下都能烂掉皮肉。旁边还有几簇叶子细长的,
是腐心草,也是要命的东西。我盯着它们,眼珠子干得发烫。医书里写过,以毒攻毒,
险中求生。我伸出抖得不成样子的手,用尽最后一点力气,扯下几片鬼哭藤的叶子,
又揪了一把腐心草,塞进嘴里。苦。剧苦。我蜷缩起来,眼前彻底黑了下去。
2疗伤再睁开眼,看到的是低矮的茅草屋顶。空气里有淡淡的草药苦味。
一个头发胡子都白得像雪的老头,正背对着我,在一张破木桌上捣药。
石臼发出沉闷的咚咚声。我试着动了一下,浑身骨头像散了架。“醒了?”老头说,
“阎王殿门口转了三圈,命够硬。”我张了张嘴,
只发出一点声音:“水…”老头慢悠悠转过身,递过来一个豁了口的粗陶碗。水是温的,
带着土腥气。我贪婪地喝着,水流带来一丝活气。“鬼哭藤加腐心草,你也真敢往肚里塞。
”老头浑浊的眼睛瞥了一眼我搁在破被上的左臂。“能活下来,就行。”老头哼了一声,
又转过去捣他的药:“你这丫头,心里揣着事儿,比那疫病还毒。”我没吭声。
何明轩推我上马车时那张冰冷的脸,清晰地烙在我脑子里。这副破败的身子,
是我活下来的代价,也是我复仇唯一的本钱。日子就在这深山的破茅屋里一天天熬过去。
老头脾气古怪,话不多,逼我喝那些苦得舌头发麻的药汁时,下手却毫不含糊。
我跟着他辨识草药,看他用最简陋的器具处理那些山间采来的根茎叶。身体的虚弱成了常态,
稍微多走几步就喘不上气,深秋的风一吹就能让我咳上半天。但脑子是前所未有的清醒。
两年。京城方向的天空,有时会被远处的火光映红。那是焚烧尸体的浓烟。
瘟疫像一张贪婪的巨口,吞噬着人命。直到一个初春的清晨,山风带来隐约的钟声,一下,
又一下,远远地从京城方向传来。老头正晒着草药,动作停住了。他侧耳听了很久,
只说了一句:“丧钟停了。”瘟疫,过去了。我站在茅屋门口,望着京城的方向。
风吹起我洗得发白的粗布衣襟,空空荡荡地晃着。胸腔里那颗被恨意包裹的心,
沉重地跳了一下。该回去了。3归来京城还是那个京城。大街依旧车水马龙,人声鼎沸。
只是空气里那股子浓烈的艾草和石灰混合的驱瘟气味,还没散尽,
固执地提醒着人们刚刚过去的噩梦。我坐在“回春堂”内堂。脸上覆着一层轻纱,
只露出一双眼睛。身上的衣裳是普通的细棉布,料子甚至比不上大户人家得脸的丫鬟。
但没人敢小觑“回春堂”新来的这位女大夫。他们称我为,圣手娘子。“娘子,
您看张员外家老太太这头风……”掌柜的弓着腰,手里捧着一本厚厚的诊金册子,语气恭敬。
我接过册子,指尖掠过那些令人咋舌的数字。张员外…李尚书…王将军…这些名字,两年前,
他们府上的管家见了我这“玉神医”,也不过是点点头。如今,为了请动“圣手娘子”出诊,
银子流水似的抬进来。“放着吧。”掌柜的连忙应声退下。我走到窗边,推开一条细缝。
楼下街角,锣鼓喧天,一队仪仗正浩浩荡荡地行来。簇新的官轿,红彤彤的伞盖,前呼后拥。
轿帘被风吹起一角,露出里面端坐的人影。一身簇新的深绯色官袍,衬得他面如冠玉。
何明轩。不过两年,他已从翰林院修士,青云直上,成了吏部炙手可热的何侍郎。
春风得意马蹄疾。恨意像冰冷的潮水,无声无息地漫上来,淹没了五脏六腑。
为了他的“大局”,他把我推进焚尸炉。如今,他倒成了这大局里的新贵,受万人敬仰。
凭什么?“娘子,”掌柜的又小心翼翼地在门外探头,“吏部何侍郎府上递了帖子,
说是府上老夫人心口疼的老毛病又犯了,请您过府瞧瞧。”何明轩?我猛地转身,
突然觉得造化弄人。真是……天意。“备车。”我说。4求医何府的气派比两年前更盛。
朱漆大门,锃亮的铜钉,门口的石狮子都像是新洗刷过。管家一路小跑着把我引到后宅正院。
空气里弥漫着上等檀香的味道。“老夫人就在里面,劳烦娘子了。
”管家在雕花木门外停住,躬身道。我刚要抬手推门,门却从里面猛地被拉开。
一个穿着藕荷色锦缎裙衫的年轻女子差点和我撞个满怀。她身后跟着两个端着水盆的丫鬟。
“哎呀!”女子惊呼一声,柳眉倒竖,看清我蒙着面纱的脸时,
脸上那点惊慌立刻变成了毫不掩饰的嫌恶,“你是何人?怎敢擅闯内院?
不知道老夫人病着需要静养吗?”管家吓得脸都白了,忙上前一步:“表**息怒!
这位是回春堂的圣手娘子,侍郎大人特意请来给老夫人瞧病的!”“圣手娘子?
”女子上下打量我,眼神刮过我的面纱和朴素的衣着,嗤笑一声,“藏头露尾,
别是什么江湖骗子吧?表哥也真是的,什么人都往家里领!这要是过了病气给老夫人,
谁担待得起?”她正是何明轩新娶的娇妻,户部侍郎家的千金,柳如茵。这时,
一个清朗又带着急切的声音传来:“茵儿!不得无礼!”何明轩匆匆从廊下走来,
他似乎和两年前一样身姿挺拔。他先是安抚地看了一眼柳如茵,然后转向我,
脸上堆起恰到好处的温和笑意:“娘子见谅,内子年轻,不懂规矩,冲撞了娘子,
还望娘子海涵。家母的病,就全仰仗娘子妙手了。”他的笑容无懈可击,眼神诚恳。
可我看着他,只看到他当年隔着马车布巾,那双冰冷如井的眼睛。我微微颔首,算是回应,
径直绕过柳如茵,走进弥漫着药味的里屋。柳如茵被我无视,气得跺了跺脚,
狠狠剜了我的背影一眼。何老夫人躺在锦被里,脸色蜡黄,捂着心口哎呦哎呦地**。
我上前诊脉,脉象浮滑,是虚火上扰,加上忧思郁结。这病根,
恐怕跟何明轩的步步高升脱不了干系。我开了方子,无非是清心降火、疏肝解郁的寻常药。
何明轩亲自将我送到二门处,言辞恳切:“多谢娘子。家母这病,缠绵多时,京中名医束手,
娘子一剂良方,定能解她沉疴。诊金方面,娘子不必顾虑。”我停下脚步,
隔着面纱看着他:“侍郎大人孝心可嘉。只是老夫人这病,根在忧思。忧思过重则伤脾,
脾土不固则心火更旺。”“大人如今位高权重,前程似锦,何不让老夫人多看看这满门荣耀,
少些无谓的忧思,这病,或许去得更快些。”何明轩脸上的笑容僵了一瞬。他何等聪明,
岂会听不出我话里的弦外之音?他母亲这忧思,忧的恐怕就是他这官位能否坐得稳、坐得久!
他眼神闪烁了一下,探究地看向我蒙着面纱的脸,似乎想穿透那层薄纱看清我的表情。最终,
他只是更客气地拱了拱手:“娘子金玉良言,明轩受教了。定当谨记。”5蛇毒没过几日,
宫中传出消息,三皇子所豢养的西域灵蛇突然发狂。咬伤了数名内侍,
最后竟窜入了正在御花园举行的赏春宴。席间顿时大乱。混乱中,
何明轩为了在御前“护驾”,奋不顾身地去驱赶那毒蛇,
结果反被那暴怒的蛇一口咬在小腿上。消息传到回春堂时,我正在分拣药材。
掌柜的绘声绘色:“听说那蛇毒烈得很!太医院的院判大人当时就在场,
一看何侍郎那伤口迅速发黑肿胀,连说怕是……怕是得立刻截肢保命!否则毒气攻心,
神仙难救!何侍郎当场脸就吓白了!”我捻着药草的手指一顿。截肢?
对一个志得意满、前途无量的年轻侍郎来说,废了一条腿,比杀了他还难受。“宫里来人,
急召娘子入宫救治!”掌柜的压低声音,带着一丝与有荣焉的兴奋。放下药材,我净了手。
面纱覆上脸庞,遮住所有表情。宫禁森严。我被太监引着,穿过一道道朱红高墙,
来到一处偏殿。殿内弥漫着血腥和草药混杂的气味,气氛凝重。
几个穿着太医官服的老者围在床榻边,摇头叹气。龙椅旁坐着面色沉郁的皇帝。还有一人,
负手立在稍远些的窗边。权倾朝野的左都御史,肖思年。他的目光似乎不经意地扫过门口,
落在我身上,带着审视,只是一瞬,又移开了。床榻上,何明轩面如金纸,额上冷汗涔涔,
左小腿肿胀发黑,伤口处流出的血都是暗紫色的。他死死咬着唇,
眼中充满了巨大的恐惧和绝望,看到我进来,那绝望里又燃起一丝抓住救命稻草般的火光。
“圣手娘子!”他嘶哑地喊,声音因剧痛和恐惧而扭曲,“救我!求你救我!
我不能……不能没有腿!”他挣扎着想坐起来,被旁边的太医慌忙按住。
太医院院判上前一步,语气沉重而无奈:“娘子,此乃西域黑线王蛇之毒,霸道无比。
老朽等已尽力施救,然毒入血脉,上行极快。为保何侍郎性命,唯有……唯有断肢一途!
迟则恐生不测啊!”殿内一片无声。皇帝眉头紧锁,目光落在我身上。
窗边的肖思年依旧没什么表情,但那双眼睛,却一直盯着我。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
我走到榻前,低头查看何明轩肿胀发黑的小腿。伤口狰狞,毒气确实已蔓延开。我伸出手指,
在伤口上方几寸的地方,不轻不重地按了一下。“啊!”何明轩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
身体猛地弹起,又被死死按住,痛得浑身痉挛,涕泪横流。我直起身,目光平静地扫过众人,
最后落在痛得几乎昏厥的何明轩脸上,隔着面纱,我的声音清晰地传遍整个大殿,
带着一种近乎冷酷的平淡:“截肢保命?倒也不必如此麻烦。
”何明轩布满血丝的眼睛骤然瞪大,里面爆发出狂喜的光芒。太医们惊疑不定。
皇帝身体微微前倾。窗边的肖思年,脸上似乎多了一点玩味的表情。我继续道,
每一个字都像冰珠砸在玉盘上:“只是这腿,就算保下来,每逢阴雨寒冬,
筋骨深处如万蚁啃噬,痛入骨髓,且终身跛足。侍郎大人,可愿受此活罪?
”何明轩脸上的狂喜瞬间凝固,如同被泼了一盆冰水,迅速褪去血色,变得惨白如纸。跛足?
终身剧痛?那和废人有什么区别?在朝堂上,他如何立足?在那些同僚面前,
他岂不成了永远的笑柄?巨大的恐惧,让他一个字也说不出来。皇帝眼中闪过一丝复杂。
肖思年的目光,再次落在我身上,那审视的意味更浓了,仿佛要将我这层薄纱彻底看穿。
“如何?”我再次开口,目光只盯在何明轩那张失魂落魄的脸上,“是要命,还是要腿?
大人,速做决断。毒,可不等人。”何明轩最终选了他的腿。或者说,
他选择了那渺茫的不成为瘸子的希望,以及更重要的,不成为官场笑柄的可能。
我当着皇帝和太医院众人的面,用金针封住他腿上几处要穴,减缓毒血上行。
然后取出一柄小刀,在烛火上燎过,利落地划开他发黑的皮肉。黑紫色的脓血涌出。
我用特制的药汁反复冲洗创口,挤出毒血,敷上厚厚一层解毒生肌膏。整个过程,
何明轩痛得死去活来,惨叫连连,最后生生晕厥过去。“毒血已清大半,余毒需慢慢拔除。
”我洗净手,对皇帝回禀,“命是保住了,腿也保住了。只是这跛足和阴痛之症,
恕我无力回天。”皇帝看着榻上昏死过去的何明轩,又深深看了我一眼,
最终只疲惫地挥了挥手:“有劳娘子。赏。”我垂首谢恩。起身时,
感觉到一道极具穿透力的目光落在我背上。不用回头,我也知道那是肖思年。
何明轩保住腿但他终身跛足的消息,很快传遍了京城的大街小巷。曾经风光无限的何侍郎,
成了人们茶余饭后既同情又嘲弄的谈资。他告了长假,躲在府里,再不敢轻易见人。
皇帝虽未明着斥责,但那份“赏赐”之后,吏部几个要紧的差事,都落到了旁人头上。
他费尽心机攀上的高位,已然摇摇欲坠。6疫病再起京城刚喘过一口气,
一场更诡异的疫症毫无征兆地爆发了。病起急骤,染上的人,往往三日内便痛苦死去。
与两年前的瘟疫不同,此疫凶险更甚,且无迹可寻。太医院束手无策,
京兆府的衙役抬尸都抬不及,恐慌像瘟疫本身一样迅速蔓延。
回春堂的门槛几乎被求医的人踏破。我夜以继日地诊病配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