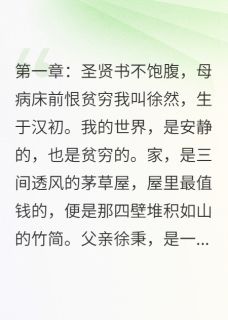第一章:圣贤书不饱腹,母病床前恨贫穷我叫徐然,生于汉初。我的世界,是安静的,
也是贫穷的。家,是三间透风的茅草屋,屋里最值钱的,便是那四壁堆积如山的竹简。
父亲徐秉,是一位典型的穷秀才,他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奉为圭臬,
每日领着我诵读经文,从《诗》到《书》,从《礼》到《春秋》。他总说,书中自有千钟粟,
书中自有黄金屋。可我活了十八年,从未见过一粒“千钟粟”,也未见过半点“黄金屋”。
我只知道,我们家的米缸,常年见底;我只知道,母亲为了给我和父亲省下口粮,
常常只喝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米汤。竹简的墨香,混杂着贫穷的霉味,
构成了我全部的少年时代。我曾试图改变。我问父亲,为何不去城中富户家做个西席,
也能换些钱粮。父亲却吹胡子瞪眼,斥我“浑身铜臭,玷污圣贤”。他说,我徐家三代读书,
耕读传家,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于是,我只能继续埋首于故纸堆中,
在那些“子曰诗云”里,消磨着青春,也消磨着对未来的所有幻想。我以为,我的人生,
便是在这清高与贫穷交织的网中,窒息而死,如我的父亲,我的祖父。改变这一切的,
是母亲的倒下。那是一个深秋的午后,母亲在院中浆洗衣物时,猛地咳出一口血,
然后便昏倒在地,再也没能站起来。城里最好的郎中被我请了来,他捻着胡须,反复诊脉,
最后长叹一声,摇了摇头。他说,母亲是积劳成疾,寒气入体,已伤及肺腑,若想救命,
需一味产自燕赵之地的“紫河车”作为主药,辅以温补之方,或可续命。只是那药材,
千金难求。“千金……”父亲听到这两个字,颓然坐倒在地。我们家,
连十个大钱都拿不出来,何谈千金?父亲没有像我想象中那样去想办法,
他只是反复地、神经质地念叨着那句我听了无数遍的话:“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生死有命啊……”我看着躺在床上,面如金纸,呼吸微弱的母亲,
再看看这个只会怨天尤命的父亲,一股前所未有的、冰冷的恨意,从我心底升起。我恨的,
不是天,也不是命。我恨的是“贫穷”。是贫穷,让母亲只能躺在这里等死。是贫穷,
让我这个熟读诗书的儿子,束手无策。是贫穷,让父亲那满腹的圣贤道理,
变成了一个天大的笑话。“君子固穷”,好一个君子固穷!那一刻,我对我所学的一切,
产生了巨大的怀疑。如果圣贤之道,不能让我守护我的至亲,那这“道”,于我何用?
我做出了一个决定。一个在父亲看来,大逆不道、欺师灭祖的决定。我要卖书。
卖掉那些父亲视若生命,却换不来一文钱的竹简。我要用它们,去换母亲的命。
第二章:一卷计然策,胜读十年书我终究是小看了父亲对那些竹简的执念。
当我提出要卖书时,他暴怒了。他第一次,动手打了我。那根用了多年的戒尺,
狠狠地抽在我的背上,一下又一下。“你这个孽子!不肖子孙!”他气得浑身发抖,
“你要卖掉我徐家的根!我打死你这个不孝的东西!”我没有反抗,也没有躲闪。
我只是挺直了脊梁,任由那疼痛蔓延。我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父亲,书没了,
可以再抄。娘要是没了,就真的没了。孰轻孰重,您自己掂量。”说完,我不再顾他的怒吼,
扛起一箱最破旧的竹简,冲出了家门。我背上的伤,**辣地疼。可我的心,更疼。
来到城中最大的书肆,掌柜是个精明的胖子。他翻了翻我的竹简,脸上露出鄙夷的神色。
“都是些《周书》《尚书》的残篇,字迹也寻常,不值钱。”他伸出三个指头,
“最多给你三十个钱。”“三十钱?”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可是一整箱的书简!
光是这些竹子,都不止这个价!”“爱卖不卖。”掌柜冷笑一声,“如今天下初定,
谁还看这些老掉牙的东西?大家要看的,是黄老之学,是纵横之术。你这些,送人都没人要。
”我抱着那箱竹简,站在人来人往的市集上,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我视若珍宝的学问,
在别人的眼里,竟一文不值。我一连跑了好几家书肆,得到的答复,大同小异。
他们用一种看傻子一样的眼神看着我,仿佛我扛着的,不是知识,而是一堆无用的垃圾。
夕阳西下,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做最后的尝试。那是一家偏僻的小店,
店主是个干瘦的老头,似乎对我的书更感兴趣。他一卷一卷地看,看得极为仔细。
就在他拿起最后一卷破旧的《周书》时,箱底的一根颜色明显不同的竹简,滚落了出来。
那竹简呈深褐色,比其他的简要细,也更光滑。老者眼前一亮,捡了起来。
只见上面用极小的篆字,刻着一行字。“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老者的手,
猛地一抖。他抬起头,用一种极其复杂的眼神看着我:“年轻人,这……这东西,
你从何而来?”我心中一动,也凑了过去。计然,是范蠡的老师。传说他有七策,能安邦,
能富国。范蠡助越王勾践复国,用的就是这计然之策。“这是我家祖传的。”我撒了个谎。
老者死死地盯着那根竹简,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他忽然对我说:“年轻人,你这箱书,
我全要了。我给你……三百钱!”三百钱!比之前所有书商出的价,高了十倍!
我的第一反应是狂喜,但随即,一股警觉涌上心头。他要的,不是这箱书,而是这根简。
“我不卖了。”我当机立断,从他手中夺过那根竹简,将其他的书推给他,“这些,
你给我一百钱,就都归你。这根,是我家的传家宝,不能卖。”老者愣住了,
脸上写满了懊恼和不甘。但他最终,还是点了点头。我揣着那一百钱,和那根神秘的竹简,
飞也似地跑回了家。那个夜晚,我反锁上房门,第一次,没有点亮油灯去读圣贤书。
我展开了那卷竹简。上面没有仁义道德,没有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有的,
只是最直白、最**的,关于“利”的智慧。“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
贱下极则反贵。”“旱则资舟,水则资车,此理之然也。”“乐观时变,人弃我取,
人取我与。”“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一句句,一行行,
像一道道惊雷,劈开了我过去十八年,被仁义道德禁锢得严严实实的思想。原来,天地万物,
皆可为货。时机变化,皆可为利。原来,治国与治家,富国与富家,其“理”,是相通的。
我一夜未眠。窗外的天空,泛起鱼肚白时,我做出了人生中,第二个重要的决定。弃文从商。
我不要再做什么“君子固穷”的梦。我要用这卷竹简上的智慧,去与天争,与命争。
我要让我的母亲活下去。我要让我徐家,再也不受这贫穷之苦!第三章:万事俱备,
只待时变我用那一百钱,给母亲抓了三天的药。郎中说,这只能吊着命,关键,
还是要那味主药。我剩下的钱,不多了。这是我唯一的本钱。我没有再急着去赚钱,
而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反复地、逐字逐句地,研究那卷竹简。我将其中的智慧,
总结为几个关键:一曰“时变”。竹简上说,白圭“乐观时变”,就像伊尹、吕尚谋划政权,
孙子、吴起运用兵法一样。一个成功的商人,必须像最敏锐的猎人,
时刻观察着天时、地利、人和的变化,从中发现商机。二曰“人弃我取”。
当所有人都追逐某样东西,导致其价格昂贵时,就要果断卖出。当所有人都抛弃某样东西,
导致其价格低廉时,就要果断买入。这不仅仅是商业策略,
更是一种反人性的、需要巨大勇气的博弈。三曰“知所本末”。
竹简上引用了《周书》的话:“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
虞不出则财匮少。”农、工、商、虞,缺一不可。但根本,在于“农”。以末(商业)致财,
用本(土地)守之。这才是长久之道。四曰“通之”。天下万物,产地不同,需求也不同。
让货物从“有余”的地方,流向“不足”的地方,这便是“通”。而“利”,
就藏在这“通”的过程之中。我将这几条,深深刻在脑子里。我明白,我空有理论,
却没有实践。我缺的,是一个机会。一个可以让我实践“计然之策”的,“时变”的契机。
我每天,除了照顾母亲,就是去市集上,静静地观察。我观察米价、布价、盐价的波动。
我听那些南来北往的客商,谈论着天下的新闻。哪里丰收了,哪里又发生了灾祸。我的父亲,
见我整日不读书,只是在市井厮混,气得大骂我是“自甘堕落”。我没有与他争辩。他不懂,
我正在读的,是一本比《春秋》更复杂,比《尚书》更深奥的大书。这本书的名字,
叫“天下”。机会,在我等待了半个月后,终于来了。那是一个傍晚,天空中忽然乌云密布,
电闪雷鸣。一场数十年未见的暴雨,倾盆而下。这场雨,一下,就是十几天。渭河的水位,
一日三涨。田地被淹,房屋被毁。整个关中地区,一片汪洋。恐慌,开始蔓延。
所有人都知道,大水过后,必有大灾。粮食,会成为最宝贵的东西。于是,
城里所有的米商、粮铺,都开始疯狂地囤积粮食,闭门不售。米价,像疯了一样,
一天一个价。人们的脸上,都写满了焦虑和恐惧。而我,在看到那泛滥的河水时,
心里却猛地一跳。机会来了。竹简上清清楚楚地写着:“水则资车”。这四个字,
在我的脑海里,反复回响。我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去抢购粮食。我知道,我手里的这点本钱,
在那些大粮商面前,不值一提。我不可能在粮食上,赚到什么钱。我必须,
走一条别人没有走的路。一条,“人弃我取”的路。
我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无法理解的决定。我拿着我仅剩的、准备给母亲买药的七十个钱,
开始大量的,收购那些被雨水浸泡过的,几乎一文不值的木材、木炭和薪藁。那些木材商人,
看我的眼神,就像在看一个**。“年轻人,这木头都泡烂了,只能当柴火烧,还生不着火。
你买这玩意儿干嘛?”“疯了吧?有钱不买米,买这些湿柴火?”我不管别人的嘲笑。
我只是不停地买,买,买。我租下城外一个废弃的货仓,把那些湿漉漉的木头、木炭、薪藁,
堆积如山。我看着那些在我眼中,闪着金光的“朽木”,心里无比笃定。我知道,大水,
总会退去。而洪水退去之后,紧接着的,必然是寒冷的,漫长的冬天。到那个时候,
人们最需要的,不是已经回落到正常价格的粮食。而是,可以用来修缮房屋的木材,
和可以用来取暖的,最最基本的——柴火。万事俱备。现在,我只需要,等待“时变”。
等待,天晴。第四章:天下皆囤粮,我独买朽木接下来的一个月,是我人生中最难熬,
也最关键的一个月。大雨终于停了,但积水未退。整个城市,都泡在一片浑浊的泥水之中。
恐慌的情绪,在米价的飞涨中,达到了顶点。城中的富户,早已囤积了足够的粮食。
而贫苦的百姓,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米价,从一斗三十钱,涨到了一斗一百钱,甚至更高。
易子而食的传闻,开始在街头巷巷流传。我的父亲,也坐不住了。我们家的存粮,已经见底。
他放下读书人的清高,第一次,低声下气地,求我把手里的钱拿出来,去换几斗高价米。
“徐然,算为父求你了。再不买米,我们都要饿死了!”他老泪纵横。我看着他苍老的脸,
心里不是没有动摇。但我知道,我不能。我一旦动用了这笔钱,我所有的计划,
都将功亏一篑。“父亲,您放心。”我攥紧了拳头,指甲深深地陷进肉里,“最多再过十天,
我们家不仅有米吃,还会有肉吃。”父亲以为我疯了,他指着我的鼻子,
大骂我“不孝”、“冷血”,骂我为了钱,连家人的性命都不顾。我没有解释。因为我知道,
任何解释,在现实的饥饿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我不仅要承受家人的不解,
还要忍受外界的嘲笑。我收购湿木头的“壮举”,早已传遍了整个市集。
我成了所有人眼中的疯子和傻瓜。那个卖给我书简的干瘦老头,特意找到了我。
他看着我租下的、堆满朽木的仓库,痛心疾首。“年轻人,我以为你得了计然公的真传,
是个奇才。没想到,你竟如此不智!”他指着那些湿木C漉的木头,“‘水则资车’,
是说大水过后,陆路不通,需要用车来运输货物。不是让你来买这些泡了水的破木头啊!
你……你这是把计然公的脸,都丢尽了!”我看着他,只是笑了笑。我没有告诉他,
我对“水则资车”这四个字,有我自己的理解。竹简上所说的“理”,不是死的教条,
而是活的智慧。它需要根据不同的“时变”,做出不同的应对。现在的关中,缺的不是货物,
而是生存的基本物资。车,能拉什么?拉不来可以立刻住进去的房子,
也拉不来可以立刻点燃的温暖。真正的煎熬,来自内心。每一天,我都在和自己打仗。
我看到母亲的病,因为缺少药物,日渐沉重。我看到父亲的眼神,从愤怒,变成了绝望。
我听到邻居们,在背后指指点点,说我为了钱,已经丧心病狂。我有无数次,
想冲进那个仓库,把所有的木头都劈了当柴烧。但每到这个时候,竹简上的那句话,
就会在我脑中响起:“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这是信念的博弈。我赌的,
不仅是我那七十个钱的本金。我赌的,是我对“计然之策”的理解,是我对未来的判断,
是我徐然,自己的命运!我挺住了。第七天,水位开始下降。第十天,官府开始组织人手,
修缮堤坝。第十五天,积水基本退去,露出了满目疮痍的、被泡得发白的大地。恐慌的情绪,
开始转变。人们不再只关心粮食。他们开始关心,自己那被冲毁的家园,和即将到来的,
寒冷的冬天。我知道,我的“时变”,终于要来了。第五章:人皆弃之我独取,
水则资车待天晴洪水退去后的第十天,关中迎来了第一场雪。比往年,早了整整一个月。
气温骤降,寒风刺骨。城里,出现了一种诡异的景象。那些之前被炒到天价的米,
价格开始松动、下跌。因为朝廷的救济粮,终于运到了。而且,大水过后,
不少富户急于出手囤积的粮食,换取现金,来修缮他们同样被水泡过的豪宅。米,
不再是问题。取而代之的,是新的、更迫切的问题。取暖。以及,重建。
那些在洪水中幸存下来的人们,哆哆嗦嗦地,挤在官府搭建的临时窝棚里。他们需要木炭,
需要柴火,来抵御这突如其来的严寒。那些房屋被毁的家庭,无论是富户还是贫民,
都需要大量的木材,来重建家园。一夜之间,木、炭、柴,这些在水灾中,
最被人鄙夷、视若垃圾的东西,成了最抢手的硬通货。价格,开始以一种疯狂的姿态,
向上攀升。上好的木炭,从一斤两个钱,涨到了二十个钱,而且有价无市。普通的柴火,
价格也翻了五倍。而我,在所有人都还在为米价下跌而扼腕时,打开了我的仓库大门。
那堆积如山的、经过了近一个月晾晒的木材和薪藁,虽然品相依然不佳,
但在刺骨的寒风面前,它们就是希望,就是生命。第一个找上门的,是城里最大的富户,
张员外。他那富丽堂皇的宅子,有一半的房梁都被水泡烂了,急需更换。
他看着我满仓的木材,眼睛都绿了。“徐……徐公子,”他搓着手,态度谦卑得,
让我几乎认不出来,“您这木头,怎么卖?”我没有立刻报价。我只是淡淡地说:“张员外,
现在城里,除了我这里,您还能找到第二家,有这么多现成木材的吗?”他的冷汗,
一下子就下来了。他知道,现在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的手里。
我没有像他当初囤米时那样,漫天要价。我只开了一个比平时高出五倍的价格。
这是一个很高的价格,但对于急需的他们来说,又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价格。竹简上说,
“贵上极则反贱”。我不做一锤子买卖。我要的,是细水长流。张员外几乎没有犹豫,
立刻成交。有了张员外的“榜样”,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全城。我的仓库门口,
第一次,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富户们来买木材,贫民们来买柴火。车水马龙,络绎不绝。
那些曾经嘲笑我“疯了”的木材商人,此刻,正用一种见了鬼一样的眼神看着我。
他们想从我这里进货,再转手卖出,被我断然拒绝。“人弃我取,人取我与。
”当初你们抛弃它们的时候,就该想到有今天。短短半个月,我仓库里的存货,被抢购一空。
我数着铜钱,手都在发抖。七十个钱的本金,变成了……八百钱!翻了,不止十倍!
我拿着沉甸甸的钱袋,没有一丝一毫的耽搁,立刻冲向了城里最大的药铺。“掌柜,
把你们店里最好的‘紫河车’,给我包起来!”我把钱袋,重重地,拍在柜台上。
掌柜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震惊和敬畏。他知道,眼前这个衣衫褴褛的年轻人,
已经不再是半个月前,那个穷困潦倒的书生了。而是,凭着一次精准的、反人性的判断,
在这场天灾中,硬生生杀出一条血路的,真正的“时变者”。
我捏着那包用油纸包好的、价值连城的药材,飞奔回家。天晴了。我徐然的天,终于晴了。
第六章:一桶金,是商道,也是孝道当我把那包昂贵的药材,和新买的米、肉,
一起放在父亲面前时,他愣住了。他拿起那包药,打开闻了闻,又看了看我,嘴唇哆嗦着,
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哪……哪来的钱?”他终于问,声音沙哑。“卖木头赚的。
”我平静地回答。“卖木头?”他显然不信,“就你那些湿柴火,能卖这么多钱?
”我没有多做解释,只是把钱袋里的铜钱,倒了一部分在桌子上。叮叮当当的声音,
清脆悦耳,也刺痛了他的眼睛。父亲呆呆地看着那些铜钱,又看了看我,眼神复杂到了极点。
有震惊,有疑惑,但更多的,是一种他自己都不愿承认的……挫败。
他一生信奉的“君子固穷”,被我用最直接、最粗暴的方式,击得粉碎。
他没有再骂我“不孝”,也没有再提“铜臭”二字。他只是沉默地,拿起药,转身进了厨房,
亲自为母亲煎药。那佝偻的背影,在灶火的映照下,显得既固执,又落寞。母亲的病,
在有了主药的调理下,一天天好了起来。她的脸上,重新有了血色。我们家的餐桌上,
也终于,顿顿都能见到荤腥。我用赚来的钱,把漏雨的屋顶,重新修缮了一遍。我还给父母,
都添置了厚实的新棉衣。家里,第一次,有了“家”的样子。温暖,安稳。父亲对我的态度,
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不再逼我读书,也不再对我冷言冷语。他只是常常,一个人,
坐在那堆卖剩的竹简前,一坐,就是一下午。我知道,他的信念,动摇了。而我,
则在思考着我的下一步。这八百钱,是我的第一桶金。它救了母亲的命,
也暂时改善了我们的生活。但这点钱,在真正的“富”面前,依然不值一提。
我不能满足于此。一次成功的投机,靠的是勇气和运气。但要想成为真正的“货殖者”,
必须要有可持续的、成体系的商业模式。我再次拿出了那卷竹简。上面,
记载着猗顿和乌氏倮的故事。猗顿,本是一个穷困潦倒的儒生。
他在听说朱公(范蠡)巨富之后,前去请教。朱公告诉他:“子欲速富,当养五牸。
”“牸”,就是母畜。猗顿听从了他的建议,跑到西河(今山西南部)的山中,
大力发展畜牧业,十年之间,富可敌国。他还发现,河东郡的池盐,是天下之宝。于是,
他又开始经营盐业,最终,与古代的王侯,齐名并富。乌氏倮,
则是当时西戎地区的一个牧主。他将牲畜卖掉,换成奇特的丝织品,去贿赂戎王。
戎王的回报,是给了他一片可以俯瞰整个山谷的牧场。当戎人部落间发生冲突,需要**时,
都会到他的牧场来。于是,他就在此地,交易牛马。十几年后,他的牛马,
多到以山谷来计算。秦始皇听说了他,甚至给了他与大臣一同上朝议事的殊荣。这两个故事,
给了我巨大的启发。他们成功的共同点,在于,
都找到了一个具有“垄断性”或者“稀缺性”的资源。猗顿,找到了“盐”。乌氏-倮,
找到了“马”。并且,他们都利用了“地域差”。将一个地方“有余”的,
贩卖到另一个地方“不足”的,从中赚取巨额的利润。我徐然,要走的路,也应该是这样。
关中平原,物产丰饶,但它也缺东西。缺什么?
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此中国人民所长用,
皆中国人民所仰给者也。”我的目光,跳出了小小的关中。我看向了,整个天下。
我做出了一个,让父母再次震惊的决定。我要离开家。我要带着我的资本,去周流天下。
去亲眼看看,山西的竹,山东的盐,江南的金。我要找到,属于我徐然的,“盐”和“马”。
这一次,父亲没有再阻拦我。他只是在我临行前,将我拉到一旁,塞给我一个布包。
“这里面,是五十个钱。是……我存了半辈子的束脩。”他看着我,眼神复杂,
“外面不比家里,万事,小心。”我捏着那个沉甸甸的布包,点了点头。我知道,
这不仅仅是五十个钱。这是我那个固执了一辈子的父亲,对我,对我的“商道”,
一次无声的、笨拙的,却又无比郑重的,认可。第七章:读万卷书,
不如行万里路离开家乡的那一刻,我心中没有离愁别绪,只有一种挣脱牢笼的快意。
我没有立刻去做什么大买卖,而是选择了一种最笨,也最扎实的方式——行走。
我加入了南来北往的商队,有时候是运送粮食的牛车队,有时候是贩卖布匹的马帮。
我付给他们一些钱,换取一个同行的资格和一份安全。我从关中出发,一路向东。
我亲眼见到了,在山东的临淄,家家户户都在纺织。那里的“齐纨”,薄如蝉翼,光滑如水,
是天下贵妇们最追捧的奢侈品。我也见到了,海边的渔民,如何将打上来的鱼,
制成鱼干和鱼酱,销往内陆。更见识了,那白花花的池盐,是如何从盐池中被开采出来,
成了维系天下人生命的必需品。我又折向南下,渡过大江。我看到了,江南的竹林,
浩如烟海。那些坚韧的竹子,被制成竹简、竹席、竹器,源源不断地运往北方。我也看到了,
在豫章(今南昌)的铜矿里,无数的矿工,如何从地底深处,挖出冶炼铜钱的矿石。
金、锡、丹砂……这些在书本上,只是一个个冰冷的名字,此刻,都变成了我眼前,
活生生的、充满了财富气息的产业。我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记。
我不再只关心价格的“贵贱”,而是开始研究,价格背后的“所以然”。
为什么齐地的丝绸最贵?因为它有独特的桑蚕品种和纺织工艺。为什么江南的木材好?
因为它有得天独厚的湿润气候。我开始理解,竹简上所说的,“相其地形,知其肥瘠,
则知其五谷之所宜。观其习俗,其民人之所好,则知其货之所流。
”地理、气候、物产、习俗……这些,才是决定商品价值和流向的,最根本的“道”。
读万卷书,真的不如,行万里路。这一路,我也见识了“商”的艰辛。我看到,
商队在崎岖的山路上,因为一匹马失足,而损失了半车的货物。我看到,
商人们为了节省开销,啃着最硬的干粮,喝着最脏的河水,睡在最简陋的通铺里。我也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