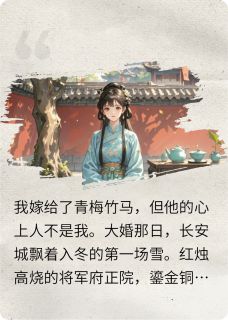我嫁给了青梅竹马,但他的心上人不是我。大婚那日,长安城飘着入冬的第一场雪。
红烛高烧的将军府正院,鎏金铜炉里燃着昂贵的龙涎香,暖烟袅袅缠上梁间悬着的大红囍字,
却暖不透空气里的滞涩。萧策站在妆台前,一身大红织金婚服,衬得他肩宽腰窄,
墨发用玉冠束起,侧脸线条冷硬如刀削。他手里捏着那支要为我绾发的赤金镶珠步摇,
指尖悬在我发间,迟迟未落。“阿砚,”我轻声唤他的字,试图打破这沉默。“雪落得紧,
母亲说戴这支步摇暖些。”他睫毛颤了颤,终是垂下手,步摇“咔”地卡在发间,
力道却重了些,珠串撞得我耳尖发疼。“沈清沅,”他开口,声音比窗外的雪还冷。
“你知道我为何应下这门婚事。”我知道。吏部尚书沈家与镇国将军萧家是世交,
我与他自幼在一处长大。他曾爬过长安城最老的那棵青梧树,摘了满枝槐花扔我怀里,
笑说“清沅接住,这是给你的嫁妆”;我曾蹲在他家演武场边,用绣帕替他擦额头的汗,
听他喘着气说“等我成了将军,就护着你”。可这些,都停在三年前。三年前,
他那位寄居在萧家的表妹苏落雪,染了肺疾去了。苏落雪是江南来的孤女,
会弹《平沙落雁》,能画一手簪花小楷,笑起来时眼角有颗小小的泪痣,
像江南烟雨中沾了露的梅。萧策待她极好,好到长安城里人人都知,镇国将军心里,
早晚会娶那位苏表妹。直到她病逝。萧老夫人病了大半年,临了拉着我和萧策的手,
哭着说“阿砚心里苦,清沅你性子稳,替我好好看着他”。我爹也叹着气劝:“清沅,
萧家于咱们有恩,阿砚他……需要个人陪着。”我望着萧策那双失了光的眼,点了头。
“我应下婚事,是为了母亲,也是为了沈家与萧家的情分。”他转过身,背对着我,
婚服下摆扫过地面的红毯。“清沅,委屈你了。往后你是将军府主母,
吃穿用度我不会亏待你,但……”他顿了顿,声音低得像叹息,“我的心,你别要。
”红烛爆了个灯花,噼啪一声,映得他背影孤绝。我攥着袖中的帕子,那帕子上绣的并蒂莲,
是我绣了三个月的嫁妆。指尖掐进掌心,疼得眼眶发热,却还是弯了弯唇。“好。阿砚,
我知道分寸。你我是青梅竹马,我不求别的,只愿你平安,将军府安稳。”他没再说话,
转身去了书房。那夜,正院的红烛燃到天明,帐内始终只有我一人。婚后的日子,
像一碗温吞的白水,没什么滋味,却也挑不出错处。萧策待我极客气,
客气得像对待一位相熟的世交女眷。他每月初一十五会宿在正院,却从不会近我的身,
只在屏风外铺张软榻,和衣而卧。晨起时,他会等我梳妆好一同去给老夫人请安,
饭桌上会替我布菜,却从不会问我一句“合不合口”。将军府的中馈很快交到我手里。
我学着打理家事,查账、采买、调度下人,从一开始对着厚厚的账本犯愁,
到后来能随口报出库房里每匹绸缎的成色。萧策从不过问,只在我偶尔忙到深夜时,
会让小厮送来一盏温着的莲子羹,却从不会亲自来看看。府里的下人都是人精,
见主母不得宠,渐渐也有了怠慢的心思。有次厨房送来的晚膳,汤是凉的,
清蒸鱼带着土腥味。我没作声,让丫鬟端去小厨房,自己挽了袖子热汤,
又重新调了酱汁淋在鱼上。刚端上桌,萧策却回来了。他一身戎装未卸,
甲胄上还沾着城外的风尘,显然是从军营直接回来的。他站在廊下,
看着我在小厨房的灶台边忙碌,眉头几不可察地皱了皱。“怎么亲自下厨?”他走进来,
声音里带着些疲惫。“厨房许是忘了添柴,汤凉了。”我擦了擦手,端起汤碗递给他,
“你刚回来,趁热喝些暖身子。”他接过汤碗,指尖触到碗壁的温度,愣了愣。次日,
管厨房的厨娘就被杖责了二十板,发去了庄子上。
萧老夫人私下拉着我的手笑:“还是你有办法,阿砚这孩子,就是嘴硬心软。”我笑着应了,
心里却清楚,他不是为我,只是为了将军府的规矩。他是镇国将军,府里主母受了怠慢,
传出去丢的是他的脸。真正让我心头泛起涟漪的,是那年上元节。长安城里张灯结彩,
萧老夫人兴致高,拉着我们去街上看灯。人群挤攘,我被个莽撞的少年撞得踉跄,
眼看要摔倒,手腕突然被人攥住。是萧策。他的手掌宽大,带着常年握剑的薄茧,力道很稳,
将我拉回他身边。“人多,跟紧些。”他低声说,目光扫过我被撞红的手肘,眉头又皱了皱。
那一刻,街上的喧嚣、花灯的明灭,仿佛都成了模糊的背景。我望着他紧抿的唇,
鼻尖突然一酸——这是他婚后第一次碰我,不是出于规矩,不是出于责任,
只是下意识的护着。可这涟漪很快就散了。走到朱雀大街时,迎面撞上了礼部侍郎家的**。
那**手里捏着盏兔子灯,看见萧策,眼睛亮了亮,福了福身:“萧将军,沈夫人。
”她顿了顿,又笑着说。“前几日我去法华寺上香,见苏表妹坟前的松柏枯了些,
便让人补种了几株,将军若有空,可去看看。”萧策的身子猛地一僵。
攥着我手腕的手骤然松开,力道大得我指尖都麻了。他看向那**,
声音里带着我从未听过的急切:“落雪坟前的松柏枯了?何时的事?
”“约莫是前几日雪大压的。”他没再说话,甚至没回头看我一眼,翻身上了随从牵来的马,
疾驰着往城外法华寺去了。我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灯火深处,手肘上的疼还在,
心里却更疼。原来,他不是不会急切,只是他的急切,从不属于我。老夫人叹了口气,
拍了拍我的手:“清沅,别往心里去。阿砚他……就是念旧。”我点点头,
笑着说“我知道”,可眼泪还是没忍住,落在了胸前的衣襟上,很快被风吹干,像从未流过。
开春后,北境告急。匈奴铁骑踏过雁门关,连破三城,边关八百里加急的军报,
雪片似的送进长安。朝会上,萧策主动请缨出征。那天他回府时,天已经黑了。
他直接去了书房,我让丫鬟炖了参汤送过去,却被小厮拦在门外:“夫人,将军正在看军图,
说谁也不见。”我捧着参汤站在书房外,听着里面传来翻动纸张的沙沙声,站了许久。
直到参汤彻底凉了,才转身回房。第二日一早,他要启程。我起了大早,在正厅等他。
桌上摆着我连夜收拾的行囊——里面有厚厚的棉衣,伤药,还有几包他爱吃的椒盐核桃,
是我让人赶制的。他走进来,看见行囊,愣了愣。“北境冷,这些棉衣是用新收的羊绒絮的,
比寻常棉絮暖些。”我指着行囊,轻声说。“伤药有两种,红瓶的治外伤,白瓶的是止血粉,
你让亲兵随身带着。还有核桃,行军闷了,可解闷。”他没说话,只是看着我。
我从袖中取出个小小的平安符,递给他。那符是我去法华寺求的,求了三个月,
每日清晨去寺里跪拜,只求他平安。符袋里,我偷偷掺了我的头发——民间说,青丝相赠,
可系住性命。“这个你带着。”我把平安符塞进他手里,指尖触到他掌心的温度,
慌忙缩了回来。“阿砚,我在府里等你回来。”他握着平安符,
指腹摩挲着符袋上绣的青梧叶,那是我们小时候常爬的树,沉默了很久。“清沅,
”他突然开口,声音有些哑。“府里的事,辛苦你了。母亲年纪大了,你多替我照看。
”这是他第一次跟我说“辛苦”。我眼眶一热,用力点头:“你放心,我会的。
”他翻身上马,立于府门前。春风拂起他的衣袍,也吹乱了我的发。他看着我,眼神复杂,
终是勒转马头,疾驰而去。我站在府门口,望着他的身影消失在巷口,
手里还攥着他刚碰过的平安符袋,指尖冰凉。萧策走后,我成了将军府真正的主心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