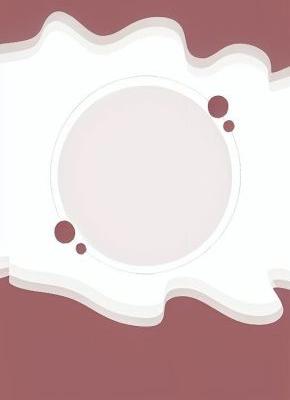和叶玄盛结婚五年,贺禧扮演着完美的叶太太。直到他初恋回国,
她平静地递上离婚协议:“叶总,角色扮演该结束了。
”叶玄盛冷笑撕碎协议:“游戏规则由我定。”后来,拍卖会上他目睹她挽着新欢,
一掷千金拍下他公司急需的地皮。红酒倾倒在离婚协议上,他声音嘶哑:“贺禧,回家。
”而她笑着点燃那张纸:“叶玄盛,火葬场的灰,呛到你了吗?
”第一章:完美赝品深夜十一点,叶氏总部顶楼的总裁办公室依旧灯火通明,
巨大的落地窗外是流淌的都市霓虹,窗内却只有文件翻动的细微声响和键盘单调的敲击。
贺禧将最后一杯温度正好的蓝山咖啡轻轻放在宽大的实木办公桌边缘,
恰好在他伸手可及又不妨碍文件的位置。杯垫是暗金色的枫叶纹样,
与他今日的领带夹微妙呼应。她往后退了半步,目光平静地掠过他微蹙的眉心和专注的侧脸。
五年,足够将很多事变成肌肉记忆。比如他咖啡的浓度,七分烫,不加糖,
只需一粒方糖搁在旁侧的小碟里;比如他习惯用的万宝龙签字笔,
笔帽一定要朝向右上角四十五度;比如他深夜工作时,室内空调必须恒定在二十二度,
空气湿度不能低于百分之四十。这些琐碎的、近乎苛刻的细节,
是她用五年时间一点点打磨进自己骨血里的“叶太太守则”。她是叶玄盛最得体的摆设,
最无声的背景,最……完美的赝品。是的,赝品。贺禧心里从未模糊过这个定位。
她记得五年前那场轰动全城的婚礼,记得神父面前他毫无波澜的“我愿意”,
更记得新婚夜他掐着她下巴,眼底是冰冷的警告:“贺禧,记住你的身份。
叶太太这个头衔我给你,你只需要做好分内的事,别奢望其他。尤其是,”他顿了顿,
每个字都淬着寒冰,“别去打扰墨莉。”墨莉。那个远在海外求学的芭蕾舞者,
叶玄盛心尖上真正的白月光。她贺禧,不过是家族利益权衡下,一个暂时填补空缺的影子。
这桩婚姻,是她濒临破产的家族递出的救命稻草,
也是叶玄盛为安抚家族、等待真爱归来的权宜之计。起初不是没痛过,没挣扎过。
少女时代那点朦胧的仰慕,在现实冰冷的铜墙铁壁前撞得粉碎。但她很快认清了现实。
感情是奢侈而无用的东西,不如实际点。当好这个“叶太太”,
至少能稳住摇摇欲坠的家族企业,能给病重的父亲支付天价医疗费。
她用一种近乎残忍的冷静,将自己重新组装,剥离了不必要的喜怒哀乐,
只留下精准的观察、妥帖的执行和无可挑剔的仪态。手机在口袋里震动了一下,
不是叶玄盛的——他极少主动联系她,有事多半通过特助。是一条匿名的彩信。贺禧点开,
瞳孔几不可察地微微一缩。照片拍得有些模糊,但足以辨认。机场VIP通道,
男人高大挺拔的背影小心翼翼护着身侧娇小的女人,女人戴着一顶别致的宽檐帽,侧脸柔美,
正是墨莉。而叶玄盛那件西装,贺禧认得,是她上周才送去的定制款,
袖扣是她亲自选的蓝宝石,此刻在机场惨白的灯光下,折射出刺眼的光。发信时间,
三小时前。算算航程,此刻,他们应该已经坐在城中某处静谧的餐厅里,
或许是他常去的那家俯瞰江景的顶楼法餐厅,那里有墨莉最爱的鸢尾花和年份香槟。
心脏某处传来一丝极细微的、几乎要被忽略的刺痛,像一根埋藏多年的绣针,
轻轻锈蚀了边界。贺禧按熄屏幕,指尖冰凉。该来的,总会来。
办公桌后的男人终于合上最后一份文件,揉了揉眉心,抬眼看向她。他的目光惯常是淡漠的,
带着长久居于上位者的审视,此刻或许因为疲惫,略显松散。“还没走?”他问,
声音听不出情绪。“司机在楼下等着了。”贺禧微笑,弧度标准,
是镜子前练习过无数次的那种,“明天上午十点,与瑞丰的李总在高尔夫球场有约,
下午三点公司季度董事会,晚上七点,您父亲希望您回老宅用餐,说是墨莉**回国了,
想一起聚聚。”她语气平稳地报出行程,如同最精密的日程表,没有泄露丝毫个人情绪,
甚至在提到“墨莉”时,音调都没有任何起伏。叶玄盛似乎有些意外她如此直接地提及,
眼神在她脸上停留了两秒,想捕捉些什么,却只看到一片完美的平静。
他几不可闻地“嗯”了一声,算是回应。“另外,”贺禧从随身携带的文件夹里,
抽出一份薄薄的、却显得异常沉重的文件,轻轻推到他面前光滑的桌面上,“这份文件,
需要您看一下。”叶玄盛垂眸,目光落在首页加粗的标题上——《离婚协议书》。
时间仿佛凝固了一瞬。空气里只剩下中央空调低沉的风声。他脸上的疲惫骤然褪去,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冰冷的、极具压迫感的锐利。他慢慢抬起眼,视线从文件移到贺禧脸上,
像是第一次真正打量她。贺禧依旧站在那里,背脊挺直,穿着剪裁合宜的珍珠白套装,
长发一丝不苟地挽起,露出优雅而脆弱的脖颈。她还是那个无可挑剔的叶太太,
但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那层温顺顺从的壳,似乎裂开了一道细微的缝隙,
泄露出里面冰冷坚硬的本质。“什么意思?”他开口,声音比方才低了几度,
带着山雨欲来的危险气息。贺禧迎着他的目光,唇边的微笑未曾改变,
甚至更从容了些:“字面意思,叶总。墨莉**回来了,我的‘角色扮演’也该结束了。
这五年,感谢您的‘关照’。协议条款很清晰,我放弃叶家的一切财产分割,
只带走我个人的物品。这样,对大家都好。”“角色扮演?”叶玄盛咀嚼着这四个字,
忽然嗤笑一声,那笑声里没有温度,只有浓浓的讥讽和不以为然的掌控欲,“贺禧,
你是不是忘了,这场游戏,从一开始,规则就由我定。”他身体前倾,手肘撑在桌面上,
那双深邃的眼眸紧紧锁住她,带着不容置疑的强势:“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
我说了算。不是你递上一张纸,就能说了算的。”他的目光扫过那份协议,
像看着一件无关紧要的垃圾。然后,在贺禧的注视下,他伸手,
两根修长有力的手指捏起那份协议,慢条斯理地,一下,又一下,将其撕成了两半,四半,
碎片。雪白的纸屑纷纷扬扬落下,落在昂贵的波斯地毯上,落在她光洁的鞋尖前。
“收好你的本分,”他语气平淡,却字字千斤,“叶太太。明天晚上,跟我回老宅。
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你清楚。”贺禧看着地上那些碎片,脸上的笑容终于淡了下去,
却没有他预想中的惊慌、愤怒或哀求。她只是极轻地点了下头,仿佛早就料到会是如此。
“好的,叶总。”她应道,声音平稳无波,“没什么事的话,我先回去了。司机等久了不好。
”说完,她不再看他,转身,步伐平稳地走向办公室大门。高跟鞋踩在地毯上,
发出闷而规则的声响,一步一步,远离这个她扮演了五年牢笼主角的地方。
直到门扉在她身后轻轻合拢,隔绝了那道一直钉在她背上的、复杂而冰冷的视线。
叶玄盛盯着紧闭的门板,眉心的刻痕许久未曾散去。地上那些纸屑刺眼地存在着,
提醒着他刚才发生的一切。贺禧的反应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她不该是哭着哀求,
或是用家族利益作为筹码谈判吗?怎么会如此平静,平静得……像早已心死,
只等一个解脱的形式?心头莫名掠过一丝极淡的烦躁,被他立刻压了下去。
不过是个识趣点的棋子罢了,还能翻了天不成?墨莉回来了,这才是最重要的事。
他抬手松了松领带,目光转向窗外璀璨却冰冷的夜景,将那个突然变得有些陌生的妻子身影,
暂时抛诸脑后。贺禧走进专属电梯,镜面门映出她毫无表情的脸。电梯下行,失重感传来。
她缓缓抬手,抚上心口。那里,很安静。没有意料中的痛彻心扉,也没有解脱后的狂喜,
只有一片荒芜的平静,以及尘埃落定后的释然。也好。他亲手撕碎的,不仅仅是那份协议,
也是她最后一点微不足道的、关于这场婚姻形式的幻想。火种已经埋下,只待风来。
第二章:老宅宴席叶家老宅坐落在城西山脚,占地广阔,是历经几代沉淀下来的世家气象。
夜色中,宅邸灯火通明,却透着一股疏离的庄严。贺禧挽着叶玄盛的手臂踏入客厅时,
里面已经笑语盈然。“玄盛回来啦!”叶母最先看到他们,笑着迎上来,目光掠过贺禧时,
带着惯常的、挑剔的打量,确认她衣着得体,妆容精致,才几不可察地点了下头,
随即热切地转向叶玄盛身后,“这位就是墨莉吧?真是百闻不如一见,比照片上还要水灵!
”墨莉就站在叶父身旁,穿着一身鹅黄色的连衣裙,衬得肌肤莹白,长发柔顺地披在肩头,
笑容温婉含蓄,带着艺术家的纯净气质。她微微颔首,声音轻柔:“伯母好,打扰了。
”“不打扰不打扰!你能回来,我们不知道多高兴!”叶母亲热地拉住墨莉的手,
将她引到沙发主位,完全将贺禧晾在了一边。贺禧早已习惯,不动声色地抽回自己的手,
叶玄盛也顺势松开,他的注意力显然已被墨莉吸引。
贺禧安静地走到客厅一侧的单人沙发坐下,像个无声的背景板。“阿盛,
”墨莉抬起盈盈的眼眸看向叶玄盛,带着些许腼腆和依赖,“伯父伯母太热情了,
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应该的。”叶玄盛的声音是贺禧很少听到的温和,
他在墨莉身边的沙发坐下,姿态放松,“这里也是你的家。”“就是,”叶母接过话头,
瞥了一眼安**着的贺禧,意有所指,“有些人是外人,住了几年也还是外人。
莉莉你不一样,你从小就跟阿盛要好,我们早就把你当自家人看了。”话里的刺,
鲜明而直接。叶父皱了皱眉,轻咳一声:“好了,人都齐了,开饭吧。”餐厅里,
长桌铺着雪白的餐布,银质餐具闪闪发光。座次分明,叶父叶母坐在主位,
叶玄盛自然挨着墨莉,贺禧则被安排在长桌的另一端,离主位最远的地方,
紧挨着上菜的侧门。席间,话题几乎全部围绕着墨莉展开。她在国外的演出,获得的奖项,
对未来的规划……叶母听得满脸欣慰,不时给墨莉夹菜,叶父虽然话不多,
但看向墨莉的眼神也充满慈爱。叶玄盛更不必说,他会细心地替墨莉剥好虾壳,
在她说话时专注倾听,嘴角始终噙着一丝淡淡的笑意。那是一幅温馨美满的家宴图,
而她贺禧,是这幅图上一个突兀的、多余的墨点。“贺禧,”叶母忽然像是才想起她,
隔着长长的餐桌望过来,语气随意,“听说你父亲那边,最近情况又不太好?
医院的费用还跟得上吗?要是吃力,就跟家里说,总不能让亲家那边太难堪。
”话语看似关切,实则将贺禧以及她家族的窘迫摊开在所有人面前,尤其是墨莉面前。
这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施舍,更是提醒她,她以及她所拥有的一切,都仰仗着叶家的鼻息。
贺禧握着银勺的手指微微收紧,指节泛白,
但脸上却适时地流露出恰到好处的感激与局促:“谢谢妈关心,目前……还能应付。
”叶玄盛抬眸看了她一眼,那目光冷淡而遥远,
仿佛在评估一件物品是否还能维持基本的功能。他没有出声。墨莉看了看贺禧,
柔声开口:“贺**家里有困难吗?如果有需要帮忙的地方……”“她能处理。
”叶玄盛截断了墨莉的话,语气是不容置疑的平淡,
甚至还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对贺禧“险些添麻烦”的不耐,“吃饭吧。”贺禧低下头,
慢慢舀了一勺汤。温热的汤汁滑过喉咙,却带不起丝毫暖意。桌布下,无人看见的角落,
她松开的手心里,留下了几个月牙形的浅浅印记。这就是她五年的婚姻。
在需要她扮演恩爱夫妻出席场合时,她是光鲜亮丽的叶太太;在叶家的私人领域里,
她就是这样一个透明的、随时可以被提醒自身处境的外人。宴席接近尾声,
佣人端上餐后水果。叶母又拉着墨莉聊起了芭蕾,说起叶玄盛小时候偷偷跑去看墨莉演出,
还送过花。“那时候阿盛可傻了,送了一大束红玫瑰,还把自己零花钱全买了,
结果被我发现,训了一顿。”叶母笑着回忆。墨莉脸颊微红,嗔怪地看了叶玄盛一眼。
叶玄盛也笑了,那是贺禧从未见过的、带着真实温度的笑意。贺禧安静地吃着水果,
一块甜瓜,异常清脆,也异常冰凉。忽然,墨莉轻轻“嘶”了一声,捂住了脚踝。“怎么了?
”叶玄盛立刻倾身过去,神色关切。“没什么,旧伤而已,今天站久了有点疼。
”墨莉摇摇头,但秀气的眉头蹙着。“你总是不会照顾自己。”叶玄盛语气带着责备,
更多的却是心疼,他自然而然地站起身,“我车里有药油,上次从国外带的,对旧伤有效,
我去拿。”他起身离席,步伐匆匆。叶母见状,看向贺禧,语气理所当然地吩咐:“贺禧,
你去厨房看看,给莉莉煮杯参茶,定定神。莉莉身体弱,不比有些人粗生粗养。
”命令的口吻,如同指使一个佣人。贺禧抬起眼,这一次,她没有立刻顺从地应声。
她缓缓放下银叉,与骨瓷碟子轻轻碰撞,发出清脆的一声“叮”。
整个餐厅似乎都因为这声轻响安静了一瞬。叶母不悦地皱起眉。贺禧却站了起来,
脸上甚至还带着那种温顺的微笑。她走到墨莉身边,微微弯下腰,
用只有她们两人能听到的音量,轻柔而清晰地说:“墨莉**。”墨莉有些诧异地抬头看她。
“你知道吗?”贺禧的嘴角噙着笑,眼神却平静无波,像深不见底的寒潭,“叶玄盛他,
对花生严重过敏。一点点花生碎末,就能让他进急救室。”墨莉愣住了,不明所以。
贺禧继续用那种轻柔的语调,慢条斯理地说:“所以这五年来,叶家的厨房,
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与花生相关的东西。连炒菜用的油,都是指定的、绝无花生成分的品牌。
他书房里常吃的安神香,是我找中医特调的,里面有一味药与花生相克,
我试了三十多种配方才避开。”她看着墨莉渐渐睁大的眼睛,笑意更深了些,
也更冷了些:“他喝咖啡只喝蓝山,七分烫,旁边要放一粒方糖,但不是用来加的,
只是他习惯看着。他工作到深夜容易胃疼,疼的时候不会说,但左手会无意识按着上腹。
这时候,温在旁边的蜂蜜水,温度要刚好六十度,太烫伤胃,太凉无效。”“他右肩有旧伤,
阴雨天会酸疼,需要特定的**手法,顺时针三十六下,逆时针三十六下,力度要沉而不滞。
他睡觉很轻,对光线和声音极度敏感,所以卧室的遮光窗帘有三层,
所有电器指示灯都必须贴住,空调风口绝不能对着床。”“哦,还有,
”贺禧仿佛在闲聊家常,“他心情不好的时候,喜欢一个人待在书房,不是真的处理公务,
只是对着窗外发呆。这时候,最好不要打扰,只要在门口放一杯清水就好。
他……”“你跟我说这些做什么?”墨莉终于忍不住打断她,脸色有些发白,
声音带着不自知的颤抖。这些话,像细密的针,
扎进她刚刚构建起的、关于她和叶玄盛亲密无间的幻梦里。她突然意识到,这五年的空白里,
是另一个女人,以她完全陌生的方式,填充了叶玄盛生活的每一个细节。贺禧直起身,
居高临下地看着她,脸上那层温顺的假面彻底剥落,只剩下冰冷的、近乎残酷的清醒。
“没什么,”她淡淡地说,声音恢复了正常的音量,足以让餐厅里所有人都听见,
“只是突然觉得,我这五年‘叶太太’,当得还挺称职的。毕竟,要把一个男人的生活习惯,
事无巨细地刻进骨子里,也是需要点本事的,对吧?”她说完,不再看任何人,
包括刚刚拿着药油走到餐厅门口、骤然停住脚步、脸色铁青的叶玄盛。贺禧转身,
对着主位上脸色难看的叶父叶母,微微颔首:“爸,妈,我有点不舒服,先回去了。
你们慢用。”然后,她挺直背脊,一步步,稳稳地,从死寂的餐厅中走了出去。
经过叶玄盛身边时,没有停留,没有侧目,仿佛他只是门口一尊无关紧要的装饰品。
夜风拂过廊下,带着山间的凉意。贺禧深深吸了一口气,冰冷的空气灌入肺腑,
冲刷掉胸腔里最后一丝沉闷。身后那座灯火通明的华丽牢笼,
以及笼中那些或震惊、或愤怒、或难堪的面孔,正在被她彻底抛下。宴席未散,
演员已提前离场。而这出戏的**,才刚刚开始。
第三章:玫瑰荆棘自老宅那场不欢而散的宴席后,贺禧与叶玄盛之间的关系降到了冰点以下,
进入了某种诡异的“静默战”状态。贺禧不再去公司送咖啡,也不再过问他的行程,
仿佛彻底卸下了“叶太太”的职责。她大部分时间待在他们位于市中心的顶层公寓里,
但叶玄盛明显减少了回来的次数,即使回来,也常常是深夜,带着一身酒气或陌生的香水味,
径直去往客房。贺禧乐得清静。她开始频繁外出,
不再局限于那些乏味的贵妇茶会或慈善拍卖。她重拾了婚前一度热爱的油画,
报名了高级课程,一画就是一整天。她也会独自去看冷门的地下乐队演出,
在喧嚣的音乐里放空自己。
她甚至开始接触一些叶玄盛绝对不会允许她接触的“危险”人物——比如,
通过一位做独立艺术策展人的老同学,认识了顾川。顾川,
这个名字在最近的财经版和花边新闻里出现的频率颇高。顾家背景深厚,势力盘根错节,
近几年他本人更是以敏锐的投资眼光和雷霆手段在商界崭露头角,
风格是出了名的低调却强势,与叶氏在几个领域存在隐性的竞争关系。他本人相貌英俊,
气质冷峻,是媒体追逐的焦点,却鲜少有绯闻。他们的第一次正式见面,
是在一个极私密的高端艺术沙龙。贺禧的一幅小尺寸风景写生被策展人同学极力推荐,
挂在了不太起眼却足够业内人士看到的角落。顾川在那幅画前停留了许久。“笔触很压抑,
”他走到正在角落安静喝酒的贺禧身边,开门见山,声音低沉,“但色彩深处,
有光想挣扎出来。很有趣的矛盾。”贺禧有些意外地抬眼看他。
很少有人第一眼看到那幅描绘阴霾天空与顽强大地的画,会这样解读。大多数所谓的收藏家,
只会夸赞技巧或构图。“顾先生懂画?”她礼貌地问,带着疏离。“不懂,”顾川答得干脆,
目光却锐利地落在她脸上,仿佛在审视另一幅更复杂的作品,“但我懂人。贺**,幸会。
”他知道她是谁。贺禧立刻明白了。在这个圈子里,叶玄盛的妻子,
这个身份比任何头衔都更引人注目,也更容易被轻视。
但顾川的眼神里没有常见的打量、怜悯或暧昧,只有一种纯粹的、评估似的兴趣。后来,
接触多了几分。有时是在画展,有时是在某个小众的音乐厅,
巧合得让贺禧几乎要怀疑是刻意安排,但顾川的举止始终保持着令人舒适的边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