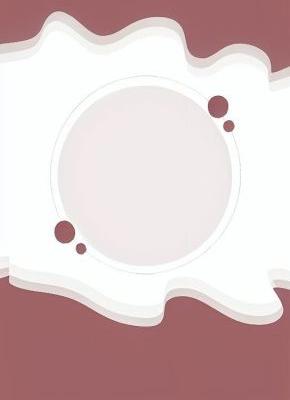陆时衍的公寓大得像座没有魂的宫殿。
意大利进口的大理石地板能映出人影,却永远留不下温度;客厅里那盏水晶吊灯缀着上百颗棱镜,白天折射着窗外的天光,晃得人眼睛发疼,夜里只开一盏落地灯,昏黄的光圈缩在沙发周围,剩下的空间全浸在浓得化不开的黑暗里。
我住的客房在最角落,窗外对着的是冰冷的防火墙,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只有偶尔掠过的霓虹,在墙上投下转瞬即逝的光斑,像极了我偶尔闪过的、不该有的期待。
我成了这座宫殿里最隐秘的影子。
白天躲在房间里,不敢碰客厅的沙发,不敢开厨房的冰箱,连走路都要放轻脚步,怕惊扰了这“华丽”背后的死寂。
衣柜里挂满了陆时衍让人送来的衣服,丝绸、羊绒,件件昂贵,却没有一件合我的身。
他给我的“温存”,看着体面,裹在身上却全是刺骨的冰凉。
我常常坐在窗边的地毯上,手里握着母亲留下的银镯子,镯子内侧刻着“浅晴”“浅予”两个名字,磨得发亮。
阳光透过玻璃照在镯子上,暖不透我指尖的凉,反而让指缝里的薄茧更清晰。
那是从前在餐厅端盘子、在便利店搬货时磨出来的,是我曾为“活下去”拼过的证明,如今却成了“囚笼”里无用的印记。
夜里的公寓会稍微“活”一点,却只活在陆时衍的掌控里。
他通常在深夜回来,身上带着酒气和陌生的香水味,钥匙转动锁孔的声音像定时炸弹,让我每次听到都忍不住绷紧神经。
有一次他回来得早,我正站在厨房想烧点热水,可刚摸到水壶,就被一双有力的手臂从身后野蛮地抱住。
陆时衍的下巴抵在我的颈窝,呼吸里的酒气混着他身上惯有的冷香,烫得我皮肤发麻。
“阿晴,”他的声音带着情动的沙哑,手指隔着薄薄的睡衣,轻轻摩挲我腰侧的皮肤,
“别闹脾气了,我知道错了……下次不会让你等这么久。”
我的身体瞬间僵住,像被冰刺扎进了骨头里。
我闭上眼睛,指甲狠狠掐进掌心,血腥味在舌尖散开:
我不是夏浅晴,我是苏浅予,是他用来报复苏家、用来填补思念空缺的工具。
可我不敢动,不敢说,只能任由他抱着,任由他的吻落在我的耳垂、我的脖颈,每一下都像在凌迟我的尊严。
直到他的动作越来越失控,我才听见自己的声音,细得像丝线:“陆时衍,我是苏浅予。”
这句话当头一盆冷水,瞬间浇灭了陆时衍的温情。
他猛地推开我,力道大得让我踉跄着撞到身后的料理台,后腰传来一阵钝痛。
他后退半步,眼底的柔情全褪成了冰,嘴角勾起刻薄的冷笑:“苏浅予?我当然知道你是苏浅予。”
他弯腰,手指生硬地捏住我的下巴,强迫我抬头看着自己,“怎么?还想替你姐姐占着我的心思?别忘了协议上写的——你的身体是我的,心思也该收一收。你和你父亲一样,骨子里都是肮脏的,靠出卖尊严换好处,别妄想得到不属于你的东西,包括我的一点关注。”
我的下巴被捏得生疼,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被他硬生生逼了回去。
我知道,眼泪在陆时衍面前没用,只会招来更狠的羞辱和嘲讽。
低下头,我看着自己的鞋尖,声音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事:“我知道了。”
可只有我自己清楚,他每一个字,都在割裂我的心脏,疼得缓慢又绵长。
夜里躺在冰冷的床上,总能想起母亲还在的时候,母亲抱着我说“浅予要永远骄傲地活着”,可现在,我连骄傲的资格都没有了。
我开始学着用冷漠伪装自己:
他抱我的时候,我会僵硬身体,像个没有灵魂的木偶;他说刻薄话的时候,我会垂下眼睛,假装没听见;甚至他偶尔给我带回来从前爱吃的甜点,也只会说“谢谢”,然后放进冰箱,直到放坏了再扔掉。
我以为这样就能减少痛苦,可夜深人静的时候,心脏还是会抽痛。我不明白,为什么陆时衍可以对夏浅晴那么好:
他会记得夏浅晴不吃香菜,会在夏浅晴说冷的时候立刻递过外套,会把夏浅晴的照片放在钱包里;可对我,只有利用和伤害。
难道就因为我是“苏浅予”,不是他心里的“阿晴”吗?
变故发生在一个雨夜。
那天我淋了点雨,夜里就发起了高烧,浑身滚烫,意识模糊间,我只觉得冷,冷得像掉进了冰窖。
迷迷糊糊中,我听见门锁响,以为是幻觉,直到一双微凉的手覆在了额头上。
我猛地睁开眼,模糊的视线里,是陆时衍皱着眉的脸。
“你找死?”
他的语气很冲,带着不耐烦,可那只手却没立刻拿开,指尖的凉意透过滚烫的皮肤,传到心里,竟让我觉得有一丝暖意。
我下意识地抓住他的袖口,像抓住最后一根浮木,声音微弱:“好冷……”
陆时衍的身体一僵,低头看了看被我攥住的袖口,没说话,转身去了客厅。
我昏昏沉沉地等着,以为他会像以前一样不管我,可没过多久,他就拿着退烧药和温水回来,还带来了家庭医生。
医生给我打针的时候,我半梦半醒间,感觉陆时衍站在床边,呼吸有些急促,甚至对医生说“烧得厉害,得物理降温”时,他竟亲自拿了湿毛巾,敷在我的额头上。
那毛巾的温度刚刚好,带着他指尖的余温,我差点就以为,他是在乎我的。
可第二天早上,这份错觉就被彻底打碎。
我醒来时,床头放着温水和药片,陆时衍坐在沙发上看文件,西装已经穿得整齐,脸上没有丝毫波澜。
听到我翻身的动静,他头也不抬地说:
“醒了就把药吃了,别装可怜。我没那么容易心软,只是怕你死了,没人照顾夏浅晴—我还需要你这个‘好妹妹’替我盯着她。”
我的手顿在半空,刚升起的一点暖意瞬间凉透。
顺着他的目光,我看向他的袖口。
昨天被我攥过的地方,褶皱还没抚平,像一道没愈合的疤,可他的话,却比刀还锋利。
我默默拿起药片,就着温水咽下去,药片在喉咙里卡了一下,苦得眼眶发酸。
真正的折磨,是夏浅晴的“探望”。
夏浅晴第一次来的时候,拎着一个精致的保温桶,进门就笑着喊“时衍”,声音甜得发腻,仿佛她才是这座公寓的女主人。
看到我,她快步走过来,伸手就拉住我的手,掌心的温度很暖,却让我觉得被毒蛇缠上,浑身不舒服。
“妹妹,辛苦你了。”夏浅晴笑得温柔,眼睛弯成了月牙,可目光却飞快地扫过我身上的真丝睡裙。
那是陆时衍前几天让人送来的,料子极好,却不是我喜欢的风格,
“时衍脾气不好,有时候说话冲,你多让着点他。他心里是在乎你的,不然也不会让你住在这里。”
我没说话,只是轻轻抽回了手。
看着姐姐夏浅晴红润的脸色,嘴唇涂着淡淡的口红,头发烫成了精致的卷发,哪里有半分“病危”的样子?
可上次视频的时候,夏浅晴还虚弱地说
“妹妹,我好怕,不知道能不能撑过下次手术”。
这时陆时衍走过来,自然地接过夏浅晴手里的保温桶,语气是我从未听过的温柔:
“怎么来了?医生不是让你多休息吗?”
“人家想你了嘛。”夏浅晴靠在他的胳膊上,像个撒娇的孩子,然后转头对我说,
“妹妹,我炖了鸽子汤,补身体的,你也喝点吧。对了,时衍,你别对妹妹太粗鲁了,她还小,不懂事,有时候可能会做错事,你多教教她就好。”
“不懂事”三个字,像一根细针,狠狠扎进了我的心里。
我看着夏浅晴眼底一闪而过的得意。
那是胜利者的姿态,是在宣告“你不过是我用来稳住他的工具”。
我晚突然觉得一阵反胃,转身想去洗手间,却不小心撞到了身后的茶几,茶几上的玻璃杯掉在地上,摔得粉碎。
“哎呀,妹妹怎么这么不小心?”
夏浅晴立刻走过来,假装要扶我,语气里却带着责备,
“这杯子是时衍很喜欢的,你怎么这么毛躁?”
陆时衍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看向我的眼神又冷了回去:
“收拾干净。”
我蹲在地上,捡着玻璃碎片,指尖被划破了也没察觉。
鲜血滴在白色的大理石地板上,像一朵朵刺眼的罂粟花。
我听着客厅里夏浅晴和陆时衍的投怀送抱的笑声,心里的怀疑越来越重。
姐姐的病,真的有那么严重吗?
后来夏浅晴又来过几次,每次都带着“关心”,却每次都有意无意地挑事。
有一次她走后,我在沙发缝里发现了一张医院的缴费单,日期是夏浅晴说“在家休息,浑身无力”的那天,缴费项目赫然写着“美容针注射”。
我拿着那张单子,手开始禁不住发抖。
我想起母亲去世前说的话:“浅予,你姐姐心思重,你要多让着她,但也要保护好自己。”
原来母亲早就看出来了吗?
姐姐的病,或许从一开始就不简单?
那天晚上,陆时衍回来的时候,我还坐在沙发上,手里攥着那张缴费单。
灯光下,我的脸色苍白如纸,眼底是藏不住的疲惫和痛苦。
陆时衍看到了单子,走过来,没等我说话,就从我手里抽走单子,揉成一团,扔进了垃圾桶。
“别胡思乱想。”
他的语气很平淡,却带着粗暴的压迫感,“夏浅晴的病,轮不到你管。你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扮演好‘情人’,照顾好我,就够了。”
我抬起头,看着他的眼睛,想问他“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想问他“你对我的所有残忍,都是为了她吗”,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我知道,就算问了,也得不到答案,反而会招来更多的伤害。
窗外的雨又开始下了,敲在玻璃上,发出沉闷的声音。
我蜷缩在沙发上,看着空荡荡的客厅,突然觉得这座华丽的公寓,根本不是囚笼,而我的心,才是。
被陆时衍的刻薄、夏浅晴的伪善、自己的无能为力牢牢锁住,连呼吸都带着疼。
黑暗里,只有心脏抽痛的声音,清晰得可怕,提醒着我:
人生,早就坠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再也爬不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