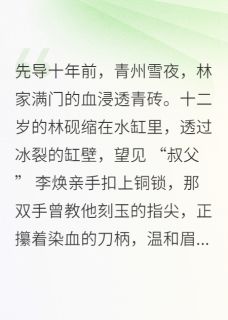先导十年前,青州雪夜,林家满门的血浸透青砖。十二岁的林砚缩在水缸里,
透过冰裂的缸壁,望见“叔父”李焕亲手扣上铜锁,那双手曾教他刻玉的指尖,
正攥着染血的刀柄,温和眉眼在刀光里淬成寒冰。十年后,琼林宴上,
新科状元楚砚腕间朱砂痣随烛火震颤。他故意倾翻酒盏,让琥珀色酒液漫过李焕官袍,
又将刻着“守拙”的端砚转了半圈——砚底隐纹与林家旧物分毫不差。
他盯着仇人骤然绷紧的指节,听见十年前的锁链声在耳畔重响。
裂成两半的“焕”字玉佩,地牢锈锁磨出的指痕,
半幅藏着杀机的画卷……当楚砚在金銮殿叩请入东宫时,棋盘上的每粒棋子,
都浸着林家的血。这场以命为注的棋局,落子便再无回头路。
第一章金殿藏锋琼林宴的鎏金盏刚碰到唇边,楚砚的手腕突然微不可察地一偏。
琥珀色的酒液泼在锦缎官袍上,洇出深色的痕迹。李焕猛地抬头,
烛光恰好落在楚砚露出的皓腕上——那枚殷红的朱砂痣在雪白肌肤上跳动,
像极了十年前那个总爱跟在他身后的少年。「放肆!」身旁的吏部尚书厉声呵斥,
「新科状元竟敢冲撞李大人!」楚砚慌忙放下酒杯,长揖到地时,袖口扫过案几,
将一方端砚推得转了半圈。「晚辈该死!」他声音带着恰到好处的惶恐,额发垂落遮住眉眼,
「方才看李大人衣上绣的青松出神,竟忘了分寸。」李焕捻着胡须的手指骤然收紧。
青州林家的公子林砚,当年最爱缠着他讲解松鹤图。「无妨。」李焕的声音听不出喜怒,
目光却像淬了冰,「楚状元祖籍青州?」楚砚起身时,恰好让烛光照亮侧脸。
他的眉骨比记忆中更锋利些,眼神却纯澈得像山涧清泉:「正是。大人也知晓青州?」
「十年前青州出过桩大案,」李焕端起新斟的酒,指尖在杯沿摩挲,「林家满门抄斩,
楚状元可有印象?」宴席瞬间安静下来。谁都知道林家灭门案是李焕一手督办,
此刻提起无异于在刀尖上跳舞。楚砚却像是没听出弦外之音,笑着翻转手中端砚。
石质温润的背面,「守拙」二字筋骨分明,与当年林家书房里那方祖传砚台分毫不差。
「晚辈那时才七岁,只记得林家教子极严。」他指尖轻叩砚台,
「家父说林老爷连砚台都要刻上家训,可惜……」话音未落,李焕突然将酒杯重重顿在案上。
瓷杯与青玉案相撞的脆响,让满座官员都噤了声。「可惜什么?」
李焕的目光如鹰隼般锁定他,「可惜林家通敌叛国,落得个满门抄斩的下场?」
楚砚的肩膀轻轻一颤,慌忙低下头:「晚辈失言。」这场插曲很快被歌舞掩盖,
楚砚却敏锐地察觉到,有两道阴冷的视线始终黏在他背上。直到宴席散场,他故意落在最后,
看着李焕的背影消失在朱红宫门外,嘴角才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他沿着宫墙缓步而行,
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腕间的朱砂痣。十年前也是这样的夜晚,
李焕就是在琼林宴后带着禁军闯入林府,那把染血的刀,此刻仿佛还抵在他的脖颈上。
状元府的烛火亮到三更。楚砚坐在窗边擦拭那方端砚,
砚底暗格突然弹出——里面藏着半幅泛黄的画卷,画中锦衣少年正趴在案上临摹书法,
身旁站着的官员眉眼温和,正是十年前的李焕。「吱呀」一声,窗棂被夜风吹开。
楚砚迅速将画卷摊在书案中央,吹灭烛火的瞬间翻身躲进梁上。三个黑衣人如鬼魅般落地,
为首者直奔书案,指尖刚触到画卷,楚砚突然从梁上跃下,靴底精准地踩在他手背。
「李大人的手段,还是这么见不得光。」火折子骤然亮起,照亮楚砚含笑的脸。
黑衣人抽刀的瞬间,他已抄起案上的砚台斜劈过去。端砚在青砖地上裂成两半,
他顺势抬脚踢向一块锋利碎片,碎片如飞刀般精准划破为首者的咽喉。另外两人对视一眼,
挥刀直扑过来。楚砚侧身避开刀锋,扯下悬挂的幔帐猛地甩出。丝绸缠住刀刃的刹那,
他反手抽出墙上悬挂的佩剑,剑锋在烛火下划出冷冽的弧线。惨叫声戛然而止时,
楚砚正用黑衣人腰间的玉佩擦拭剑上的血。那玉佩雕成貔貅模样,
与十年前李焕送他的生辰礼一模一样。「告诉李大人,」他将染血的玉佩丢在尸体旁,
「这画是赝品,多谢他费心了。」次日早朝,楚砚捧着奏折跪在金銮殿上。
阳光透过雕花窗棂落在他身上,素色官袍衬得他愈发清隽。「陛下,臣愿入东宫,
为太子殿下伴读。」文武百官一片哗然。谁都知道太子与李焕势同水火,新科状元这步棋,
走得未免太险。皇帝捻着佛珠的手指一顿:「楚爱卿可想清楚了?东宫可不是好去处。」
「臣只想为陛下分忧。」楚砚叩首时,余光瞥见李焕站在班列中,嘴角噙着若有若无的笑意。
果然,李焕出列奏道:「陛下,楚状元才华横溢,确是太子良师。」他顿了顿,
目光扫过楚砚,「臣举荐楚爱卿兼任太子侍读,常伴左右。」楚砚心中冷笑。
李焕这是想把他放在眼皮底下监视,顺便借他的手搅乱东宫。「准奏。」
皇帝的声音在大殿回荡,「楚砚,即日起入东宫当值。」退朝时,李焕故意与楚砚擦肩而过,
低声道:「老夫府中藏有几幅青州古画,或许楚状元会感兴趣。」他眼角的皱纹里藏着算计,
像是在抛出诱饵。走出宫门时,李焕的轿子恰好停在石阶下。轿帘被风吹起,
露出李焕那双深不见底的眼睛。「楚状元,」轿内传来低沉的声音,「今晚到老夫府上一叙?
」楚砚望着天边掠过的孤雁,缓缓拱手:「敢不从命。」他知道,这场棋局才刚刚开始。
而他布下的第一颗子,已经稳稳落在了李焕的棋盘上。暮色四合时,
楚砚提着食盒站在李府门前。朱漆大门上的铜环闪着冷光,像极了当年锁住林家大门的那副。
管家引着他穿过九曲回廊,月光透过雕花窗洒在地上,碎成一片斑驳的银霜。正厅里,
李焕已端坐案前,面前摆着两副碗筷。「尝尝这个。」李焕夹起一块水晶肘子,「青州名菜,
楚状元应该不陌生。」楚砚盯着碗里油光锃亮的水晶肘子,肥肉上的油珠顺着瓷碗边缘滑落,
像极了当年从父亲胸口滴落的血。胃里猛地一阵痉挛,
十年前那个雪夜的记忆瞬间冲破闸门——他缩在水缸里,啃着冻成石块的馒头,
听着母亲的惨叫声被利刃切断。「多谢大人。」他强压下喉间的腥甜,「晚辈如今素食。」
李焕放下筷子,突然从袖中取出一枚玉佩。月光下,那枚刻着「焕」字的暖玉泛着温润的光。
「这是十年前一位故人所赠,」李焕的手指摩挲着玉佩,「楚状元觉得眼熟吗?」
楚砚的心脏骤然缩紧。那是他十二岁生辰时,李焕亲手为他刻的。「玉质上乘,」
他垂下眼帘,掩去眸中的惊涛骇浪,「只是晚辈孤陋寡闻,未曾见过。」李焕突然笑了,
将玉佩丢回袖中:「或许是老夫看错了。」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听说楚状元想教太子书法?」「略尽绵薄之力。」「太子性子急躁,」
李焕的声音陡然转冷,「楚状元可要好好引导。若是教不好……」他顿了顿,
指尖在案上轻轻敲击,「青州可不止林家一个前车之鉴。」楚砚缓缓抬头,
烛火在两人之间投下交错的阴影。李焕的目光像淬了毒的冰锥刺过来,
那双曾手把手教他握笔的眼睛里,如今只剩下翻涌的阴鸷与狠戾,
仿佛在掂量如何将他碎尸万段。「晚辈明白。」他微微一笑,起身告辞时,
故意将腰间的香囊蹭落在地。锦缎香囊散开,掉出半块断裂的玉佩——正是那枚「焕」
字玉的另一半。李焕的瞳孔骤然收缩。楚砚弯腰去捡时,
指尖故意在他靴尖上划了一下:「大人见笑了,这是家母留的念想。」
直到楚砚的背影消失在月色中,李焕才捡起那半块玉佩。断裂处的纹路严丝合缝,
十年前那个少年的脸,与方才楚砚含笑的眉眼重叠在一起。「来人。」
李焕的声音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去查,楚砚的生辰。」窗外的风卷着落叶掠过廊下,
像极了十年前那个雪夜,林府里此起彼伏的哀嚎。楚砚站在街角回望李府,
袖口下的手紧紧攥着那方裂成两半的端砚。「叔父,」他对着空气轻声说,「我回来了。」
夜色渐深,状元府的灯又亮了起来。他从床底暗格取出一个锈迹斑斑的铜锁,
这是当年林府地牢的钥匙。十年间,他每天都会摩挲锁孔里的纹路,
就像在反复演练复仇的每一步。窗外的夜枭又叫了一声,他吹灭烛火,
身影融入黑暗——李焕派来查他生辰八字的人,此刻应该已经到了巷口。楚砚铺开宣纸,
蘸着朱砂写下两个字——「守拙」。墨迹未干时,窗外传来夜枭的啼叫,他知道,
李焕的第二波试探,已经在路上了。第二章棋局反噬东宫偏殿的檀香燃到第三寸时,
楚砚将密信推到太子面前。洒金宣纸上的墨迹还带着潮湿的腥气,
像极了当年林家地牢石缝里渗出的血。「李焕在漠北私藏了三万石粮草。」
楚砚指尖点过信上的朱砂标记,「昨夜羽林卫亲军看到他的人在城外接货,
车辙印深得能埋进半只脚。」太子赵衡猛地拍响案几,玉冠上的珍珠簌簌发抖。
他盯着信末那个歪扭的「焕」字印章,喉间滚出粗重的呼吸:「这个老匹夫!
上次构陷我私藏兵器不成,竟敢克扣边军粮草!」楚砚垂下眼帘,掩去眸底的冷笑。
这封信是他仿李焕笔迹写的,
连印章上的裂纹都复刻得分毫不差——当年李焕教他刻章时,特意在「焕」
字右下角留了道斜痕,说是「君子藏锋」。「殿下慎言。」他适时出声劝阻,
袖口下的手却将另一枚蜡丸捏得更紧,「李大人如今是父皇跟前的红人,没有铁证……」
「铁证就在他府里!」赵衡豁然起身,龙纹箭袖扫落了案上的茶盏,「明日早朝,
本宫定要他好看!」瓷片碎裂的脆响惊飞了檐下的夜鹭。楚砚望着太子怒冲冲离去的背影,
弯腰拾起一块带茶渍的碎片——边缘锋利得能划破指尖,
正适合用来撕开这场棋局的口子。次日五更,天还蒙着层青灰色,
楚砚就被太监拽着衣袖往大殿跑。宫道两侧的宫灯在风里摇晃,
照得他官袍上的补子忽明忽暗,像极了当年林家灭门那日,天边翻滚的乌云。
「楚大人还不知道吧?」太监跑得气喘吁吁,「太子殿下一早就在金銮殿候着了,
说是要参李大人一本!」楚砚握着袖中蜡丸的手猛地收紧,冰凉的蜡油沁进掌心。
比他算好的时辰早了半个时辰,这头被激怒的幼狮,怕是要提前撞进李焕的陷阱里。
刚踏入殿门,就听见太子的怒吼撞在金砖地上:「父皇!李焕私藏粮草意图不轨,
请您下旨抄家!」李焕站在百官之首,玄色官袍上的仙鹤仿佛要扑过来啄人。
他慢悠悠地出列,朝皇帝躬身时,余光像淬了毒的针,直直扎向楚砚:「陛下明鉴,
太子殿下怕是被奸人蒙蔽了。」皇帝捻着佛珠的手指顿在「佛」字上,
鎏金念珠硌出深深的红痕:「哦?李爱卿有何证据?」李焕拍了拍手,
两名侍卫拖着个麻袋摔在殿中央。粗麻破开的刹那,
楚砚的瞳孔骤然收缩——麻袋里滚出的,竟是他昨夜丢在李府后墙的蜡丸,
此刻正插着支雕翎箭,箭羽上还沾着他府里特有的孔雀蓝丝线。
「这是今早在东宫墙角发现的。」李焕捡起蜡丸,指甲刮过上面的火漆印,「里面的信说,
要太子伪造证据构陷老臣,事成之后……」他顿了顿,声音陡然拔高,「许他废长立幼!」
满殿哗然炸得楚砚耳膜生疼。他看着李焕从袖中抽出另一封密信,
信封上还沾着北狄特有的狼图腾火漆。「这是今早截获的北狄使者密信。」李焕展开信纸,
宣纸上的字迹扭曲如鬼爪,赫然是太子的笔迹。「父皇您看!」他将信举过头顶,
「太子竟与北狄约定,借兵三万逼宫夺权!」皇帝猛地将佛珠砸在龙椅扶手上,
檀木珠子滚得满地都是:「逆子!你还有什么话说?」赵衡脸色惨白如纸,
手指着李焕却发不出声音。楚砚看着他发抖的膝盖,突然想起十年前那个雪夜,
父亲也是这样跪在李焕面前,喉咙被刀柄抵住,连辩解的机会都没有。「陛下息怒。」
楚砚出列跪倒,官帽上的簪子磕在金砖上,「太子殿下或许只是一时糊涂……」「糊涂?」
李焕冷笑一声,玄色靴底狠狠碾过地上的檀木佛珠,珠子碎裂的脆响像极了骨头断裂声,
「勾结外敌可是要诛连九族的!楚大人想替他垫背?」楚砚的额头抵着冰凉的地面,
声音却稳得像块石头:「臣不敢。只是密信之事疑点重重,不如先将太子殿下禁足东宫,
查明真相再定罪不迟。」皇帝的喘息声渐渐平复。楚砚知道,
这步缓兵之计成了——禁足东宫,才好让他下一步棋。三日后的黄昏,
东宫墙角的爬山虎又爬高了半尺。楚砚提着食盒站在禁苑外,看着侍卫换岗的间隙,
将掺了麻药的鱼干丢进墙内。东宫的朱门落锁时,楚砚正蹲在墙根下喂猫。
那只三花猫是他前日从李府后巷捡的,左前腿有道疤痕,像极了当年救过他的那条猎犬。
「喵呜——」猫突然弓起脊背,冲着假山后的阴影哈气。楚砚慢悠悠地起身,
拍了拍沾着猫毛的衣袖:「殿下躲了这半日,腿不麻吗?」赵衡从假山后踉跄走出,
锦袍上沾着草屑。他盯着楚砚的眼睛,声音抖得像秋风里的落叶:「是你?
那封密信是你……」「是我写的。」楚砚打断他,从袖中掏出个油纸包,「但这个,是真的。
」油纸包里滚出枚铜制令牌,上面刻着「废太子府」四个阴文。
赵衡的瞳孔骤然放大——那是他二哥的信物,三年前二哥被废黜时,
这令牌早就该随着府衙一同烧毁了。「李焕当年帮着废太子敛财,
账本就藏在令牌背面的暗格里。」楚砚将令牌抛给赵衡,「你把这个交给三皇子,他会帮你。
」赵衡接住令牌的手突然被抓住。楚砚的指尖冰凉,
死死扣着他的脉门:「殿下可知这令牌为何会在我手里?」他突然拔剑划破自己的手臂,
鲜血瞬间染红了月白袖口。「昨夜李焕派来的刺客,用的就是这种剑。」剑锋抵在赵衡咽喉,
「十年前斩林家满门的刀,也是这个制式。」「殿下可记得那批刀的锻造记号?」
楚砚掀起袖口,露出小臂上淡粉色的疤痕,「左刀鄂有个‘焕’字,就像这样——」
他用鲜血在赵衡手心里画了个歪扭的字。赵衡的喉结剧烈滚动。楚砚看着他眼中的恐惧,
突然笑了——就像当年李焕看着父亲跪在地上发抖时那样。「现在信了?」他收剑回鞘,
血珠滴在青砖上,晕开细小的红梅,「三日后祭祀大典,是你唯一的机会。」
三日后的祭天台上,楚砚捧着祭文的手微微出汗。他偷偷抬眼,
看见李焕身边的礼部侍郎正往香炉里撒着什么。青烟突然变浓,
呛得皇帝咳嗽起来——那是**的味道,李焕竟想在祭天台上动手脚。
檀香在青铜鼎里翻腾,将皇帝的脸熏得忽明忽暗。他眼角的余光瞥见李焕站在礼部侍郎身后,
正用手指在袖中打暗号。「……以承天意,永保江山……」楚砚读到此处突然停顿,
指尖点向祭文的第三行,「这句话,是谁添的?」百官的目光齐刷刷投向礼部侍郎。
那老臣顿时面如土灰,扑通跪倒在地:「臣、臣不知!是、是誊抄时就有的!」
楚砚举起祭文对着阳光,纸背上隐约透出另一种墨迹:「此句笔法凌厉,倒像是……」
他抬眼看向李焕,嘴角勾起抹冷笑,「像极了李大人前日给国子监博士写的寿帖。」
李焕的脸色瞬间铁青。那寿帖是他亲笔所书,前日还被楚砚借去「临摹学习」,
此刻祭文上的字迹,连他刻意藏起的笔锋都模仿得丝毫不差。「楚大人休要血口喷人!」
李焕厉声喝道,袖中的手却攥紧了那枚「焕」字玉佩——这是他今早收到的,
说是楚砚在东宫墙角遗落的。楚砚突然抓起祭台上的青铜匕首,
划破掌心的刹那将血滴在祭文上:「祭天在上!此句若出自我手,甘受天打雷劈,永堕轮回!
」鲜血滴在祭文上,恰好晕染了那个添上去的句子。皇帝盯着那团模糊的红,
突然将青铜酒爵砸在地上:「查!给朕彻查!」楚砚看着李焕紧绷的侧脸,
舔了舔唇角的血腥味。这一步棋,终于将李焕的棋子逼到了悬崖边。
而他藏在袖中的那半块玉佩,正随着心跳微微发烫——下一步,该让这对断裂的玉,
彻底见光了。第三章旧物惊魂李府的朱门刚推开一条缝,楚砚就闻到了熟悉的龙涎香。
十年前林家宴客时,父亲总爱焚这种香,直到李焕带着禁军闯进来,
香灰才在血泊里凝成扭曲的形状。「楚大人里面请。」管家弓着腰引路,
指尖在袖中反复摩挲——那是李焕教的暗号,若楚砚有异动,就按动廊柱里的机括。
正厅的紫檀木案上摆着尊玉雕貔貅,碧绿色的翡翠在烛火下泛着冷光。
楚砚的指尖刚触到貔貅的独角,就听见身后传来脚步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