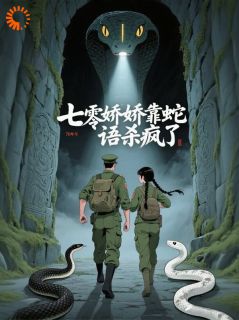1957年6月22日夏至清晨,林初夏和她的龙凤胎哥哥,在吉省春城市第一人民医院呱呱坠地。
满月那天,他们的名字也正式落定。
女孩叫林初夏,男孩叫林朝晖,他们还有一个三岁的姐姐,林春棠。
林家五口人,在这座东北工业重镇,开始了新的生活。
林初夏很快确认,这是一个与她前世历史高度相似的平行时空。
然而,这份认知带来的不是欣喜,而是隐隐的忧虑。
她清晰地记得紧随其后的1958-1962年,那场席卷全国,饿殍遍野的大饥荒!
这个年代,是真的会饿死人的!
通过父母的谈话和家里的环境,林初夏了解到:
父亲林长生,22岁,是春城市第一汽车制造厂(当地人习惯称“一汽”)的二级技术工人,每月工资36元。
母亲姜淑怡,21岁,在市纺织厂做车间女工,月工资25元。
双职工家庭,在这个绝大多数人还在为温饱挣扎的年代,绝对是令人羡慕的“富贵”人家了,吃穿用度比普通家庭宽裕许多。
林初夏一家5口和爷爷奶奶还有大伯一家5口住在独栋小院里。
爷爷奶奶住在正屋,大伯一家5口住在东厢房,林初夏一家5口住在西厢房。
一家子虽有拌嘴,但是日子过的倒是不差。
爷爷奶奶在家帮忙做饭照顾孩子,大伯林长喜继承爷爷的工作在粮食局上班,大伯母孙琴贵在日化厂工作。
大伯一家有3个儿子。
大堂哥林继业,今年7岁;二堂哥林继强,今年4岁;三堂哥林继辉,今年2岁。
几个孩子正是调皮捣蛋的时候,不仅把家里闹的鸡飞狗跳,邻居也是苦不堪言。
林初夏一家虽然住西厢房里,面积不算阔绰,但姜淑怡硬是收拾出两间规整的屋子,处处透着这个能干主妇的利落劲儿和那个年代特有的朴素整洁美学。
推开刷着蓝灰色油漆的木门,一眼望去,屋里收拾得板板正正,溜光水滑。
地面是红砖墁地,被扫得一尘不染,墙角连根头发丝儿都难找。
最显眼的是那张靠墙摆放的枣红色方桌,桌面擦得能照出人影。
桌面上,一个藤编的托盘里,印着鲜艳大朵牡丹花的暖水瓶和两个描着红双喜字样的白底搪瓷缸子,码放得整整齐齐被一块红蓝格子布罩住。
托盘边是一个木头发条座钟,每到整点就“噹噹噹”的敲个不停。
窗台边,木制的简易洗脸架稳稳地立着,三条毛巾按照颜**分开来,对折得棱角分明,搭在横杆上。
洗脸架下层并排放着两个红色搪瓷脸盆,盆底印着一个“囍”字,盆沿有些许磕碰掉瓷的痕迹,露出里面黑色的底铁,但整体擦得锃亮发光。
两把刷毛磨得有点发散的牙刷放在被当成牙缸的铁皮罐头里,一盒白色的乐口净牌牙粉,扁圆铁盒装的人参牌雪花膏,和一块黄色散发着硫磺皂味的固本肥皂,都规规矩矩紧挨着窗台排列。
视线转到占据了房间相当大面积的火炕上。
炕上最醒目的家具就是靠着炕梢墙壁立着的炕琴。
这炕琴是深红色的,表面刷着亮油,柜门镶嵌着印有传统松鹤延年图案的玻璃画,色彩浓郁,寓意吉祥。
打开黄铜的柜门拉手,里面整整齐齐地码放着一床床厚实暄软的大棉被和同样厚实的棉褥子。
被面多是大红色印着牡丹凤凰的绸缎,被垛叠得四四方方棱角分明。
炕上铺着芦苇席,夏天凉爽,冬天上面再铺一层厚实的棉褥子。
墙上贴着劳动最光荣的宣传画和伟人语录日历。
这个家被打理的井井有条,林初夏对这个家里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
她确信自己确实投生了一个富贵人家。
但这份富贵在即将到来的天灾人祸面前,又能支撑多久?
林初夏心中蒙上了一层阴影。
作为婴儿,她首要的任务是健康成长。
她渐渐适应了小小的身体,三个月努力抬起小脑袋,四个月笨拙地翻身,六个月能稳稳坐住,八个月后满炕乱爬,十个月扶着墙颤巍巍站起来,一周岁时,终于能摇摇晃晃地迈出人生的第一步。
周岁生日那天,林家老宅里充满了欢声笑语。
林初夏憋足了劲,在父母期待的目光中,清晰地喊出了“妈妈!”“爸爸!”,喜得年轻的父母当场多喝了二两地瓜烧。
哥哥林朝晖不甘示弱,也扯着嗓子吼出了“mia~mia~”和“啵啵”,虽然含糊不清,但也算正式加入了会说话的行列,赢得一片掌声。
林初夏格外珍惜这个不重男轻女,对儿女一视同仁的温暖家庭。
芯子里是成年人的她,努力扮演着乖巧懂事的老闺女角色。
一岁多能走稳后,她就拒绝大人喂饭,坚持用小木勺笨拙的扒拉碗里的玉米面糊糊,常常吃得满脸满身都是。
她还自觉帮姐姐担负起看顾傻哥哥的任务。
父母上班后,照顾弟妹的责任自然落在半大的林春棠身上。
小小年纪的林春棠经常站在小马扎上,把锅里温着的剩饭端出来,林初夏总是尽量自己吃,然后帮着姐姐按住那个满地乱爬,不肯老实吃饭的哥哥林朝晖,方便姐姐把勺子塞进他嘴里。
灾难,如同她记忆中的阴影,如期而至。
1958年夏,南方传来洪水肆虐的消息。
进入1959年,北方大地仿佛被放进了蒸笼,气温异常升高,天空吝啬得不肯降下一滴雨。
田里的庄稼苗焦黄枯萎,老农蹲在地头,绝望地拍打着干裂的泥土,嚎啕大哭。
城里的气氛也一天比一天紧张,供应量全部减半。
林家饭桌上的变化是最直观的信号。
往日偶尔能见的果光苹果、橘子瓣糖彻底消失了。
粥越来越稀,玉米面饼子越来越小,掺杂的野菜和树叶比例越来越高。
餐桌上再也听不到孩子们争抢食物的嬉闹,只有沉默的吞咽。
饥饿感像无形的藤蔓,缠绕着家里的每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