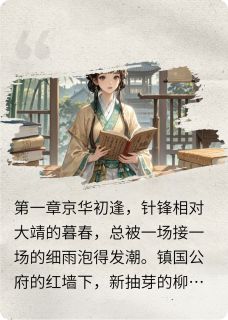大靖的暮春,总被一场接一场的细雨泡得发潮。镇国公府的红墙下,新抽芽的柳枝垂在积水里,映出墙内隐约的丝竹声——今日是萧策凯旋的庆功宴,京中权贵几乎都到齐了。
沈清辞坐在临水的游廊下,指尖捻着一枚刚落的玉兰花瓣。她穿一身月白绣玉兰花的襦裙,裙摆扫过青石板时,带起细碎的香风。廊外的戏台上正演着《破阵乐》,鼓点打得震天响,她却觉得聒噪,不如手边这盏冷茶来得清静。
“清辞,陛下可要见你呢。”母亲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带着难掩的笑意,“快去见过镇国公府的萧世子,就是那位刚从雁门关回来的少年将军,听说……”
沈清辞没听母亲后面的话,只顺着她的目光望去。只见庭院入口处,一个身着玄色劲装的少年正大步走来。他约莫二十岁年纪,肩宽腰窄,墨发用一根简单的玉簪束着,额角还带着点未褪尽的风霜。最惹眼的是他腰间的佩剑,剑鞘上缠着圈暗红的绸带,像是浸过血,走一步,那绸带便晃一下,与周遭的富贵气格格不入。
“那就是萧策?”旁边有人低叹,“果然是少年英雄,听说他十七岁就上了战场,这次更是以五千骑兵破了蛮族三万大军。”
沈清辞微微蹙眉。她不喜欢这般张扬的人,尤其厌恶那些靠杀伐博取功名的武将——父亲常说,真正的太平,从不是靠刀枪拼出来的。
正想着,那少年竟径直朝游廊走来。他似乎没看路,脚下的靴子碾过廊边的青苔,带起的泥水溅到了沈清辞的裙摆上,留下几个深色的印子。
“抱歉。”萧策的声音低沉,却没半分歉意,目光扫过她的裙摆时,甚至带了点漫不经心,“沈**的裙子,倒是比边关的帐篷娇贵。”
沈清辞抬眼,撞进他眼底。那是双极亮的眼睛,却像淬了冰,藏着沙场带来的戾气。她缓缓放下手中的花瓣,声音清泠如琴:“萧将军的靴子,也比京中纨绔的马蹄铁粗野。只是这游廊是赏景的地方,不是演武场,将军若想踏泥,不如回营里去。”
萧策挑了挑眉。他早听说沈尚书家的嫡女是京中第一才女,琴棋书画无一不精,却没想到是这般伶牙俐齿的性子。他故意往前半步,高大的身影几乎将她罩住:“沈**懂什么?我这靴子踏过的,是护着你们安稳赏花的疆土。”
“哦?”沈清辞仰头看他,嘴角勾起一抹淡笑,“那敢问将军,雁门关外冻死的流民,是不是也该谢你这双靴子护了他们的‘安稳’?”
这话戳中了萧策的痛处。他这次虽打了胜仗,却也因粮草不济,没能救下关外被困的百姓,正为此耿耿于怀。他脸色一沉,刚要反驳,却见沈清辞已站起身,福了福身:“失陪。”
她转身离去时,月白的裙摆扫过他的靴边,带起一阵极淡的玉兰香,竟让他到了嘴边的话,硬生生咽了回去。
廊外的雨又开始下了,淅淅沥沥打在芭蕉叶上。萧策望着沈清辞的背影消失在回廊尽头,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剑鞘上的红绸——这京城里的女子,原来比边关的蛮族还难对付。
他不知道,沈清辞回到内室后,对着铜镜抚了抚鬓角。镜中的自己,脸色虽平静,耳根却悄悄红了——方才离得太近,她竟闻到他身上淡淡的硝烟味,混着点阳光晒过的皂角香,说不出的……特别。
“**,怎么了?”侍女见她发愣,好奇地问。
沈清辞回过神,拿起桌上的狼毫:“没什么,练字吧。”
笔尖落在宣纸上,写的是《孙子兵法》里的句子。可写着写着,那笔画却渐渐歪了,竟有点像萧策方才踏在她裙摆上的泥印子。她皱着眉把纸揉了,心里暗骂一句“粗人”,却不知这“粗人”的影子,已悄悄落进了她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