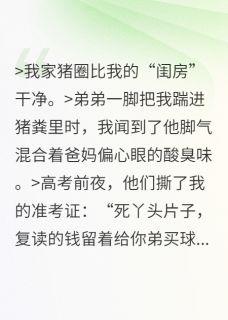>我家猪圈比我的“闺房”干净。>弟弟一脚把我踹进猪粪里时,
我闻到了他脚气混合着爸妈偏心眼的酸臭味。>高考前夜,
他们撕了我的准考证:“死丫头片子,复读的钱留着给你弟**鞋!”>我笑了,
钻进弥漫农药味的猪棚——那晚我觉醒了闻出病灶的能力。>复读费?我卖知了壳赚够了。
>录取通知书寄来那天,我故意念错弟弟的志愿代码。>“妈,
我闻到你子宫里长了三个瘤子。”>“爸,你肝上的囊肿快爆了吧?
”>看着他们惊慌失措的脸,我闻到了恐惧的甜香。我家那猪圈,比我的“闺房”还讲究点。
至少猪粪是新鲜的,不像我屋里,霉味和灰尘搅和在一起,吸一口都剌嗓子。“滚开!
挡老子路了!”苏天宝,我那个被爹妈捧上天的宝贝弟弟,
穿着新买的、能闪瞎人眼的耐克鞋,一脚踹在我腰眼上。我像个破麻袋,噗嗤一声,
结结实实栽进猪圈刚清理出来还没来得及运走的粪堆里。温热,粘稠,
一股子发酵过头的酸腐味儿猛地糊了我一脸。我挣扎着抬起头,猪粪糊住了眼睛,
黏在头发上,滴滴答答往下淌。透过模糊的视线,我看见苏天宝叉着腰站在圈外头,
一脸得意地笑。那崭新的球鞋,鞋底还沾着点我家猪的“馈赠”。
就在那股恶臭直冲天灵盖的时候,另一股更刁钻的味道,像根生锈的针,
猛地扎进了我鼻腔深处。又酸又馊,还带着点腐烂海鲜的腥气,
顽固地盘踞在苏天宝那双崭新的耐克鞋里,
和他身上那股被宠坏的、理所当然的傲慢味儿搅和在一起。这是我亲弟弟的脚气。
混合着我爸妈几十年如一日,只偏向他一个人的心肠里沤出来的那股酸腐气。**绝配。
我撑着黏糊糊的粪水想爬起来,手心按下去,滑腻腻的。
我妈张翠花那张刻薄的脸出现在猪圈矮墙上方,撇着嘴,眼皮耷拉着,
像看一堆垃圾:“嚎什么嚎?弄点粪就哭爹喊娘!赶紧滚出来,把猪喂了!
天宝晚上要吃排骨,别磨蹭!”她眼神扫过我沾满粪污的破旧T恤,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
仿佛那粪不是她儿子踹我进去沾上的,而是我自己跳进去打滚弄脏的。她扭身就走,
肥硕的**一扭一扭,空气里只留下她身上劣质雪花膏的香精味,
还有一句轻飘飘的嫌弃:“啧,脏死了。”我扶着湿滑的土墙,指甲缝里塞满了黑泥和粪渣。
那股脚气混合着偏心眼的酸臭味,还在我鼻子里打转,像根烧红的铁丝,烫得我脑子嗡嗡响。
行,苏穗,你记住了。这味儿,刻骨铭心。高考前一天,空气闷得能拧出水。
我把自己关在那间弥漫着灰尘和霉味的小隔间里,手指死死攥着那张薄薄的准考证。
油墨印着我的名字,苏穗,那是我唯一能抓住的、逃离这个家的绳索,勒得我指节发白。
我把它按在胸口,隔着薄薄的旧汗衫,能感觉到自己心脏跳得像要撞碎骨头。一遍,又一遍,
默背着那些公式、单词,每一个音节都带着血腥味,
那是我用无数个在猪圈旁借着微弱灯光啃书的夜晚熬出来的。门板被“砰”一声撞开,
劣质三合板震得掉灰。我爸苏大强那张被劣质白酒泡得浮肿发红的脸探进来,
满嘴酒气像一盆馊水泼了我一脸。他身后跟着我妈张翠花,
还有那个吊儿郎当、嚼着口香糖的苏天宝。“死丫头片子,躲这儿装什么蒜?
”苏大强舌头都大了,摇摇晃晃地朝我逼过来,眼睛浑浊地扫过我手里的准考证,
像是看到了什么脏东西,满是厌恶。我下意识地把准考证往身后藏,
脊梁骨紧紧抵住冰冷的土墙,墙皮的碎屑簌簌地往下掉。“藏?藏个屁!
”张翠花尖利的声音刺破空气,她肥胖的身子灵活地挤开苏大强,
那只粗壮、沾着油污的手像老鹰抓小鸡一样,带着一股子葱蒜味和常年不散的灶台烟火气,
精准无比地攫住了我的手腕。指甲深深掐进我的皮肉里,疼得我倒抽冷气。“拿来吧你!
”她猛地一拽,力气大得惊人。我整个人被扯得向前踉跄,手里的准考证瞬间被夺走。“妈!
还给我!那是我的高考证!”我的声音都变了调,带着哭腔和绝望的嘶哑。我扑过去想抢,
苏天宝却嬉皮笑脸地挡在了前面,用他那比我壮实一圈的身体轻松地把我撞开。
我跌坐在冰冷坚硬的地上,尾椎骨传来一阵钝痛。“你的?”张翠花捏着那张薄薄的纸片,
三角眼里全是鄙夷和不耐烦,嘴角向下撇着,法令纹深得像刀刻,“考考考,就知道考!
考上了又咋地?复读不要钱啊?死丫头,心比天高!”她唾沫星子喷到我脸上,
“那钱留着给你弟买双新球鞋多实在!他那双耐克都穿旧了!”“就是!
”苏天宝在旁边帮腔,得意地晃了晃脚上那双据说值好几百块的鞋,
鞋帮上还沾着昨天踹我时留下的、已经干涸发黑的猪粪印子,“姐,你一个女的,
读那么多书有啥用?早点出去打工给我攒钱娶媳妇儿才是正经!”张翠花不再看我,
那双粗糙的手捏着我的准考证,就像捏着一张废纸。她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只有一种卸下包袱般的轻松。刺啦——纸片撕裂的声音,在死寂的小隔间里炸开,
比打雷还响。一下。刺啦——两下。刺啦——三下。她动作麻利,
带着一种家常便饭般的熟练,
几下就把那张承载了我所有希望和汗水的纸片撕成了指甲盖大小的碎片。然后,她手一扬。
无数白色的小纸片,像一场冰冷的、绝望的雪,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落在我汗湿的头发上,
落在我因惊愕而大睁的眼睛上,落在我沾满灰尘和猪圈气息的破旧衣服上,
落在我冰冷的手背上,最后,无声地覆盖了肮脏的地面。世界一片死寂。
只剩下我粗重的喘息,和苏天宝得意又刺耳的笑声。我瘫坐在地上,背靠着冰冷的土墙。
那些碎纸片像冰冷的雪花,粘在脸上、头发上、衣服上。
苏天宝刺耳的笑声和张翠花刻薄的数落声嗡嗡地响,像一群讨厌的苍蝇在耳边盘旋,
又渐渐模糊、远去。我看着地上那些刺眼的白。每一片,都像一把钝刀,
在割我早就麻木的心。疼吗?好像也没那么疼了。就是空,空得像个被掏穿了的破口袋,
冷风呼呼地往里灌。我甚至扯了扯嘴角。大概是想笑?结果牵动了脸上的肌肉,比哭还难看。
“笑?你还有脸笑?”张翠花叉着腰,唾沫星子喷到我脸上,“赶紧滚去猪圈!
那几头猪饿得嗷嗷叫,你想饿死它们啊?明天不许去考试!听见没?敢去,腿给你打断!
”她骂骂咧咧地推搡着还在傻乐的苏天宝往外走,苏大强打了个响亮的酒嗝,
摇摇晃晃地跟上。门板被重重地甩上,劣质合页发出不堪重负的**,
震得墙皮又掉下来几块。隔间里彻底黑了,只剩下我粗重的呼吸声。
地上的碎纸片在门缝透进来的最后一点微光里,白得瘆人。我撑着冰冷的地面站起来,
两条腿软得像面条。没哭,一滴眼泪都挤不出来。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破门,
外面天也快黑透了。院子里空荡荡的,堂屋的灯亮了,传来苏天宝嚷嚷着要看动画片的声音,
还有张翠花哄宝贝儿子的、刻意放软的语调。那声音像针,细细密密地扎着我。我像个影子,
悄无声息地飘过院子。猪圈在院子最西头,紧挨着臭气熏天的旱厕。
那股混合着粪便、泔水、猪身上热烘烘腥臊气的味道,平时闻着只想吐,
今天却像某种诡异的召唤。我拉开那扇摇摇欲坠、用几块破木板钉成的圈门。
几只半大的猪哼哼唧唧地凑过来,湿漉漉的鼻子拱着食槽。圈里刚清理过,
地上铺了层新垫的干土,但那股浓烈的味道依然无孔不入。角落里,
放着半瓶兑了水的猪饲料,旁边还有个空了的棕色农药瓶,盖子丢在一旁。
下午张翠花给猪栏边驱虫喷药用的,刺鼻的农药味还没散尽,混在猪圈固有的臭味里,
形成一种令人头晕目眩、喉咙发紧的混合毒气。我走过去,靠着那半人高的矮墙,
滑坐到地上。背脊贴着粗糙冰冷的土坯墙,新垫的干土沾了一裤子。那浓得化不开的臭味,
混着农药残留的刺鼻辛辣,像无数只小虫子,疯狂地往我鼻腔里钻,往我脑子里钻。
胃里一阵翻江倒海,我猛地弯腰干呕起来,喉咙里火烧火燎。呕了半天,只吐出一点酸水,
灼烧着食道。眼前阵阵发黑,耳朵里嗡嗡作响,全是杂音。苏天宝的嘲笑,张翠花的辱骂,
苏大强的酒嗝,
有那刺耳的、准考证被撕碎的“刺啦”声……无数声音碎片在脑子里高速旋转、碰撞、炸开。
“呕——”又是一阵剧烈的反胃。这一次,不仅仅是生理上的恶心。
一股冰冷、粘稠、仿佛来自深渊的绝望感,混杂着那令人窒息的恶臭和农药味,
狠狠地攫住了我。意识像断了线的风筝,飘飘忽忽地往下坠。黑暗彻底吞噬我之前,
我好像看到角落里那只空的农药瓶,瓶口残留的一点褐色液体,在昏暗的光线下,
泛着诡异的光。不知过了多久,也许只是一瞬,也许是漫长的一个世纪。我猛地睁开眼睛。
猪圈里一片漆黑,只有猪偶尔发出的哼唧声和粗重的呼吸。但我眼前的世界,却彻底变了样。
不是视觉上的变化,而是……气味。无数种气味,以前被我忽略的,
或者根本无法感知的气味,如同潮水般汹涌地灌入我的鼻腔。
每一丝气味都带着清晰的棱角和色彩,浓烈得近乎实质。
汗腺味、排泄物的腐败酸气、饲料的谷物霉味、泥土的土腥气……这些混杂的臭气依旧存在,
但此刻,它们被一层层剥开、解析。我甚至能清晰地“闻”到身下干土里残留的农药分子,
那是一种冰冷的、带着死亡气息的甜腻腥气,像无数细小的毒针,扎着我的嗅觉神经。
最强烈的,是离我最近的那头半大黑猪。它身上散发出一股浓烈的、带着腥甜的铁锈味,
源头在它的腹部深处。这味道让我太阳穴突突直跳,本能地感到危险和不适。
还有我自己的衣服,沾满了猪粪和呕吐物的酸馊味,
皮肤上还残留着被苏天宝踹倒时沾上的……一股微弱的、腐败的甜腥气?来自他的脚?
脑子里像被塞进了一整本气味百科全书,每一个信息都在疯狂冲击我的认知。
我惊恐地张大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这是……怎么回事?那农药……把我脑子熏坏了?
还是……我真的要疯了?就在这时,圈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一条缝。
一束手电筒的光柱胡乱地扫了进来,伴随着张翠花不耐烦的吼叫:“死在里面了?
猪饿得拱墙了听不见?赶紧滚出来弄点吃的!别磨磨蹭蹭装死!”光柱晃过我的脸。
那一瞬间,借着那束刺眼的光,我清晰地“闻”到张翠花身上传来的味道。
除了她惯有的劣质雪花膏、厨房油烟和汗味之外,一股极其隐晦、带着点腐烂甜腥的浊气,
正从她的小腹深处幽幽地散发出来,像阴暗角落里滋生的霉菌。我猛地打了个寒颤。
那不是普通的体味。那股腐烂的甜腥……像极了刚才那头病猪腹部的铁锈味,只是位置不同。
手电光移开,张翠花骂骂咧咧地走了。我瘫在黑暗里,心脏狂跳,几乎要撞碎胸腔。
鼻子里充斥着各种复杂到令人眩晕的气味信息,一个荒诞又可怕的念头,像冰冷的毒蛇,
缠住了我的心脏。我好像……能闻出“病”的味道了?高考考场,我终究是没去成。
张翠花像是防贼一样盯着我,家里的锄头镰刀都被她收进了她和苏大强那屋,
连院门都从外面挂了把生锈的大锁。苏天宝那几天格外兴奋,像看管犯人一样在院子里晃悠,
时不时踹一脚猪圈门,吼一句:“姐,死了没?没死吱个声啊!”我缩在猪圈旁边的草棚里,
那是我的“新房间”,四面漏风,地上铺了点干草。
张翠花扔进来两个硬得像石头的窝窝头和一罐子咸菜疙瘩,算是施舍。“吃吧,省着点!
复读的钱还没着落呢,就知道糟蹋粮食!”她隔着门缝,声音尖利。我抓起那冰冷的窝头,
指甲掐进粗糙的表面。窝头散发着一股陈年谷物的霉味,咸菜疙瘩是齁死人的盐味。但此刻,
我的鼻子捕捉到了更多。窝头深处,一丝极其微弱的、类似黄曲霉素的苦涩霉味;咸菜里,
除了过量的盐,还有一点点……腌制容器不干净带来的、类似阴沟水的腥气。
我面无表情地把窝头塞进嘴里,用尽力气撕咬、咀嚼。霉味和咸到发苦的味道充斥口腔。
每咽下一口,都像是在吞咽仇恨的砂石,磨得喉咙生疼。复读?指望他们?做梦。我需要钱。
立刻,马上。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何况是我这个猪圈里的“死丫头片子”。白天,
张翠花和苏大强下地,苏天宝也跑出去跟狐朋狗友鬼混。
家里只剩下我和那几头哼哼唧唧的猪。我像一具游魂,在破败的院子里转悠,
鼻子像最精密的雷达,疯狂地扫描着一切可能换钱的气味。墙角堆着的破烂?
散发着铁锈和灰尘的死气,废品站都不收。灶膛里没烧尽的柴火?只有呛人的烟味和灰烬味。
鸡窝?几只瘦骨嶙峋的老母鸡下的蛋,张翠花每天数得清清楚楚,少一个都能把我皮扒了。
气里充斥着各种味道:泥土的潮湿、草木的微腥、灶台残留的油烟、还有……一种极其微弱,
却异常清晰的“声音”。吱——吱——吱——是知了。夏日的背景音。但这声音传入我耳中,
却自动转化成了气味信息。不是知了本身的虫味,而是……它们褪下的壳。
那种空心的、轻飘飘的蝉蜕,
带着一种极其干燥、微带土腥、又有一点点类似陈旧纸张的独特气味。这味道很淡,
混杂在无数更浓烈的气味里,几乎难以分辨。但在我此刻异常敏锐的嗅觉下,
它像黑暗中的萤火虫,清晰地凸显出来。蝉蜕!中药店收这个!
我记得以前在镇上的中药铺子门口,看到过收购蝉蜕的小牌子!
一股微弱的电流瞬间窜过我的脊背。希望,像豆大的火苗,在无边的绝望黑暗里,
噗地一下点燃了。接下来的日子,我变成了一个真正的“野人”。天不亮,
趁着那一家三口还在死猪一样的鼾声中,我就悄无声息地翻出低矮的院墙(张翠花锁了门,
但墙矮得可怜)。像条灵敏的猎犬,一头扎进村子后山那片最茂密的树林。露水打湿了裤腿,
荆棘划破了手臂,我全然不顾。我的鼻子成了唯一的向导。那些极其微弱、干燥的蝉蜕气味,
如同黑夜里的星辰,清晰地指引着方向。树根旁,潮湿的落叶下,散发着浓郁的腐殖质气息。
但我的嗅觉穿透这层气味,精准地捕捉到下面那一点干燥的土腥和旧纸味——找到了!
一枚棕褐色、半透明的蝉蜕紧紧贴在树根上。粗糙的树干纹路里,细小的缝隙中,
也藏着这些小小的宝藏。我踮起脚,指甲小心翼翼地抠挖,像在挖掘价值连城的珍宝。
高处的树枝杈上,气味信号更强。我咬着牙,不顾树皮的粗糙磨破掌心,一点点爬上去。
汗水流进眼睛,**辣地疼。手指触碰到那轻飘飘的空壳,心里就踏实一分。每天,
我背着那个从垃圾堆里捡来的、破了好几个洞的化肥袋子出门。回来时,
袋子里装着满满的、干燥轻盈的蝉蜕。我把它们藏在我睡觉的草棚最深处,用干草仔细盖好。
袋子散发出的浓烈干燥土腥和虫壳气味,是我闻过最安心的味道。
张翠花偶尔狐疑地打量我:“死丫头,一天天野哪去了?身上脏得跟鬼一样!”她凑近一点,
想闻闻我身上有没有偷懒的“证据”。在她靠近的瞬间,
我鼻子里猛地冲进一股比前几天浓烈得多的腐烂甜腥气,源头直指她小腹。
这味道让我胃里一阵翻搅,差点当场呕出来。我强忍着,垂下眼,
声音低得像蚊子哼:“……割猪草。”“哼,算你识相!
”她大概觉得我这副鹌鹑样翻不出浪,扭着肥硕的腰走了,
留下那股令人作呕的腥甜味在空气里久久不散。蝉蜕积攒了小半袋。那天下午,
我背着那个破袋子,像个移动的垃圾堆,走了十几里坑洼不平的土路,
来到了镇上唯一的那家“回春堂”中药铺。药铺里弥漫着各种草药混合的浓郁苦香,
当归的土腥,黄连的极苦,甘草的微甜……无数种气味信息洪流般冲击着我的鼻腔,
让我一阵眩晕。柜台后面坐着个戴着老花镜的干瘦老头,正在慢悠悠地碾药。我鼓足勇气,
把破袋子小心翼翼地放在他面前高高的柜台上,
袋子散发出的浓烈土腥味立刻盖过了周围的药香。“老……老师傅,
”我的声音因为紧张而干涩发抖,“收……收蝉蜕吗?”老头抬起眼皮,
浑浊的老眼透过镜片扫了我一眼,又落在那脏兮兮的破袋子上,眉头皱起,满是嫌弃。
他没说话,拿起柜台上一根小木棍,有些粗鲁地拨拉开袋子口,往里瞅了瞅。“啧,
品相一般,沾的土太多。”他语气冷淡,带着城里人看乡下人的那种疏离,
“晒得也不够干透,摸着还有点潮气。”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汗水顺着额角往下流,
混着脸上的尘土,又痒又难受。我攥紧了拳头,指甲掐进掌心,
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不那么抖:“我……我弄得很干净了,都是好壳子……您,您看看,
能值多少?”老头用木棍扒拉了几下,又拈起一小撮凑到鼻尖闻了闻,
那动作带着明显的敷衍。他眉头依然皱着:“行吧,看在你个小姑娘跑一趟不容易。
一块五一斤,顶天了。”一块五一斤!我背上的汗水瞬间变得冰凉。我起早贪黑,
在树林里钻了那么多天,手上、胳膊上全是划痕,就值这点钱?这点钱,
连买本复习资料都不够!绝望像冰冷的潮水,瞬间淹没了我。鼻子发酸,视线模糊,
我死死咬着下唇,尝到了铁锈般的血腥味。不能哭,苏穗,不能在这哭!
就在我几乎要崩溃的时候,
一股极其强烈、带着辛辣苦涩和浓烈土腥气的味道猛地从柜台后面涌了过来。
这味道霸道无比,瞬间盖过了铺子里所有其他药味,甚至压过了我袋子里蝉蜕的土腥。
它像一根烧红的针,狠狠扎进我的鼻腔深处!味道的源头,
就在老头手里正拿着准备碾的那把深褐色、根须状的药材上!
“咳咳咳……”老头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脸憋得通红,手里的药材都差点掉地上。
他捂着胸口,咳得上气不接下气,浑浊的老眼里都咳出了泪花。“您……”我下意识地开口,
脑子里被那股霸道的药味和老头撕心裂肺的咳嗽声塞满,一个名字脱口而出,“……您这咳,
是不是喝多了川贝母?那东西劲儿太大了,您肺受不了的,像……像有把沙子在里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