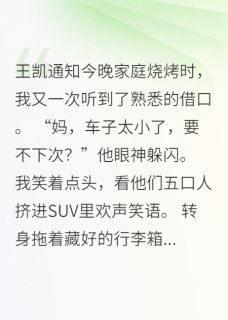王凯通知今晚家庭烧烤时,我又一次听到了熟悉的借口。“妈,车子太小了,要不下次?
”他眼神躲闪。我笑着点头,看他们五口人挤进SUV里欢声笑语。
转身拖着藏好的行李箱离开,身后是孙子的欢呼声。当晚孙子补课回来喊饿,
儿媳甩锅:“补习费都花完了哪有钱?”孙子熟练把手伸向我:“奶奶,五百块钱,
吃烧烤!”“奶奶一起去?”我试探问。他瞪眼:“你太老了,坐不下车!
”监控恰好录下儿子归来的暴怒:“老东西卷走了钱?”门外的我轻拉行李箱,
走进开满玫瑰的老年公寓电梯。那里有位烤鱼不放香菜的老邻居,正等我去海边。
王凯的电话打来时,我正把最后一件叠得整整齐齐的薄开衫放进半开的行李箱里。
手机在床头柜上嗡嗡震动,屏幕亮起“儿子”两个字。我看着那名字跳跃了几秒,
才吸了口气,按下了接听键。“喂,凯凯?”我的声音放得和往常一样温和。“妈,
”电话那头,王凯的声音带着点习惯性的、不容置疑的调子,“今晚家里聚餐,
我跟你弟媳周静、还有孙子孙女,大家一起去吃城西那家‘老地方烧烤’,
你也别费神做饭了。嗯……那个,”他顿了顿,像在组织语言,
又像只是单纯觉得空气有点稀薄,“我瞅着家里的SUV……五个人坐进去都够呛,地方小,
挤得很!要不…你歇着,等下次?”又来了。一模一样的台词。
只是对象从丈夫变成了孙子孙女。像一把用旧了的钝刀,每一次落下,
都在老地方留下更深的刻痕,反反复复地提醒我,那个“坐不下”的位置,
永远都留给我——王凯口中的“妈”,曾经也年轻过的秦慧芳。心脏某个地方猛地一缩,
又被一种奇异的冰冷麻木感覆盖过去。
我甚至能清晰地勾勒出他那张脸此刻的表情——不敢与我对视,视线必定是飘向车窗,
或者窗外任何一处没有我的地方。那眼神,
总是带着一种混合了推搪、一丝不自在和理所当然的东西。“哎,好,好。”我开口,
声音控制得极平稳,甚至还努力地扬起一丝我惯常能露出的那种包容笑意。
那笑意曾经是我在这个家安身立命的铠甲,温顺、安全、毫无威胁。“你们吃好,
玩高兴点就行。我自个儿弄点吃的,清静。”清静。这个词从舌尖滑过,
像一粒裹了苦胆的糖。电话那头似乎松了口气,
传来几声孩子(尤其是小孙子闹闹)兴奋的嚷叫:“噢!吃烧烤喽!吃烧烤喽!
”那欢快的童声像鞭子,隔着电波抽打在我心上。
王凯大概又嘱咐了句什么“自己注意身体”之类没滋没味的客套,便匆匆挂断了。
房间里霎时死寂。行李箱敞开着口,像无声的呼唤。窗外的暮色正缓缓流淌进来,
把房间染成一片昏黄。不到半个小时,楼下传来了车门开关的声音,
夹杂着小孩子更加清晰响亮的欢笑声,还有周静尖着嗓子的催促:“闹闹别蹦!赶紧上车!
萌萌跟上!”声音里满是计划达成、即将享乐的放松愉悦。我慢慢踱到窗边,
撩开纱帘一角向下望。
那辆黑色的七座SUV像一个镀了暮色的庞然大物(其实后面空着俩座位),
王凯正熟练地指挥着交通。儿子王凯动作麻利地拉开副驾驶门,
妻子周静抱着两岁的小萌萌费力地钻进后座中间的位置。十五岁的大孙女,王佳莹,
带着少年人特有的对集体活动那种微微的、但掩饰不住的兴奋感,一扭身也钻进了后座,
紧挨着她妈妈。最后是主角登场——十岁的宝贝孙子王闹闹,像个得胜的将军,
几乎是蹦跳着蹿进后座最后一个位置,车窗随即降下,露出他雀跃的胖脸。王凯绕到驾驶位,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抬头朝我窗户的方向瞥了一眼。我的手指猛地一紧,
纱帘被我攥出了深深的褶皱。那一瞬间,我怀疑他是否看见了隐藏在帘子后的、我的眼睛。
他的动作似乎迟疑了零点一秒,但那点不自然很快被拉开车门、坐进去的动作彻底抹掉。
引擎闷闷地吼叫一声,亮起尾灯,车子毫不拖沓地、稳稳当当地倒了出去,
汇入小区主干道的车流,消失在我视线之外,只留下淡淡的汽车尾气味道,
混杂着暮春傍晚花草的气息。直到再也看不到车尾灯,我还站在那里。
窗框边缘那冰冷的触感透过指尖传上来,凉意一路蔓延到心里。原来真正的告别,
有时候就是这么没有声音。没有想象中的质问和哭闹,连一个可以指责的背影都吝啬给予。
只有孩子们天真无邪的欢叫,像针,细细密密地扎在早已千疮百孔的心上。
他们不在乎奶奶为什么不去,只在乎自己要玩的开心。我成了理所当然被“优化”掉的部分,
成了一个模糊的背影。缓缓放下酸涩的手臂,转身走回卧室。
我走到墙边那张老旧的五斗橱前。橱顶玻璃下,压着一张微微泛黄的全家福。
照片上的阳光炽热得仿佛能灼烧指尖,刺得我眼睛微微眯起。那时丈夫王德海还在世不久,
被推着站在我身边的位置。他的手很自然地搭在我的肩头,笑容沉稳。
王凯那时还是个初入社会、锋芒毕露的青年,旁边刚进门的媳妇周静年轻美丽,
腼腆地偎着他。更小一些的闹闹才三岁,圆乎乎的脸蛋笑得像个福娃,
被我和老伴儿紧紧拥在怀里。每个人都沐浴在一片叫“未来”的光晕里,显得那样圆满,
找不到一点点裂痕。“德海,”我的指腹无意识地、细细地抚过照片上丈夫的脸,
声音轻得像怕惊扰了什么,“你倒是走了利索,一了百了。留我在这……”喉头骤然发堵,
后面的话咽了回去,化成一声沉重又滚烫的叹息。照片上他柔和的目光仿佛在说:忍忍吧,
家和万事兴。这句话是我大半辈子的圭臬。可到头来,家像个吸饱了水的海绵,
把我的付出、隐忍、存在感,都无声无息地吸干了。压着照片的玻璃框边缘有些割手,
就像这个家留给我的无形边缘。心口那种积压已久的沉坠感陡然变得清晰、冰冷而锐利。
够了。真的够了。我不想在生命最后的岁月里,
仅仅做一个会呼吸、会付账、却永远坐不下车的家具。血液里属于“秦慧芳”自己的东西,
被磨蚀了几十年后,终于挣扎着发出微弱却清晰的呐喊。
一股从未有过的决断力冲垮了那名为“忍耐”的堤坝。
个只存在于全家福里、需要时是点缀、不需要时就被“空间不足”的理由排除在外的影子了。
行李箱早已准备妥当。没什么好再犹豫和留恋的了。房间里最后一丝暮光也消隐无踪,
取而代之的是外面道路灯透进来的清冷光芒。我拉上箱子的拉链,
环视这个住了几十年的屋子,东西几乎没动——他们喜欢的就留下吧,
属于我的痕迹本就少得可怜。我拖着箱子,
金属轮子在客厅光洁的地板上发出沉闷而有节奏的滚动声,像是生命行进时低沉的鼓点。
每一步都沉重,却又奇异地带来一种挣脱淤泥般的轻松感。
钥匙被我轻轻放在鞋柜显眼的地方。开门,关门,落锁。没有回头。楼道里声控灯应声而亮,
冰冷的白光将我的身影投在墙壁上,拉得很长。
隐约还能听到小孙子闹闹兴奋地叫嚷“我要吃烤鸡翅”的声音透过那紧闭的门板钻出来,
微弱却刺耳。“再见了,”我在心里轻声说,“这个……家。”电梯门无声地滑开,
我拖着唯一的行李走了进去,感觉像是跨过了某个无形却坚实的门槛。
身后的门彻底隔绝了里面残余的属于“家”的烟火气和冰冷现实。
在电梯微微加速下降带来的轻微失重感中,我知道,
一段新的、或许孤独但至少不再被当作“空间不足”的累赘的日子,要开始了。那晚,
城市的霓虹刚刚亮起不久,带着夏日燥热喧闹的空气仿佛凝固在小区里每一家窗户上。
我回到那个熟悉的小区门口,但没有直接回家。我在对面的街心公园长椅上坐下,
身边挨着安静的行李箱。头顶树荫浓密,遮住了路灯的光,也把我藏进一片暧昧的阴影里。
目光却能清晰地投过去,落在我刚离开的那个家的楼下。没多久,单元门那边果然有了动静。
门被很用力地撞开,带出里面灯光和人声的碎片。“砰”的一声响在夜晚格外突兀。是闹闹!
他背着那个塞得鼓鼓囊囊的巨大书包,身影跟炮弹似的冲了出来,
像一头困兽刚刚挣脱了无形的栅栏。孙子王闹闹显然刚下补习班回来,书包还重重压在背上,
嘴里却已经响亮地嚷嚷开了,带着强烈的情绪:“饿死啦!我要吃烧烤!现在就要吃!
”他那带着哭腔的宣告在沉静的夜里传出很远,
路灯下他胖乎乎的脸蛋因为情绪激动而涨得通红。紧接着,
儿媳周静穿着宽松的居家服跟了出来,手里还拎着个不大的购物袋,显然是没准备让他如愿。
她一把扯住闹闹的手腕,声音带着被孩子闹腾出的火气和一种习惯性的推卸口吻:“吃吃吃!
你就知道吃!钱呢?你看看你这书包里装的都是补习班的账单!
家里那几个钱全给你塞进辅导老师口袋了,哪还有余钱给你去烧?烤?做梦!
”她故意把“烧”和“烤”两个字咬得特别重,
眼神还不忘往楼道的方向瞟了一眼——那是我平时常出现的地方。她的目光扫过来时,
我下意识地往树影里缩了缩。这动作几乎成了身体本能。闹闹捕捉到妈妈瞟过去的这一眼,
立刻像得到了某种指令,或者说,是找到了唯一可能通往烧烤的道路。他猛地转过头,
那双小眼睛像最灵敏的探测器,一下子精准地“定位”到了马路对面树影下坐着的我。
他完全无视了车流,以一种近乎蛮横的加速度朝我冲过来,
一把推开还在抓着他另一只手腕的妈妈,毫不犹豫地、直直地站到了我面前。
小小的、带着薄汗的、属于男孩的手掌啪地一声摊开在我眼皮底下。“奶奶!钱!快给我钱!
我要吃烧烤!给我五百块!”他命令道,声音又脆又急,没有丝毫的迂回和客气,
理直气壮得仿佛是拿回自己的东西。空气似乎都凝滞了。
我能感觉到身旁空气的温度骤然下降了几分。周静站在几步开外,抱着手臂,
脸上是一副“看吧,只能这样了”的表情,默许着,甚至带着点看好戏的悠闲。
远处传来的汽车喇叭声都显得遥远而不真实。我看着摊在眼前的这只小手,粉红,肉乎,
指甲缝甚至还有点没洗干净的铅笔灰。就是这样一双手,
不久前还在全家福里被我珍爱地捧着。我抬起眼,脸上的肌肉艰难地调动出一个僵硬的笑容,
像一张不熟悉的面具:“闹闹,什么……什么烧烤这么贵啊?要五百块?
”声音干涩得厉害,喉咙像被砂纸磨过。我试图从口袋里摸出我的老花镜盒,
仿佛这样能缓解这一刻的窒息。“哎呀奶奶你好烦!”王闹闹立刻不耐烦地跺了跺脚,
小眉头拧成结,嘴巴撅得老高。他飞快地开始掰着圆滚滚的手指头,
熟练地给我算起了我完全不在场的消费明细:“爸爸开车!要油钱!妈妈、我、妹妹!
还有爷爷!我们五个人!一个人最少一百!一百乘五等于五百!五百块刚刚好!懂了吗?
五百!快给我!”爷爷。他说爷爷也要喝酒。提到王德海,
那根冰冷的刺又扎进心里最柔软的地方。一股难以言喻的悲凉混着一点点被点燃的荒诞怒火,
沿着脊椎爬上来。也许是被这清晰的、把我排除在外的算术刺痛,
也许是最后一点点残存的侥幸心被逼到了墙角。我看着他亮闪闪的、只装着烧烤的眼睛,
终于听见自己的声音飘出来,带着一点微弱得近乎祈求的试探:“……那…那奶奶呢?
你们都去吃,奶奶…奶奶也想去……行不行?”那小心翼翼的语气,
连我自己都觉得陌生又卑微,像个等待审判结果的犯人。话一出口,
脸颊就不受控制地发起烧来。“奶奶,你怎么回事!”闹闹的声音猛地拔高,
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他翻了个巨大的白眼,声音里充满了理所当然的嫌弃和干脆利落的拒绝,
“你?你去什么去呀!你多大年纪了?烧烤那都是烟熏火燎的,呛死了!再说,
爸爸的车里哪儿还有地方坐你啊?坐不下!你去了根本挤都挤不进去!老实待家里吧啊!
”他小手一挥,似乎觉得已经跟我解释清楚了,那神态,
简直像在打发一个没眼力见儿想凑热闹的小孩。
他那双童稚的眼眸里没有丝毫对奶奶的温情体谅,只有纯粹的被阻拦的烦躁。烟熏火燎?
原来我身体不适的借口如此轻易地被堵回来。空间不够?又是这个理由,
像一个无法打破的咒语。连十岁的孩子都能如此熟练地运用这个理由来排除我了。
原来在所有人眼中——包括这个我曾把整颗心都掏给他的小孙子——我的存在感,
就只等于那辆车物理空间的“有”或“无”。胸口像被一块浸透了冰水的厚重棉絮死死堵住,
又冷又沉,压得我几乎喘不上气。指尖冰凉麻木,一直蔓延到四肢百骸。
最后一丝挣扎熄灭了,只剩下无边无际的灰烬在飘荡。
“原来……是这样……”我几乎是无声地嗫嚅着,每一个字都像是用尽了残存的力气,
刮擦着生痛的喉咙。我没再看那个摊开的手掌,
也没有去看儿媳周静脸上可能的任何表情——那一定充满了“早跟你说别问”的潜台词。
拖着笨重的行李箱,我不再说话,一步一步艰难地转过身。
箱子沉重的轮子在凹凸不平的花砖地面上碾过,
发出一种迟缓、费力、像是随时要卡住的拖沓声音。
身后儿媳周静终于有点不耐地提高声音问:“妈?闹闹的钱?”我依旧没有回头,
那个“五百”像一个可憎的魔咒。我只是举了一下手,手腕软弱无力地挥了挥,
示意他们自行处理,或者,让他们找别人要去吧。身后隐隐传来周静低声的抱怨,
“搞什么……”以及闹闹带着哭腔不依不饶的叫声,“我的烧烤!我要吃!奶奶!钱!!
”那声音越来越远,越来越模糊,最终被黑暗的树影和小区外模糊的车流声彻底吞没。
这黑暗的街景从未如此刻般陌生而充满拒绝。路灯的光芒像冰冷的探照灯,
在我拖着老弱身躯缓慢跋涉的影子上移动。肩胛骨的刺痛和膝盖熟悉的酸涩一齐涌上,
提醒着我的确不再年轻。原来人的心变老变硬,只差这样一个夜晚,
一顿永远坐在位置外的烧烤。家?那个亮着灯的方向,仿佛已是海市蜃楼,
触手可及却从未拥有。**在老年公寓电梯冰冷的轿厢壁上,看着数字一层层往上跳。
手机嗡嗡震动起来。是个陌生的座机号码,尾号带着一股莫名的熟悉感,
属于我刚刚逃离的那个小区物业。我迟疑了一下,按下接听键。“喂?是……秦慧芳女士吗?
”对方是个年轻男人,语气里有按捺不住的激动和一丝邀功的意味,“我是小赵啊,
物业监控室的小赵!您家王先生和王太太在家是吧?
哎哟他们刚回去没多久那个场面可就……您绝对猜不到!我们监控全拍下来了!
真叫一个精彩!您要过来看看不?”监控?拍下来了?我的神经猛地一紧,
某种冰冷的预感攫住了我。“我...不在家。”我的声音干涩异常。“没事没事!
”小赵在电话那头更兴奋了,“有密码授权也能远程看!我给您账号开权限!
您登‘安居眼’APP瞅瞅就知道了!啧啧,太有料了!王太太那脸色……哎哟!我不说了,
您快看!”挂了电话,冰冷的电梯“叮”一声,到了我租住的十八楼。门外走廊灯光柔和。
我拖着箱子,步履沉滞地走到新租下的1815号房门口,手抖得几乎插不准钥匙孔。
推开门,一股清新干燥带着一点点新家具气息扑面而来。但此刻我无心感知这新的安全壳,
几乎是扑到沙发前,用冰凉的手指慌乱地掏出手机,
下载、登录那个叫“安居眼”的监控APP。很快,
被切割成四个熟悉的画面:我家客厅、玄关、还有覆盖小区门口和楼下停车区域的户外探头。
APP发出嗡鸣,提示有新的事件录像。我颤抖着点开那条标记着“高动态”的视频片段。
时间戳回到约一个小时前。那辆黑色的SUV刺眼地停在我家单元门口的车位上。
王凯一家鱼贯下车。不同于出发时的兴致勃勃,此刻车厢里蔓延的是低沉的气压。
王凯率先摔上车门,后备箱自动弹开,周静和闹闹跟在后面,佳莹抱着睡熟的萌萌走在最后。
他们一路沉默着进入单元楼门禁。电梯上行。门开。视频切换到室内玄关视角。
王凯径直冲向鞋柜——那个他曾无数次打电话找不到钥匙时我都会提醒他放钥匙的位置。
他的目光凶狠地扫视着空空如也的柜面,随即像一头被激怒的棕熊,
猛地转向旁边的我原先的房间方向,拧开门把手大力推开!屋内空荡,
连一丝属于我的气息都像被风吹散了。视频只能听到他粗重的、难以置信的吸气声。“妈呢?
!”他暴吼出声,像一道撕裂空气的惊雷,震得整个楼道仿佛都晃了晃。
那声音里充满了失算的狂怒和瞬间爆发的惊愕,与平日客气的敷衍判若两人。
他猛地冲进客厅,目光像扫雷仪一样疯狂扫过每个角落。周静跟在后面,她似乎也愣住了,
手里还拿着萌萌的外套。闹闹似乎被爸爸的暴怒吓到,瑟缩了一下,
但立刻梗着脖子喊:“奶奶没给我烧烤钱!”下一秒,
王凯的身影带着一股毁灭性的狂暴旋风般从客厅冲出来。他冲到客厅电视柜前,
猛地拉开最下面一格的抽屉——那个只有我和已故的老伴知道暗格秘密的抽屉。他弯腰,
整个肩膀都在用力的颤抖。视频画质很好,清晰地捕捉到他侧脸上瞬间凝固的表情,
然后就是血管暴跳的额头和脖子上贲张的青筋。“啪!”一声巨响。
他用拳头狠狠砸在抽屉隔板上,整个手都在剧烈的颤抖,
那是一种无法抑制的愤怒和失算的惊惧混合的生理反应。他抬起头,转向周静,
那双眼睛里布满赤红的血丝,声音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每一个字都带着尖锐的回响:“钱!
老东西……她把柜子底下的钱卷走了!”他的声音因为剧烈起伏的情绪而扭曲着,
像一只咆哮的困兽,充满了被狠狠戳破伪装的暴戾和一丝掩盖不住的恐慌。监控无声,
但那“卷走”两个字,如同淬了毒的冰锥,刺穿屏幕,直直扎进我的心窝。
视频画面微微晃动,大概是王凯愤怒之下移动撞到了什么。旁边屏幕一角的闹闹吓呆了,
瞪圆了眼睛,嘴巴张得能塞进一个鸡蛋。视频画面边缘,一直安静跟着的周静终于有了反应。
她的脸骤然间失去所有血色,像刷了一层白灰。她像被什么东西重重击中身体,
猛地踉跄一步,后背“砰”地撞在鞋柜的门板上,发出沉闷的回响。紧接着,
她的手下意识地捂住了自己的心口位置,大口喘着气,身体顺着柜门向下滑,
瘫坐在冰冷的地板上,两眼茫然地瞪着天花板空洞洞的灯。
那张曾刻薄的脸此刻只剩下最原始的、巨大的惊慌和空洞,仿佛赖以生存的基础被瞬间抽空。
钱……那被她视为囊中物的、能用来解决一切问题的钱……没有了!画面剧烈地晃动了一下,
似乎是王凯暴躁地在客厅里踱步,不小心撞到了放置摄像头的架子。旋即视频戛然而止,
最后定格的,是王凯狂躁而茫然的背影,以及瘫坐在鞋柜旁像一滩软泥的周静。屏幕黑了。
手机从我陡然脱力的手中滑落,跌进软软的沙发里,发出一声轻微的闷响。
身体里所有的力气,连同最后的暖意,都在刹那间被彻底抽干。我颓然地向后靠去,
脊梁硌在沙发并不柔软的靠背上,冰凉的触感清晰无比。卷走钱?那柜子底下压着的三万块,
是我省吃俭用几十年为老伴准备的养老金,他没能花完,弥留之际拉着我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