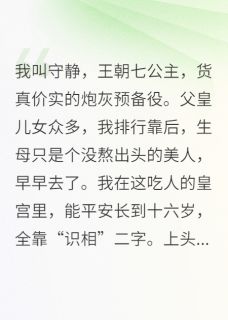络腮胡狐疑地盯着我,又看看地上盖着破床单、一动不动只偶尔痛苦**两声的男人(谢天谢地他还知道配合哼哼),眉头紧锁。
旁边一个年轻点的兵丁小声嘀咕:“头儿,看着像是摔的,味儿挺冲……”
络腮胡没说话,目光像探照灯一样在我脸上和院子里来回扫射。那审视的目光,几乎要把我看穿。
时间仿佛凝固了。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我低着头,死死掐着自己的手心,用疼痛维持着表面的镇定和凄苦。
终于,络腮胡的目光落回我脸上,带着审视和警告:“逃荒来的?户籍呢?”
我心里咯噔一下。户籍?这玩意儿我怎么可能有!我连身份都是假的!
“官爷……”我声音抖得更厉害了,带着绝望,“我们……我们是从北边遭了灾逃过来的,路上……路上遇到流匪,包袱都被抢了,户籍……户籍文书也丢了……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个没人住的破院子落脚……求官爷开恩!”我膝盖一软,作势就要跪下。
络腮胡不耐烦地挥挥手,像是嫌弃我哭哭啼啼:“行了行了!没户籍就是流民!按律要抓去服劳役的!”他话锋一转,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贪婪,“不过嘛……看你男人伤成这样,也干不了活。算你们运气好!最近镇上不太平,有逃犯流窜,你们关好门户,别乱跑!听到什么动静,立刻报官!知道吗?”
“是是是!谢谢官爷!谢谢官爷开恩!”我忙不迭地点头哈腰,一副感恩戴德的模样。
络腮胡又扫了一眼死气沉沉的小院和“重伤”的男人,大概是觉得实在榨不出什么油水,也懒得再纠缠,大手一挥:“走!去下一家!”
三个兵丁转身,骂骂咧咧地走远了。
直到他们的脚步声彻底消失在巷子口,我才像被抽干了所有力气,双腿一软,靠着门框滑坐到地上,后背的冷汗已经浸透了衣衫。
好险……暂时混过去了。
我喘着粗气,心有余悸地看向院子里。
那个叫“拾安”的男人,不知何时睁开了眼睛。虽然眼神依旧虚弱涣散,但比刚才清明了一些。他正定定地看着我,眼神复杂,带着探究和一丝难以言喻的……茫然?
“你……”我张了张嘴,劫后余生的虚脱感和对这个麻烦来源的怨气交织在一起,一时竟不知该说什么。
他挣扎着想坐起来,牵扯到伤口,痛得闷哼一声,额头上瞬间渗出冷汗。
“别动!”我下意识地喊出声,语气带着点命令。随即又觉得不妥,放软了声音,“你……你伤得很重,乱动伤口会裂开。”
他果然不动了,只是那双深不见底的眼睛,依旧一瞬不瞬地看着我,声音嘶哑地问:
“……拾安?我……叫拾安?”
得,这位爷,好像真把脑子摔坏了?还是失血过多迷糊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失忆?这戏码也太老套了吧?可看他那茫然的眼神,又不像是装的。
我看着他身上还在缓慢洇血的伤口,叹了口气。不管他是真失忆还是假失忆,眼下这烂摊子,我是甩不掉了。
把他丢出去?且不说外面风声紧,巡查兵刚走,随时可能回头。就凭他这一身伤和浓重的血腥味,丢出去就是个死。死在我门口,或者被巡查兵发现盘问,我绝对脱不了干系。
收留他?养个来历不明、身受重伤、还可能失忆的男人?这简直是给自己埋了个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炸的雷!
我烦躁地抓了抓头发。
目光扫过他苍白的脸,干裂的嘴唇,还有那身被血污浸透的破烂衣服。
算了。
炮灰公主也有炮灰公主的底线。见死不救,我守静还做不出来。
先救人吧。就当……就当是捡了个麻烦的工具人!等他伤好了,能走动了,立刻让他滚蛋!
我认命地站起身,走到他身边,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点:“你叫拾安。我叫守静。暂时……你是我男人。记住了。”
他看着我,眼神依旧茫然,但似乎努力理解着我的话,半晌,才低低地“嗯”了一声,算是回应。
“能起来吗?地上凉。”我问。
他尝试着动了动,眉头紧锁,显然极其费力。
我无奈,只好弯腰,抓住他没受伤的那边胳膊,用尽吃奶的力气,试图把他架起来。他也很配合,咬着牙,用没受伤的腿支撑着,几乎是半靠在我身上,踉踉跄跄地往堂屋里挪。
短短的几步路,走得异常艰难。他大半个身子的重量都压在我瘦小的肩膀上,压得我龇牙咧嘴,汗水瞬间冒了出来。浓烈的血腥味和男人身上特有的汗味混合在一起,直冲鼻腔。
好不容易把他弄到堂屋角落那张我刚收拾干净、铺了点干草的破板床上,我累得差点虚脱,扶着墙直喘粗气。
拾安靠在冰冷的土墙上,脸色惨白如纸,冷汗淋漓,嘴唇都失了血色,显然刚才那几步耗尽了他仅存的力气。他闭着眼,胸膛微弱地起伏着。
不能让他死在这!
我打起精神,跑去厨房烧热水。水开了,舀到木盆里,又翻出我仅有的、还算干净的两块旧布(其中一块是我的洗脸巾),端着盆回到堂屋。
“忍着点,伤口得清理。”我对他说道,语气尽量放平缓。
他睁开眼,看了我一眼,没说话,只是微微点了点头,眼神里带着一种近乎麻木的平静。
我深吸一口气,小心翼翼地掀开盖在他身上的破床单,然后去解他染血的衣襟。
衣服黏在伤口上,稍微一动,他就疼得浑身肌肉紧绷,牙关紧咬,发出压抑的抽气声。
左肩的伤口很深,像是被什么利器刺穿,边缘有些红肿外翻,还在缓慢地渗着暗红色的血水。右腿的伤在靠近大腿外侧,是一道长长的撕裂伤,皮开肉绽,看着就疼。身上还有不少细碎的擦伤和淤青。
这绝对不是简单的“砍柴摔伤”!更像是……经历过激烈的搏斗或者追杀!
我心里警铃大作,但手上动作没停。用温热的布巾,沾着热水,一点一点,极其小心地擦拭伤口周围的血污和泥土。每一次触碰,都能感觉到他身体的瞬间僵硬。
没有药,我只能尽量把伤口清理干净。又撕下另一块相对干净的布条(我的擦脚布……算了,顾不上了),用热水烫过拧干,笨拙地给他包扎了一下,至少能止止血。
做完这一切,我累得腰都快直不起来了。盆里的水已经变成了浑浊的暗红色。
拾安靠在墙上,闭着眼,呼吸似乎平稳了一些,但脸色依旧难看。
“饿吗?”我问。
他缓缓摇头,声音嘶哑:“……水。”
我赶紧去倒了碗温水,扶着他的头,小心翼翼地喂他喝了几口。
看着他虚弱的样子,我一阵头疼。家里那点糙米,我自己都吃不饱,现在又多了一张嘴,还是个重伤号……这日子,真是雪上加霜。
接下来的日子,我陷入了水深火热。
“桥头代写摊”是彻底不敢去了。外面风声紧,巡查兵时不时就在街上晃悠,盘问生面孔。我这张脸,虽然比画像上憔悴粗糙了不少,但难保不会被有心人认出来。
收入来源断了。
更要命的是,家里多了个嗷嗷待哺(主要是需要汤药)的重伤号。
拾安的情况时好时坏。高烧反反复复,伤口也时有红肿。人大部分时间都昏昏沉沉的,偶尔清醒,眼神也是茫然的,除了知道自己叫“拾安”,是我“男人”,其他一概不知,像个懵懂无知的大号婴儿。
我每天的主要工作,变成了:
天不亮就起床,去河边最僻静的地方洗沾了血污的布条(晾晒都得偷偷摸摸,生怕被人看见)。
去镇外野地里挖点能认得的、据说有点消炎作用的野菜(比如蒲公英、马齿苋)。
把家里仅存的那点糙米,熬成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米汤,自己喝米汤,把稠一点的米粒捞给他补充体力。
用捣碎的野菜敷在他的伤口上(死马当活马医)。
定时给他喂水,擦洗降温(主要是物理降温,没药)。
晚上还得提心吊胆,听着外面的动静,生怕巡查兵再来,或者这个失忆的麻烦精半夜断气。
几天下来,我眼窝深陷,瘦得脱了形,比刚逃到临水镇时还要狼狈。
唯一值得“欣慰”的是,拾安虽然失忆又重伤,但求生欲似乎很强,很配合。喂他吃就张嘴,喂他水就喝,给他清理伤口也咬牙忍着,不喊不叫。清醒的时候,就用那双深不见底、带着茫然和一丝不易察觉探究的眼睛看着我忙忙碌碌,偶尔会低低地说一句:“……谢谢。”
谢个屁!我在心里腹诽。要不是你,我能这么惨?
这天下午,我又在院子里,对着那小块菜地发愁。刚冒头的几颗小青菜蔫头耷脑的,家里最后一把糙米也见底了。拾安的高烧还没退干净,伤口依旧红肿。
山穷水尽。
难道……真的要用金叶子了吗?那是娘亲留给我最后的保命钱,用了,就真的什么都没了。
就在我内心天人交战,无比挣扎的时候,院门被轻轻敲响了。
“叩、叩叩。”
声音很轻,带着点试探。
我吓得一个激灵,汗毛倒竖!抄起墙角的扫帚,紧张地盯着院门:“谁?!”
“守静姑娘?是我,跳跳。”
一个刻意压低的、带着点怯意的熟悉声音传来。
跳跳?!我那个在“送亲”路上,被我假死抛下的贴身宫女?!
她怎么会找到这里?!难道……她是来抓我的?!
巨大的惊恐瞬间攫住了我!我握紧了扫帚柄,指节发白,声音都变调了:“你……你怎么找到这里的?你想干什么?”
“姑娘!姑娘你别怕!”门外的跳跳声音带着哭腔,“我不是来抓你的!我……我是逃出来的!我找到这儿不容易,你先开门让我进去,外面……外面有人在找我!”
逃出来的?被人找?
我将信将疑,但听她声音里的恐惧不似作伪。犹豫再三,我咬了咬牙,慢慢拉开了院门。
门外站着的果然是跳跳。
她比分开时更瘦了,穿着一身半旧不新的粗布衣裳,头发简单地挽着,脸上带着长途跋涉的疲惫和惊惶,怀里紧紧抱着一个鼓鼓囊囊的蓝布包袱。
看到我,她眼圈一红,眼泪刷地就下来了:“姑娘!真的是你!你还活着!太好了!”她下意识地想扑过来,但看到我警惕的眼神和手里的扫帚,又生生顿住脚步。
“你……”我依旧不敢放松,“你怎么找到我的?谁在找你?”
“姑娘,说来话长!”跳跳急切地回头看了看巷子口,压低声音,“那天你……你‘走’了之后,队伍乱成一团。礼部侍郎怕担责,就按你说的,把你……把你‘安葬’了,然后派人快马加鞭回京报丧。后来……后来听说狄戎那边发现公主是假的,大怒,要兴师问罪。朝廷为了平息事端,就把所有责任都推给了死人……就是姑娘你!说你是偷了宫中重宝逃走的‘逃奴’,下了海捕文书……”
这些我都猜到了。
“那你怎么……”
“我是姑娘的贴身宫女啊!”跳跳眼泪掉得更凶,“队伍回京后,我就被关起来审问,问我知不知道姑娘的计划,是不是同伙……我被打怕了,只能一口咬定什么都不知道。后来……后来宫里说要把我发配到北边最苦的浣衣局去,我知道去了就是死……就……就趁押送的人不注意,跳了河……”
我心口一紧:“你……”
“我命大,没死成,被下游的渔民救了。”跳跳抹了把泪,“我养好伤,不敢回京,也不敢回家乡,怕连累家人。我……我就想着,姑娘你以前说过,你娘亲在江南好像有个小院子……我就一路打听,一路往这边走。路上听说这边贴了告示抓‘逃奴’,画像像姑娘,又听说这临水镇西头河边新搬来个年轻女子……我就猜可能是姑娘!刚才在巷子口,好像看到有官差在盘问路人,我怕被认出来……姑娘,让我进去吧!求你了!”
她说的情真意切,逻辑也通顺。看着她风尘仆仆、惊惶无助的样子,我终究还是心软了。
她是我在宫里唯一一个勉强算得上亲近的人。当年我娘还在时,她就在我身边伺候,虽然胆小怕事,但心肠不坏。她若真想出卖我领赏,大可不必冒险自己找来。
我侧开身:“进来吧,快!”
跳跳如蒙大赦,赶紧闪身进来,我立刻关上门,落了栓。
她进了院子,一眼就看到堂屋门口破板床上躺着的拾安,惊得瞪大了眼睛:“姑……姑娘!这……这是谁?”她看看拾安,又看看我,眼神里充满了难以置信的震惊和一丝……古怪的猜测?
我脸一热,赶紧解释:“别瞎想!他是我……捡的!受了重伤,失忆了!暂时……暂时对外说是我男人,叫拾安!为了应付巡查!”
跳跳张着嘴,半天没合拢,显然被我这个“捡男人”的操作惊呆了。
“行了行了!别愣着了!”我打断她的震惊,“你说有人找你?怎么回事?”
跳跳回过神来,脸色又白了:“是……是宫里派出来追捕‘逃奴同党’的人!我跳河跑了以后,他们一直在找我!我路上好几次差点被他们抓住!刚才在镇口,我好像看到他们的身影了,所以才……”
追兵!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我自己的麻烦还没解决,跳跳又带来了新的追兵!
我眼前一黑,感觉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
“姑娘,我……我是不是给你惹麻烦了?”跳跳看着我难看的脸色,怯生生地问,抱着包袱的手指都捏得发白,“我……我带了点东西……”她说着,赶紧把怀里的蓝布包袱打开。
里面有几件半新的女子衣裳(应该是她自己的),一小袋大概两斤重的糙米,一小罐盐,还有……一个沉甸甸、用油纸包了好几层的小包。
跳跳小心翼翼地解开油纸包。
里面赫然是几块切割整齐、黄澄澄的金锭!还有一小把碎银子!
“这……”我倒吸一口凉气!
“是姑娘的!”跳跳压低声音,飞快地说,“那天姑娘‘走’后,队伍乱糟糟的,没人顾得上清点你的嫁妆箱子。我……我偷偷把箱子底暗格里,娘娘留给你的那些金叶子……还有几件值钱但不起眼的首饰……都拿出来了!路上变卖了一些换了盘缠,剩下的都在这里!我想着……万一姑娘真……真需要呢?”
我看着那黄澄澄的金子,再看看跳跳那张带着后怕却又透着点小聪明的脸,一时间百感交集。
娘亲留给我保命的金叶子,兜兜转转,竟然以这种方式,又回到了我身边!还是这个我一直以为胆小怕事的小宫女,冒着天大的风险替我保存下来的!
“跳跳……”我嗓子有点堵,鼻子发酸。
“姑娘,你别哭!”跳跳慌了,手忙脚乱地把金子包好,塞到我手里,“现在不是哭的时候!金子你收好!外面追兵在找我,肯定也会找到这镇上来!我们……我们该怎么办啊?”
怎么办?
我看着手里的金子,又看看床上昏迷不醒的麻烦精拾安,再看看眼前这个忠心耿耿却又带来新麻烦的跳跳。
一个大胆到近乎疯狂的念头,在我绝望的脑海里,如同野草般疯长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