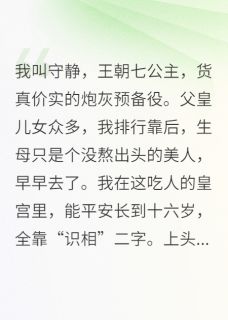光躲,是没用的!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五十两白银的悬赏,
足以让这小镇上的每一个人都变成潜在的敌人!必须主动出击!我猛地攥紧了手里的金锭,
坚硬的棱角硌得掌心生疼,却带来一种奇异的、破釜沉舟的力量感。“跳跳,”我抬起头,
眼神是从未有过的锐利和决绝,“你会演戏吗?”跳跳茫然:“啊?演戏?”“对!
演一场大戏!”我咬着牙,一字一句地说道,“演一场‘情深义重、不离不弃’的大戏!
”我指着床上昏睡的拾安:“他,是我们这场戏的男主角,我的‘好夫君’,重伤垂危,
需要救命!你,是我的‘好姐妹’,千里迢迢来投奔我!而我——”我深吸一口气,
斩钉截铁:“是一个为了救夫君,愿意散尽家财、砸锅卖铁的痴情妻子!”跳跳目瞪口呆,
显然被我这个大胆的计划惊呆了。“姑……姑娘,这……这能行吗?”“不行也得行!
”我眼神发狠,“这是唯一的活路!外面的人都在找‘逃奴’和‘同党’,我们越躲,
越可疑!反而把自己摆在明面上,演一出苦情戏,
把自己变成这镇上人人都知道、人人都可能‘同情’的可怜虫!追兵反而不敢轻易动我们!
至少,不敢明目张胆地动!”这叫反其道而行之!这叫灯下黑!跳跳似懂非懂,
但看我神色坚决,用力点了点头:“姑娘,我听你的!你说怎么演,我就怎么演!”“好!
”我立刻开始部署,“首先,立刻去请郎中!用银子!请镇上最好的郎中!
动静闹得越大越好!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为了救‘夫君’,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
”“其次,跳跳,你去镇上布庄,扯几尺素色的粗麻布回来,要快!再买点便宜的香烛纸钱。
”跳跳更懵了:“姑娘,买这些……做什么?”我冷笑一声,眼神瞥向拾安:“给他预备着!
对外就说,郎中说……我夫君伤得太重,怕是……熬不过今晚了!”苦肉计,
要演就演**!只有“将死之人”,才能最大程度地博取同情,
也才能解释为什么我这个“妻子”会突然“散尽家财”!跳跳打了个寒颤,
看着床上“将死”的拾安,眼神充满了敬畏。姑娘这招……也太狠了!“最后,
”我拿出最大的一块金锭,掂了掂,塞给跳跳,
“去镇上的米铺、肉铺、杂货铺……挨家挨户,买!买米!买肉!买油!买盐!
买一切生活必需品!不要讲价!就按他们说的买!买完告诉他们,我家遭了难,
夫君快不行了,多谢他们关照!记住,要哭!哭得越惨越好!要让整个镇子都知道,
我守静为了夫君,把压箱底的钱都掏出来了,以后的日子……怕是难了!”我要用金子开路,
用“悲情”造势,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走投无路、重情重义、即将失去依靠的可怜寡妇形象!
当所有人都知道我是个“掏空了家底救夫”的可怜人,
谁还会相信我是那个“盗取重宝”的“逃奴”?五十两悬赏?那点钱,
跟我“倾家荡产”救夫的行为比起来,简直像个笑话!跳跳捧着沉甸甸的金子,手都在抖,
但眼神却亮了起来:“姑娘,我明白了!我这就去!”她像一阵风似的冲了出去。
我则深吸一口气,走到床边,看着依旧昏睡的拾安。他眉头紧锁,似乎在忍受着痛苦。“喂,
拾安,”我俯下身,在他耳边低语,带着点恶狠狠的意味,“你最好给我争气点!
别真死了!老娘花了这么多金子救你,你要是敢蹬腿,我做鬼也不放过你!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威胁起了作用,还是回光返照,拾安的睫毛剧烈地颤动了几下,
竟然缓缓地、极其艰难地睁开了眼睛!他的眼神依旧虚弱涣散,但似乎比之前清明了一点点,
带着一种深不见底的疲惫和……一丝难以言喻的复杂光芒。他看着我,
干裂的嘴唇翕动了一下,似乎想说什么,却只发出微弱的气音。“你醒了?”我有点意外,
随即板起脸,“醒了正好!听着,计划有变!
你现在的身份是重伤垂危、随时可能嗝屁的倒霉蛋!
我是你倾家荡产救你、快要守寡的苦命老婆!给我演好了!要是露馅,大家一起玩完!懂?
”他看着我,眼神里那点复杂的光芒闪了闪,最终归于一片沉寂的茫然。
他极其缓慢地、幅度很小地点了一下头,然后又疲惫地闭上了眼睛。很好,很上道。
我直起身,开始酝酿情绪。悲苦,绝望,还有一丝为了夫君豁出一切的决然……没过多久,
小院就炸开了锅。跳跳连哭带嚎,几乎是拖着镇上最有名、也最贵的张老郎中冲进了院子,
一路哭喊:“郎中!求您救救我姐夫吧!我姐姐把家底都掏空了,您一定要救救他啊!
”动静之大,引得左邻右舍纷纷探头探脑。
张老郎中一看拾安那浑身是血(大部分是之前凝固的旧血)、气若游丝的样子,再搭上脉,
眉头就拧成了疙瘩,连连摇头:“伤得太重!失血过多,
邪毒内侵(其实就是伤口感染发烧)!这……这怕是……”“郎中!
”我“噗通”一声就跪在了老郎中面前,眼泪说来就来,哭得撕心裂肺,“求求您!
救救我夫君吧!他才二十出头啊!家里不能没有他啊!要多少钱我都给!我把房子卖了都行!
求您救救他!”我一边哭,
一边从怀里(其实是从跳跳刚买回来的包袱里)掏出两块白花花的银子(用碎银临时拼的),
不由分说塞到老郎中手里。老郎中看着手里的银子,又看看哭得快要晕厥过去的我,
还有旁边同样哭成泪人的跳跳,叹了口气:“唉!造孽啊!老夫……尽力而为吧!
”他开了方子,都是些名贵的药材(在我授意下,跳跳特意强调要贵的)。跳跳拿着方子,
揣着银子,又是一路哭嚎着冲去药铺抓药,生怕别人不知道我家在倾家荡产地救命。紧接着,
跳跳开始了她的“购物狂”表演。“掌柜的!给我来二十斤精米!”“老板!
割五斤上好的五花肉!”“大婶!油!给我打满这一罐!”“大叔!盐!要最细的那种!
”她出手阔绰,根本不问价,给钱爽快。但每买一样东西,她都要红着眼眶,
来救命了……这些……这些是预备着……办后事……和以后过日子用的……”说到动情处,
眼泪哗哗地掉,引得围观众人一阵唏嘘同情。“唉,真可怜啊……”“是啊,
小守静多好的姑娘,怎么摊上这事儿……”“看她哭的,
心都碎了……”“听说她男人是为了上山给她采药才摔的?真是重情重义啊……”“啧啧,
这钱花的……怕是棺材本都搭进去了吧?”流言像长了翅膀,飞快地在临水镇传播开来。
不到半天功夫,整个镇子都知道了:镇西河边新搬来的小媳妇守静,她男人为了给她采药,
摔成重伤,眼看活不成了。这小媳妇有情有义,变卖了所有值钱的东西,
倾家荡产请郎中抓药,还提前备下了办后事的东西……真是闻者伤心,见者落泪。
“倾家荡产救夫”的苦情戏码,成了临水镇最热门的话题。我那小破院,
也成了全镇同情的焦点。当一队明显是外地人、穿着便服但眼神锐利的汉子出现在镇上,
不动声色地打听“最近有没有陌生女子投宿”或者“有没有形迹可疑之人”时,
得到的回答几乎是一致的:“陌生女子?有啊!守静姑娘她小姨子刚投奔来!哭得那个惨哟!
”“形迹可疑?没有没有!要说可怜,就数镇西河边守静家最可怜了!男人快死了,
家底都掏空了,造孽啊!”“你们是外地来的?行行好,要是认识什么神医,
去给守静家男人看看吧!那姑娘,太不容易了!”追兵们面面相觑。
他们得到的线索是追捕两个年轻女子(我和跳跳),目标明确。
可眼前这情况……一个快死的男人?一个倾家荡产救夫的可怜小媳妇?一个来奔丧的小姨子?
怎么看,都和“盗取重宝的逃奴”搭不上边。他们不死心,又悄悄摸到我院子附近观察。
看到的景象是:院门半开着(我故意留的缝),院子里弥漫着一股浓重的药味。
我穿着半旧的素色衣服(跳跳带来的),眼睛肿得像桃子,坐在院子里的小板凳上,
守着一个小药炉,一边抹眼泪一边扇火熬药。
跳跳则红着眼睛在晾晒刚洗好的白麻布(预备当孝布用的)。堂屋里,
隐约传来男人痛苦的**声(拾安很配合),还有老郎中沉重的叹息:“……尽人事,
听天命吧……”整个小院笼罩在一片愁云惨淡、生离死别的悲情氛围中。
追兵们在巷子口观察了半天,最终领头那个摇了摇头,低声道:“不像。撤吧,别处再找找。
”他们悄无声息地退走了,如同从未出现过。当跳跳气喘吁吁地跑回来报信,
说那些人走了时,我扇着炉火的手才终于停了下来。后背的衣衫,早已被冷汗浸透。成了。
这兵行险着的苦肉计,暂时成了!我们成功地把“逃奴”的身份,
淹没在了“苦命鸳鸯”的悲情故事里。接下来的日子,压力骤减。巡查兵再来,
态度都好了不少,甚至还带着点同情:“守静家的,你男人……好些没?唉,
想开点……”镇上的人看我的眼神,也充满了怜悯和善意。
隔壁的赵大娘时常送点自家种的青菜过来,河对岸的李木匠听说我家桌子腿坏了,
主动过来帮忙修好,还分文不收。“苦命人,都不容易。”他们总是这样说。而拾安,
这位戏里的“将死之人”,在张老郎中那几剂贵得要死、药效也确实不错的汤药灌下去,
以及我每天雷打不动的蒲公英马齿苋“野菜糊糊”外敷内服下,
竟然真的……一点点好转了起来!高烧退了,伤口的红肿慢慢消了下去,虽然依旧虚弱,
但脸色不再是吓人的死灰,眼神也清明了不少。偶尔能自己坐起来喝点粥了。这恢复速度,
连张老郎中都啧啧称奇:“小伙子底子好!命硬!阎王爷不肯收啊!
”我看着他能自己端着碗喝粥的样子,心里五味杂陈。一方面庆幸这“道具”没报废,
我的金子没白花(虽然心疼得要死)。另一方面……这家伙怎么还不滚蛋?
伤好了就该识相点走人了吧?然而,拾安似乎完全没有“滚蛋”的自觉。伤好了些,
能下地了,他就开始默默地帮**活。我扫地,
他就拿簸箕在旁边等着倒垃圾(虽然动作迟缓)。我打水,
他就伸手想接过水桶(被我瞪回去了)。我做饭,
他就坐在灶膛前笨拙地添柴火(好几次差点把火弄灭)。甚至我种菜,他也拖着伤腿,
拿着小铲子想帮忙松土(结果把刚冒头的菜苗铲掉两颗)。沉默,笨拙,但……存在感极强。
我忍无可忍:“喂!拾安!你伤好得差不多了吧?是不是该考虑考虑……你自己的去处了?
”我暗示得很明显。他抬起头,看着我,眼神依旧带着点失忆后的茫然,
但深处似乎多了点别的什么。他沉默了几秒,声音低沉沙哑:“我……没地方去。
”“没地方去?”我挑眉,“那也不能赖在我这儿吧?我们非亲非故的!
之前那是权宜之计!”“我记得,”他忽然开口,眼神定定地看着我,“是你说的,
我是你男人。”我:“!!!”一口老血差点喷出来!“那是演戏!演戏你懂不懂?!
”我气急败坏,“为了活命!骗外面那些人的!”他垂下眼帘,
长长的睫毛在苍白的脸上投下阴影,声音低低的,
带着一种近乎执拗的固执:“外面的人……信了。”“……”我竟无言以对。是啊,
外面的人都信了!全镇人都知道“守静家的男人”大难不死,活过来了!
他现在要是突然“消失”了,我怎么解释?说他伤好了就抛下我这个“救命恩妻”跑了?
那我的“情深义重”人设不就崩了?万一引起新的怀疑怎么办?我瞪着他,他也看着我,
眼神坦荡(?)又带着点无辜(?)。跳跳在一旁剥着豆子,看看我,又看看拾安,
小声嘀咕:“姑娘……拾安大哥……干活还挺勤快的……”这丫头,胳膊肘往外拐!
我气得肝疼。这叫什么事儿啊!捡个麻烦,还甩不掉了?行!算你狠!
我恶狠狠地说:“想留下?可以!但我这不养闲人!你得干活!重活累活都是你的!饭管饱,
工钱没有!就当抵你的药钱和饭钱了!什么时候抵够了,什么时候滚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