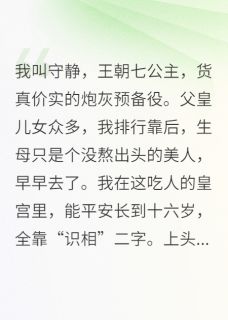战争的消息如同阴云,沉沉地压在临水镇上空,也压在我们这个小院每个人的心头。
拓跋安(或者说,拾安)变得更加沉默。他不再望向北方,只是埋头干活。
劈的柴堆满了半个院子,水缸永远都是满的,屋顶的破瓦被他修补得严严实实。
他甚至无师自通地学会了编竹筐、修农具,手艺居然还不错。只是偶尔,在夜深人静时,
我能看到他独自坐在老桃树下,望着星空,背影沉寂得像一块化不开的寒冰。我知道,
他心里的战场,远比外面的更加惨烈。跳跳也察觉到了气氛的凝重和拾安的变化,
变得格外勤快,变着法儿地做好吃的,试图用食物的温暖驱散阴霾。小丫头很聪明,
从不问不该问的。北方的战火终究还是无情地烧了过来。不是军队的直接入侵,
而是战争的副产品——流民。先是零星几个,衣衫褴褛,面黄肌瘦,带着惊惶的眼神。后来,
成群结队,拖家带口,像潮水一样涌入相对安稳富庶的江南。临水镇这个小小的水乡,
也被波及了。镇外的破庙、桥洞下,挤满了无家可归的人。
饥饿、疾病、绝望的气息在空气中弥漫。镇上有限的存粮和善意很快被消耗殆尽,
恐慌和排外的情绪开始滋生。“这些流民,偷鸡摸狗!昨天张婶家的鸡就被偷了!
”“可不是!还带着病!万一染上瘟疫怎么办?”“官府也不管管!把他们赶走!”茶馆里,
街面上,类似的抱怨越来越多。我和跳跳去买米,价格已经翻了好几倍,还经常断货。
看着那些蜷缩在墙角、饿得奄奄一息的孩子和老人,心里像压了块大石头。这天傍晚,
我们刚收摊回来,就听见院墙外传来压抑的哭泣声和虚弱的哀求。
“好心人……行行好……给点吃的吧……孩子快不行了……”我打开院门。
只见一个面黄肌瘦的妇人抱着个两三岁、气息微弱的孩子,跪在门口。妇人身边,
还跟着一个七八岁、同样瘦骨嶙峋、眼神惊惶的小女孩。看到我开门,
妇人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不住地磕头:“夫人!求求您!给口吃的吧!孩子发烧两天了,
一口奶水都喝不上了……求您发发慈悲!下辈子我做牛做马报答您!”跳跳心软,
眼圈立刻红了,看向我:“姑娘……”我沉默地看着那孩子烧得通红的小脸,
听着他微弱的哭声,再看看妇人绝望的眼神和小女孩的恐惧。战争的残酷,
第一次如此**裸地呈现在我眼前。这些人和我一样,只是想要活下去的普通人。“进来吧。
”我侧开身。妇人千恩万谢,抱着孩子,拉着女儿,踉跄着进了院子。
跳跳赶紧去厨房熬米汤。
我则翻出之前张老郎中给我开的、还剩一点的退烧草药(拾安伤好后就没再用),
让妇人捣碎了给孩子敷上。拾安站在堂屋门口,沉默地看着这一切。
他的眼神落在那对逃难的母女身上,落在那孩子痛苦的小脸上,
深邃的眼底翻涌着极其复杂的情绪——有痛楚,有挣扎,还有一种深沉的悲悯。
妇人喝了点热米汤,恢复了些力气,抱着依旧昏睡的孩子,哭诉着她们的遭遇。
她们来自北边一个被战火摧毁的小镇,男人被抓了壮丁,生死不明。她们跟着同乡一路南逃,
路上婆婆病死了,只剩下她们孤儿寡母三人。
“听说江南好……有活路……可到了这里……”妇人绝望地摇头。跳跳听得眼泪汪汪,
把家里仅剩的两个鸡蛋都煮了,塞给那小女孩。小女孩怯生生地接过,狼吞虎咽,差点噎着。
看着她们,一个念头,如同黑暗中划过的流星,猛地击中了我!我豁然转头,看向拾安。
他仿佛感应到了我的目光,也抬眼看我。四目相对,无需言语,某种默契在无声中达成。
“跳跳,”我深吸一口气,声音带着一种破釜沉舟的决断,“把家里所有的米,都拿出来!
熬一大锅粥!”跳跳一愣:“啊?姑娘,那我们……”“照做!”我的语气不容置疑。
跳跳虽然疑惑,还是立刻跑去了厨房。我又看向拾安:“你去镇口,
把赵大娘、李木匠、还有街口开茶馆的王掌柜……把能请到的、心善的街坊都请来!
就说……就说我守静,有事相求!”拾安深深地看了我一眼,没有问为什么,
转身大步流星地走了出去,高大的背影在暮色中显得异常坚定。妇人抱着孩子,
茫然又惶恐地看着我:“夫人……您这是……”我对她露出一个安抚的笑容:“别怕。
你们……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这院子,以后,就是你们的家。”妇人愣住了,
随即泪水汹涌而出,抱着孩子又要下跪:“恩人!您是大恩人啊!”很快,
小院里挤满了被拾安请来的街坊邻居。大家看着院子里的流民母女,又看看我,都面露疑惑。
我站在堂屋的台阶上,看着一张张熟悉或不太熟悉的面孔,清了清嗓子,
朗声说道:“各位街坊邻居!今天请大家来,是想跟大家商量件事!”众人安静下来,
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大家也都看到了,北边在打仗,流离失所的人越来越多。临水镇,
是我们共同的家,不能见死不救!可光靠一家一户,杯水车薪!”我顿了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