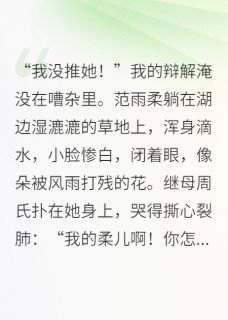“我没推她!”我的辩解淹没在嘈杂里。
范雨柔躺在湖边湿漉漉的草地上,浑身滴水,小脸惨白,闭着眼,像朵被风雨打残的花。继母周氏扑在她身上,哭得撕心裂肺:“我的柔儿啊!你怎么这么命苦!要是你有个三长两短,娘也不活了!”
爹范守仁铁青着脸,看我的眼神像刀子,恨不得剜下我的肉。“范清霜!你竟敢谋害亲妹!毒妇!我范家怎么出了你这么个孽障!”
周围的丫鬟婆子低着头,眼神却偷偷瞟我,里面全是幸灾乐祸和鄙夷。我知道她们在想什么:看吧,这个扫把星,克死亲娘,现在又要害死受宠的庶妹了。
“爹,我真的没推她。”我的声音干涩,指甲深深掐进掌心。湖边湿滑的泥地上,只有我和范雨柔凌乱的脚印,还有她滑倒时带下来的一小块松动的草皮。可没人看,没人信。
“你还敢狡辩!”爹怒吼一声,扬手就朝我脸上扇来。
那巴掌带着风声,又快又狠。我本能地想躲,脚下却像生了根。躲?躲了只会换来更狠的毒打。这些年,习惯了。
“啪!”
清脆响亮。脸颊**辣地疼,嘴里泛起一股铁锈味。耳朵嗡嗡作响,眼前发黑。
“老爷息怒!息怒啊!”周氏适时地扑过来,抱住爹的胳膊,哭喊道,“清霜她…她也是一时糊涂!她心里苦啊,怨我这个继母,怨柔儿分了老爷的宠爱…都是我这个做母亲的没教好她!要打要罚,您冲我来吧!”她哭得情真意切,字字句句却坐实了我的“罪行”和“恶毒”。
爹胸膛剧烈起伏,指着我的鼻子,手指都在抖:“看看!看看你周姨!到了这个时候还在替你求情!你呢?心如蛇蝎!来人!把这个孽女给我拖回她院子,关起来!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放她出来!也不准给她饭吃!让她好好反省!”
两个粗壮的婆子立刻上前,一左一右抓住我的胳膊,像拖死狗一样把我往回拽。我的鞋掉了一只,踩在冰凉的石子路上,硌得生疼。经过周氏身边时,她抱着悠悠“转醒”、嘤嘤哭泣的范雨柔,侧过头,用只有我能看清的角度,对我露出一个极快、极冷的笑。
那笑像淬了毒的针。
我被狠狠掼进自己偏僻破旧的小院。院门“哐当”一声落了锁。
“大**,您就安分待着吧,别给咱们找事儿。”婆子隔着门缝,阴阳怪气地丢下一句。
夕阳的余晖从破旧的窗棂挤进来,在地上投下几道昏黄的光柱,灰尘在光里跳舞。屋子里一股子潮湿的霉味。**着冰冷的墙壁滑坐到地上,脸颊肿着,**辣的疼,嘴里那股腥甜味一直没散。
饿。从早上到现在,水米未进。
桌上只有半壶凉透了的白水。我爬过去,抱起壶对着嘴灌了几口。凉水滑过喉咙,稍微压下了点火气和干渴,胃里却更空了,拧着劲地疼。
没人送饭。爹说了,不准给饭吃。
窗外传来前院隐约的喧闹,丝竹声,劝酒声,还有范雨柔娇弱又带着点得意的笑声。今天是十五,府里照例家宴。我?一个刚“谋害”了亲妹的罪人,只配在冷屋里饿着。
我蜷缩在冰冷的砖地上,抱着膝盖。地上的寒气透过薄薄的夏衣往骨头缝里钻。这就是我在范家的日子。亲娘生我时难产去了,留下个“克母”的名头。爹厌弃我,觉得我晦气。周氏进门后,面上对我嘘寒问暖,背地里使了多少绊子,捧杀、挑拨、陷害……范雨柔更是得了她的真传,小小年纪,装可怜、栽赃陷害的手段炉火纯青。
今天这出落水戏,不过是她们母女俩无数次构陷中,最明目张胆的一次。因为三天后,就是选秀女初筛的日子。我这个名义上的“嫡长女”,是范雨柔这个“庶女”最大的绊脚石。她们要彻底踩死我,让我连参选的机会都没有。
胃饿得一阵阵抽痛。我摸索着走到床边,掀开破旧的褥子,在床板的一个隐秘角落里,摸出一个小小的油纸包。里面是两块硬得像石头的杂粮饼子,不知道藏了多久。这是我唯一的存粮,防备着周氏哪天连馊饭都不给我时用的。
我掰下一小块,放进嘴里,用唾液慢慢濡湿,一点点艰难地往下咽。干硬的饼渣刮着喉咙,生疼。我面无表情地咀嚼着,像在啃噬自己的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