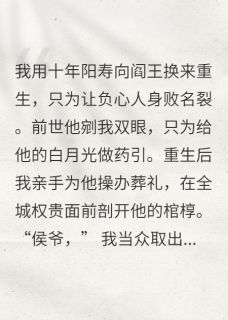我用十年阳寿向阎王换来重生,只为让负心人身败名裂。前世他剜我双眼,
只为给他的白月光做药引。重生后我亲手为他操办葬礼,在全城权贵面前剖开他的棺椁。
“侯爷,”我当众取出血淋淋的指骨,“滴血验亲吧。”血珠滚落的瞬间,
他藏在暗处的白月光尖叫出声。而我的银针已抵住她凸起的小腹——“别急,
下一个就验你偷来的龙种。”——————1黄泉买命血,黏稠得化不开,
像打翻的胭脂匣子糊满视野。最后一点光被彻底吞噬前,是陆沉渊那双淬了寒冰的眼,
和他手中薄刃剜入我眼窝的剧痛。他温热的呼吸喷在我耳际,情话般残忍:“阿月,
清漪的眼睛坏了,借你的用用……你一向最懂事的。”懂事?是啊,十年痴心,
换他一句“懂事”,和一对血窟窿。魂魄离体,悬在侯府雕梁之上。
我看见我的尸身被草席一卷,丢进乱葬岗野狗争食的深坑。我看见陆沉渊拥着柳清漪,
将我那双曾盛满星子的眼,如同镶嵌珍宝般小心植入她的眼眶。柳清漪倚着他,
指尖抚过新得的“礼物”,娇声软语:“沉渊哥哥,这双眼真亮,看你看得真清楚呢。
”陆沉渊低笑,吻她眉心:“你的眼睛,自然是最好的。”滔天的恨意焚烧着残魂,
引来了黄泉路上的引魂使者。那声音非男非女,带着亘古的漠然:“江浸月,怨气冲天,
徘徊不散。阎君开恩,许你一个机会。十年阳寿,换你重回三日之前。代价是,
此身如灯油熬尽,事成魂飞魄散。你可愿?”愿?我几乎要笑出魂魄的颤音。剜眼之痛,
尸骨无存之辱,岂是魂飞魄散能偿!我对着虚空嘶吼,恨意凝成实质:“愿!用我灰飞烟灭,
换他陆沉渊身败名裂,永坠无间!换她柳清漪,得而复失,生不如死!
”刺骨的阴寒裹挟着巨力撕扯,我坠入无底深渊。2灵堂惊雷再睁眼,
浓重的檀香混着纸钱焚烧的呛人气息涌入鼻腔。
触手是冰冷滑腻的紫檀木——是陆沉渊那口价值千金的阴沉木寿棺!
指尖传来的真实触感让我浑身颤栗。低头,素白孝衣加身,臂缠黑纱。灵幡高悬,白烛泪垂,
偌大的忠勇侯府灵堂,一片死寂的哀荣。
“夫人……您、您节哀啊……”贴身侍女青霜红肿着眼,怯怯地扶我。
我猛地攥紧她的手,指甲几乎掐进她肉里。三日!
我真的回到了陆沉渊“暴毙身亡”、停灵侯府的第三天!前世,就是今日,我悲恸欲绝,
强撑病体主持丧仪,
却在三日后被突然“活过来”的陆沉渊污蔑勾结外男、意图谋夺侯府家产,
从此打入地狱,最终落得剜眼惨死!好一个金蝉脱壳,好一个栽赃陷害!
灵堂外传来司仪尖细的唱喏:“吉时到——!起灵——!
”沉重的棺盖被八名壮汉缓缓抬起。堂下,满城权贵云集,有真心吊唁的,
更多是来看我这新寡的落魄侯夫人如何收场。一道道目光或同情、或怜悯、或幸灾乐祸,
织成一张无形的网。就是此刻!“慢着!”我厉喝出声,声音因极致的恨意而尖利,
撕裂了灵堂的肃穆。所有目光瞬间聚焦在我身上。我猛地推开青霜,
踉跄扑向那口即将被抬走的棺椁。素白孝衣在疾奔中扬起,像一只扑向烈焰的蝶。“夫人!
不可惊扰侯爷英灵啊!”管家陆忠惊骇欲绝,扑上来阻拦。我侧身避开,
积蓄了两世的恨意在这一刻爆发,双手狠狠扒住沉重的棺盖边缘,十指瞬间被粗糙木刺刮破,
鲜血淋漓也浑然不觉。在众人惊恐的抽气声中,
我爆发出不似人声的嘶吼:“开——棺——!”“轰隆!
”棺盖被巨大的力道掀开一道骇人的缝隙!
阴沉木特有的森冷气息混合着防腐药料的怪味扑面而出。棺内,陆沉渊身着侯爵蟒袍,
面色惨白,双目紧闭,躺得“安详”。死寂。针落可闻的死寂笼罩了整个灵堂。
所有人都被我这惊世骇俗的举动震得魂飞魄散。3白骨为证我喘息着,背靠冰冷的棺木,
目光如淬毒的冰锥,缓缓扫过堂下每一张惊骇、鄙夷、愤怒的脸。最终,定格在角落阴影里,
那个一身素净、却难掩身段风流、正用帕子掩着口鼻,肩头微微颤抖的身影——柳清漪!
她果然在!来看我的笑话?来看陆沉渊如何诈死脱身?“诸位!”我拔高声音,
带着一种孤注一掷的疯狂,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我江浸月,十六岁嫁入侯府,
十年操持,自问无愧于心!然今日,我不得不惊扰侯爷‘安眠’!
只因有一桩关乎侯府血脉、关乎列祖列宗清誉的天大丑闻,压得我喘不过气!
压得这忠勇侯府的牌匾,都要蒙尘!”“胡言乱语!江氏,你疯了不成!
”陆家族老气得浑身发抖,指着我的鼻子大骂,“还不快将这疯妇拖下去!
”几名陆家旁支子弟就要上前。“谁敢!”我猛地从袖中抽出一柄寒光闪闪的匕首!
那是我前世临死前藏下的唯一利器!刀刃映着我苍白却决绝的脸,
也映着满堂权贵惊惧的眼神。我高举匕首,字字泣血:“我今日,便以这侯府主母之身,
以我十年青春为祭!请诸位做个见证!我要问一问这棺中‘亡夫’——”话音未落,我转身,
在所有人肝胆俱裂的注视下,将匕首狠狠刺入陆沉渊的右手!“噗嗤!
”利刃入肉的声音沉闷而惊心。“啊——!”尖叫声四起,有人当场晕厥。
我面无表情,手腕用力一剜!一块连着皮肉、沾着暗红血渍的森白指骨,
被我生生从陆沉渊僵硬的手指上撬了下来!鲜血,顺着棺木边缘蜿蜒流下,
滴落在白色的丧幡上,触目惊心。我捏着那截带着体温的、血淋淋的指骨,高高举起。
血腥气在灵堂弥漫。我的声音冷得像地狱刮来的风,
带着刻骨的恨意和一种玉石俱焚的疯狂:“‘侯爷’!别装睡了!今日当着满城勋贵的面,
当着陆家列祖列宗的牌位!我们——滴血验亲!”4暗影惊魂“滴血……验亲?!
”这四个字如同平地惊雷,炸得灵堂内所有人大脑一片空白!
所有人的目光都死死盯在我手中那截血骨上,又惊恐地看向棺木中那只血肉模糊的手。
忠勇侯府……血脉有疑?“江浸月!你竟敢如此亵渎侯爷尸身!污蔑侯府血脉!你这毒妇!
我要杀了你!”陆忠目眦欲裂,状若疯虎地扑过来。
早有准备的青霜带着几个我暗中收买的粗壮仆妇死死拦住他。灵堂内一片混乱,
尖叫声、怒骂声、器物倾倒声响成一片。我丝毫不为所动,目光如鹰隼,
精准地捕捉到角落里的柳清漪!她脸上的血色褪得干干净净,身体抖得像秋风中的落叶,
一只手死死捂着自己平坦的小腹,那双新得的、曾属于我的美丽眼睛里,
盛满了巨大的恐惧和难以置信!
“不……不可能……她怎么会……”她失魂落魄地喃喃,下意识地后退,
想要躲进更深的阴影里。晚了!就在她心神剧震、方寸大乱之际,
我如同鬼魅般穿过混乱的人群,瞬间逼近她身前!藏在袖中的另一只手闪电般探出,
三根细如牛毛、淬着幽蓝暗光的银针,精准无比地抵在了她微微凸起的小腹上!
冰冷的针尖隔着薄薄的衣料,传递着死亡的威胁。柳清漪浑身僵硬,连尖叫都卡在喉咙里,
只剩下牙齿咯咯打颤的声响。她惊恐万分地瞪着我,仿佛看到了从地狱爬出来的恶鬼。
我凑近她惨白如纸的脸,唇角勾起一抹淬着寒冰的笑意,声音压得极低,却字字如刀,
清晰地凿进她的耳膜和灵魂深处:“柳姑娘,别急着晕。
”“待验明‘侯爷’真身……”“下一个,就轮到你肚子里这个——‘偷’来的龙种了!
”她的瞳孔骤然缩成针尖!巨大的恐惧和绝望瞬间将她淹没,身体一软,直直向后倒去。
而我手中的银针,稳稳悬停,针尖幽蓝的光芒,在灵堂摇曳的白烛光影下,
闪烁着死神般的微笑。5血溅玉碗柳清漪瘫软的身体被身后侍女慌乱扶住,才没当众出丑。
灵堂内死寂得可怕,所有目光都聚焦在我手中那截血骨和柳清漪煞白的脸上。滴血验亲?
龙种?每一个词都足以让这簪缨世家天翻地覆!“一派胡言!江氏妖言惑众,亵渎侯爷,
污蔑柳姑娘清誉!来人!拿下她!”陆家族老须发皆张,嘶声怒吼。
几个陆家旁支子弟再次硬着头皮上前。“我看谁敢!”一声苍老却蕴含威严的低喝响起。
众人循声望去,只见一直沉默坐在主位、闭目捻着佛珠的老太君——陆沉渊的祖母,
缓缓睁开了眼。那双老眼浑浊,此刻却射出锐利如鹰隼的光,扫过混乱的灵堂,
最终落在我身上,带着审视,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沉痛的期待。“让她验。”三个字,
重若千钧。陆家族老如遭雷击:“老太君!这……”“验!”老太君手中佛珠重重一顿,
发出沉闷声响,“侯府百年清誉,容不得半点污秽!
今日若验不出个所以然……”她森冷的目光钉住我,“江氏,老身亲自送你进诏狱,
挫骨扬灰!”压力如山崩海啸般压来。我脊背挺直如松,指甲深深掐进掌心,
用疼痛维持最后的清醒。前世剜眼之痛,岂是这威胁可比?我捧着那截血骨,
一步步走向早已备好的白玉碗。碗中清水澄澈,映着我苍白如鬼的倒影。
“请族老、请各位大人见证!”我声音嘶哑却清晰。匕首寒光一闪,
毫不犹豫地划破自己的指尖。殷红的血珠滚落,滴入碗中清泉,如同投入石子的湖面,
晕开一圈圈涟漪。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空气凝固了。我深吸一口气,
将手中那截属于陆沉渊的、尚带着一丝诡异体温的指骨,轻轻放入血水交融的玉碗之中。
时间仿佛被拉长了无数倍。血,在水中丝丝缕缕地散开。那截森白的指骨,静静地躺在碗底。
一秒,两秒……没有相融!我的血如同有生命般,在骨头上打了个旋,便泾渭分明地散开,
如同清水滴在油脂之上!“哗——!”短暂的死寂后,是足以掀翻屋顶的哗然!“没融!
血没融进去!”“天爷!难道侯爷真的……不是陆家血脉?!”“这怎么可能!
侯爷可是老侯爷亲生的……”“亲生的?
老侯爷当年可是……”窃窃私语瞬间变成汹涌的浪潮,
无数道震惊、猜疑、鄙夷、甚至带着隐秘兴奋的目光,
如同利箭般射向那口敞开的阴沉木棺椁!陆家族老们面无人色,摇摇欲坠。
管家陆忠更是瘫软在地,抖如筛糠。6药香破局“不可能!”一声凄厉的尖叫划破喧嚣。
柳清漪不知哪来的力气,挣脱了搀扶的侍女,踉跄着扑到玉碗前。
她死死盯着碗中那泾渭分明的血与骨,美丽的脸上扭曲着疯狂和难以置信,
新得的、曾属于我的眼睛里,此刻只剩下惊惶。“假的!一定是假的!是你!江浸月!
是你在水里动了手脚!”她猛地指向我,指尖因激动而颤抖:“你恨沉渊哥哥!
你恨他冷落你!所以你用妖法污蔑他!这水有问题!
这骨头……这骨头说不定根本不是沉渊哥哥的!”“哦?”我冷眼看着她垂死挣扎,
唇角勾起一抹冰凉的弧度,声音不高,却清晰地压过所有嘈杂,“柳姑娘倒是提醒我了。
验骨之法,古已有之,讲究骨正血亲,滴血渗入方为至亲。诸位大人若不信这碗水,
尽可另取清水,当场再验!至于这骨头……”我话音一顿,目光如同淬毒的冰棱,
刺向柳清漪:“是不是陆沉渊的,柳姑娘你——不是最清楚吗?
”柳清漪被我噎得脸色由白转青,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夫人!
”青霜适时捧上另一个盛满清水的玉碗,碗底清晰映着堂中悬挂的“忠勇传家”匾额。
“请族老验水。”我退开一步,姿态磊落。一位德高望重的翰林院老学士,
在众人注视下亲自上前,以银针试水,又仔细嗅闻,最终沉声道:“水清无垢,确无异常。
”柳清漪最后的侥幸被击得粉碎,身体晃了晃。“至于这骨头……”我缓步走回棺椁旁,
居高临下地看着里面“沉睡”的陆沉渊。他脸色依旧惨白,
但那紧抿的、毫无血色的薄唇,在我前世临死的记忆中,曾吐出最刻薄恶毒的话语。我俯身,
冰冷的指尖拂过他冰凉的脸颊,动作轻柔得近乎诡异,声音却如同寒冰碎裂:“我的好夫君,
为了演好这场‘暴毙’的戏,你可是煞费苦心啊。用了南疆秘制的‘龟息散’,脉息断绝,
体如寒冰,连仵作都能瞒过……真是好手段。”“龟息散?!”老太君猛地攥紧了佛珠,
老眼射出骇人的精光,“南疆禁药?”“正是此物。”我直起身,
从袖中取出一个不起眼的油纸小包,当众展开,
露出里面残留的、散发着奇异微甜气味的淡黄色粉末。“此药奇诡,能令人假死三日,
状若真亡。然有一致命弱点——服药者周身血液会变得极其‘排外’,莫说他人之血,
便是自身血液离体稍久,亦难相融!这碗中滴骨不亲,便是铁证!而这药……”我猛地转身,
锐利的目光如同实质的刀刃,狠狠刺向脸色惨白如纸的柳清漪,一字一句,
敲骨吸髓:“正是三日前,由你柳清漪,亲手掺入侯爷的参汤之中!
那盛汤的‘青玉莲瓣盏’,此刻正藏在你贴身侍女春桃的妆匣暗格里!盏底残渣,一验便知!
柳姑娘,你还要如何狡辩?!”7银针锁龙“轰——!”柳清漪如遭五雷轰顶,
整个人彻底僵住,脸上最后一丝血色也消失殆尽,只剩下死灰般的绝望。她精心策划的局,
她以为天衣无缝的“假死脱身、栽赃嫁祸、携子上位”的连环毒计,
在我这重生厉鬼面前,竟被一层层剥开,血淋淋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不……不是我……沉渊哥哥救我……”她语无伦次,下意识地护住小腹,
惊恐地看向棺中。“沉渊哥哥?”我嗤笑出声,带着无尽的讽刺,“你的沉渊哥哥,
此刻怕是正懊恼,这龟息散药效未过,他想‘醒’来替你解围,也是有心无力吧?
”我步步紧逼,手中那三根幽蓝的银针再次抬起,
在灵堂摇曳的烛光下闪烁着致命的光泽:“他救不了你。现在,该轮到你了,柳清漪!
”“你、你想干什么!”柳清漪吓得魂飞魄散,连连后退,却被混乱的人群挡住去路。
她身旁的侍女春桃早已被两个粗壮仆妇按住,吓得尿了裤子。“干什么?”我笑容森然,
目光如同冰冷的毒蛇,缠绕上她微微隆起的小腹,“方才不是说了么?滴骨验亲已毕,
证明棺中这位‘忠勇侯’,是个冒牌货!那你这肚子里,
口口声声说是他‘遗腹子’的孽种……”我故意拖长了音调,
满意地看着她因恐惧而扭曲的脸。“自然也该验明正身!
”“看看究竟是哪个胆大包天的野男人,敢给这‘已死’的侯爷戴绿帽子!
”“又或者……”我猛地欺近她,银针的寒芒几乎要刺破她腹部的衣料,声音压得极低,
如同恶魔的低语,只钻入她一人耳中:“……看看这‘龙种’二字,
究竟是你攀龙附凤的痴心妄想,还是确有其事,给这满城勋贵,再添一桩惊天丑闻?!
”“龙种”二字如同烧红的烙铁,烫得柳清漪浑身剧颤!她终于彻底崩溃,
心理防线被这接踵而至、直击要害的指控彻底击垮!“啊——!!
”她发出一声凄厉到不似人声的尖叫,双手死死抱住头,状若疯癫,“不是我!我没有!
是陆沉渊逼我的!是他!是他让我下药!是他让我勾引陛下!是他想用这个孩子……”话,
戛然而止!柳清漪如同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扼住了喉咙,惊恐地瞪大了眼睛,
死死捂住了自己的嘴!她失言了!她竟然在极度恐惧下,吐露了那个最不能提的名字!
“陛下?”“勾引陛下?”“龙种……难道是真的?!”整个灵堂彻底炸了!
如果说之前滴骨验亲只是侯府私德有亏,那此刻柳清漪失口吐露的“陛下”二字,
就如同在滚油中泼入冷水,瞬间引爆了足以打败整个朝堂的惊雷!
所有勋贵官员的脸色都变了,惊骇、恐惧、难以置信交织在一起!
老太君手中的佛珠“啪嗒”一声断裂,檀木珠子滚落一地。她死死盯着柳清漪,
浑浊的老眼里翻涌着惊涛骇浪和滔天的愤怒!
就在这死寂与惊骇达到顶点的时刻——“圣旨到——!”灵堂外,
一声尖利高亢、穿透力极强的太监唱喏,如同九天惊雷,轰然炸响!
8圣旨惊魂“圣旨到——!忠勇侯府上下,跪迎——!
”尖细的嗓音带着不容置疑的皇家威严,如同冰冷的铁鞭抽打在每一个人的神经上!灵堂内,
时间仿佛被彻底冻结。前一秒还因“陛下”二字而掀起的惊涛骇浪,
瞬间被这更恐怖的皇权之威死死压了下去。所有嘈杂、议论、尖叫,
如同被掐住了脖子的鸭子,戛然而止。只剩下粗重压抑的喘息声,
和心脏疯狂擂鼓般的咚咚声。沉重的脚步声由远及近,伴随着甲胄摩擦的铿锵声。
两队身着明光铠、手持长戟的禁卫军鱼贯而入,冰冷的铁面下目光如电,
瞬间将混乱的灵堂控制住,肃杀之气弥漫。紧接着,
一个身着绛紫色蟒袍、面白无须、眼神阴鸷的老太监,手捧一卷明黄圣旨,缓步踏入。
他目光如毒蛇般扫过狼藉的灵堂、敞开的棺木、瘫软的柳清漪,最终落在我身上,
嘴角似乎勾起一丝难以察觉的弧度。“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老太监展开圣旨,
尖利的声音在死寂的灵堂回荡,每一个字都像冰锥砸落,“惊闻忠勇侯陆沉渊英年早逝,
朕心甚恸!然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侯府主母江氏,惊扰亡者,当众剖棺取骨,
行滴血验亲之妖妄事,更污言秽语,攀扯宫闱,惊扰圣听!其行乖戾,其心可诛!着,
即刻锁拿入宫,交予慎刑司,严加讯问!钦此——!”“锁拿入宫!慎刑司!
”这几个字如同丧钟敲响!慎刑司,那是比诏狱更恐怖的地方!进去的人,不死也要脱层皮,
绝无可能完整地走出来!陆家族老们脸上瞬间露出一丝狂喜和怨毒。柳清漪瘫在地上,
眼中爆发出劫后余生的、扭曲的快意。老太君死死攥着断掉的佛珠链,嘴唇翕动,
却发不出任何声音,老眼第一次看向我,带上了深切的、绝望的悲悯。“夫人!
”青霜凄厉地哭喊,想要扑过来,却被禁卫军冰冷的戟尖拦住。
两个如狼似虎的禁卫军大步上前,沉重的铁链哗啦作响,就要套上我的脖颈!
整个灵堂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有恐惧,有怜悯,更多的是看死人般的冷漠。
就在那冰冷的铁链即将触及我肌肤的刹那——“且慢!”我猛地抬头,眼中没有半分恐惧,
只有一种近乎燃烧的疯狂和孤注一掷的决绝。我无视近在咫尺的铁链,
目光越过凶神恶煞的禁卫军,死死钉在那宣旨的老太监身上,
声音因为极致的紧绷而微微发颤,却异常清晰,带着穿透人心的力量:“王公公!这圣旨,
我江浸月接不得!”老太监王德全阴鸷的眼睛危险地眯起:“哦?江氏,你想抗旨?
”他的手轻轻一挥,更多的禁卫军围拢上来,杀气腾腾。“非是抗旨!”我挺直脊梁,
素白的孝衣在肃杀铁甲中显得格外单薄,却又带着一种奇异的、宁折不弯的孤绝。我抬起手,
指向那口敞开的阴沉木棺椁,指向棺中“沉睡”的陆沉渊,
更指向地上抖如筛糠、面无人色的柳清漪,每一个字都如同从牙缝中挤出,
带着泣血的控诉:“而是此案,关乎国本!”“棺中之人,身份存疑,滴骨不融,铁证如山!
此乃欺君罔上,混淆天家血脉之始!”“地上之妇,柳氏清漪,亲口招供,
受命于‘陆沉渊’,勾连宫闱,秽乱龙床,更身怀‘龙裔’!此乃祸乱宫闱,动摇国本之实!
”“陛下!”我猛地转向皇城方向,声音陡然拔高,如同杜鹃啼血,响彻整个死寂的灵堂,
“臣妇江浸月,今日剖棺取骨,滴血验亲,非为私怨!实乃以命为引,敲响这侯府深宅内,
欲倾覆我大梁江山的——第一声丧钟!”“陛下若此时锁拿臣妇入慎刑司灭口,
岂非坐实了这滔天阴谋?!岂非让这乱臣贼子、祸国妖妃,逍遥法外?!臣妇死不足惜!
然大梁百年基业,陛下万世圣名,将置于何地?!”字字如刀,句句泣血!灵堂内,
死一般的寂静。只有我嘶哑的余音在梁柱间回荡。王德全脸上的阴鸷凝固了,
握着圣旨的手指微微发白。所有禁卫军的动作都停了下来。勋贵官员们个个面如土色,
冷汗涔涔,大气不敢出。柳清漪彻底瘫软,如同烂泥。
就在这令人窒息的死寂中——“咳…咳咳……”一阵微弱却清晰无比的咳嗽声,
突兀地、如同鬼魅般,从那口敞开的阴沉木棺椁中,幽幽地传了出来!
9蟒袍染血那声咳嗽如同投入死水的巨石,瞬间炸碎了灵堂令人窒息的死寂!所有目光,
惊骇欲绝地射向那口敞开的阴沉木棺椁!只见棺中,“已死”的忠勇侯陆沉渊,
睫毛剧烈地颤动了几下,覆盖着一层诡异灰败的脸色在烛光下扭曲,紧闭的薄唇艰难地张开,
又发出几声压抑不住的、仿佛要将五脏六腑都咳出来的闷响。
他试图抬起那只被剜去指骨、血肉模糊的右手,剧烈的疼痛让他浑身痉挛,
喉间溢出痛苦的低吟。“侯爷……侯爷醒了?!”“诈、诈尸?!”“是龟息散!
药效过了!”惊呼声、抽气声、混乱的脚步声再次响起,但这一次,
所有情绪都裹挟着巨大的恐惧和难以置信!王德全老太监阴鸷的眼中第一次闪过惊疑,
握着圣旨的手紧了紧。禁卫军的铁戟下意识地对准了棺椁方向,却又不敢真正上前。
就在这众目睽睽、惊魂未定之际,我动了。没有半分犹豫,如同早已演练过千百遍。
素白的身影在肃杀铁甲中如同鬼魅,瞬间扑至棺椁边缘!
渊那双因剧痛和强行苏醒而布满血丝、尚带着茫然与惊怒的眼睛刚刚聚焦的刹那——“噗!
”我手中那柄曾剜下他指骨的匕首,带着积攒了两世的滔天恨意,
毫不犹豫地、狠狠扎进了他左肩!力道之大,穿透了华丽的侯爵蟒袍,深深没入骨肉!
“呃啊——!”陆沉渊发出一声不似人声的惨嚎,身体猛地弓起,
剧痛彻底驱散了龟息散残留的麻痹,那张曾令无数闺秀倾心的俊脸,
因极致的痛苦和猝不及防的袭击而扭曲变形,冷汗瞬间浸透鬓角。猩红的血,
如同怒放的曼珠沙华,在他明黄色的蟒袍肩头急速晕染开一片刺目的狰狞。“侯爷!
”“沉渊哥哥!”陆忠和柳清漪的尖叫撕心裂肺。我却笑了。
俯身贴近他因剧痛而剧烈喘息的脸,染血的指尖带着冰冷的恶意,
缓缓抚过他因痛苦而滚动的喉结,如同毒蛇的信子舔舐猎物。声音不高,
却带着淬骨的寒冰和刻骨的嘲讽,清晰地送入他耳中,
也送入所有被这血腥一幕震得魂飞魄散的众人耳中:“陆沉渊,你这‘死’而复生的戏,
唱得可还尽兴?”“不妨当着陛下亲使的面,好好说说……”我的手指猛地用力,
指甲几乎嵌入他颈侧的皮肉,
迫使他涣散的瞳孔对上我燃烧着地狱烈焰的双眼:“你让柳清漪,
怀上这所谓的‘龙种’时……”“是穿着这身象征忠勇的侯爵蟒袍?
”“还是——”我的声音陡然拔高,如同厉鬼索命的尖啸,带着玉石俱焚的决绝,
响彻整个灵堂:“穿着你前朝逆党余孽的——染血囚衣?!
”10龙鳞逆鳞“前朝余孽?!”“染血囚衣?!”这四个字,比“滴骨不融”,
比“秽乱龙床”,比“诈尸”更加石破天惊!如同九天之上降下的灭世神雷,
狠狠劈在每一个人的天灵盖上!整个灵堂的空气仿佛被瞬间抽空,陷入一种真空般的死寂。
连陆沉渊肩头的匕首带来的剧痛似乎都凝固了,他布满血丝的瞳孔骤然缩紧,
里面翻涌起惊涛骇浪般的惊骇、恐惧,以及一丝被彻底撕开伪装的、疯狂的杀意!
王德全老太监那张万年阴鸷的脸,第一次失去了所有血色!他握着圣旨的手剧烈地颤抖起来,
尖声厉喝:“妖妇住口!禁卫军!拿下她!快拿下她!堵住她的嘴!”这一次,
命令带着前所未有的恐慌。如狼似虎的禁卫军不再顾忌,铁链哗啦作响,
冰冷的戟尖带着破风声直刺而来!“谁敢动她!”一声苍老却蕴含着雷霆之怒的断喝,
如同古钟轰鸣,硬生生压下了禁卫军的动作!一直沉默如山、捻着断裂佛珠的老太君,
猛地从主位上站了起来!她佝偻的腰背挺得笔直,浑浊的老眼此刻爆射出骇人的精光,
如同沉睡的怒狮苏醒,带着尸山血海中淬炼出的、足以震慑千军的凛冽杀气!
她的目光没有看禁卫军,没有看王德全,甚至没有看棺中血流如注的陆沉渊,
而是死死钉在我脸上,那目光锐利如刀,仿佛要穿透我的皮囊,直刺灵魂深处!“江浸月!
”老太君的声音如同金铁交击,带着不容置疑的威压,“你可知,‘前朝余孽’四字,
出口便是诛灭九族之祸!若无铁证,老身第一个活剐了你!”压力!
比圣旨锁拿更沉重百倍的压力轰然降临!
这是来自陆家真正定海神针、曾随先帝马踏山河的诰命老封君的滔天威势!我喉头一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