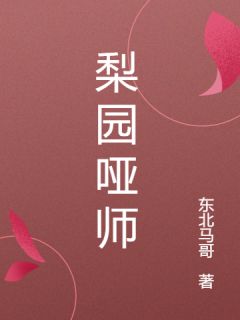苏晚棠的指甲几乎要掐进皮影竹棍里。
竹棍是陈三娘用后山的苦竹削的,纹路里还留着老人掌心的温度。
她望着顾昭腰间的玉佩,那抹温润的白晃得她眼尾发酸——这是三天里第二个对她说"跟我走"的人,上一个是陈三娘,在冬夜里攥着她的手断气前,说的是"别怕,守着戏"。
"姑娘。"顾昭的声音放得更轻,像怕惊飞檐下的燕。
他注意到她指尖在发抖,顺着她的目光看向墙角的皮影箱——箱盖裂了道缝,用麻线缠着,箱身沾着洗不净的泥点,倒像块被岁月啃过的老树皮。
再往窗外看,废弃戏棚的竹架歪在月光里,棚顶的破布被风掀起一角,露出底下褪色的"棠影"二字,那是陈三娘用红漆写的,说是要等她能开口唱大戏那天,换成金漆。
苏晚棠突然松开竹棍。
竹棍"咔"地磕在桌沿,惊得顾昭眉心一跳。
她弯腰捡起针,又指向地上的皮影箱,再转身指了指窗外的戏棚。
动作很急,指尖扫过桌角时擦破了皮,渗出点血珠。
顾昭顺着她的指引望去,忽然懂了——这箱子装着她和养母二十年的岁月,那戏棚的断梁上还挂着陈三娘临终前缝的皮影帘子,青衫书生和红衣娘子的影子,在风里晃得像未唱完的半出戏。
"我知道。"他蹲下来,与她平视。
玄色锦袍沾了些墙角的灰,却丝毫不显狼狈,"我在江南打听过陈婆婆。"他说,"她教你调灯影的角度,教你用皮影的眼尾替窦娥哭,教你把《牡丹亭》的游园惊梦演得比真花还鲜。"他伸手,指尖虚虚碰了碰她手背上的血珠,"她若还在,会愿意看你守着这破棚子,还是看你把她教的戏,唱给天下人听?"
苏晚棠猛地缩回手。
喉间像塞了团浸了水的棉花,涨得她眼眶发热。
她想起三天前顾昭往她竹筐里扔银锭时,她摸出半块冷炊饼要塞给他,他却笑着摇头,说"你演的窦娥比我见过的所有花旦都像"。
那时候她就觉得,这人眼睛太亮,亮得像要把她藏在皮影里的心事都照出来。
夜更深了。
顾昭起身时,衣摆扫过她脚边的破蒲团。
他没再说什么,只将一块帕子轻轻放在她手边——帕子是月白的,绣着玉茗楼的海棠纹,角上还留着他掌心的温度。
门"吱呀"合上的刹那,她听见他在门外说:"明早我再来。"
月光爬上窗棂时,苏晚棠摸出床底的木匣。
匣底压着张泛黄的纸条,陈三娘的字迹歪歪扭扭,是临终前用最后力气写的:"晚棠,戏是你说话的方式,不要怕别人听不见,只要他们看得懂。"纸角沾着暗红的血,是老人咳在帕子上,又蹭到纸上的。
她用指腹摩挲那行字,仿佛能摸到陈三娘枯瘦的手指,正一笔一画教她认戏文。
"阿娘。"她无声地唤,喉咙里滚出含混的气音。
这是她第一次在心里叫出声,像含着颗化不开的糖。
记忆突然涌上来——七岁那年暴雨冲垮戏棚,陈三娘背着她在雨里跑,皮影箱顶在头顶,说"别怕,阿娘在";十五岁她生疹子,陈三娘用体温焐热她的手,教她在被窝里用筷子当竹棍练手法;去年冬夜,老人咳得喘不上气,却还笑着替她补窦娥的水袖,说"等阿娘好了,咱们去京城,让那些大戏楼瞧瞧,哑女的戏才最勾魂"。
窗纸被风掀起一角,凉丝丝的夜风吹在脸上。
苏晚棠忽然想起陈三娘常说的话:"戏子的根不在戏台,在看客的心里。"她望着墙上摇晃的皮影影子——窦娥的水袖,杜丽娘的团扇,唐明皇的冕旒,全是陈三娘一针一线缝的。
可这些影子再活灵活现,能看见的不过是巷口的老棋翁、卖糖葫芦的老张,还有洗衣的小媳妇。
鸡叫头遍时,苏晚棠把木匣里的东西一件件装进包袱:陈三娘补了三次的旧棉袄,半块没吃完的桂花糖(是去年她生辰老人买的),还有那张带血的纸条。
最后她抱起皮影箱,箱底的麻线突然断了,露出里面塞着的半吊铜钱——是陈三娘攒了三年的,说等她能登台那天,给她做身绣金线的戏服。
晨光漫进院子时,顾昭站在篱笆外。
他换了件青衫,手里提着食盒,见她出来,眼尾先弯了:"我猜你没吃早饭。"食盒里是温着的桂花糕,甜香混着晨露的湿意,钻进她鼻子里。
她望着他腰间的玉牌,忽然伸手,指了指自己的包袱,又点了点头。
顾昭的呼吸顿了顿。
他从怀里摸出枚羊脂玉牌,牌面刻着"玉茗"二字,背面是缠枝海棠纹。"这是玉茗楼的通行令。"他将牌子轻轻放在她掌心,"到了京城,你报我的名字,没人敢为难你。"
苏晚棠捏紧玉牌。
玉牌的温度透过掌心漫进血管,像陈三娘当年握她手教她拉线时的温度。
她望着顾昭,目光从他微翘的眼尾,落到他唇角的笑纹上。
这一次,她没再移开视线——她想让他看见,自己眼里的光,比皮影戏里的灯烛更亮。
"明日启程。"顾昭说,"玉茗楼的戏班子,该添个会用影子说话的角儿了。"
苏晚棠低头整理包袱。
发间的铜铃轻响,像是应了。
她最后看了眼旧屋——窗台上陈三娘种的野菊开了,金黄的花瓣在风里颤。
忽然想起昨夜梦里,陈三娘站在戏棚下冲她笑,说:"晚棠,去把阿娘没唱完的戏,接着唱。"
京城的方向,飘来若有若无的锣鼓声。
晨雾未散时,苏晚棠跟着顾昭进了京城。
青石板路被马蹄踏得咚咚响,她攥紧包袱的手指泛白——那里面装着陈三娘的旧棉袄、半块桂花糖,还有皮影箱底的半吊铜钱。
转过朱漆牌楼,"玉茗楼"三个镏金大字撞进眼里,戏楼飞檐上的铜铃被风拨响,和她发间的铜铃应和着,像陈三娘生前哼的小调。
"到了。"顾昭停在后门,伸手替她拂去肩头的晨露。
他腰间的玉牌晃了晃,"我先去前堂理事,让赵大娘带你认认后台。"
后台门帘掀起时,混着脂粉与木屑的气味涌出来。
苏晚棠看见个穿青布裙的妇人正往铜盆里倒热水,手背堆着肥肉,抬头时眼尾的褶子挤成一团——是赵大娘。
"少东家。"赵大娘擦了擦手,目光扫过苏晚棠的粗布包袱,嘴角往下一耷拉,"这就是您说的新跑龙套?"
顾昭点头:"她叫苏晚棠。"
"哑的?"赵大娘嗓门陡然拔高,"您当玉茗楼是慈善堂?
跑龙套也得喊个'报——'字,她倒好,金口难开!"
苏晚棠攥紧包袱带。
陈三娘说过,戏子的嘴是唱的,不是吵的。
她垂眼盯着赵大娘脚边的铜盆,盆底沉着半枚铜钱,和她皮影箱里的那半吊,纹路竟一般。
"赵管事。"顾昭声音沉了些,"我信她能行。"
赵大娘的肥肉颤了颤,堆出笑:"您说行就行。"她转身从木柜里抽出件灰扑扑的戏服,"最末排的跑龙套,自己找位置坐。"戏服"啪"地甩在苏晚棠脚边,带着股霉味。
后台靠墙摆着十几张木凳,最边上那张沾着墨汁。
苏晚棠蹲下身拾戏服,瞥见凳下塞着团皱巴巴的戏谱——《牡丹亭》的《惊梦》折,字迹歪歪扭扭,像是哪个小徒弟抄的。
换衣间的布帘被人掀开。
赵雪儿踩着绣鞋进来,鬓边的水钻簪子闪得人眼晕。
她扫了眼苏晚棠怀里的灰戏服,涂着丹蔻的手指挑起自己的月白裙角:"这不是少东家带来的哑巴?"
苏晚棠低头解包袱。
陈三娘补的旧棉袄露了个角,赵雪儿的笑声像银铃:"穿这破布也想登台?
我去年赏给丫鬟的旧衫都比这体面。"
"雪儿姑娘。"赵大娘端着茶盏凑过来,"少东家交代了,让她多学学。"
"学?"赵雪儿对着铜镜描眉,"她连《游园》的腔都哼不全,学什么?"她突然把眉笔一甩,"我头饰歪了!
哑巴,过来给我理理。"
苏晚棠走过去。
赵雪儿的珠钗沉甸甸的,她用竹簪轻轻挑正,珠串叮铃作响。
赵雪儿忽然偏头:"你碰疼我了!"
苏晚棠指尖一顿。
赵大娘在旁冷笑:"哑巴手笨,雪儿姑娘担待着。"
"算了。"赵雪儿甩了甩水袖,"晚上《长坂坡》,我演糜夫人,你...就演具死尸吧。"她涂着胭脂的唇勾起,"躺台上别乱动,省得坏了我的戏。"
苏晚棠没应声。
她望着镜中自己的影子——发间铜铃,腰间皮影箱的穗子,都静悄悄的。
可她心里有团火,烧得喉头发紧。
陈三娘说,戏子的魂在戏里,不在嘴上。
夜幕降临时,后台点起了羊角灯。
苏晚棠蹲在道具箱旁,看武生们练枪。
饰演赵云的周班主扎着硬靠,枪花耍得跟风轮似的。
她数着他的步子:一步、两步、枪尖挑起的角度...连他额角的汗落在哪里,都记进了骨头里。
"发什么呆!"赵大娘踢了踢她的皮影箱,"死尸该上场了。"
舞台的幕布后,苏晚棠听见锣鼓点密起来。
她躺下时,木板硌得后背生疼,可她盯着台顶的琉璃灯,想起陈三娘教她的:"死有千般样,冤死的眼要睁,累死的手要蜷,你得把魂儿留在戏里。"
枪尖扫过鬓角的刹那,她的手指缓缓蜷进泥土里——那是小兵临死前想抓住最后一把乡土;眼皮轻轻颤了颤——那是他望着远方未归的妻儿,咽不下最后一口气;连唇角都扯出半道极浅的纹——像在笑,又像在哭。
"娘!"前排突然传来孩子的哭声,"他...他真的死了!"
老夫人掏出手帕抹眼睛:"这小兵演得...比赵云还让人心疼。"
穿锦袍的公子捏着茶盏,指节发白:"你们看他的手,指甲缝里全是泥,跟真在战场上爬过似的。"
后台,顾昭掀开半幅幕布。
台上的"死尸"像块被揉皱的破布,可那双眼睛——他想起昨夜在江南巷口,女孩蹲在皮影灯下,影子里的窦娥也是这样,眼尾带着股子不屈的狠劲。
大幕落下时,掌声如雷。
赵雪儿卸了妆过来,鬓角的水钻暗了:"那死尸抢了我的戏!"
赵大娘赔着笑:"雪儿姑娘别气,到底是个跑龙套的..."
顾昭没说话。
他望着台边那个蹲在地上收拾戏服的身影——她的皮影箱敞着,里面的窦娥皮影在烛火下摇晃,水袖像是要甩进人心里。
"赵管事。"顾昭突然开口。
赵大娘打了个激灵:"少东家?"
顾昭的目光扫过刚才"死尸"躺过的位置,又落在苏晚棠发间轻响的铜铃上:"今晚那个'死尸'..."
他没说完。
后台的烛火忽明忽暗,将两人的影子拉得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