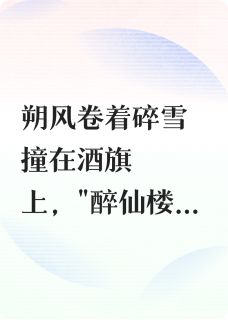朔风卷着碎雪撞在酒旗上,"醉仙楼"三个褪色的金字在暮色里晃得像将熄的烛火。
沈彻把最后一块冻硬的麦饼塞进嘴里,粗粝的麸皮刮得喉咙生疼,他仰头灌下半瓢冷水,
冰碴子顺着食道滑下去,在丹田处凝成一团寒意。隔壁桌的赌徒突然掀了桌子,
骨牌散落时带起的风扫过沈彻的靴尖。他垂着眼皮数着地上的裂纹,
那道从门槛延伸到墙角的缝已经宽得能塞进小指,去年冬天还只是道细痕。"姓秦的,
敢出老千?"络腮胡壮汉揪住对面青衫客的衣领,腰间弯刀撞在桌角,发出沉闷的嗡鸣。
周围酒客作鸟兽散,只有掌柜的在柜台后抱着算盘发抖,算珠碰撞声像牙齿打颤。
沈彻慢慢抹掉嘴角的饼屑,指腹触到下颌新冒的胡茬,扎得有些痒。
他来这破落户镇子已三月,从秋末守到深冬,每天算着积雪的厚度,
等着一个或许永远不会来的人。青衫客突然笑了,笑声里裹着冰碴子:"王当家的,
您掂量掂量,这副骨头经不经得起您的刀?"他手腕轻翻,三枚骨牌凭空出现在指间,
转得像飞旋的蝶。壮汉的脸涨成猪肝色,拔刀的手顿在半空。沈彻认出那是黑风寨的王奎,
上个月刚抢了镇西张屠户的女儿,此刻刀柄上还缠着块红绸,想必是那姑娘的嫁妆。
"姓秦的,别以为会两手戏法就......"王奎的话卡在喉咙里,
青衫客指间的骨牌突然射出,一枚钉在他手背,另外两枚**桌面,正好夹住他握刀的虎口。
骨牌入木三分,切口处凝着白霜。沈彻的瞳孔缩了缩。那手法不是戏法,是"寒月指",
当年雪山派的绝技,据说已随掌门夫妇战死在嘉峪关外。青衫客慢悠悠起身,
玄色腰带松开半寸,露出里层月白锦缎。沈彻的心跳漏了一拍——那锦缎上绣着半朵雪莲,
另一半该是被剑劈开的,和他藏在衣襟里的那块玉佩一模一样。
"阁下是......"沈彻的声音有些发紧,左手不自觉按在腰间。
那里别着柄三寸七分的短刀,刀鞘是寻常的黑檀木,却比同尺寸的重三成。青衫客转头时,
沈彻看见他左眼下方有颗朱砂痣,像滴凝固的血。"这位兄台有何见教?
"他笑的时候眼角会起细纹,让那张本该俊朗的脸添了几分沧桑。王奎趁两人说话,
突然挥拳砸向青衫客后心。沈彻几乎是本能地抬腿,靴底正中王奎膝盖弯。壮汉惨叫着跪下,
撞翻的酒坛在地上砸出个黏糊糊的坑,酒液渗进雪地,晕开深色的渍。"多谢。
"青衫客拱手,指尖的温度似乎比旁人低些,"在下秦越。"沈彻盯着他腰间的玉佩,
那半朵雪莲的花瓣边缘有处缺口,是被剑气崩的。五年前嘉峪关那场血战,
他亲眼看见师父用"裂刃"劈开这枚玉佩,将带缺口的一半塞进师娘手里。"沈彻。
"他报上名字时,听见自己的牙在打颤,不是因为冷。
秦越的目光在他腰间顿了顿:"沈兄带着短刀,却不像走江湖的。""混口饭吃。
"沈彻扯了扯衣襟,遮住露出的玉佩一角,"秦兄的寒月指,是雪山派的功夫?
"秦越的笑淡了些:"早就不是了。"他俯身拔出桌上的骨牌,白霜遇热化作水汽,
"沈兄若不嫌弃,我做东。"掌柜的不知何时端来两坛新酒,酒液在陶碗里晃出琥珀色的光。
秦越倒酒时,沈彻看见他右手无名指第二节有圈浅痕,像是常年握某种特殊兵器磨的。
"听说黑风寨最近在找一个带刀的年轻人。"秦越抿了口酒,眼风扫过窗外,
"沈兄可知此事?"沈彻的指尖在碗沿转了半圈:"镇上带刀的不少。
""但带'裂刃'的只有一个。"秦越放下酒碗,响声不大,却让沈彻的后颈瞬间沁出冷汗,
"五年前嘉峪关,沈惊鸿的儿子,沈彻。"积雪从房檐滑落,
砸在窗台上的声音像块巨石落地。沈彻握紧短刀,刀鞘里的铁家伙似乎在发烫,
那是用父亲断剑重铸的刃,十七岁生辰那天,师娘亲手交给他的。"秦兄认错人了。
"他起身时带倒了板凳,木头撞在地上的声音惊飞了檐下的麻雀。秦越突然笑了,
从怀里掏出个用油纸包着的东西:"沈惊鸿夫妇的骨灰,你要不要?"沈彻的呼吸骤停。
油纸包上还沾着沙粒,那是嘉峪关特有的五色砂。他记得父亲倒下时,胸口插着三支透骨钉,
母亲抱着他的尸身,被乱箭射成了筛子。"你是谁?"沈彻的声音像被砂纸磨过。
"送骨灰的人。"秦越把纸包推过来,"雪山派覆灭那晚,我在乱葬岗挖了三天。
"他的指甲缝里似乎还嵌着黑泥,"沈惊鸿临终前说,若他儿子活着,让你忘了裂刃,
忘了血海深仇,找个小镇安稳度日。"沈彻的指腹抚过油纸包的棱角,
骨灰的重量比想象中轻,却压得他膝盖发软。他突然想起十五岁那年,
父亲教他练"裂刃十三式",第三式总也练不对,父亲用剑鞘敲他的背:"彻儿,
练剑先练心,心不稳,刃就裂。""谁灭了雪山派?"沈彻的声音在发抖,
短刀的刀柄被冷汗浸得发滑。秦越仰头饮尽碗中酒,
喉结滚动的弧度像吞下一柄剑:"江湖人称'玉面修罗'的谢临渊,还有他背后的'影阁'。
"这个名字像冰锥刺进沈彻的太阳穴。谢临渊,三年前以一己之力覆灭江南七派,
据说他的"碎心掌"能让人笑着断气。更可怕的是影阁,没人见过影阁的人,
只知道被盯上的人活不过三更。"你知道的太多了。"沈彻突然拔刀,
三寸七分的短刀在暮色里泛着青幽的光,刃口有锯齿状的纹路——那是裂刃的标志。
秦越却动也不动,只是挑眉:"杀了我,你就永远不知道谢临渊为什么非要灭雪山派。
"他的指尖在桌上画了个符号,像朵被劈开的雪莲,"这是影阁的密记,沈惊鸿死前,
正带着这个去找武林盟主。"沈彻的刀停在秦越咽喉前一寸,
刃尖的寒气让对方的皮肤起了层鸡皮疙瘩。他看见秦越左眼的朱砂痣在跳动,
像有血要渗出来。"我凭什么信你?""就凭这个。"秦越解开衣襟,心口处有道狰狞的疤,
从锁骨延伸到肚脐,"影阁的'穿心箭'留下的,我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时,
手里攥着半块雪莲玉佩。"沈彻的视线落在那道疤上,箭伤的形状和父亲胸口的透骨钉吻合。
他慢慢收刀,刀入鞘时发出清脆的响声,惊得隔壁桌的油灯晃了晃。"骨灰我收下了。
"沈彻把油纸包揣进怀里,贴近心口的位置,"谢临渊在哪?"秦越笑了,
眼角的细纹里像藏着风雪:"正月十五,洛阳城,聚宝阁拍卖会。听说影阁要拍一件东西,
谢临渊会亲自到场。"窗外的雪突然大了,酒旗被压得直不起腰。
沈彻望着远处黑沉沉的山影,黑风寨就在那山里,王奎的尸体刚才被拖走时,
在雪地上留下两道长长的血痕。"正月十五还有四十天。"沈彻给自己倒了碗酒,
酒液里映出他布满红血丝的眼睛,"这四十天,我得练练裂刃。
"秦越的手指在桌上敲出奇怪的节奏,像是某种暗号:"我知道个地方,
有雪山派失传的剑谱。"他凑近时,沈彻闻到他身上有松烟墨的味道,"但你得答应我,
杀了谢临渊后,把这个交给武林盟主。"那是块巴掌大的羊皮卷,
上面用朱砂画着复杂的地图,角落盖着个朱砂印,像朵盛开的雪莲。
沈彻把羊皮卷折成小块塞进靴筒,那里还藏着半块玉佩。两瓣雪莲合在一起,
正好能拼成完整的图案,只是中间有道无法弥合的裂痕。"明天一早出发。
"沈彻喝完最后一口酒,起身时带起的风卷走了桌上的残雪,"去什么地方?""断魂崖。
"秦越的声音裹在风雪里,带着种宿命般的寒意,"雪山派历代掌门的埋骨地。"天未亮时,
沈彻被冻醒了。他缩在破庙的神龛后,怀里的骨灰坛硌得肋骨生疼。秦越靠在香案边打盹,
青衫下摆沾着的雪已经化了,在地上积出一小滩水。沈彻摸出短刀,
借着从破窗透进来的微光打量。刀身比普通短刀宽半寸,刃口的锯齿是父亲亲手打磨的,
说是能锁住对手的兵器。刀柄缠着鲛鱼皮,五年过去,原本银白的纹路已变成深褐色,
浸满了汗渍和血。"裂刃十三式,你会几式?"秦越突然睁开眼,声音带着刚睡醒的沙哑。
沈彻收刀入鞘:"前三式。"秦越坐直身子,指节捏得咯咯响:"沈惊鸿的得意门生里,
有个叫柳长亭的,你认识吗?"这个名字像根针,刺破了沈彻刻意封存的记忆。柳长亭,
父亲最器重的弟子,比他大五岁,总爱揪他的辫子。雪山派覆灭那天,
柳长亭带着他从密道逃走,却在半山腰被追兵截住。"他死了。"沈彻的声音有些发闷,
"为了护我,被透骨钉穿了心口。"秦越的目光暗了暗:"他没死。"他从怀里掏出块玉佩,
和沈彻的半块一模一样,只是缺口在另一边,"这是在断魂崖捡到的,上面有柳长亭的剑穗。
"沈彻的呼吸猛地加快,那块玉佩的边缘有个极小的刻痕,是他小时候用剑尖不小心划的。
那年他十岁,柳长亭把自己的玉佩给他玩,结果被他摔出个缺口,
为此父亲罚他在雪地里跪了三个时辰。"他还活着?"沈彻抓住秦越的手腕,
对方的皮肤冰得像块铁,"你见过他?"秦越掰开他的手:"三年前在江南见过一面,
他成了影阁的人。"沈彻踉跄着后退,撞在神龛上,香炉里的残灰被震得扬起,迷了他的眼。
柳长亭,那个总把烤好的野兔腿塞给他的师兄,那个说要带他去看江南桃花的人,
成了灭门仇人的爪牙?"不可能。"沈彻的声音在发抖,
"师兄不会......""人是会变的。"秦越站起身,青衫在晨光里泛着冷光,
"尤其是在断魂崖那种地方待过的人。"沈彻突然想起柳长亭被透骨钉击中时的眼神,
没有痛苦,只有种奇怪的解脱。当时他以为是错觉,现在想来,那更像某种约定。"我们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