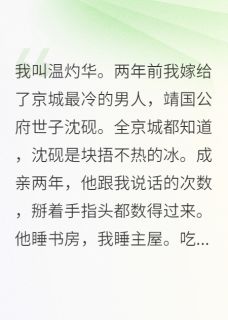我叫温灼华。两年前我嫁给了京城最冷的男人,靖国公府世子沈砚。全京城都知道,
沈砚是块捂不热的冰。成亲两年,他跟我说话的次数,掰着手指头都数得过来。他睡书房,
我睡主屋。吃饭不同桌,走路不同行。外人眼里,我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璧人,关起门来,
比住客栈还生分。我图什么?图他靖国公府的泼天富贵?我家也不差。图他世子妃的虚名?
这头衔戴着硌得慌。就图他那张脸?确实好看。剑眉星目,鼻梁挺直,嘴唇薄得像刀锋。
可再好看的脸,天天对着个冰雕,也腻味了。我爹娘劝我忍忍,说沈砚性子是冷,
但为人方正,后院干净,总比那些花天酒地的强。行吧,方正,干净。方正得像块棺材板,
干净得像雪山顶的石头。日子就这么不咸不淡地过着。直到那天,我生辰。我自己都忘了。
爹娘远在江南,沈砚更不可能记得。府里的下人大概也不知道。晌午,
我坐在花园凉亭里嗑瓜子,看池子里的胖锦鲤打架。贴身丫鬟云雀风风火火跑进来,
脸跑得通红。“**!世子爷……世子爷派人送东西来了!”我眼皮都没抬,吐掉瓜子壳。
“哦,又是库房里清出来的陈年旧货?这次是发霉的缎子还是长虫的参?
”沈砚偶尔会“赏”我东西。流程固定:他的长随捧个匣子过来,
面无表情地说:“世子爷吩咐,给少夫人。”放下就走,绝不多说一个字。匣子里的东西,
多半是府里库房积压的陈货,或者外头谁孝敬他、他又用不上的玩意儿。像打发叫花子。
云雀喘着气,摇头:“不是!是个大箱子!抬进来的!看着……看着挺沉!
”我这才有点意外。沈砚送东西,向来是轻飘飘一个匣子,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抬箱子?
头一遭。“抬进来看看。”两个粗使婆子吭哧吭哧抬进一个半人高的樟木箱子,
放在厅堂中央,闷响一声。箱子看着有些年头了,边角磨损得厉害,挂着把黄铜旧锁。
云雀递给我一把小巧的黄铜钥匙。“送东西的人说,钥匙给您。”我接过钥匙,冰凉的。
心里有点犯嘀咕。沈砚搞什么名堂?总不会在里面装个人头吓唬我吧?咔哒。锁开了。
我掀开沉重的箱盖。一股陈年的纸张和墨汁混合的味道扑面而来。满满一箱,全是书。
确切地说,是账本。厚厚实实,蓝布封面,码放得整整齐齐,边角都磨出了毛边。
最上面一本封皮上写着“靖国公府外庄田亩总录(甲辰年)”。我随手拿起最上面一本,
沉甸甸的。翻开来,是熟悉的、属于沈砚那种一丝不苟的馆阁体。墨色已有些黯淡,
但字迹清晰,记录着府外各处田庄的地亩、产出、佃户、缴税,事无巨细,条理分明。
后面一本是“商铺流水(乙巳年)”。再一本是“库藏器物册(丙午年)”。
年份从我们成亲前两年,一直到……上个月。整整一箱子,全是靖国公府最核心的产业账目!
是他沈砚这些年亲自经手、一笔一划记录的心血!我脑子嗡地一声。他疯了?把这东西送我?
什么意思?试探我?还是……他真觉得我是个管家的料?我捏着那本厚厚的账册,指尖发凉。
这比送我一颗人头还让我心慌。“云雀,”我把账本丢回箱子,像丢开一块烙铁,
“把箱子盖好,抬回世子书房去。”“啊?”云雀傻眼了,“抬回去?**,
这可是……”“抬回去!”我加重语气,“告诉送箱子的人,就说少夫人说了,
看不懂这些劳什子,别放这儿占地方!”箱子被原封不动抬走了。我坐回凉亭,
瓜子也嗑不下去了,心里像堵了团乱麻。沈砚这闷葫芦,到底打的什么算盘?
一下午都心神不宁。傍晚,沈砚回来了。他没像往常一样直接钻书房,
而是破天荒地走到了我屋外的廊下。隔着雕花窗棂,我看见他穿着深青色常服,
身形挺拔得像棵松,夕阳给他侧脸镀了层淡淡的金边,也照不暖他眼底的冷。“箱子,
”他开口,声音和他的人一样,没什么温度,“为何退回?”我倚着门框,手里绞着帕子,
尽量让声音听起来平静无波:“世子爷的东西太金贵,我怕弄丢了,赔不起。
还是放您书房稳妥。”他沉默地看着我,那目光沉沉的,像深潭的水,让人捉摸不透。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说:“那是给你的。”“给我?”我扯了扯嘴角,有点想笑,
“给我做什么?当柴火烧?还是让我学着当个账房先生?”他眉心几不可察地蹙了一下。
“你是世子妃。”“哦,”我拖长了调子,“原来世子妃的职责是看账本?那可真新鲜。
我以为就是顶着个名头,当个摆设呢。”话一出口,带着我自己都没察觉的怨气。
沈砚的唇抿得更紧了,成了一条冷硬的直线。他没再说话,只是看着我,
那眼神深得让我有点发毛。半晌,他转身走了,背影挺直,带着一股生人勿近的寒气。行,
又谈崩了。我砰地关上门,心里那点火气蹭蹭往上冒。莫名其妙!送一箱子破账本,
还指望我感恩戴德?这事像根刺,扎在我心里。沈砚似乎也跟我杠上了。隔了几天,
他又送东西来。这次是个小匣子。云雀战战兢兢捧进来。“**……”我打开。
里面躺着一支老山参,品相极好,根须分明,用红绸垫着。旁边还有一张薄薄的洒金笺。
上面只有三个字:补身子。还是他那笔冷硬的字。我盯着那支参,又看看那三个字,
只觉得一股邪火直冲天灵盖。补身子?我身体好得很!他这是在暗示我什么?
还是觉得我太瘦弱,不配做他们沈家的媳妇?“啪!”我合上匣子,丢给云雀,
“送去小厨房,晚上炖汤,给世子爷好好补补!他日夜操劳,殚精竭虑,才需要大补!
”云雀吓得脸都白了。东西照例被退回。沈砚没再来问。只是府里的气氛,更冷了。
下人们走路都踮着脚尖,大气不敢出。我和沈砚,彻底陷入了冷战。不,比冷战更糟,
是冰封。日子在沉默和压抑中滑过。这天午后,外面下起了淅淅沥沥的雨。我百无聊赖,
想起前些日子整理嫁妆时翻出的一本江南游记,便让云雀去书房找找。云雀去了半晌,
空着手回来,一脸为难:“**,您说的那本游记没找着。
不过……奴婢在您放绣样的那个旧樟木小箱子里,看到几本……账册?”“账册?”我一愣,
“我哪有什么账册?”我的嫁妆产业自有陪房管事打理,账本都在他们手里。
“就是……看着像是世子爷书房里的那种蓝皮册子。”云雀比划着,“压在箱子最底下,
用一块旧锦缎包着。”我的心猛地一跳。沈砚的账本?怎么会在我放绣样的小箱子里?
一种说不清的预感攫住了我。我起身:“带我去看看。
”那个旧樟木小箱子是我从娘家带来的,一直放在卧房角落,
放些零碎绣样、花样子和几件不常戴的小首饰。箱子不大,锁早就坏了,用根布条松松系着。
我解开布条,掀开箱盖。熟悉的丝线和布料味道。我拨开上面几层五颜六色的绣样,
手探到底部。指尖触到一块厚实冰凉的锦缎。我把它抽了出来。沉甸甸的一包。解开锦缎,
露出里面三本厚厚的蓝皮账册。封皮上没有字迹,看着比沈砚书房那些还要旧一些。
我拿起最上面一本,指尖有些发颤。翻开。第一页,依旧是沈砚那种工整到刻板的馆阁体。
但不是田亩商铺,也不是库藏器物。是诗。工工整整抄录的诗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既见君子,
云胡不喜?”一页页翻下去,全是《诗经》里那些热烈直白的情诗。字迹一笔一划,
力透纸背,和他平日里批阅公文、记录账目时一模一样,透着股严肃的虔诚。
我呼吸有些急促,心口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翻到中间,夹着一张泛黄的宣纸。
上面不是抄录,而是一首新作。字迹略显青涩,墨迹深深浅浅,像是写写停停,
带着犹豫和克制。“上元灯如昼,人潮涌如流。惊鸿一瞥处,心湖骤生皱。素衣胜新雪,
笑靥压星斗。欲语唇齿闭,恐惊天上偶。咫尺天涯路,默默随其后。烟火绽又落,
人散空巷口。唯余心上影,徘徊不肯走。”落款处没有名字,只有一行小字:乙未年上元夜,
灯市。乙未年……那是五年前!五年前的上元灯会!我脑子里轰的一声,一片空白。
记忆的闸门猛地被冲开。那一年我刚及笄,随父母从江南来到京城省亲。上元夜,贪看热闹,
和丫鬟挤散了。人潮汹涌,我被推搡得站立不稳,差点摔倒。慌乱间,
一只有力的手臂稳稳扶住了我的胳膊。我惊魂未定地抬头。灯火阑珊处,
一张年轻男子的脸映入眼帘。眉目极好,只是冷得像覆了层霜,眼神锐利如鹰隼。
他穿着墨色锦袍,身量很高,周身带着一种生人勿近的疏离贵气。他很快松开了手,
仿佛刚才的搀扶只是我的错觉。只冷冷丢下一句:“站稳。”便转身,消失在人海里。
快得像一场幻觉。我只记得那双眼睛,冰冷,深邃,还有他袖口掠过时,
一丝极淡的、清冽如雪后松针的气息。后来我才知道,那晚在灯市遇到的是靖国公府的世子,
沈砚。可那之后,直到我们成亲,中间隔着漫长的三年,我再没见过他。两家议亲时,
我甚至都没认出他来。只记得他是个冷面冷心的贵公子。原来……是他?
这首诗……是他写的?写的是……我?那个“素衣胜新雪,笑靥压星斗”的人……是我?
我拿着那张泛黄的纸,手抖得厉害,几乎拿不住。胸口有什么东西在剧烈地冲撞,酸涩,
胀痛,还有一丝荒谬绝伦的难以置信。那个冰块一样的沈砚,那个连话都懒得跟我说的沈砚,
那个送我账本和人参像打发下属一样的沈砚……在五年前的上元夜,灯火阑珊处,
对我一见倾心?还偷偷写了情诗?这简直比太阳从西边出来还离谱!我像被烫到一样,
猛地合上账本,把那首诗胡乱塞回去,用锦缎紧紧裹住。心跳得擂鼓一样,脸上火烧火燎。
不可能!一定是哪里弄错了!也许……也许这账本根本不是他的?
也许是府里哪个账房先生抄录的?可那字迹……那力透纸背、工整刻板的馆阁体,
分明就是沈砚的!还有那首新诗里的描述……时间、地点、衣着……丝丝入扣!
巨大的冲击让我头晕目眩。我跌坐在椅子上,脑子里乱成一锅粥。沈砚那张万年冰山脸,
和纸上那句炽热又胆怯的“欲语唇齿闭,恐惊天上偶”反复交织,割裂得让人窒息。为什么?
如果他五年前就……那他为什么娶了我,却把我当空气?
为什么要用那种冷到骨子里的方式对我?送账本……送人参……他到底想干什么?
无数个问号在我脑子里炸开,搅得我心神不宁,坐立难安。接下来的几天,我像丢了魂。
看到沈砚,眼神不由自主地飘过去,想从他脸上找到一丝当年灯下那个写情诗的少年的影子。
可他依旧是那副冷冰冰、拒人千里的模样,眼神扫过我时,平静无波,
仿佛我只是廊下的一根柱子。这更让我觉得那箱子里的诗像个荒诞的梦。直到那天下午。
我午睡刚醒,头还有些昏沉。云雀端了碗冰镇酸梅汤进来,放在小几上。转身时,
袖子不小心带倒了旁边那个放绣样的旧樟木箱子。箱子本来就没锁好,盖子翻倒,
里面的绣样、花样子哗啦散了一地。“哎呀!”云雀惊呼,慌忙蹲下去捡。
我的目光却死死盯住了箱子底部——那三本蓝皮账册的一角露了出来!几乎是同时,
房门被推开。沈砚走了进来。他大概是刚从外面回来,身上还带着暑气,
深色的外袍衬得他面容愈发冷峻。他的目光习惯性地扫过室内,然后,
精准地落在了散落一地的杂物中,那三本显眼的蓝皮册子上。时间仿佛凝固了。
他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得干干净净。那双总是平静无波、深不见底的眼眸里,
第一次清晰地裂开一道缝隙,露出底下汹涌的惊涛骇浪和……一丝被窥破的狼狈与恐慌。
他猛地抬眼看向我。那眼神锐利如刀锋,带着难以置信的质问和一种被侵犯领地的冰冷怒意。
我被他看得心头一凛,下意识地挺直了背脊,一股莫名的委屈和倔强冲了上来。凭什么?
是他偷偷摸摸写了这些东西,藏在我的箱子里!现在倒像是我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你……”沈砚的声音异常沙哑紧绷,像是从齿缝里挤出来,“谁让你动我的东西?
”这句话彻底点燃了我积压已久的火气。“你的东西?”我站起身,
毫不示弱地迎上他冰冷的视线,指着地上那三本册子,声音因为激动而微微发颤,“沈砚!
你告诉我,这是什么?是你们靖国公府哪一年的田亩总录?还是哪家商铺的流水细账?
”沈砚的脸色更加难看,嘴唇抿成一条苍白的直线,下颌线绷得死紧。他没有回答,
只是眼神里的风暴更盛,死死盯着我。我被他这默认的姿态气得浑身发抖,
一股脑地把憋在心里的话全倒了出来:“五年前的上元灯会!‘素衣胜新雪,笑靥压星斗’?
‘欲语唇齿闭,恐惊天上偶’?沈砚!你告诉我!你写的这是谁?
你当年既然……既然……”那个词在我舌尖滚了滚,终究带着羞耻和难堪没能出口,
“那你为什么娶了我,又把我当个摆设一样晾着?冷着!两年!整整两年!
你跟我说话超过十句吗?你正眼看过我吗?你送账本!送人参!你把我当什么?
一个需要你施舍点‘责任’的物件吗?”我越说越激动,眼泪不争气地涌了上来,
模糊了视线:“你既然那么喜欢你的账本!那么喜欢你的规矩!你娶**什么?
你心里装着别人,你写这些酸诗干什么?现在被我发现了,你倒恼羞成怒了?沈砚!
你到底把我温灼华当什么了?!
”积压了两年的委屈、不甘、迷惑和此刻被那箱子情诗搅起的惊涛骇浪,
化作连珠炮般的质问,砸向那个沉默冰冷的男人。沈砚站在原地,
像一尊骤然被雷击中的石像。他脸上所有的冰冷、愤怒、紧绷,在我一声声泣血的质问中,
寸寸碎裂。他看着我汹涌的眼泪,听着我嘶哑的控诉,那双深潭般的眼睛里,风暴渐渐平息,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空洞的茫然和……痛楚。他张了张嘴,喉结剧烈地滚动了几下,
却没能发出任何声音。我看着他这副样子,心口像是被一只冰冷的手狠狠攥住,又疼又闷。
失望像冰冷的潮水瞬间淹没了愤怒的火焰。他连解释都不屑。我累了。
“好……好得很……”我胡乱抹掉脸上的泪,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世子爷放心,
是我僭越了,是我动了不该动的东西。我这就走,不碍您的眼!”说完,
我再也无法在这个令人窒息的房间里多待一秒,猛地推开挡在身前的沈砚,
跌跌撞撞地冲出了房门。“灼华!”身后传来沈砚一声急促的、带着从未有过的慌乱的低唤。
我没有回头。雨下得更大了,豆大的雨点砸在青石板上,溅起冰冷的水花。
我冲出靖国公府高高的门楼,一头扎进茫茫雨幕里。雨水瞬间浇透了我的头发和衣衫,
冰冷的贴在身上,刺骨的寒意却比不上心头的万分之一。去哪?我不知道。只想离那个地方,
离那个人,远远的。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雨里走着,泪水混着雨水,模糊了视线。
街上的行人匆匆躲避着大雨,没人注意一个失魂落魄的女人。不知走了多久,
天色渐渐暗沉下来。雨水似乎小了些,变成了缠绵的冷雨丝。我浑身湿透,冷得牙齿打颤,
筋疲力尽。抬眼望去,前面似乎有一座废弃的土地庙,黑黢黢的门洞敞开着,
像一张沉默的嘴。我再也支撑不住,踉跄着走了进去。庙里很破败,蛛网遍布,
神像也残破不堪,落满了厚厚的灰尘。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潮湿的霉味和尘土气。
角落堆着些散乱的干草,大概是以前乞丐留下的。**着冰冷的、布满灰尘的墙壁滑坐下来,
蜷缩成一团。湿冷的衣服贴在身上,寒意一丝丝侵入骨髓。我抱紧自己,
身体抑制不住地发抖。外面雨声淅沥,庙里死寂一片。黑暗和寒冷包裹着我,
绝望像冰冷的藤蔓缠绕上来。就在意识有些模糊的时候,庙门口传来急促沉重的脚步声,
踏碎了雨夜的寂静。一道高大挺拔的身影逆着门外微弱的天光,出现在破败的庙门口,
挡住了外面所有的风雨。是沈砚。他显然也是一路冒雨寻来,墨色的锦袍湿透了,
紧贴在身上,勾勒出紧绷的线条。发冠有些歪斜,几缕湿发凌乱地贴在额角和苍白的脸颊上。
他一手扶着门框,胸膛剧烈起伏着,喘息粗重。昏暗中,他那双眼睛却亮得惊人,
像燃烧着两簇幽暗的火焰,死死地锁在我身上。四目相对。空气仿佛凝固了。
只剩下他粗重的喘息声和我自己擂鼓般的心跳。他一步步走了进来,
靴子踩在满是灰尘的地上,发出沉闷的声响。每一步,都像踩在我的心尖上。
他在我面前蹲了下来。距离很近,
他身上冰冷的雨水气息和那股熟悉的、清冽如松针的味道混合着,扑面而来。他伸出手,
似乎想碰碰我湿透冰冷的脸颊,指尖却在快要触及时,猛地顿住,蜷缩起来。
“灼华……”他的声音嘶哑得厉害,带着一种我从未听过的、近乎破碎的颤抖,
“别怕……我来了。”我看着他,看着这个从来冷硬得像块冰的男人,此刻浑身湿透,
狼狈不堪,眼底却翻涌着毫不掩饰的痛楚和……害怕?害怕?这个词用在沈砚身上,
简直荒谬。我别开脸,声音因为寒冷和疲惫而虚弱:“你来干什么?看我笑话?”“不!
”他急切地否认,声音拔高了些,带着一丝恐慌,“我……”他深吸一口气,
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才把那句盘旋在心底多年的话,
艰难地、一字一句地吐出来:“那首诗……写的……是你。”我猛地一震,
难以置信地看向他。昏暗中,他脸上所有的冰冷面具都消失了,
只剩下一种近乎**的坦诚和孤注一掷的决绝。那双深邃的眼睛里,
翻涌着我从未见过的、浓烈得化不开的情愫。“五年前,上元灯会,人潮里,
你穿着素白绣梅的斗篷,回头对我笑了一下……”他的声音低沉而缓慢,
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回忆里艰难地抠出来,“就那一下……我就知道,完了。
”我怔怔地看着他,忘记了寒冷,忘记了愤怒,只剩下巨大的震惊。
“我找了你很久……”他继续说,眼神有些失焦,仿佛陷入了久远的回忆,
“后来才知道你是江南温家的姑娘。我……我想上门提亲。可那时……父亲病重,
国公府风雨飘摇,二叔他们虎视眈眈……我身为世子,一步都不能错。
”他的声音里透出深重的疲惫和压抑。“我告诉自己,等一切安稳了,就去江南求娶。
我……我派人打听你的消息,知道你爱读诗,爱江南的小点心,怕冷……我就想着,
等我去的时候,该带些什么……”他的目光落在我脸上,带着一丝小心翼翼的探寻。
“后来……后来我听说,你……你似乎……”他顿住了,喉结滚动,像是咽下某种苦涩,
“似乎对我那个不成器的庶弟……沈钰,颇有好感?”沈钰?我脑子里嗡地一声。
那个轻浮浪荡、只会吟几句歪诗的沈家二公子?我对他有好感?什么时候的事?!
我拼命回想,终于从记忆的角落里扒拉出一点模糊的印象。好像是有一回,
在某个无聊的赏花宴上,沈钰当众念了首咏牡丹的诗,辞藻华丽,引得几个闺秀掩嘴轻笑。
我当时……似乎也礼貌性地扯了扯嘴角?就因为这个?!“所以……”我艰难地开口,
声音干涩,“你以为我喜欢沈钰?”沈砚闭了闭眼,浓密的睫毛在苍白的脸上投下阴影,
遮住了眼底翻涌的痛苦。“是。我的人……是这么回禀的。说你看沈钰念诗时……笑了。
”我简直气笑了,又觉得荒谬透顶,一股悲凉涌上心头。“所以,你就认定我喜欢你弟弟?
然后你就……放弃了?连问都不问我一句?”“没有放弃!”沈砚猛地睁开眼,急切地反驳,
眼底是深不见底的痛楚和挣扎,“我怎么可能放弃!可那时……父亲刚走,府里乱成一团。
二叔联合族老,质疑我承爵的资格,处处刁难。沈钰……他母亲是二叔的亲妹,
他们……他们巴不得把我拉下来,扶持沈钰上去!
”他的声音因压抑的愤怒而紧绷:“我若在那时强行求娶你,只会把你卷进这场漩涡!
温家远在江南,鞭长莫及!他们动不了我,难保不会对你下手!用你来牵制我、打击我!
我……我不敢赌!”他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后怕和一种近乎绝望的恳求:“灼华,
我不敢赌!一丝一毫的风险,我都不敢让你承担!”我看着他痛苦挣扎的样子,
心口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闷闷地疼。原来……是这样?“后来……后来陛下圣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