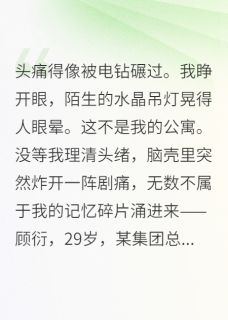头痛得像被电钻碾过。我睁开眼,陌生的水晶吊灯晃得人眼晕。这不是我的公寓。
没等我理清头绪,脑壳里突然炸开一阵剧痛,无数不属于我的记忆碎片涌进来——顾衍,
29岁,某集团总裁,结婚三年,妻子林晚,出身底层,性格懦弱,是整个顾家的出气筒。
而我,也叫顾衍,只是个刚加班猝死的社畜。「醒了?」门口传来刻薄的女声,
「林晚那个小**呢?让她给我滚出来!」一个烫着卷发的中年女人叉着腰站在卧室门口,
身后跟着个打扮得花里胡哨的年轻女孩。记忆告诉我,这是原主的妈张翠兰,和继妹顾婷。
我还没吭声,顾婷就尖着嗓子喊:「哥,你可算醒了!林晚把你送回来就躲房间里,
肯定是做了亏心事!妈发现她偷偷存了三万块,是不是想贴补她那个穷酸娘家?」
卧室门被推开,林晚端着水杯出来,身上还穿着洗得发白的旧T恤。她的手腕很细,
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泛白,看到张翠兰时,肩膀明显瑟缩了一下。「妈,那钱是我……」
「闭嘴!」张翠兰冲上去就想打她,「我们顾家好吃好喝养着你,你还敢藏私房钱?
我看你就是没安好心!生不出儿子就算了,还想卷钱跑路?」林晚下意识后退,
水杯摔在地上,碎玻璃溅到她的脚踝,划出血痕。我皱了皱眉。按照原主的记忆,
他此刻应该像往常一样冷眼旁观,甚至会帮着他妈训斥林晚。可不知怎么,看到那道血痕时,
我的脚踝也跟着一阵刺痛。错觉?「哟,还敢躲?」顾婷突然端起桌上一碗刚煮好的面条,
二话不说就朝林晚泼过去,「我让你装可怜!」滚烫的面汤大半泼在林晚的手背上,
她疼得闷哼一声,手背瞬间红透起泡。就在这时,我的左手手背突然像被火燎似的剧痛起来,
那痛感和林晚手背上的烫伤位置一模一样,甚至连灼烧的范围都分毫不差!我猛地跳起来,
疼得倒抽冷气。张翠兰和顾婷都愣住了。「哥,你咋了?」顾婷一脸莫名其妙。我没理她,
死死盯着林晚通红的眼睛。她没哭,只是咬着嘴唇,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却倔强地不肯掉下来。而我手背的疼,还在一阵阵加剧,像是有无数根针在扎。「你……」
我想说点什么,却发现喉咙发紧。「顾衍,你少在这装模作样!」张翠兰回过神,
指着我的鼻子骂,「为了这么个不下蛋的鸡跟你妈翻脸?我看你是被她灌了什么迷魂汤!」
林晚突然开口,声音很轻,却带着一种我从未听过的冰冷:「我没有藏私房钱,
那是我妈住院的手术费。」「你妈?」张翠兰嗤笑,「那个老不死的早就该入土了,
花这冤枉钱干嘛?」「她是我妈。」林晚抬起头,第一次直视张翠兰,
「就像顾婷是你女儿一样。」「你找死!」张翠兰被戳中痛处,扬手就给了林晚一个耳光。
「啪」的一声脆响。几乎同时,我的右脸传来**辣的疼,耳朵里嗡嗡作响,
跟被人狠狠扇了一巴掌没两样。这次我看得清清楚楚,林晚的脸颊迅速浮起五道指印,
而我的右脸,也同步泛起了热意。不是错觉!
那块昨天被林晚不小心碰掉的古玉碎片……记忆里,原主当时还骂了她一顿,说她毛手毛脚,
把顾家的传家宝都摔了。难道是因为那个?「够了!」我吼了一声,冲过去挡在林晚面前。
张翠兰和顾婷都惊呆了。在她们的印象里,我从来不会护着林晚。「哥,你疯了?」
顾婷尖叫,「你居然帮她?」我没管她们,只是低头看林晚。她的眼眶更红了,
却不是因为疼,而是因为震惊。她看着我的眼神,就像在看一个陌生人。「你……」
她嘴唇动了动,最终还是把话咽了回去,绕开我就往客厅走。我想拉住她,
手背的灼痛却突然变本加厉,疼得我手一缩。林晚回了客房,「砰」地一声关上了门。
「反了!真是反了!」张翠兰气得跳脚,「顾衍,你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
要么让她把钱交出来,要么就跟她离婚!」顾婷在一旁煽风点火:「就是啊哥,
这种不下蛋还敢顶嘴的女人,留着干嘛?你看她刚才那眼神,简直要吃人!」
我没心思听她们废话,满脑子都是刚才那两次同步的痛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走到客房门口,想敲门,手刚抬起来,就听见里面传来压抑的哭声。很轻,像小猫在呜咽,
却一下下扎在我心上。紧接着,一种难以言喻的酸楚和绝望涌上心头,不是我的情绪,
却清晰得仿佛与生俱来。「再忍下去,我会死的……」她在里面小声说,带着哭腔。
我的心脏猛地一揪,像是被什么东西攥住了。这是林晚的想法?感知共享还包括情绪?
**在门上,第一次认真回想原主的记忆。结婚三年,林晚包揽了所有家务,
对我妈和顾婷的刁难从来都是忍气吞声。原主不仅不心疼,还觉得她理所当然,
甚至在她被顾婷推下楼梯流产时,还骂她不小心,害顾家断了香火。畜生。
我在心里骂了原主一句,也骂了刚才还想冷眼旁观的自己。不知过了多久,客房的门开了。
林晚背着一个旧背包,眼眶红肿,脸上的巴掌印还没消。「我走了。」她看都没看我,
声音平静得可怕。「你去哪?」我脱口而出。她停下脚步,回头看我,眼神里没有爱,
没有恨,只有一片死寂:「顾衍,我们离婚吧。」我愣住了。张翠兰和顾婷听到动静跑出来,
一听离婚,脸上都露出喜色。「离得好!」张翠兰拍手,「早就该离了,
谁稀罕你这种扫把星!」顾婷假惺惺地说:「林晚姐,你别冲动啊……不过你要是真走了,
我哥肯定能找个更好的。」林晚没理她们,只是看着我:「离婚协议我会让律师寄给你。」
说完,她转身就走。我看着她的背影,手背的灼痛和脸颊的**感还在隐隐作祟,
心里那股绝望的情绪越来越浓。「不准走!」我突然冲过去抓住她的手腕。她的手腕很凉,
很细,我一用力就硌得慌。林晚猛地甩开我的手,像是被烫到一样:「顾衍,别碰我。」
她的眼神,让我想起记忆里她流产那天,躺在病床上看我的样子,一模一样的冰冷和疏离。
「我……」我想解释,却不知道该说什么。说我不是原来的顾衍?说我能感受到她的疼?
她会信吗?林晚没再说话,拉开门就走了出去。楼道里传来她渐行渐远的脚步声。我的心,
像是被掏空了一块。张翠兰还在骂骂咧咧,顾婷在旁边附和,可我一个字都听不进去。
我走到客厅,捡起昨天被摔碎的古玉碎片。碎片边缘很锋利,我不小心划破了手指,
血珠滴在上面,瞬间被吸收了。就在这时,手背的灼痛突然消失了,
脸颊的**感也退了下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空荡荡的、让人发慌的感觉。
我低头看着自己的手,又看了看紧闭的大门。林晚真的走了。而我,好像有什么东西,
跟着她一起消失了。客房的门还开着,我走进去,里面很简陋,只有一张床和一个旧衣柜。
床头柜上放着一个相框,是我们结婚时的照片。照片上的林晚笑得很腼腆,眼里有光,
而原主则一脸不耐烦。我拿起相框,指尖划过照片上她的脸。突然,脑海里又传来她的声音,
很轻,很疲惫,像是在对自己说:「再忍下去,我会死的。」这一次,伴随着声音的,
是心脏被狠狠攥住的剧痛。我知道,这不是错觉。那块古玉,把我和林晚绑在了一起。
她的疼,她的苦,她的绝望,我都能清清楚楚地感受到。而我,不能让她真的消失。
绝对不能。林晚走后的第一个晚上,我在客厅坐了整夜。古玉碎片被我收在丝绒盒子里,
放在茶几上。月光透过落地窗洒进来,碎片边缘泛着冷光。没有了林晚在这个家,
那股若有似无的消毒水味(她总爱把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张翠兰惯用的廉价香水味,呛得人发晕。后半夜,我突然一阵头晕目眩,
喉咙又干又疼,像是被砂纸磨过。这感觉太熟悉了——是林晚的感冒加重了。我猛地站起来,
抓起车钥匙就想往外冲。可冲到门口才想起,我不知道她在哪。手机里没有她的新消息,
通话记录停留在上周她问我回不回家吃饭,我回了句「没空」。
胸口突然传来一阵尖锐的酸楚,比头晕更难受。那是林晚缩在某个角落,
抱着膝盖默默掉眼泪的情绪。「别找了。」张翠兰不知什么时候站在卧室门口,穿着花睡衣,
「那种女人,离了咱们顾家活不了三天,迟早自己滚回来。」我回头瞪她,右脸还隐隐作痛,
昨天她扇林晚的那巴掌,力道真够狠的。「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饶不了你。」
我说这话时,声音都在抖。张翠兰被我吓了一跳,随即跳着脚骂:「反了你了!我可是你妈!
你为了个外人咒我?」「她不是外人。」我攥紧拳头,手背的烫伤疤痕还没消,
「她是我老婆。」「老婆?」顾婷从她房间探出头,一脸嘲讽,「哥,你怕不是烧坏脑子了?
她连个孩子都生不出来,算哪门子老婆?再说了,谁知道她外面有没有人。」
这话像针一样扎进我耳朵。原主的记忆里,顾婷不止一次在他面前说林晚坏话,
说她在公司和男同事走得近,说她回娘家时见过陌生男人。原主从来没怀疑过,
因为他根本不在乎林晚。但现在,我能清晰地「听」到林晚每次被人背后议论时,
心里那股针扎似的难堪。「闭嘴。」我冷冷地说,「再让我听见你胡说八道,
就从公司滚出去。」顾婷在我公司做行政,仗着我的关系,天天迟到早退,
还克扣实习生工资。她脸都白了:「哥,你……」「滚回去睡觉。」我没再看她,
转身回了书房。接下来的几天,我像疯了一样找林晚。去她娘家问,她妈说她没回来,
只是托人捎了笔钱,说自己去外地打工了。去她以前常去的公园、书店,都没有踪迹。
张翠兰和顾婷看我魂不守舍,不仅不帮忙,反而变本加厉地添堵。那天我正在开视频会议,
张翠兰突然闯进办公室,把一叠照片摔在我桌上。「你自己看!」她气得浑身发抖,
「这就是你护着的好老婆!」照片上是林晚和一个陌生男人站在医院门口,
男人扶着她的胳膊,看起来很亲密。我的心猛地一沉,不是因为怀疑,而是因为通过感知,
我清楚地「看到」——那天林晚是去给她妈拿检查报告,下楼梯时差点摔倒,
是路过的医生扶了她一把。「这是市一院的王医生。」我盯着张翠兰,「你从哪弄来的照片?
」张翠兰愣了一下,随即嘴硬:「我不管是谁!孤男寡女在医院门口拉拉扯扯,像什么样子!
」「她妈肺癌晚期,你知道吗?」我提高了音量,会议室里的人都停了下来,
「她存的那三万块,是给她妈化疗的,你知道吗?」这些都是我托人查到的。
林晚的妈妈三个月前查出癌症,她怕我知道了不高兴,一直自己扛着,白天上班,
晚上去做**。张翠兰被问得哑口无言,脸一阵红一阵白。「你……你调查我?」
她强装镇定。「我只是不想再被你们当傻子耍。」我把照片扫到地上,「从今天起,
别再管林晚的事。」张翠兰气呼呼地走了,会议也没法继续开。我揉着太阳穴,一阵烦躁。
这时,顾婷发来微信,说她在我抽屉里发现了林晚的工资卡,问我要不要没收。
我直接回了句「滚」。晚上回到家,刚进门就听见张翠兰在哭哭啼啼。
「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个白眼狼啊……」她坐在沙发上,对着电话那头哭诉,
「娶了媳妇忘了娘,为了那个不下蛋的鸡,连亲妈都骂……」是打给老家的亲戚。我没理她,
径直走向卧室。刚打开门,就被一股霉味呛得皱眉。我的床被搬到了客房,
主卧里堆满了杂物——都是林晚的东西。
她的衣服、books、还有她攒了很久才买的缝纫机(她喜欢做手工),全被扔在地上,
上面还泼了水,有些布料都发霉了。「你干什么?」我冲出去质问张翠兰。她挂了电话,
理直气壮地说:「反正她也不回来了,留着这些破烂占地方。我明天叫收废品的来拉走。」
「谁让你动她东西的!」我气得发抖,心脏突然一阵抽痛——是林晚的情绪,
那种被人践踏心爱之物的愤怒和委屈。「我是你妈,动她点东西怎么了?」张翠兰站起来,
「顾衍,我告诉你,你要是敢把她找回来,我就死在你面前!」「你敢!」我指着门口,
「现在就把她的东西收拾好,不然我就把你这些年偷偷给顾婷转的钱,全转到公司账户上!」
原主的记忆里,张翠兰这几年以各种名义,从公司账上挪了不少钱给顾婷买奢侈品,
这事要是捅出去,顾婷就得蹲监狱。张翠兰的脸瞬间白了,她没想到我会知道这事。
「你……你什么时候……」「别管我什么时候知道的。」我盯着她,「要么收拾东西,
要么看着顾婷进去,你选一个。」张翠兰没敢再犟,悻悻地去收拾林晚的东西。我蹲在地上,
小心翼翼地把那些被弄湿的布料捡起来,手抖得厉害。每拿起一件,就像有根针在扎我的心。
林晚刚嫁给我的时候,总说要给我做件西装外套,说外面买的不合身。
她攒了半年工资买了这台缝纫机,每天下班就躲在客房缝缝补补,
却因为被顾婷嘲笑「穷酸样」,一直没敢给我看。我以前怎么就没发现,自己错过了这么多?
收拾到半夜,终于把所有东西归置好。我累得坐在地上,浑身酸痛。突然,
小腹传来一阵隐隐的坠痛,很轻微,却很清晰。这感觉很陌生,不像是疼痛,
更像是一种……很微妙的牵扯感。紧接着,脑海里闪过一个模糊的画面——林晚坐在床边,
手里拿着一张纸,眼泪滴在上面,晕开了墨迹。我猛地站起来,冲进客房。
林晚的东西都放在衣柜里,我翻了半天,终于在一个旧钱包的夹层里,